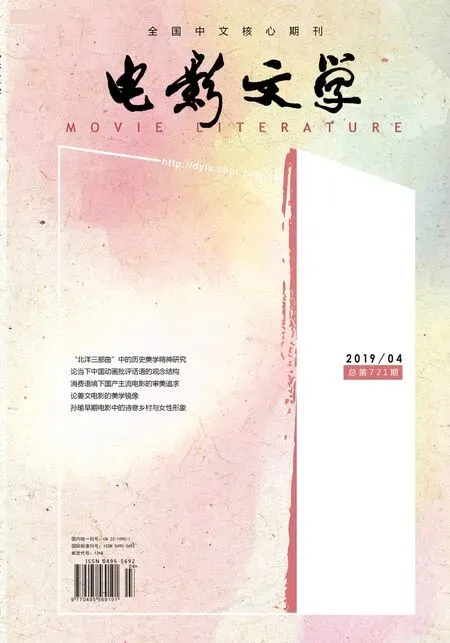景觀·仿真·神圣人
——科幻電影中的“危機”想象
戴小晴 (重慶師范大學 新聞與傳媒學院,重慶 401331)
科幻電影是想象的產物,它承載著現時世界的圖像景觀與社會權力空間的投射,后人類、后電影、后理論的諸多話題都可以延展到科幻電影中一探究竟。電影好比視覺化的展布,導演在其中涂抹的色彩經過解碼還原為當下人類的精神困境。進入21世紀的科幻電影,在批判色彩和理論認知上都拋棄了對未來世界的憧憬渴望,轉而在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交纏中迷失了自我,這似乎蘊含著當下社會的動蕩與無處安放。
可以看到,符號化的景觀社會、仿真的超現實主義以及對于未來世界的難民想象,作為科幻電影的精神范式與精神困境,將科幻電影與現實世界進行了價值重構,透露出當代電影人對于未來世界的擔憂和畏懼。無論其外表如何光彩奪目,科幻電影在本質上是滿含憂郁的。
一、景觀:感官代碼空間
斯派克·瓊斯導演的電影《她》是一部未來世界的情感哀歌,人類與機器的虛擬情感使人如鯁在喉,然而其描繪的理想世界卻是冰冷孤寂的,暗合了影片的孤獨內核。由色彩、城市構筑的未來城市“景觀”,將人與人隔絕開來。《她》并沒有落入科幻世界技術爆炸的窠臼中,反而投射到未來人類的情感狀態,反思其真實與虛擬的雙重精神困境。
居伊·德波在《景觀社會》一書中描繪了這樣一種圖景:生活中各方面分離出的影像群(images)匯成一條河流,以致生活的統一性不能被重建,進而“重新將他們自己編組為新的、整體的,關于現實的片段景色,只能展現為一個純粹靜觀的孤立的偽世界”。[1]3在他看來,“景觀是一種表象的肯定和將全部社會生活認同為純粹表象的肯定”[1]4。景觀以影像作為中介,勾連了整個社會,在這個充溢著虛假“現實”的場域中,個體生命都不自覺地陷入被“催眠”的集體無意識。
正如《她》所呈現的那樣:在后現代的科幻電影中,未來城市是由符號、代碼構建起來的,完全由傳媒所操縱的感官媒介的多邊形城市,人們身處的城市空間已不再是19世紀政治、工業化垂直城市。如果延展德勒茲的無器官身體理論,或許這就是“無器官的城市身體”。《她》展現了一個極致的感官代碼空間,無處不在的社會領地被景觀包圍。未來城市拂去市井化氣息,轉變為感官代碼的集中性表達。外在的景觀模式與符號代碼取代城市真相,精致的生活圖景實質是無根之木,內里是現代人揮之不去的孤獨和冷酷。
景觀多維度地挑戰固有社會結構:一方面,在社會意識體系中,景觀疏離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如:西奧多無法消解和反抗景觀的無形控制,單向度地沉溺于景觀,即感官代碼空間之中。通過擬象、擬聲轉化而來的“女友”薩曼莎——人工智能操作系統OS1,是西奧多默然屈從的“真實”,跌入誘人的景觀。從某種意義上,西奧多拒絕了和本真社會的深層交流,操作系統OS1才是他的情感依附。
另一方面,在空間功能的界定中,景觀又模糊了公共與私人領域的界限。視覺映像在公共領域無孔不入,同時也強勢霸占了個體私人領地,存在的一切都轉化為無數表象。《她》中的未來城市,是被景觀奴役的城市,景觀的在場斥逐了空虛能指。對于生活在這個感官代碼空間的群體來說,公共領域是一個同質化、中性化的冷漠空間。智能化的、超現代化的智能科技高層次地滿足了未來人的需求,即使在西奧多絕對的私人領域里,操作系統OS1也實現了和他的親密“接觸”,更是無時無刻不被“需要”。由此,作為景觀的擬真“女友”薩曼莎自然而然地跨越了私人領地的界限,西奧多徹底淪為景觀的囚徒。當然,西奧多只是這個感官代碼空間中的象征個體,作為這個城市空間中的每個個體,都在竭力尋求身份認同,難以對抗系統。
同時,“景觀通過碾碎被世界的在場和不在場所困擾的自我,抹殺了自我和世界的界限;通過抑制由表象組織所堅持的在謊言的真實出場籠罩之下的所有經驗事實,抹殺了真與假的界限”[1]101。而在另一部科幻電影《頭號玩家》中,“綠洲”是全民狂歡的虛擬游戲宇宙,也是全民救贖的希望寄托,在那個博弈場,現實世界的邊緣人也有成為超級英雄的可能性。在這里,“綠洲”即是后人類的景觀,個體在虛幻的景觀里,尋求游戲的快感,偏離了真相世界;又在真實世界與景觀社會的來去往復中,混淆了真相與表象。
縱觀科幻電影,對于未來世界的想象都是泛景觀化的,未來城市的圖景是純粹現代社會的隱喻象征,逃脫不出符號化抽象演繹。與現代社會相比,未來社會造就了人與本真更為巨大的鴻溝,科技并沒有彌補人的精神退化,反而加劇了人的物化和異化。由于景觀的無所不在,人類事實上成為“觀看—被看”的雙重展品。
二、仿真的欣快癥:賦魅與祛魅
《頭號玩家》中的超真實世界——“綠洲”,實質上是一個未來仿真社會的投影。正如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所言,冷酷的數碼世界吸收了隱喻和換喻的世界,仿真原則戰勝了現實原則和快樂原則。當進入虛擬現實的境地后,每個玩家脫離自己現實的身體符號,轉而選擇一種與自己無關的身份幻象。真實的符號代替了真實本身,即雙重操縱延宕所有的真實過程。在場的是游戲角色——“符號”的我,而非本真的“我”。在這個擬態空間,身份、形貌、性別甚至物種等都可以任憑自己抉擇,無須顧忌與現實世界的關聯性缺失,現實完全消解在影像和符號的迷霧之中,滿足了觸覺神秘主義的全部想象。
鮑德里亞認為,我們進入到一個“仿真”構成的新社會,一切以符號相互交換,形成一個“原本”缺失的社會,追溯仿真產生的根源,指向形象的非指涉性。“所有的這一切定義了一個數碼空間,用模式的極化、散射和引力定義了一個代碼磁場。”[2]94他說:“現實在超級現實主義中的崩潰,對真實的精細復制不是從真實本身開始,而是從另一種復制性中介開始……真實化為烏有,變成死亡的諷喻,但它也因為自身的摧毀而得到鞏固,變成一種為真實而真實,一種失物的拜物教——它不再是再現的客體,而是否定和自身禮儀性毀滅的狂喜:即超真實。”[2]96
前面提到,城市是一種冷漠的空間,而貧民窟裸露的鋼筋水泥、凌亂無章,它只是一種城市形態的極端表達,遭到隔離的禁閉中心。游戲玩家在現實困境的絕望邊緣無法尋求獲得感,而這個游戲“建筑群”卻能讓瀕臨崩潰的個體找回現實缺失的刺激、快樂、欲望等心理需求,更能實現現實世界不可能實現的一切。總之,在“綠洲”這個仿真世界打破現實世界的規則和圍墻。玩家在“綠洲”這個如同判決生死的符號場所中付出所有,一旦破敗,便意味著徹底失敗,甚至他們會選擇死亡,拋棄現實社會的生命屬性。現實的生存狀態已經顯得無足輕重,所有人都在“認同仿真模式的各自瘋狂中被排列起來的了,這種代碼的壟斷擴散到了各處的城市組織中,它才是真正的社會關系形式”[2]104。
因為擬象的仿真原則,真實和模型之間的差異消失了,超真實出現。玩家在游戲進程中的暴力、破壞、涉槍等違反現實社會準則的行為,在這個仿真緯度都是被允許的。這樣一來,罪惡感、絕望和死亡的符號所體現的絕對快樂便可以取代焦慮、死亡本身——這是“仿真的欣快癥”。整個現實都淪為“現實的游戲”,嘗試在現實世界中被禁止的行為,所有人生活在現實的“美學”幻覺中。
對于虛擬游戲世界的狂熱,其實是一種對本真世界的回避,趨重于一種符號化的身份象征,從而取代真正的“我”。后現代社會,尤其是未來高技術時代,城市空間愈來愈立體化,為了更加擺脫現實世界對于我們的控制,是科技不斷被“賦魅”的內在需求。這個被“賦魅”的仿真世界,把人與人之間的本真交集,引入到一個象征符碼編織的偽象征構境,消極接受日常現實異化的人類將徹底落入形式/符號的監禁之中,然而吊詭的是,這又不得不是一個“祛魅”的過程。
三、神圣人:后人類的“難民”想象
斯皮爾伯格的《少數派報告》中,利用可以感知未來的超能力人,對社會犯罪行為進行預判,罪犯會在實施犯罪前就遭受到懲罰。可以說,這些擁有“先知”的超能力人就是法律力量的集中體現。而約翰則是這個犯罪預防組織的主權者,即擁有至高權力的人。在某天一覺醒來,他發現自己變成了昔日同事的抓捕對象,從擁有至高權力的人淪為“神圣人”,成為徹底的“赤裸生命”(bare life)——也就是神圣人的生命,這些人可以被殺死,但不會被祭祀。整部電影旨歸在于揭露至高權力與赤裸生命的對抗。
為了揭示生命政治的內在結構,“神圣人”在吉奧喬·阿甘本的研究中,具有核心地位。“神圣人”(sacred sacer)包含了“雙重排除”的特征:他們不僅被排除在俗世法律之外(可以被殺死),并且同時被排除在了神法之外(不能被祭祀)。[3]
福柯借用“監獄”來擬喻現代社會,那么阿甘本則將目光伸向“集中營”,將其視為現代共同體形態的典范,而集中營本身就是一個政治空間的典范。電影《少數派報告》里的那個未來世界,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看作后現代的“集中營”,至高領域的政治結構是由負責預測的超自然人和權力執行者組成,他們擁有至高決斷的絕對權力。在“先知”們做出預判時,“罪犯”的生命便被排除在他本來應該受到保護的空間,生命遭到棄置。約翰的赤裸生命就是其生命被政治化的結果,代表法律力量的先知,可以無條件把一個人變成“神圣人”,而他們的判斷是否無誤,人們無從知曉。
電影中約翰的遭遇隱喻了整個社會空間的生存危境:和阿甘本強調的一樣,在現代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有可能隨時成為“神圣人”。在那里,政治變成生命政治,神圣人實已與公民身份相混淆(公民下降為神圣人)。因為現代社會這個集中營的根本特征,是這個空間的例外狀態被常態化,所以在集中營被懸置、被排除、被例外這樣的“緊急狀態”,已經成為一種永恒的緊急狀態。電影中權力擁有者,竭力制造一個永久性的緊急狀態,在保護集中營群體的名義下,本質上干涉/介入了生命甚至可以隨時將公民轉化為赤裸生命,身處在這個集中營的在場之中,個體面臨的“神圣人”危機是無時不在的。
由此可以展開想象,后現代社會的集中營空間,是泛化的。在集中營里,赤裸生命與政治生活進入一個人無可區分的地帶,后人類在生命政治中,隨時可能會墮落成“神圣人”,貶為赤裸生命的“難民”。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反思:現代社會里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難民。
四、結語
科幻電影屬于一個歷史范疇,表述著一個時代的基于現代社會又超脫于現代社會的幻想與情感。科幻電影作為一種文化表征,反映出復雜深沉的時代癥候。現代人類逐漸過渡到后工業社會,一個充斥著機械、人工智能的時代悄然到來,科幻電影中的未來想象很多都在變成現實。然而關于科幻世界的媒介景觀和權力機制似乎也離我們越來越近——人與人的隔閡遠大于人與智能機械的隔閡,無所不在的監視體系進入私人領地,智能系統可以操縱人的精神世界。不禁懷疑,這樣的未來世界與我們內心幻想的世界是否一致?科幻電影勾勒的烏托邦,反而將人類捆縛于狹小孤寂的空間里,吞并掉其所剩無幾的內心情感,隨時可能落入主權控制的境地,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現實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