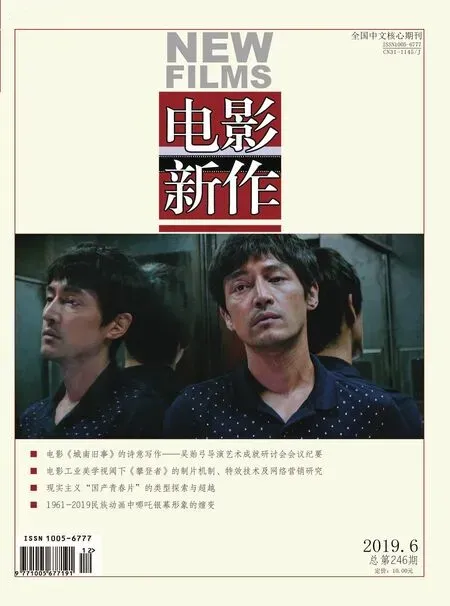網絡大電影中“系列片”樣式的生產與傳播
張 強
網絡大電影(簡稱網大)經過幾年的發展,已從行業草創階段走向了快速發展期。網大《道士出山》借院線電影《道士下山》熱度的方式被摒棄,粗糙的制作已經不能滿足市場需求,行業準入門檻越來越高,幾經調整后由簡單的“制作-放映”模式開始向“備案-制作-審核-定級-宣發-放映”式的類電影市場運作。與此同時,網大也在尋求可被網絡受眾接受的生產和傳播模式,在市場方面符合大數據運作的信息反饋和共享,加強分眾傳播下的信度和效度,并且在影像文本的創作中與院線電影彰顯差異性。
在對網大生產和傳播的觀察中,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網大集中以“系列片”的樣式出現,包括“大夢西游”“魔游紀”“四大名捕”等為片名的網大不再是單集的形式,而是制作成一系列相同題材的電影,例如“魔游記”系列一共制作了六部,“罪途”系列制作了三部,項氏兄弟電影的“四大名捕”系列也還在不斷地制作中。這些依市場消費意識制作的“系列片”在網大總數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成為當下影像生產的主要方式,滿足了流行文化下的網絡傳播需求。以“系列片”出現的網大契合了市場的需要,在類型的復制和創新中尋找與觀眾有效的互動方式,培養了長期穩定的受眾群體。本文試圖從市場角度分析“系列片”樣式的成因,以及文本傳播的再生性系統。
一、“系列片”作為市場化需求
通過對網大“系列片”樣式的觀察,不管是“大夢西游”系列,還是“僵尸來了”“狄仁杰”等其他系列,他們都有穩定的制作團隊,通常由同一家公司出品和制作,并且選擇同一平臺進行獨家發行。從奇幻題材到僵尸、古裝題材,穩定的制作團隊保證了該系列在故事銜接、視效風格、角色設計上形成統一性,一旦其中一部形成良好的口碑和較高的熱度,就會提高觀眾對該系列其他電影的關注。據“2018中國網絡視聽發展研究報告”統計,有96.2%的網大屬于“獨播影片”,并且總數的95.1%在“優愛騰”播出,在票房分賬榜單前20名中,屬于“系列片”生產的網絡大電影就有16部。從資金回報來看,“系列片”樣式的創作成為一種有效的市場手段,帶給觀眾新的審美體驗,建立了契合媒介融合語境下的影像生產機制,削弱與同期院線電影的黏合度。
回溯歷史,集中地以“系列片”樣式的電影生產在上世紀20年代末期就已經出現,明星公司就根據平江不肖生的小說《江湖奇俠傳》改編成《火燒紅蓮寺》,一連拍了18集之多,其掀起的“火燒”系列電影則更多,其他武俠神怪片例如《荒野女俠》《關東女俠》也都拍了13集。網大形成的“系列片”同90年前的武俠神怪片都處在市場化探索的初級階段,但顯然已不可同日而語。較于院線電影,網大在利用大數據(Big Date)方面更有效和便捷,電影和觀眾建立了即時性交互體驗,觀眾在搜索引擎和社交平臺的關注度可以作為數據分析的來源,彈幕、評論等方式也可以完成多層次復合式互動,Fandango、Box Office Mojo、愛奇藝指數、貓眼專業版等平臺都可以進行數據動態分析,制作方根據數據分析結果了解觀眾的偏好。在愛奇藝指數中,一部影片的內容熱度、播放設備、播放地域都可以即時搜索,受眾的性別、年齡、學歷、星座等信息也都可以查詢,與傳統電影的單向信息傳播相比更為靈活。值得一提的是,愛奇藝在2018年首先關閉代表單一指標的“播放量”,而使用“熱度”這個綜合指標,涵蓋了用戶討論度、互動量、多維度播放類指標。尋求觀眾最大點擊量和有效觀看時間的網大比院線電影對數據的分析更為依賴,制作方根據電影中的題材選擇、人物設置、視效風格依用戶的喜好選擇進行貼合性調整。“系列片”尤為如此,頭部電影在平臺播出后,觀眾的喜好會通過數據的方式反饋出來,制作方可以隨時調整余部電影的影像風格和故事內容。奇幻、僵尸等系列之所以一再被生產復制,除制作方的從業經驗外,對大數據的分析也成了參考的重要指標。
雖然可以看到很多標榜“奇幻”等題材的網絡大電影,但從近兩年的“系列片”制作情況來看,從“蹭IP”階段漸漸過渡到了“創造IP”和“IP精品化”階段。2015年網大《道士出山》以相似的片名借院線電影《道士下山》的熱度,以28萬元成本在半年內收入就達2400萬,類似情況在今天的市場已不會出現,在此期間大量出現的“僵尸”題材電影在2017年后也難尋蹤跡。“樂視十不準”“愛奇藝九禁”“搜狐七把控”中都提到了禁止“蹭IP”的作品的存在,行業自身的監管以及優秀創作人才的進入使得行業準入門檻越來越高,出品方和制作方都在尋找有效途徑滿足市場的需求,同時還要面對同期院線電影競爭的壓力。與院線電影不同,網大的播放平臺主要集中在愛奇藝、騰訊、優酷三大視頻平臺,這些平臺對自身播放的網大都有較嚴格的評價標準,內部評審團會根據網大的內容質量或者上線后的市場表現進行評估。例如愛奇藝將網大從A到E分為五個級別,每一級別的內容分成單價不同,并且針對定級后的電影匹配不同的推廣資源,A、B兩級可在愛奇藝視頻平臺的時間軸位置提前預熱,保證了影片被用戶點擊觀看的幾率,大幅度提高了影片的熱度,而從C級到E級則無保底的推廣資源。“定級制度”迫使網絡大電影的出品制作方盡可能利用手中有限的資源提高影片內容質量,否則無法保證較高的票房分賬收入。“系列片”便成為一種有效的方式,既避免了“蹭IP”現象的出現,又可將某一種類型題材精細化,形成良性的市場生態。
“項氏兄弟電影”制作的“四大名捕”系列來源于溫瑞安的武俠小說《四大名捕》,并取得了改編權,計劃在五年內制作十余部系列電影,從已上線的頭部電影《四大名捕之入夢妖靈》(2018年)來看,影片借鑒了原著中的人物形象和部分故事情節,而將“傳統武俠”風格置換成了“奇幻武俠”,穿插喜劇笑料,以夢食人,入夢解夢,畫面視效、美術置景都備受稱贊。借“奇幻”和“武俠”兩種風格的“四大名捕”系列是多數網絡大電影在制作策略上的一個典范,諸如“校園”“動作”“犯罪”“古裝”“妖道”等都以不同的方式糅合成新的類型,故事敘述上更加大膽。“項氏兄弟電影”的制作團隊同樣反映了行業特征,其制作的電影大部分都由項秋良和項河生擔任編導,項水柳和羅婧婧負責公司運營和制片工作,動作、攝影、造型等部門都有穩定的合作團隊,最大限度地保證了影片風格統一,其他網大的“系列片”都是類似的情況。“系列片”往往在場景、服裝、道具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從拍攝的實際情況來看,短時間內可以集中團隊力量以低廉的方式完成影片的拍攝工作,節省大量制作開支。再如騰訊視頻平臺上線的“魔游紀”系列包括了六部正片,同樣是由固定的制作團隊統一制作完成,并且以每兩周一部的方式上線。當我們重新審視這個問題的時候,發現網絡大電影的敘事動因與市場的聯系度遠比想象中的要高。“消費邏輯取消了藝術表現的傳統崇高地位”,這種極具后現代拼貼風格的藝術生產只有在網絡環境下才變得更有生命力。
網大的快速發展也就是近幾年的事情,視頻平臺一直在摸索拓展網絡市場的可能性,培育高質量且具有受眾黏合性的付費作品,主管部門也在不斷調整政策應對網絡大電影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幾年中,“蹭IP”現象逐漸消失,僵尸題材的熱度降低,低俗、粗糙的作品逐漸被市場淘汰,甚至有些網大連視頻平臺的自查都無法通過,臨時搭團隊草草了事的現象已無法跟上行業自身的發展。既要與院線電影建立差異性,又要面對行業自身的競爭,以“系列片”樣式“創造IP”或者將“IP精品化”使得制作到宣發的過程更節省成本,成為各大出品制作公司的內容布局方式,而且容易形成話題性。
二、“系列片”的文本生態
網絡大電影的“系列片”樣式構造了多維度的文本生態,貼合網絡傳播特征與IP的運作模式。與院線電影的系列片不同,前者在文本重建和文本切割方面更為靈活,充分發揮網絡視頻平臺數據傳輸的高效和便捷,建立一種受眾能夠積極互動反饋的信息空間,模糊文本生產的時間邊界,以間斷性且具有連續性的方式創造類文本。文本綿延使得觀眾對影像信息的接受度變得越來越復雜,以單部影片作為審美(批評)對象還是以整個系列為審美(批評)對象擺在了每個受眾者的面前。以“魔游紀”系列來看,任意一部的制作水準都有些差強人意,但是以整個系列作為關照,“魔游紀”系列所創造的世界觀和人物形象還是值得細細地品味,在“四大名捕”“靈魂擺渡”“罪途”等系列中都有類似的情況出現。
“系列片”使影像的文本內涵變得更加復雜。影像的網絡傳播將受眾納入到生產機制中,消弭影像與觀眾的距離感,可被點擊的作品像拱廊街玻璃櫥窗中的商品一樣在視頻平臺上陳列,前幾分鐘的片頭觀看如同顧客在商店里面試穿衣服,如果喜歡的話便會付費購買。“系列片”便加強了這種體驗,觀眾可以依觀影體驗進行即時地反饋,制作方會根據反饋重新構思下一部影片的風格。而視頻用戶在反饋意見的同時也建立了自審的渠道,誠如“彈幕電影”能夠使得用戶觀察自己和其他用戶的興趣點是否一致,影像信息的挖掘是否比其他用戶更加豐富。一旦用戶在“系列片”的頭部電影中獲得互動體驗的快感,會將此經驗延續至該系列的后續電影中,不斷地滿足好奇心和愉悅感。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體驗仍是以文本的再生產為前提的。以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共振”理論能夠很好地說明不同位置關系之間的空間狀態,卻無法解釋IP文本的不斷流變的延續感,以及觀眾的情感體驗。有學者將自然科學中的“遍歷”(ergodic)理論介入討論,“‘遍歷’文本所描述的是文本系統之間‘各態歷經’的關系狀態,它既包含空間性,也體現時間性、互文性和潛在可能性為其特征。”對于IP文本,“遍歷”理論更具有闡發性意義,于網絡大電影的“系列片”樣式而言,對文本切割和文本重建不純粹是美學實踐,而是一種傳播的方式和對文本內涵/外延的再定義,解釋了網絡傳播下用戶互動的復雜關系。“不論是文學作品還是其他信息,它們都不是一個基本的或穩定的意義的空間。文本之所以有意義,并不在其自身,而是由于它與其他文本之間的聯系。”前文提到的“魔游紀”等系列使得文本生態更有意味。值得一提的是,文本的互動關系有其復雜性,除具有原創IP特征的“系列片”之外,像“靈魂擺渡”系列與網絡劇《靈魂擺渡》的文本之間有密切的聯系,“陳翔六點半”系列可追溯至情景喜劇《陳翔六點半》,“四大名捕”系列則是來源于溫瑞安的小說,而“濟公”“大夢西游”“狄仁杰”則更傾向于公共式IP文本。
此外還存在另一個問題,“系列片”在文本內部是以什么樣的面貌呈現的?或者說它們用什么樣的內容吸引受眾?因為許多網絡大電影中并不比同類院線電影在制作、敘事層面更為出色。當我們從接受信息的角度去看待這個問題時,發現它們更符合“網生代”對新型網絡影像傳播的需求,既混雜著反類型敘事、生活吐槽、經典借鑒,還有更多天馬行空的影像創意,構建新的世界觀、穿插日常生活經驗都有不錯的效果,一旦這些信息使用行之有效,“系列片”在同一方面又不斷強化受眾的審美體驗。以“項氏兄弟電影”制作的網大來看,《降龍大師》用周星馳電影中的著名演員何文輝飾演樂色大師,在多處模仿、借鑒經典場景,《極道少女》致力于追求杜琪峰電影中的“儀式感”場景調度,昆汀·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電影中的經典場景得到搬演,日式漫畫中的女性符號作為重要的參照,這些都形成了很好的觀影效果,并在后續的“四大名捕”系列中發揚了此風格。即使是對經典IP作品的改編,文藝經典、現實生活的戲仿都成為一種有效方式,觀眾對原文本的熟悉和喜愛會納入到對影像作品的整體審美接受之中,傳播的效度會大大增強。原IP文本的意涵和邊界似乎變得模糊不清,文本與文本之間的流動越來越頻繁和隨意,甚至交織在一起難以分辨。不管是互文關系,還是容納受眾經驗的一個全新IP創造,都是在新媒介視閾下的生產與傳播,網絡文化介入影像作品的事實作為合理性的文本生態得到印證。
值得注意的是,“系列片”樣式的生產漸漸走向類工業化機制。從今天網大市場來看,題材細分和雜糅已是市場的主流,很難說某一影片是奇幻題材還是動作題材,創造新的類型文本已是趨勢。一旦奇幻題材比較受市場歡迎,巫術、異能、妖魔等元素都會被創作者所采用,對于目前網絡市場對作品敘事性要求還不高的情況下,這類題材很容形成類工業化模式,這也是為什么“系列片”往往有固定的團隊,因而文本復制和再生產的可能性越來越高。除了固定的制作團隊,對于影像作品而言,一種新的明星文化開始顯露。由于2015年《道士出山》的爆紅,演員彭禺厶便成為網絡受眾熟悉的形象,之后出演了很多僵尸題材的網絡大電影,甚至被塑造成“網大版林正英”,在他一系列的影片中代表了既有特殊能力又可愛善良的道士形象,“系列片”的一再生產不斷地強化觀眾的這種認知。在項氏兄弟電影的網大中,逗趣可愛的康寧、精靈古怪的何藍逗、古怪搞笑老頭岳冬峰、真誠且“靠實力單身”的劉林城等都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服裝道具、動作設計方面都準確貼合角色形象。這些人物大多反復出現在“系列片”中,使得影像符號的傳播得到延展,漸漸培養了新的網大受眾群體,在影像信息龐雜的傳播空間中,文本的再生產便是一種有效的途徑,觀眾會忽略某一信息,但不會對大量重復的影像風格視而不見。出品制作方已經意識到這一點,開始用行之有效的宣發策略擴大市場,吸引受眾付費觀看。
復雜的文本生態夾雜著市場、大數據、類型經驗、受眾多層次的互動體驗,對于近五年來迅速變化的網大市場并不奇怪了,我們更關心“系列片”為什么能夠貼合這種市場環境。后現代文化在不同的媒介中都會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并反襯流行文化構筑的文本話語空間。網絡大電影以反類型的姿態回應了“網生代”的文化訴求,將盡可能豐富的信息容納進來,符合了市場消費的邏輯,又暗含了影像文本的新態勢。從彈幕信息、影片評論來看,觀眾更多不滿意的是敘事層面,而對影像風格的大膽嘗試是欣然接受的。
三、影劇融合與媒介實踐
傳統藝術和大眾媒介的重新組合將文本的生產置于“再媒介化”(remediation)過程之中,即“新媒介從舊媒介中獲得部分的形式和內容,有時也繼承了后者中一種具體的理論特征和意識形態特征”,以往我們討論的大數據電影、彈幕電影、IP電影、“跨界”電影等樣本在以網絡為播放平臺的媒介空間中顯得曖昧不清,在“系列片”樣式中即如此,它加速了影像文化的分裂和組合,這種狀況也在媒介融合過程中有其必然性的一面。網絡大電影在生產的初級階段對創作人員沒有過高的文化品位要求,創作者和觀眾也從未把網大當做與院線電影具有相同樣貌的影像實踐,從前文談到的市場消費特性和文本生態中可見一斑。依靠網絡播放平臺,“系列片”吸收了傳統電影和電視劇的樣貌形成了獨特的影像類型,使每一部網大可以成為具有完整敘事的影像作品,同時又在風格上保持延續性。
在市場運作和文本生態層面上討論網大“系列片”樣式的生產和發展,最重要的還是依靠了網絡媒介的特性。事實上,網絡劇已經為“系列片”樣式在利用網絡平臺的優勢上提供了借鑒。自2009年《嘻哈四重奏》在網絡平臺首播以來,這種“劇集”樣式就帶給觀眾耳目一新的體驗,它的風格在今天一直得到了延續。不論是《嘻哈四重奏》,還是之后出現的《萬萬沒想到》等網絡劇都表明了“劇集”與網絡傳播的契合關系,觀眾沉溺在劇中對經典橋段的惡搞、反諷,以及對當下現實生活的調侃與借用,不論古今中外,只要是可被利用的素材都可以進行跨媒介雜糅。網絡劇的快速發展和成熟顯示了網絡平臺在影像的生產和傳播中有其特殊性的一面,既有影像風格的創新,同時又迷戀于宏大敘事的消解之中。意料之外的是,網絡劇在網大之前便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明星文化,盧正雨、白客、叫獸易小星等都因為網絡劇使他們更快地被大眾熟知。依“萬合天宜”公司為例,因《萬萬沒想到》的成功得以繼續推出《報告老板》《高科技少女喵》等網絡劇,還包括廣告、微電影、院線電影、脫口秀欄目等類型,影像生產、資本運作、明星文化圍繞著網絡平臺形成穩固的市場生態環境。網絡大電影從網絡劇的發展中找到了市場運作的經驗和影像生產的特征,同時借鑒了傳統電影的制作方式提高了其藝術性,使其在文本類型上更接近電影的特性。
借網絡劇的生產用來表明網絡對影像文化的重塑更具有代表性,這種類似于快速消費品的影像便于我們更好地認識網大的“系列片”樣式。值得注意的是,網絡劇在青年亞文化中間找到了同構(homology)關系,新的影像文化能夠與網生代的生活體驗相呼應,在不斷的生產與傳播中強化這一體驗。保羅·威利斯(Paul Willis)在《世俗文化》(Profane Culture)中就提到,“任何獨特的亞文化的內部結構特征都是有條不紊的:每一個部分都與其他部分有機地連在一起,通過彼此之間的默契,亞文化成員能夠理解他們所生存的世界”。不論是群體文化的身份認同,還是暗藏著對精英文化的抵抗,網絡媒介都提供了足夠多的發酵空間,新的影像類型形成已是必然。網大從發展之初就延續了網絡劇的文化訴求,“項氏兄弟電影”獲得小說《四大名捕》的版權之后,對原著的改編更為大膽,加入了更適合網大市場的奇幻色彩。“系列片”在借鑒網絡劇的運作模式的基礎上,又追求內容生產的電影化樣貌,使得“系列片”更像是電影和電視劇的混雜類型,在前文提到的“四大名捕”“陳翔六點半”等系列在每一集的樣貌上都更接近電影,但是又在整個系列中保持內容風格的統一性。依靠媒介而改變影像的樣貌并非網絡大電影、網絡劇所獨創,VR電影、影像裝置、數據庫電影等不同媒介所重塑的影像類型變得多種多樣,受觀影環境、觀眾訴求、播放介質影響,媒介與影像的互動關系越來越復雜。
具有影劇融合特征的“系列片”樣式在制作過程中也面臨不同的情況,在時長、敘事、風格、類型上存在差異性。從敘事形態來說,“魔游紀”“魔國志”系列所代表的網大追求部與部之間的連續性,“魔游紀”從第一部到第六部的故事是嚴密銜接的,角色行動遵從統一的世界觀設定,整個系列故事架構設定在“中土末年”時期,這樣的系列偏向于電視劇式的敘事方式,而“四大名捕”“陳翔六點半”等系列注重每部影片的獨立性,任何一部都可以作為有完整故事情節的電影。“山炮”系列稍復雜些,前兩部《山炮進城》和《山炮進城2》保持著故事情節上的連續性,其后便改編制作策略,僅保留角色定位和喜劇風格,制作了《超級大山炮之奪寶奇兵》和《超級大山炮之海島奇遇》兩部故事迥異的影片。雖然文本內部發生了變化,但都以同一IP制作發行。影劇融合的樣貌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以多樣化的方式相互交織,無論什么樣的形式,看似以市場為導向的網大其實背后都在定位內容生產的文化內涵。其實,電影頻道從嘗試制作數字電影以來,也出現了以“系列片”方式拍攝的“電視電影”,包括了“陸小鳳”“楊門女將”“火線追兇”等系列。當把“電視電影”納入討論的時候,按照電視平臺的需求制作電影同網絡平臺有著很大的區別,網大的“系列片”樣式與網絡媒介的貼合性更緊密,部與部之間的關系更符合“劇”的特征,注重IP文化的創造與重復生產,與網絡文化的互動性更頻繁,在傳播與播放的途徑上更符合當代青年人的生活方式。
“系列片”的影劇融合是基于網絡媒介形成的特性,將影像從傳統類型中解脫出來,以適應網絡文化快速地發展。從“系列片”的本文狀態來看,影劇融合的方式因出品、制作方的選擇有所不同,同時也受到政策、市場環境等方面的影響,但其所體現的文化內涵直接來源于網絡劇在媒介實踐中開創的影像風格,建立了與傳統電影和電視劇的差異性,在市場競爭中找到生存空間。在網絡大電影市場還未定型之前,多數項目選擇了“短、平、快”的方式,一旦該系列的熱度下降,出品、制作方可以隨時放棄原有IP項目的開發,這就是為什么有的“系列片”可以有六部之多,而有的“系列片”只拍了兩部便終止。影劇融合表面上作為一種藝術形式上的策略,實際上影響了影片內容的表達,劇情結構更類似于電視劇式的平鋪直敘、簡單易懂,在鏡頭運動、視覺效果等方面又追求電影化的風格,這種方式更符合網絡受眾的觀影習慣。
結語
網絡大電影在2016年的上新數量是2463部,2017年呈下滑趨勢,上新數量為1892部,到2018年直接跌至1373部,但以“系列片”樣式存在的網絡大電影都獲得了不錯的票房和口碑。近些年,不管是主管部門監管還是行業自審,“系列片”一直作為一種有效的實踐策略區分了傳統的觀影空間,以契合“網生代”審美品位為制作策略,提高影像傳播的互動程度。從呈現內容來看,“系列片”在“創造IP”和“IP精品化”的過程中用影劇融合的方式再造了文本生態,延宕了文本的時間流轉,著重強調了生產內容的青年文化特征,試圖解構經典影像的文化內涵。在互聯網的多點面傳播中,“系列片”建立了“受眾-作品-創作者”之間的有效互動,其信息共享方式誘惑受眾不斷地獲得消費快感,激活了來自日常性的生活經驗。同時,我們也看到了網大“系列片”與市場緊密的聯系,并在創造文本的同時又難免走向無序的影像拼貼之中。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