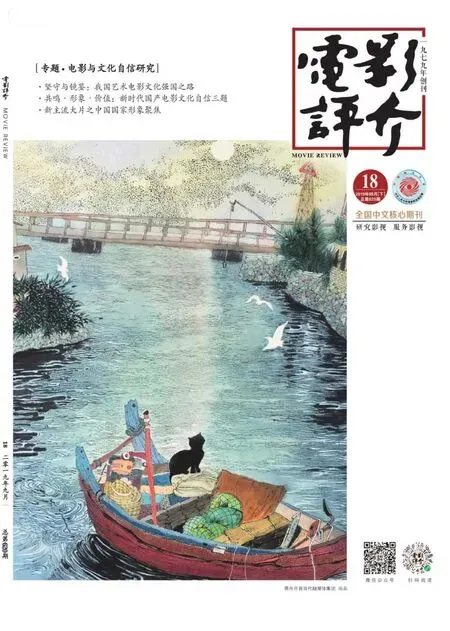《攀登者》宏微觀情感敘事解碼
宋 暉
2019年國慶節前夕,由李仁港執導的《攀登者》正式上映。作為一部主旋律影片,主要講述了中國登山隊1960年、1975年兩次從珠峰北坡登頂的事跡,在真實的歷史事件的基礎上有所改寫,使得故事有了很強的戲劇性和可看性。主演吳京在劇中占據了最大戲份,影片具有吳京近年主演影片的典型特征,即情節緊湊、注重視覺效果、將宏大敘事與情感敘事結合起來,尤其是情感敘事,比《戰狼2》更為突出和豐富。
一、宏大敘事中的家國情懷
作為一部國慶獻禮片,《攀登者》講述的是兩次攀登珠峰的具體登山者,也隱喻為國“攀登”的各行各業奮斗者。影片以兩次攀登為主線,一輕一重,重點講述了1975年,在老隊員方五洲和曲松林帶領下,李國梁、楊光等年輕隊員再次向珠峰發起登頂挑戰的故事。影片洋溢著家國情懷,在宏大的國家敘事中表現了登山運動員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
作為主旋律影片,《攀登者》追求一種史詩般的宏大敘事效果,力求將影片拍成一部體現“現代強國夢”的國家史詩。一般認為,史詩的敘事特征主要有兩種,一是要展示“廣闊的文化時空范圍”,二是在敘述中要體現“歷史的某些必然的規律性”。黑格爾認為:“史詩以敘事為職責,就必須用一件動作(情節)的過程為對象,而這一動作在它的情境和廣泛聯系上,必須使人認識到它是一件與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關的意義深遠的事跡。”[1]影片開始就是蓑羽鶴在天空自由飛翔的鏡頭,畫外音介紹這是一種鳥,為了飛越山峰,犧牲生命在所不惜。畫面隱喻了登山隊員的使命,也使得故事有了一種抒情性和史詩的悲壯性。影片簡單交代了1960年登山的背景:中國、印度面臨領土紛爭,珠峰登頂因此關系到國家大義,對于解決領土爭端有直接意義。故事從一開始就放在了國家宏大敘事的框架下展開,在影片中,更是通過演員點出了登山的意義:“我們自己的山,要自己登上去。”珠穆朗瑪峰成為一個符號象征,既是山在那兒要去征服的客觀實在,也是實現家國情懷的一個最高象征物。由于1960年登山隊為了救助隊員,丟失了攝像機,導致沒有拍攝下證明鏡頭,于是有了1975年的第二次登山:“要讓全世界看到我們登上自己的峰頂。”“要測量珠峰準確的高度,中國的高度。”
在影片中,這種家國情懷是通過反復強調表現出來的。于是我們看到,隊員在第一次登頂之后,高呼祖國萬歲;井柏然扮演的李國梁主動請纓要去擔起登山大任時說:“你們這一代人總是在國家最因難時接過國家的重任,為什么我們不能?”第二次登頂成功,吳京扮演的方五洲向總部報告時說:“報告大本營,報告祖國,中國登山隊成功登頂。”這種愛國之情是登山隊員之間的重要粘合劑,也是凝聚觀眾的向心力,國家敘事被成功放置在藝術修辭語境中。“敘事的目的就在于把一個社群中每個具體的個人故事組織起來,讓每個具體的人和存在都具有這個社群的意義,在這個社群中,任何單個的事件,都事出有因,都是這個抽象的、理性的社群的感性體現(黑格爾),這個社群或‘國家’、或是民族、或是人類。”[2]伴隨著電影進程,影片充分表現了第一代登山者的精神、第二代攀登者的情懷以及以徐纓為代表的氣象工作者、后勤工作者對攀登者不遺余力的幫助和支持。這些形象與精神已經上升為每一位觀眾的共同情感。攀登者通過攀登這一行為,將奉獻、團結、愛國主義等抽象的價值觀與強烈的家國情懷聯系起來。作為祖國象征的符號表征在影片的刻意安排下同樣一再出現,如登頂時插上的國旗、測量珠峰高度的覘標、中國登山隊在第二臺階處安裝的中國梯。這些符號表征以藝術的方式展示著祖國的形象,與影片敘事語境融為一體,成為國家敘事的重要修辭手段。
二、微敘事中的兒女情長
習近平總書記談到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時說:“一種價值觀要真正發揮作用,必須融入社會生活,讓人們在實踐中感知它、領悟它。要注意把我們所提倡的與人們日常生活緊密聯系起來,在落細、落小、落實上下功夫。”[3]如果說影片的國家敘事是通過史詩式的風格、宏大敘事和多種表征來實現的,那么劇中對于主要角色的性格和內心的表現則落實在微觀敘事上,主要是通過感情故事進行展現。與宏大的敘事相輔相成,在微敘事中體現人物情感,以情動人成為該片的重要特點。
“在絕大多數現代敘事作品中,正是敘事視角創造了興趣、沖突、懸念乃至情節本身。”[4]《攀登者》整個故事是以方五洲戀人、氣象學家徐纓的視角展開的,從她的視角講述登山隊的故事。徐纓的講述一開始就表明,兩人的感情結局是不圓滿的,給故事帶來了懸念。故事講述中,始終在全知全能的視角與徐纓的視角之間切換,給影片敘事帶來了更多的懸念與趣味。
整個影片穿插了兩段愛情故事,一段是方五洲和徐纓之間的感情故事,另一段是年輕隊員、攝影師李國梁和黑牡丹的感情故事。兩條感情線一強一弱,其中,李國梁與黑牡丹的感情故事略寫,方五洲和徐纓的感情故事則濃墨重彩,兩段感情故事在整個影片中占據很大分量,與登山故事融為一體。兩段感情均是因為登山開始,李國梁與黑牡丹是在登山隊認識,在訓練中產生感情,又因李國梁在登山中犧牲而導致剛剛萌芽的情感戛然而止。方五洲和徐纓同樣如此,由于1960年的登頂不被國際承認,方五洲因此有了心病,兩人之間有了一座無形的山,感情也隨之陷入危機和停頓。徐纓支持方五洲的登山事業,并冒著生命危險向登山隊通報氣象信息,導致肺氣腫病逝于珠峰,在臨終前向方五洲表白:“我們之間的山消失了。謝謝你讓我真正談了一次戀愛。”在這里,珠峰既是要翻越的物質的山,也是兩人要克服的心理上的山。家國情懷和兒女情懷融為一體,宏大敘事與個體微敘事融為一體,個人的感情因此不僅是抽象地和國家信仰結合了,個人和國家也融為一體。
影片不僅表現了愛情,還表現了親情和友情。隊員楊光雖患有馬凡綜合征,但仍然堅持登山,而他登山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希望過世的父親能夠在天上看到他登頂那一刻。方五洲為了救曲松林,舍棄了攝像機,導致第一次登頂沒有留下影像證明,此后10余年得不到社會理解,曲松林也因此一直無法原諒方五洲。兩人同時又有著深深的信任與默契,訓練時,一個眼神就可以站出來力挺對方。李國梁為了不拖累隊友,砍斷繩索掉入深淵。劇中對于感情的表現與故事情節緊密結合,因此,這種感情不再是灌輸性的,而是感染性的。
盡管故事的感情線設定有著獨特的刻畫人物性格和內心的作用,感情段落一般來說也符合觀眾的口味,然而,這兩段感情還是有一定的不足之處。方五洲和徐纓的感情僅僅是由于登頂得不到承認就陷于停頓,10余年不聯系,難以說服觀眾。李國梁和黑牡丹的感情戲也比較單薄,有些游離于故事主線。劇中表現浪漫情境的段落,由于受到西方電影情節的影響,與整個故事的氛圍不合。如方五洲第一次登頂成功,在興奮與喜悅中向徐纓表白,并在工廠建筑里展示攀登技巧,徐纓則在一邊念著西方小說教堂攀登求愛的段落,感受著方五洲的愛意,更像是從西方愛情電影里移植的情節。此外,黑牡丹偷偷闖入李國梁房間,想要接近對方,也顯得不合情理。
在個人情感敘事上,影片略顯老套,對于當代觀眾的審美趣味和個人傾向不夠敏感。當前觀眾認同的是“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主流敘事更多的是將個人幸福與祖國強大聯系起來,而非對立。然而《攀登者》中兩段感情無一圓滿,隱隱將個人幸福與祖國建設對立起來,并且這種對立缺乏合理情境,難以得到當前觀眾的認可。
三、當代文化語境下的情感敘事矛盾
情感敘事既是當代電影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教化、影響觀眾的重要手段。對于影片而言,對于情感的處理是影響傳播效果和票房的重要因素。如何處理情感,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
作為一部商業片,《攀登者》必然要將票房作為重要的考量,同時,影片自身作為主旋律影片和國慶獻禮片的定位,又必須要將弘揚主旋律作為主要任務,由此產生了該片在情感敘事方面的內在壓力。
對于《攀登者》而言,情感不僅具有連綴事件、推動情節的功能,更是影片表現的目標。主導情感是“為國登頂、寸土不讓”這樣一種愛國情懷,對方五洲個體而言,則又有為愛攀登的含義。《攀登者》情感敘事的基調是崇高的,在弘大敘事層面,這種崇高體現為為國家犧牲小我情感;在微敘事層面,崇高體現為個體在國家面前放棄個人兒女情懷。在《攀登者》中,一再強調的是珠峰的難以攀登,如在攀登珠峰途中,一直用字幕表明氣溫和風速。個體的渺小和珠峰的冷漠,形成令人畏懼的對比。片中有一個細節,在第二次登山時,寺廟里的喇嘛們表示,珠峰登頂不會順利,并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神并不總是慈悲的。珠峰的難以攀登在影片中有了一種絕對性,一種讓人敬畏的特質。這既是敘事的需要,也是激發觀眾崇高和悲壯情感的需要。珠峰讓人畏懼,并成為影片中要克服的對象,不僅出于愛國情懷要克服,而且為了個人情感也需要加以克服,在這個層面,家國情懷和兒女情長統一起來了。
然而,遺憾的是,影片在處理情感矛盾時的搖擺不定,導致影片的情感敘事出現了矛盾。導演李仁港說,影片的主線不是集體榮譽而是證明自己。這就與歷史上真實的登頂故事有了很大的不同,也與宏大敘事的主調產生了內在矛盾。影片的題材本身決定愛國情懷、宏大敘事必然是占據主導的,但由于商業片的內在邏輯,又使得影片導演去迎合市場、迎合觀眾、排斥宏大敘事,試圖以兒女情長去獲得觀眾認可。
強行扭轉主題的結果之一,就是兒女情長作為人物個性、證明自我的手段之一得到了過多的講述,“這種將愛情抽離出系統性來特別強調的現象,透露出強化文本消費性的意圖”[5]。這種脫離故事主干的過多的兒女情長,損害了影片的崇高感、悲壯感,使得影片失去了本該帶給觀眾的情感凈化體驗。
強行扭轉主題的結果之二,就是情感設置不合理,強行將攀登與個人情感糅合在一起,而不是尊重情感發生發展的自身邏輯,導致人物感情不符合邏輯,完全成為登山的附庸。而這又恰恰不符合當代觀眾強調情感獨立、自主的精神。
強行扭轉主題的結果之三,就是商業情感敘事目標與故事題材情感基調的矛盾。商業片的一個重要功用就是使觀眾的情感和本能在觀影中能夠得到充分宣泄和釋放,從中得到替代性滿足。因此,大團圓的結局是觀眾最為喜愛的。影片固然遵循了商業片的邏輯,將主角方五洲打造為超級英雄性的角色,每次能夠奇跡般脫險,然而對于《攀登者》而言,宏大敘事下的愛國情懷、為國奉獻一切的精神和眾志成城的集體榮譽感,是影片題材最為打動人心的部分。為了體現這一點,一個簡單的處理方式就是讓人物犧牲。犧牲生命、犧牲健康、犧牲愛情,于是有了李國梁的視死如歸、第一次登山隊長的犧牲,有了曲松林的殘疾、楊光的截肢。作為個人情感的兩段愛情,也是悲劇結尾,觀眾很難從中得到情感宣泄和替代性滿足。
強行扭轉主題的結果之四,就是對于情感的處理不合當時歷史情境。影片的個人情感敘事是拍給當代觀眾看的,但是20世紀60至70年代的情感語境與當今大眾文化語境有了很大區別,這就使得當今觀眾能夠接受的情感敘事和當時歷史語境下的情感不一樣,大眾文化語境下的世俗情感消費與歷史語境下的崇高奉獻產生了較大矛盾。對于《攀登者》而言,導致的結果就是當代觀眾無法理解方五洲和徐纓15年守望的感情故事,產生了排斥。仿佛是為了彌補前一段感情故事過于脫離當代語境的不足,影片又講述了年輕一輩李國梁和黑牡丹的感情故事。李國梁偷拍黑牡丹,黑牡丹心疼對方、在訓練中偷偷放水,黑牡丹熱情奔放、主動展開追求等這些故事情節更多像是在當代文化語境下展開的。其中,李國梁犧牲后,黑牡丹看著李國梁留下的偷拍照片泣不成聲,更是可以看到對日本電影《情書》的明顯借鑒(《情書》的男主角也是一位登山者,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巧合)。然而,盡管這段故事符合了當代觀眾的審美趣味,但是這種情感表達模式,無疑是與當時的歷史情境相悖離的,于是,盡管感情本身可以引起觀眾的共鳴,但是卻由于脫離了當時的歷史情境,同樣讓觀眾覺得虛假,難以產生代入感。
“商業性影片的情感敘事為大眾提供了釋放情緒和壓力的渠道,但并未體現個體真正的自我意識和真實需求。”[6]這句話可以說是點出了商業片情感敘事的本質。《攀登者》情感敘事始終處于游移之中,導致的結果就是影片既未滿足觀眾釋放情感的消費性欲望,也未能喚起觀眾深層的情感共鳴。
結語
2019年,國慶期間,三部主旋律電影《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同時上映。三部影片中,原來最被市場看好的《攀登者》卻在國慶檔期中墊底,盡管票房也不錯,但是相比另外兩部明顯落后。是什么使得這部影片在市場看好、檔期優先的情況下沒有成為檔期票房第一呢?
考察同檔期另外兩部影片,我們可以看到,《我和我的祖國》啟用了7名導演,吸納了大量明星演員,充分運用了流量思維,將影片打造成一部類似于春晚、能夠盡量照顧各方口味的影片,注意各方面的平衡——主題的平衡、明星的平衡、悲喜劇的平衡、現實與歷史的平衡,盡可能多地將可能的觀眾吸引到影院來。盡管有表現歷史的《前夜》《相遇》,但更多的故事發生在改革開放后,更容易得到觀眾的共鳴。《中國機長》更是直接改編自2018年川航的飛機事故。由于乘機出行已經成為中國民眾的重要出行方式,故事題材因此具有了接近性,加之同類型電影較少,題材本身又有了新奇性。同時更重要的是,這兩部影片的結果均是圓滿的(《我和我的祖國》中僅《相遇》結局不夠圓滿),符合國人對大團圓結局的偏愛。這一點,在節慶檔期尤為明顯。
相比之下,《攀登者》的故事時代背景相對久遠,與當前的文化和社會語境有所脫節,影響到了其票房。首先,在對個體情感的處理上,采用的是悲情敘事,不符合觀眾的觀影期待。其次,則是情感敘事上的邏輯性不足,難以說服觀眾。此外,《攀登者》的情感敘事與認知敘事存在巨大的矛盾。作為一部商業類型影片,《攀登者》可以歸類為行業片、災難片,觀眾期待看到的是專業知識和寫實的大場面,從而滿足自己的認知需求。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機長》基本沒有什么感情戲,卻仍然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收益,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在于影片滿足了觀眾的主要觀影訴求。盡管《攀登者》在藝術成就、敘事技巧、制作精良度上,比《中國機長》強出很多,但是過于煽情的情感敘事,忽視了觀眾的認知需求,導致在票房上未能超越對方。
《攀登者》在票房方面的挫敗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即如何更準確地把握觀眾的觀影心理,通過總結包括《攀登者》在內的主旋律電影的創作和運營經驗,從中得到一些關于主旋律電影創作和策劃、發行的共同規律。而這也需要電影界、學術界今后進一步加以研究、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