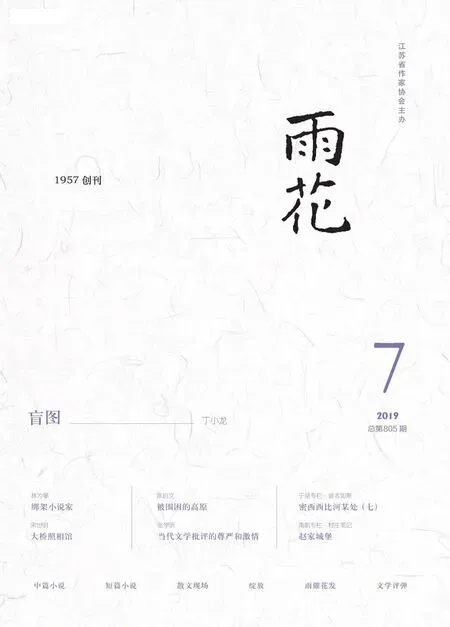對抗“存在的被遺忘”
——小說《大橋照相館》《如夢之夢》創作談
宋世明
長江大橋封閉維修,江蘇省美術館搞了一次大橋記憶史料展。最讓我動容的是那些普通人在大橋上的留影,盡管黑白老照片已經泛黃,但他們的面容是那樣單純明朗,他們的眼神是那樣熱切歡喜。此時此刻,無論是蘇北人,還是安徽人,無數人順著這橋走過去,許多人的生活、命運發生改變。
小說講的是世俗煙火,人心人性,悲歡離合,我也不能免俗。 小說,從本源上說,是世俗的。一個沒有世俗心的作家,是不可能寫出好小說的。即便像《紅樓夢》這樣從鴻蒙開辟寫起的務虛小說,作者也有一顆堅強的、具體的、無處不在的世俗心,否則,他就寫不出那種生機勃勃、栩栩如生的大觀園里的日常人情了。若從世情上看,《紅樓夢》絕非小說,而是一部偉大的非虛構作品。
但是,僅僅有世俗的煙火氣,這樣的文學作品是綿軟的快餐,是不能超越時代的,一切震撼人心、綿延后世的作品還要上升到哲學和審美的高度,還要飛躍人生的平庸,從而對人類敞開另一個世界。
有兩位作家的兩句話讓我念念不忘。蕭伯納說:“人生有兩出悲劇。一是萬念俱灰;另一是躊躇滿志。”加西亞·馬爾克斯說: “買下一張永久的車票,登上一列永無終點的火車。”作為一個作家,一生中,碰到憂慮與悲傷事情的概率一定比碰到歡樂與幸福事情的概率要高許多,因為這是寫作者的命定。但是寫作的人要堅韌,要堅韌地出生入死,哪怕萬念俱灰與躊躇滿志周而復始,哪怕明知人生列車永無終點,也要拿起筆寫下去,從而一再證明世界荒誕不經,而人為何生而為人。
人生是有限的,再活五百年僅是帝王的囈語,而人之不同于動物的地方,就在于人的精神追求總是想突破這種限制,對過往云煙竭力挽留,對未來世界充滿幻想,對人生形態努力延展。這就是文學不會滅亡的原因。
龍應臺把作家分成三種:壞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見愚昧,偉大的作家使你看見愚昧的同時認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憫。文學與藝術使我們看見現實背面更貼近生存本質的一種現實,在這種現實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還有直覺的對“美”的頓悟,對真的敬畏,對情的會心,讓平庸生活煥發出灼人的光,眩人的美麗,撼人的力,動人的情。
回看我們當下的文學創作,體量巨大,但大多精神單薄。有小聰明而無大智慧,有小抒情而無大高貴,有小苦難而無大悲憫。“當一種溫吞水式的、軟弱無力的平庸的文化正在緩慢地產生,這種文化像是一灘正在蔓延的淤泥,吞沒著一切,威脅著所有的東西”([英]齊格蒙特·鮑曼:《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代性、后現代性與知識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 頁)。
面對制造“溫吞水”的消費社會語境,作家們開始了分化,一部分人擁抱市場,喪失了獨立性和創新性,另一部分人沉溺于文學的審美幻象,在想象的游戲中探尋漢語語言的表現力和創造力之可能性,還有一部分人立足于文化的邊緣,以微觀政治的立場進行意義的抵抗。新的年輕文學力量也在不斷地涌現,但是,至少目前,他們還是一群面目不清的挑戰者,他們中更多的人還處在文學生產機制成名成家的幻象之中。
中國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氣和正直的純正品性。隨著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破壞和逐步衰弱,大多數的中國人,包括受過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內心世界的路口。而文學包括小說寫作能給我們一點點安慰嗎?能給我們一點點美感嗎?能夠讓我們的靈魂向上提升嗎?
作家如果要成為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的話,如何自救與救人,避免淪落,更或者拒絕淪為當下消費文化的生產者和代言人,精神的自由和文化的選擇將決定一切。
米蘭·昆德拉說:“我不想預言小說未來的道路,對此我一無所知。我只想說:如果小說真的要消失,不是因為它已用盡了自己的力量,而是因為它處在一個不再是它自己的世界之中。”
小說存在的理由是把生活的世界置于一片永久的光芒之中,保護我們以對抗“存在的被遺忘”。對于當代中國小說作家而言,它的使命又何嘗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