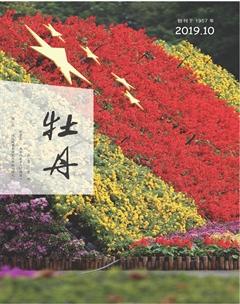從秋月看方方筆下女性對“家園”的追尋與其悲劇性
方潤
這些年來,女性題材已漸漸成為方方筆下的一個獨立視角,其作品常常以關注和思考女性命運為主,因此見解獨特、思想深刻。以《何處是我家園》為代表,方方精心設計秋月的每一段人生,從她對不同階段人生境遇的反應和轉變來剖析、揭露她的內心。如此一來,以秋月為縮影映射的那個時代女性集體的“家園喪失”感便引起更多人的思考,特別是秋月與方方其他作品中失去家園的女性不同,她的人生與自我人格都處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中,而她對失去“家園”的反應更是奮力追尋,她是這一類女性的集大成者,也是極端代表者,通過她,人們看到一個善良美好的少女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陰暗自私卻依然迷茫的。把美的東西毀滅,悲劇力量因而彰顯。
本文以《何處是我家園》中的秋月這一人物形象為代表,通過追溯她的悲慘遭遇,將她的人生分為三個階段,分析每個階段不同的選擇從而剖析她的內心世界,并以她與風兒為對象進行人物的橫向與縱向研究,以其性格轉變分析方方筆下女性對“家園”的探尋和它背后的深層次女性意識。方方這類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有關女性命運的寓言化寫作彰顯了悲劇力量和對人性思考的深刻性。
一、秋月人生的悲劇與選擇
秋月一生的傳奇經歷是方方寓言化寫作特色的體現,她的身世和命運會為讀者帶來內心的震動。她面臨很多次選擇,有的是主動做出的,有的是不得已而為之,細細深究她的每一次選擇可知,方方展示了秋月復雜糾結的心理和不穩定的精神狀態。作品中女主人公秋月的出逃歷程完全可以看作是對女性追尋理想家園的形象演繹。
“家園”的存在常常是以婚戀為核心的,這也是方方描寫女性逃不開的主題。小說《何處是我家園》更是以秋月的戀愛為開端。父母雙亡、長期寄人籬下生活在姑媽家的秋月雖然享受了良好的物質生活和教育機會,卻在冷漠勢利的家庭氛圍中感受不到家人或是親人的真切關心和疼愛,在她心里,她依然孤苦無依,精神處于無所依歸的狀態,那個保她衣食無憂的房子不過是容納她壓抑生活的住所,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家”。而她與宗子瀟的戀愛不符合她姑母的期許,因此在“家”的缺失和戀愛的沖動交織之下,秋月做出了她人生的第一個選擇,也是改變她命運的重大轉折——逃離。其實,這很讓人意外,平時弱不禁風的她竟然能毅然鼓起勇氣,戰勝來自各方面的恐懼,勇敢地隨男友私奔。這也暗示了她出逃的勇氣需要多大,她對當下生存狀態的不滿就有多深。
雖然精心謀劃,但她逃離姑母家去追尋精神棲息地的追求仍然受阻,天災人禍都在幫倒忙。秋月的精神遭受巨大打擊并產生劇烈變化。縱使整個私奔計劃極為周密,但誰也不會想到因為風兒的沖動和單純,兩人都慘遭歹人強暴。純潔天真的秋月便是從這件事開始轉變的。她不敢重返姑母家,此時面臨著原先姑母家的“家園”、與男友共建理想家園的道路都被堵死的困境,她陷入迷茫,縱使她心里多少對風兒有些惱怒與怨恨,但風兒的懺悔與殷勤稍稍給了她些許安慰。孤身二人,異地他鄉,她只好與風兒繼續流亡。但其實換位思考,一個人若是遭遇了秋月一般的飛來橫禍被人輪奸,會做出何種選擇?若是傳統女子怕早就自我了結生命,就像書中后半部分被騙受到侮辱的寶紅一樣。但與長期生長在山野間、貼近自然和傳統的保守女性寶紅不同,秋月和風兒至少不會自尋死路。那么在那種情況下,兩個妙齡少女為何不躲回家呢?即使會挨罵或挨打、接受旁人指摘批評,但和繼續流浪所帶來的女性獨特的生存恐懼、痛苦、遭際相比,這又算得了什么呢?若剖析她們二人的心理,尤其是秋月的,人們便會發現,在她心里,旁人的冷眼嘲諷和姑母家可能對她的再次精神虐待是比死亡、未知等更令她不想面對的事情。女性的精神桎梏與困境竟已如此。此處還能看小說中對性的莊重嚴苛與性的解放的比對,似乎沒有女人能逃離性枷鎖,秋月這個埋葬過去遠走他鄉的選擇也有性枷鎖束縛的推動因素。方方通過她們,尤其是寶紅反映出世俗社會對女性貞潔的傳統觀念并沒有徹底改變,雖然社會解放,但人們的思想觀念和性別偏見、性枷鎖依然扎根在社會的角角落落。
秋月人生的第三個階段是,秋月發現自己苦心經營了私奔計劃,仍不能實現追求精神家園的理想,因而心灰意冷,陷入沉淪之中,干脆開辦妓院,靠營造幻想中的“家”來麻醉自己、自我欺騙。從一開始與風兒為了生存不得已而為之,到后來生意紅火,她主動想象性地把妓院作為對自己找而不得的“家園”的替代性滿足,視其為虛幻的精神棲息地。不管是輪奸還是開辦妓院、向査老爺出賣身體,都揭示了男權文化對女性的不公正和殘酷,以身體為女性身份象征且由男人來評判價值。因此,秋月和風兒就永遠失去了自己的立身之所,只能通過向男性出賣身體討生存。更令人悲哀的是,不論是有文化的秋月還是沒文化的風兒,都認同了這一男性規定,遭遇強暴后主動自我放逐。值得慶幸的是,在這種男性主導的社會文化下,秋月能夠認清現實并面對現實,既不像脆弱的理想主義者那樣苦苦尋求男性的理解與同情,也不做逃避現實的悲觀主義者,放棄對自己命運的把握。她自始至終都在積極主動地、自發地尋找出路,她試圖在不斷的改變中尋覓得家園。一次次的摧殘與苦難,秋月在時代的重壓下變得老練、世故和富有現實的處事力,更多地學會了在夾縫中生存的能力。
二、秋月與風兒的對立統一與相互轉換
秋月與風兒的形象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對立面,但能成為相依為命的姐妹也證明她們身上存在共通性,可以說二人的形象存在對立統一的關系。首先,她們倆的名字都對自身性格有一定的象征和隱喻作用。秋月是富家小姐出身,人如其名文靜溫婉,如清秋高空懸掛的一彎缺月,美麗清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膽小懦弱,事事隱忍,恪守規矩禮法。風兒雖出身于市井間的平凡人家,活潑熱情、仗義單純、風流妖媚,沒什么文化,卻是父親和哥哥捧在手里的寶,事事依從、關愛有加,因此也放縱了她潑辣放蕩的性格。正如她的名字,她像風一樣瀟灑自如、無拘無束,事事想做便做、不計后果,但也敢于自我犧牲。
從橫向來看,風兒是秋月性格的“另一面”,她們倆合在一起才是一個完整的人物。風兒在秋月生命中的出現像是命運的安排,一個和自己截然不同的女孩子,憑借她的熱情和真誠漸漸走近秋月冰冷的心。風兒是另一個層面上秋月的化身,一個她沒能做到卻一定程度上渴望做到的自由瀟灑的自己。二人結合起來看,“秋月”便成了一個集端莊賢淑與放蕩自由于一身的多面人。
從縱向來看,秋月和風兒又各自都是性格處于發展中的人物,且一定程度上互相影響、互相轉換卻又不盡相同。在經歷了被強奸、小鎮留宿、山間開妓院等事情后,她們看透社會丑惡和人性嘴臉,風兒當初的單純開朗不見了,她任性而為、瀟灑自在的作風也有所減弱,慢慢地,學會屈服和迎合順從,可以說她是被那個社會一點點磨平棱角的女性。但她不變的甚至可以說是被激發的是她勇于犧牲自我的精神,也許是贖罪,也許是看在相依為命之情,也許還是出于貧家女孩對有學問的富家小姐的潛意識崇拜和“奴性”,她事事以秋月為先,將她的安全和利益放在自己之上,自己賣身賺錢給秋月,好事都讓給她,苦頭都自己吃。不但如此,精神上的關懷更是無微不至,總照顧秋月的心緒,雖然大大咧咧的她難免覺察不出心思細膩的秋月的很多情感,但她總在不斷努力,也因此不斷收斂自己的個性。而秋月一步步從善良柔弱、不知世事的書香門第小姐變成了富有心機、自私無情的內心強大之女性,到最后她倒是具有了一開始風兒所帶的那股“勁兒”。
秋月的經歷既讓人同情,又讓人氣憤。雖然社會的邪惡使她遭遇了不該承受之痛,但此后她所做的選擇大多都是主動的,自私自利的潛意識爆發,她為了尋求自己的“家”、精神棲息地,向當地一霸査老爺委身求全、放棄自己靈肉合一的堅守,也可以不擇手段、算計他人,為査老爺騙來寶紅供其享受,甚至可以在最后關頭拋棄一切,淡漠無情地離開。她的轉變是最大的,也最讓人嘆息。是什么促成了這一切?是社會嗎?雖然一開始可能有這部分原因,但到了山里,遇到那么多淳樸熱情、老實摯誠的山民,處于有規有矩、和平相安的小社會環境里,她何必如此走上那條路呢?這里可以看到方方在深入社會文化結構及性格心理結構層面進行探掘的努力。在當時社會解放、思想卻還沒徹底開放的社會文化中,秋月的一切動因還是源自她的內心,那種對精神家園的渴求常人難以想象,由于自小的家世、遭遇的經歷、理想的一次次破滅和現實的殘酷,她平靜的外表下藏著躁動不安、永遠得不到寧靜與歸屬的心,在沒有找到真正的“家園”以前,她的心永遠在彷徨。但其實連她自己可能都不清楚所謂的“真正的家園”是什么,她所使用的“手段”“計謀”都是她內心在尋找歸屬進行的嘗試。
三、“家園”與女性意識探析
秋月根深蒂固的“家園意識”值得人們探究,它不僅是這部作品的探討對象,更是方方這一類作品所強調的共同的悲劇根源和人物情節轉折點。其實,“家園意識”是由來已久的,自古以來,“男主外,女主內”等一整套儒家信條便把女性與“家”拴在了一起,可以說古時“家”是女性生活和生命的全部。但是,按照馬斯洛的層次需要理論,這個“家園”不僅應該能滿足女性的生理需要,更重要的是可以讓她感覺到安全、體會到歸屬與愛,體驗到自我的實現。也就是說,這個“家園”既是一個物質性的實體,要滿足女性的生理需要,又是一個女性自我能得到完全張揚的所在,能滿足女性精神層次的需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家園”成為秋月生命之所系,窮其一生也要追尋到它,使自己無處安放的心有一片精神棲息地。
正如《何處是我家園》中的秋月,方方筆下的女性常常最終走進了悲劇之中,她抓住這一矛盾焦點,深入到女性意識層面,探尋了這些女性悲劇的本質以及產生的根源。而這根源就是女性心中根深蒂固的“家園意識”與女性自身“強烈的自我遮蔽”之間難以解決的矛盾,這是一種女性生存錯位狀態,即指當下生存狀態下女性幻想世界和外部現實世界的嚴重脫離甚至對立。這體現在秋月身上明顯體現的一種差異困境。一方面,生命欲望的存在、自我情感的張揚、女性意志的覺醒,使她不甘于只做一個被動接受者,不甘于屈服,她內心有一個幻想的精神世界,所以即使柔弱依然勇敢地以私奔來反抗,此后每一個心機都是在為自己尋找精神家園這一反抗行為鋪路。然而不得不說,秋月的反抗是自私的,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為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惜傷害身邊的人、傷害山里那個淳樸美好的社會氛圍。另一方面,她依然被動地承受社會施加于她們的角色規范,通過外在界定自我,“作為他人欲望的主體被看”,這也正是為什么秋月一開始逃離姑媽家、步步經營建立妓院這個“家園”、最后卻又想要重回上層社會,她還是逃不開世俗的眼光,依然束縛在外界社會的個人定位里。方方正是要展現這一點,同時她也證明了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既對抗自身命運的暴戾,又服從內心召喚的真實,并在充滿矛盾的二者之間建立起黑夜的意識。讀者讀來內心五味雜陳,對秋月既同情又厭惡,既贊賞又批判,這恰恰彰顯了方方小說悲憫的人性力量和獨特的道德關懷,其深刻性不言而喻。
關于女性的結局和歸宿在哪里、家在哪里這一話題,方方本人談道:“我覺得女性的歸宿真是不好說。”確實,借秋月這個集大成的人物之口,作者也表達了這個觀念:“我不曉得我是從哪里出發的,最終還要到哪里去。”秋月承受著家園失落的痛苦,對尋找精神家園又是如此迷茫,對抗性的探索最終換來無望的結果,在自身墮落的同時,她的歸宿終究還是找不到。學者謝有順評價說:“舊的道德價值和生活方式對她已經沒有吸引力,但新的理想和生活又不知在哪里。”就這樣,帶著“何處是我家園”的一片茫然,秋月不計后果地苦苦追尋,然而這種追尋的失敗無疑是歷史的必然。所以,秋月的女性悲劇不是宿命的悲劇,而是像恩格斯曾提出的“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的沖突”。
(江蘇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