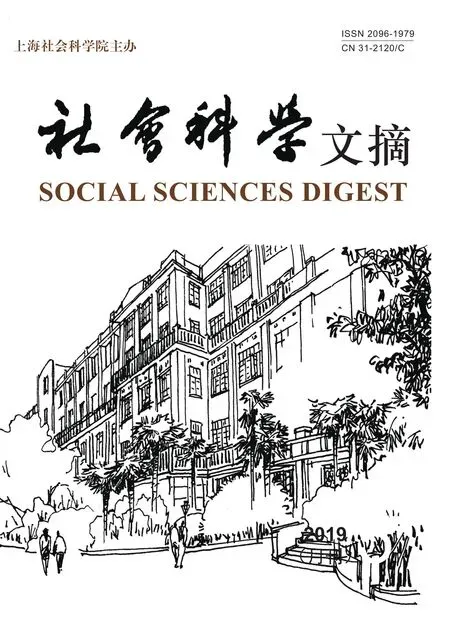中國經濟學派別:觀察與思考
——中國改革中“馬和非馬經濟學”的視角
改革開放40年已經把中國引入一個多元社會,如今的中國經濟學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思想地位在理論上的合法性無可懷疑,但西方經濟學正逐漸占據上風、成為事實上的主流。中國經濟學界呈現出明顯的多元性特點,出現了不同的甚至對立的經濟學派別。本研究只從“馬或非馬經濟學”的視角對中國經濟學界的不同派別作一觀察和思考。
“馬經話語群”和“西經話語群”
“話語群”是使用同一理論范式、話語體系和概念范疇的類學術共同體。在中國經濟學界影響最大的兩個理論范式就是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兩套話語體系有兩套概念范疇,分別在不同領域發揮主導作用,這種“普照的光”使幾乎所有的中國經濟學家都逃脫不了它的影響,留有它的印跡。
改革前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只有一個模式,作為其理論反映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只有一種聲音、一個主義、一個“學派”,都使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范式、話語體系和概念范疇。大學課堂講授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自己培養的學生也接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系統教育,所用的自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話語和概念體系,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和分析工具研究、討論中國經濟問題,講述中國故事,形成龐大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話語群。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對國外資本技術、西方管理方法和西方經濟理論的引進,特別是大量向英美等西方國家派遣留學生,大批在西方大學經過嚴格的西方經濟學系統訓練的碩士、博士回國,在把西方經濟學知識帶回國內的同時,也把西方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帶了回來。他們用不同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話語說話,用西方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和分析工具思考,用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和范疇交流。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學的經濟學教學發生了與原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西方經濟學教學與科研日益強化的同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被逐漸消弱和邊緣化。這種明確的西方經濟學價值導向的做法大大強化了人們的西方經濟學存在感,對青年學生進行大課時、大力度西方經濟學教育的結果是使年輕學者一經走上經濟學學術之路就習慣地認為經濟學就是西方經濟學,而政治經濟學不過是一門“思想政治課”。這樣年復一年,周而復始,使以西方經濟學思維方式思考問題的“西方經濟學話語群”茁壯成長,日益擴大。
“話語群”并不是個嚴格的“學派”“流派”概念而僅僅表明群內成員的話語體系相同、使用的概念范疇相同、在其成果中可以檢索到共同的“關鍵詞”,但這些詞語的使用者對其的態度可以是肯定的,也可能是否定的,有著同樣“關鍵詞”的文獻有的作者是贊同、支持,有的卻是質疑、批評,情況并不相同;同屬一個話語群并不意味著其基本立場、理論觀點、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的一致,相反,同一“話語群”的學者可以有著彼此相反的立場、觀點和政策建議而形成不同的經濟學派別。
改革開放40年,兩個“話語群”此消彼長。改革開放前“馬經話語群”一群獨大,現在的“西經話語群”已呈壓倒性優勢,而“馬經話語群”隨著其成員年齡的日益老化和新加入成員數量的邊際遞減而正加速弱化。在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一種非常耐人尋味的現象。
幾個影響比較大的經濟學派別
(一)西經話語群的三個派別
1.市場化改革派:該派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吳敬璉研究員為代表,相當一批身處高位的政府高級官員置身其中,對中國高層決策有著直接而巨大的影響,在中國的經濟學各派別中擁有最為豪華的陣容,很多成員都既是高級官員,又是知名學者。20世紀80年代改革大潮中吳敬璉流行全國的“吳市場”綽號也足以說明該派在改革中無可替代的地位和在社會各界的影響。早在改革初期的1983—1984年吳敬璉就作為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的訪問學者在美國耶魯大學進修學習,深入接觸了西方市場經濟理論。該派推崇自由市場原理,倡導競爭性經濟體制。抱怨中國模式是“強勢政府駕馭市場、國有經濟主導國民經濟”以及所謂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作為國家決策最高智囊他們卻不大熱衷“主義”的爭論,只提改革的具體主張,直接或間接參與國家政策的頂層設計,對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發展,功不可沒,但同時也善于在“體制改革”與“制度改變”的邊緣地帶發揮作用,雖時常被“新馬派”經濟學家指責為以西方經濟自由主義誤導改革、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有違國家憲法,卻很難看到他們的聲辯。
2.現代經濟學派或西經中國化派:市場化改革派重在采取行動、推動市場化進程,而現代經濟學派或西經中國化派則強調推廣理念、營銷市場化思想,二者形成鮮明對照。與市場化改革派的官方色彩不同,該派占據大學經濟學教學、科研和學科建設的重要領域,對中國的經濟學教育、普及、傳播,進一步對中國經濟學的未來、中國青年經濟學世界觀的形成,影響深遠,因而對中國下一代的成長和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培養,產生影響,這使該派比其他經濟學派別有著更久遠的考慮。該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原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田國強和廈門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洪永淼等幾位教授,清一色海歸博士,在國外著名大學接受過正規、系統的西方經濟學訓練,有著“現代經濟學”在中國之代表的美譽,其對西方經濟學運用嫻熟,善于用正宗地道的西方經濟學語言說話,具有學術的面貌,很有“科學形式”,在國內為眾多青年經濟學人所崇拜,在中國大學經濟學教研、學科建設和管理者以及研究生中有相當影響力。認為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就像數學、物理學及其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那樣是無地域和國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獨立于他國的經濟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西方經濟學是適用于任何制度條件下的經濟學,主張用西方經濟學話語講述中國故事,用中國案例來驗證、豐富西方經濟學,把“外界承認”作為中國經濟學創新和發展的目標。
3.西經背景國情派:與市場化改革派采取行動來推行市場化、西經中國化派推廣理念以營銷市場化思想不同,西經背景國情派是運用西經工具解釋中國奇跡、力挺中國崛起、強化中國自信。現代理論、留洋背景和重視國情是該派的鮮明特色,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和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教授,他們都是中國高層智囊,都有深厚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基礎,掌握先進的現代分析工具和方法,又都做著專職國情研究,比較了解中國實際,懂西經而不囿于西經,理論先進而不激進,能夠運用西方經濟學理論和方法論證、支持中國經濟發展,解釋中國奇跡,完成有份量的國情研究報告,發揮政策決策咨詢作用,在國內和國際都有很大影響力。值得指出的是,該派雖系“西經話語群”卻能對不顧國情盲目迷信西方經濟學的傾向進行批評,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情結,相反,他們用西方經濟學話語體系“釋放善意”的方法也常遭到新馬派經濟學家的激烈批判 。
(二)馬經話語群的派別
1.新馬派經濟學:主要代表為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教授程恩富學部委員,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理論宣傳和意識形態領域有重要影響力。主張以馬學為本,西學為用,國學為根,國情為據,世情為鑒,他們精于馬經、兼通西經,還懂西馬(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歐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以及世界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術研究機構都有著廣泛聯系,堪稱中國最為國際化的經濟學派別。和其他學術派別不同之處明顯在于,它有著十分強烈的主體意識、責任擔當和批判精神,是一個“戰斗學派”。表現為學派頂層設計完善,組織機構健全,與世界各國左翼學者和政黨組織保持頻繁學術交往,主持多個國際性和全國性學術組織作為該派學術新人培養和學術交流平臺,主辦多家中外學術期刊作為新馬派經濟學學術陣地,承辦多個國際國內學術論壇釋放新馬派經濟學聲音。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階級立場、基本觀點和研究方法,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理想,關注改革開放發展現實,具有很強的責任心、使命感和戰斗性,對其認為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經常進行指名道姓和不留情面的批駁,甚至對一些被認為不利于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新改革政策措施也敢于提出異議和修改建議。在工農階層和學術界都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尤其在有著改革前后兩種經歷的部分知識人群中有很大影響力,是從另一個方向直接間接對高層決策產生重要影響的學術力量。但該派也被指有些成員的觀點有過于理想化、超越階段性、不具可行性之嫌。
2.闡釋派經濟學和個性派:闡釋派經濟學在解讀中央政策、解釋和闡發中央精神方面地位無可替代,聚集著馬經話語群最多的經濟學者,一大批知名經濟學家身在其中。馬經話語群里的個性派學者之所以與眾不同,在于他們確確實實做著馬克思經濟學研究,使用馬克思經濟學話語體系和概念原理開展研究,經常活躍于全國各種政治經濟學學術活動,展示于人的是他們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功底,但他們總能研究出讓人意外的成果,即他們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出發研究得出的結論看上去往往不利于馬克思主義。
經濟學派別與改革走向
不同的學術派別決不僅僅是學術觀點的不同,更重要的還有學者基本立場、價值取向、代言人群等方面的差異,不同學術派別為不同的利益群體發聲,他們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一定的民意,這些民意都會通過種種渠道反映在國家改革、開放和發展的高層決策和具體實施方案中,不同的經濟學聲音和政策建議會化為一定的社會行動,這些行動是各領域、全方位的,有著無數的方向,先是在變化著的各個方向的邊際上然后是整體上逐漸改變著各領域行為主體的利益格局,由此規制著整個社會演進的趨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機統一和內在結合,不同學術派別對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對基本制度和經濟體制有著不同的偏好和側重。有著官方背景的市場化改革派強調改革、開放和發展的市場取向性,在國家決策咨詢領域發揮主導作用;占據高校經濟學教育領域并對教育主管部門有著巨大影響力的現代經濟學派或西經中國化派強調經典的西方經濟學的科學規范,在經濟學教育和學科建設以及人才培養領域有著舉足輕重作用;而新馬派經濟學則強調馬克思主義對中國改革的指導作用和改革的社會主義自我完善之性質不能改變,主張政策的制定和改革的推動都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輿論宣傳和意識形態領域地位顯赫。
改革走向的確定和改革政策的制定其實并不單是最高決策者的個人意志,而是個公共選擇問題。恩格斯說:“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為一個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然而從這一事實中決不應作出結論說,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里面的。”這里,恩格斯強調的就是社會選擇不是“一致同意”而是不同意志的綜合與平衡,這可能是最早的“公共選擇思想”。由于不同的利益群體的存在,任何改革方案都有一個是否遭到抵制、反對或反抗的問題,這是一個復雜的博弈過程,不同的經濟學派別實際上分別代言相應群體而參與其中。正如樊綱所言:“所謂政府政策,不過是執行這一公共選擇結果的具體形式罷了。”因為“政府不過是在它們之間周旋的一種平衡機制”,“政府政策,不過是這種利益平衡的一個產物”。汪丁丁的表述更加直白:“政治是折衷各種利益,而不是只代表一種利益。在西方民主政體下,布坎南假定每個政治家所代表的那個集團的利益可以在類似市場均衡的政治均衡中得到‘折衷’。但這不適于‘一黨執政’的情形。在后者,執政黨的領袖要負責折衷各方面的利益。”
中國改革走向和改革政策也是如此。新馬派經濟學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中的“社會主義”方向,不斷提醒決策者、引領社會公眾,不能偏離馬克思主義指導和社會主義道路,防止改革“走得太遠”超出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之外。市場化改革派和西經中國化派則更加關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市場經濟”、市場化改革,提請決策者要加快、更深地市場化。中國實際的改革決策會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總體指導思想的基礎上廣泛聽取包括不同經濟學派別在內的社會各種不同聲音,綜合、統籌、權衡各方面的意見,使改革政策達到“和而不同”的和諧效果。在這個意義上,甚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改革目標的確定本身,就是在一個長的歷史時期中決策者對各種不同意見和力量進行折衷、妥協、“和諧”的動態結果。
在這個過程中,新馬派經濟學“兩線作戰”:在實際改革進程中盯著市場化改革派,市場化改革步步進逼,經濟自由越來越多,非公經濟日益擴大;在經濟學學術和學科建設上盯著現代經濟學派或者西經中國化派,大學的經濟學教育和學科建設日益西方經濟學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被動地“你進我退”。在艱苦的“兩線作戰”中,新馬派經濟學步步退守,又不得不以攻為守,養成了“戰斗學派”的風格。但實際改革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社會主義的標準對改革的約束,隨著不斷深化改革的現實進程,不斷因“初級階段”而被放松、軟化,在各項改革的邊際上不斷觸碰新馬派經濟學家的改革“底線”和“可容忍限度”,逼著他們對原來理解的“原則”和原來掌握的“標準”作出適應性調整,以體現時代精神與時俱進。與日常行為不同的是,在創新的邊緣上“違憲”可能并不是很嚴重的事,中國改革開放這件事本身就是對原有憲法和法律的突破,當憲法本身也成了需要改革和完善的對象時,它就不再是獨立于改革進程之外的客觀參照物或者標準,改革的過程就成了制憲、改革突破、“違憲”、修憲、合憲,再改革突破、再“違憲”、再修憲,使憲法更趨完善以更適應“初級階段”要求的過程,40年改革開放我們正是這樣走過來的。這一過程中,各經濟學派別都想使中華振興、讓中國偉大,但理念各異、主張不同,正是這種經濟學理論觀點的百家爭鳴、相互制約,為國家改革決策提供了多種選擇和參考,保證了使出臺的政策更加合乎民意、符合國情,促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