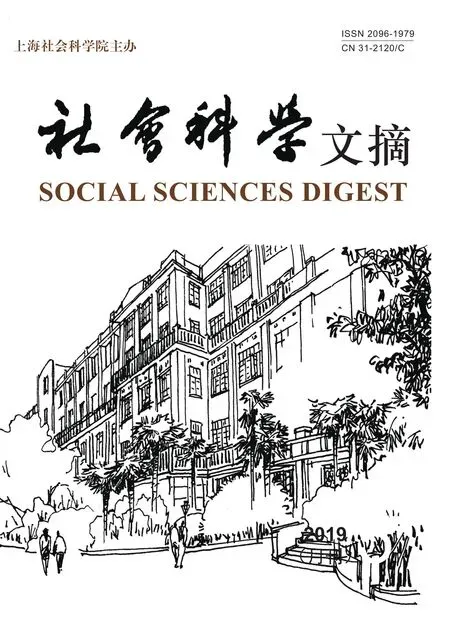明清絲綢之路與世界貿易網絡
——重視明清時代的中國與世界
從19世紀起,中國歷史就真正進入了世界歷史和歷史哲學的范疇之中。黑格爾《歷史哲學》一書,全面考察了中國歷史與世界各民族歷史的諸多同異與特性。黑格爾認為:“中國實在是最古老的國家,它的原則又具有那一種實體性,所以它既然是最古老的、同時又是最新的帝國。中國很早就已經進展到它今日的情狀。但是因為它客觀的存在和主觀運動之間仍然缺少一種對峙,所以無從發生變化,一種終古如此的固定的東西代替了一種真正的歷史的東西。”([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160頁。)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以人的絕對意志和人類精神的發展作為歷史發展的標尺,在他的眼中,中國歷史因為在宗教和精神方面受制于專制王權,所以是停滯的,沒有歷史的,也是封閉的。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影響了以后近一個多世紀歐洲歷史學對中國的歷史敘事。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起,人們才重新開始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看待中國歷史,尤其是明清中國與世界各地的貿易聯系。
“絲綢之路”研究推動世界對中國的重新認識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歐洲的漢學開始了明顯的分化,原來歐洲中心論的一系列理論和觀點遭到質疑。貢德·弗蘭克1998年出版的《白銀資本》認為從航海大發現直到18世紀末工業革命之前,是亞洲時代。《白銀資本》一書描繪了一個明清時廣闊的中外貿易的宏大畫面,將中國拉回到世界歷史的中心。([德]貢德·弗蘭克著、劉北成譯:《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美國歷史學家彭慕蘭于2000年出版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世界經濟的發展》一書詳細考察了18世紀歐洲和東亞的社會經濟狀況,認為1800年以前是一個多元的世界,沒有一個經濟中心,西方并沒有任何明顯的、完全為西方自己獨有的內生優勢。(參見[美]彭慕蘭著、史建云譯:《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頁)
與此相關聯,王國斌和羅森塔爾合著的《大分流之外:中國與歐洲經濟變遷中的政治》,圍繞著1500—1950年之間的各種世界經濟的要素進行討論。([美]王國斌、羅森塔爾著、周琳譯:《大分流之外:中國與歐洲經濟變遷中的政治》,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李伯重《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亦從全球化的角度來描述明清以來中國與世界的貿易與政治聯系。2006年,彭慕蘭與史蒂文·托皮克新出版的《貿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會、文化與世界經濟》,作者表達了“中國的歷史和世界貿易的歷史已經通過各種途徑交織在一起了”的思想。
實際上,早在19世紀后期起,西方漢學家已經開始利用第一手的調查資料與中西方文獻來重建中古時期的中外歷史。1868年起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中國進行了七次地質考察。1877年,開始出版《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書。他將中國與中亞、印度之間的貿易通道稱為“絲綢之路”(德文Seidenstrasse或Sererstrasse)。“絲綢之路”這一概念早在古希臘歷史學家馬賽林的《歷史》中就已經使用,但由于李希霍芬在此后的西方地理學界的重要影響和地位,他的這一用語成為學界公認的名稱,從此“絲綢之路”就被公認為指稱公元前后連接中國與中亞、歐洲的交通線路的專用概念,這一“再發現”產生了世界性影響。由此,歐亞古代的貿易與文化聯系也引起人們的重視。
對于歷史的描述,從封閉停滯的中國到世界貿易中心的中國的巨大變遷,反映了西方歷史學界不同時期的中國認識觀。現在我們通過中國自身的歷史文獻與檔案史料來重新看待這一時期的中國歷史,這是在以上路徑之外的一種全新的中國歷史觀。從明清檔案來看,中國與世界在陸路、海路存在著多條貿易路線:陸地上除了傳統的西向、北向的兩條絲綢之路外,還有東向的朝鮮貿易、南向的通往印度、安南、暹羅的高山之路等四條主要線路;海上除了傳統通往歐洲的海路外,尚可細分為南洋、美洲、日本等四條海路。這樣,以明清檔案還原的八條絲綢之路貿易網絡,重新展現了明清以來中外的聯系途徑。八條絲綢之路遠遠不能涵蓋所有以中國為中心的貿易路線與貿易活動,但這是一個新的認識框架,我們希望這個框架能夠描繪一部新的世界歷史。
明清時代陸上絲綢之路與貿易
從古典時代起,廣闊的亞歐大草原“為由歐亞大陸邊緣地區向外伸展的各文明中心進行交往提供了一條陸上通道。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創造了歐亞大陸古老的核心文明,而大草原則便利了這些文明之間的接觸和聯系”。([美]L.S.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第59頁)貫穿其間的貿易通道,也就是為世人熟知的絲綢之路。“沿著它,進行著貿易交往和宗教傳播;沿著它,傳來了亞歷山大后繼者們的希臘藝術和來自阿富汗地區的傳播佛教的人。”([法]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10頁)
16世紀起,“俄國同中國通商是從和這個國家交往的最初年代開始的。首先是由西伯利亞的商人和哥薩克自行開始同中國進行貿易”。([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編著,中國人民大學俄語教研室譯:《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匯編1619—1792》,第513頁)由于俄羅斯處于西歐通往中國的中間地位,所以英國也多次派使節前往俄羅斯要求開通前往中國貿易的商路。俄羅斯外務部保存的檔案記錄了1616、1617年間英國使節麥克利與俄方會談的紀要,其顯示,盡管俄羅斯設法阻止了英國的請求,但卻下令哥薩克軍人調查通往中國的商路。([俄]齊赫文斯基編:《十七世紀俄中關系》,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3頁)這些活動傳到英國,引起王室和政治家的注意。英國地理學家佩爾基斯記錄了俄羅斯人開辟的通過北方草原通往中國的商路。([英]佩爾基斯:《他的旅行歷程》第三卷,轉引自[蘇]沙斯季娜《十七世紀俄蒙通使關系》,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22頁)中國文獻《朔方備乘》記錄蒙古喀爾喀、車臣二部都曾經進貢俄羅斯鳥槍一事,認為“謙河菊海之間早有通商之事”(何秋濤:《朔方備乘》卷三十七《俄羅斯互市始末紀》),即指葉尼塞河上游與貝加爾湖之間的貿易路線。
18世紀俄國著名的文獻學家、歷史學家尼古拉·班蒂什根據俄羅斯外交事務部檔案編著的《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匯編1619—1792》一書收錄了兩件中國明代皇帝致俄皇的“國書”,其中一件標以萬歷皇帝,一件標以萬歷皇帝之子,文書記載了兩名俄羅斯使臣因通商事前往中國,中國皇帝則表達了鼓勵之意。不管這兩件文書的真實程度如何,該文件收錄在俄皇米哈伊洛維奇的外務衙門檔案中,在反映中俄早期貿易關系的文獻中具有一定價值。(兩件文書收錄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編《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匯編(1619—1792)》一書中,但根據耶穌會傳教士的識讀,認為這兩件文書時間更早,為明成祖時代致北方王公的冊封詔書。由于明清時代中國特有的天下觀,直至晚清之前,中國皇帝致外國的文書從未以國書的形式冠名。因此西方各國外交檔案中的中國皇帝“國書”,皆為翻譯明清時代皇帝的詔書、上諭而來。)
根據俄方檔案記載,第一個從莫斯科前往中國的使團是巴依科夫使團,1654年前往辦理商務,并奉有探明中國“中華帝國可以購買哪些貨物,可以運去哪些貨物,由水路或陸路達到這個國家有多遠路程”等信息的使命。([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編,中國人民大學俄語教研室譯:《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匯編(1619—1792)》,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2頁)在中國檔案中,從順治到乾隆期間至少有50件檔案內容為與俄羅斯貿易的,貿易線路涉及到從東北的黑龍江、嫩江、北京、張家口、鄂爾多斯、伊犁、哈薩克多條草原絲綢之路的商道。這反映在明清時代,傳統的草原絲綢之路進入了鼎盛時代。(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閣滿文題本,順治十二年十月初七日)
北方貿易路線上的主要商品為茶葉。據說最早進入俄國的茶葉是1640年(明崇禎十三年)俄國使臣瓦西里·斯達爾科夫從中亞卡爾梅克汗廷帶回茶葉二百袋,奉獻給沙皇。這是中國茶葉進入俄國之始。(蔡洪生:《俄羅斯館紀事》(增訂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39頁)即使在海運大開之后,通過陸路進入歐洲的茶葉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陸路運輸茶葉的質量要遠遠高于海洋運輸茶葉的質量。《海國圖志》也記錄:“因陸路所歷風霜,故其茶味反佳。非如海船經過南洋暑熱,致茶味亦減。”(魏源:《海國圖志》卷八十三《夷情備采三》,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1986頁)這種茶葉質量的差異為19世紀的歐洲人所共知。馬克斯在《俄國的對華貿易》一文中指出,恰克圖貿易中的中國茶葉“大部分是上等貨,即在大陸消費者中間享有盛譽的所謂商隊茶,不同于由海上進口的次等貨。俄國人自己獨享內地陸路貿易,成了他們沒有可能參加海上貿易的一種補償”。(馬克斯:《俄國的對華貿易》,《馬克斯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
海上絲綢之路與海洋時代
“歐洲航海者創造了一個交通、交流、交換的環球網絡,跨文化之間的互動比以往更為密集和系統了。”在傳統航路與新航路上,歐洲商船把波斯地毯運往印度,把印度棉花運往東南亞,再把東南亞的香料運往印度和中國,把中國的絲綢運往日本,把日本的銀和銅運往中國和印度。而西班牙人、荷蘭人在加勒比海、美洲建立的殖民地,使得歐洲的產品越過大西洋換來墨西哥的白銀、秘魯的礦產、巴西的蔗糖和煙草進入歐洲市場和亞洲市場。非洲的土著居民則被當作奴隸而販運到各大殖民地([美]杰利·本特利等著:《新全球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頁)。傳統的地區性貿易網絡“已經擴大為而且規模愈來愈大的擴大為世界市場”(《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頁)。根據一個從1500—1800年間7個歐洲國家抵達亞洲船只數量的統計來看,從最初的700多艘的總量增長到了6600多艘。而美洲到歐洲的金、銀販運量在這300年間則分別增長了20倍和10倍,中國的白銀進口量則從1550年的2244噸增長到1700年的6951噸([英]安格斯·麥迪森著:《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4、55頁)。葡萄牙人在記錄他們的東方貿易時說:“歐洲與東洋的貿易,全歸我國獨占。我們每年以大帆船與圓形船結成艦隊而航行至里斯本,滿載上毛織物、緋衣、玻璃精制品、英國及富朗德兒出產的鐘表以及葡萄牙的葡萄酒而到各地的海港上換取其它物品……最后,在澳門滯留數月,則又可滿載金、絹、麝香、珍珠、象牙精制品、細工木器、漆器以及陶器而返回歐洲。”([日]百瀨弘,郭有義譯:《明代中國之外國貿易》,載《明代國際貿易》,臺北學生書局1968年,第41頁)這反映了無論從數量還是種類上,進入國際市場的商品都大幅增加。
固定的商品交易所、證券市場開始出現也有重要意義。1531年安特衛普商品交易所開業,“供所有國家和民族操各種語言的商人使用”。阿姆斯特丹、倫敦此后也分別出現糧食交易所和綜合交易所。最后,處于新航路之上的港口開始成為世界貿易中心,取代大陸體系時代的陸路交通樞紐城市的地位,開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參見李吟楓:《世界市場的形成及歷史作用》,《世界歷史》1986年第2期)
起先是技術的進步帶來的探險與新航路的開辟,然后是商品與人員的全球性流動,最后是法律與文化在各地區的碰撞,一個以海上貿易路線為紐帶的海洋時代開始興起并主導了世界歷史的走向。
明清時期的全球化貿易網絡及其重要意義
置身于一個商品和貨幣、物資與人員、知識與宗教頻繁往來的時代,明清的中國不可能自外于世界。明代萬歷時期福建巡撫許孚遠在評論嘉、萬時期的海禁政策時說:“彼其貿易往來、糴谷他處,以有余濟不足,皆小民生養所需,不可因刖而廢屨者也。不若明開市舶之禁,收其權而歸之上,有所予而有所奪,則民之冒死越販者固將不禁而自止。”([明]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卷四百《疏通海禁疏》,明崇禎平露堂刻本)明清兩代都實行過的海禁政策:“然雖禁不嚴,而商舶之往來亦自若也”,但長期來看,給沿海人民甚至國計民生都帶來嚴重后果,所以地方大員多以“開洋”為主要籌劃:“莫若另為立法,將商人出洋之禁稍為變通,方有大裨于國計民生也。”([清]靳輔:《文襄奏疏》卷七《生財裕餉第二疏“開洋”》,中國基本古籍庫本)
通過數件明代天啟、崇禎年間兵部尚書有關海禁事宜的題行稿,可知明朝皇帝長期堅守的海禁政策至明末清初已與日益增多的對外貿易需求相悖。1684年,在內閣起居注中有康熙帝召集朝臣商議開海貿易的記錄。翌年即1685年,清政府在東南沿海創立粵海、閩海、浙海、江海四大海關,清廷實行開海通商政策。(李娜:《從玉帛相贈到兵戎相見:<明清絲綢之路檔案圖典>海路大西洋部分檔案解讀》,參見《第三屆“一帶一路”文獻與歷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頁)
1761年,廣東巡撫托恩多上奏“瑞典商船遭風貨沉撫恤遇難水手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朱批奏折:《英荷瑞國洋船泊黃埔,瑞典商船遭風貨沉撫恤遇難水手》,檔案號04-01-32-0402-025),請求按照慣例,給予朝貢各國或外洋各國來中國貿易的商船予以災難救助。從明清時代對朝貢體系和外洋貿易的維護來看,中國制定了明確的有關維護這一范圍廣闊的貿易秩序的措施與政策。無論是陸路貢使和商客的接待、陪護、貿易糾紛、借貸的規定,還是海路貿易中由于漂風、漂海等遇難船只、人員、貨物的撫恤、資助,都頒布有明確的措施和法令。(《大清會典》在“朝貢”條目下設有專門的“周恤”、“拯救”等,規定了朝貢貿易或者自由貿易中發生的疾病、死難、飄風、飄海等災難事件中的救助責任與賞罰措施;參閱《嘉慶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四百“禮部·朝貢”“周恤、拯救”等內容)
這些共同遵守的法令與政策,是前近代世界貿易秩序存在并得以維持、延續的重要因素。通過海、陸絲綢之路連接起來的朝貢貿易體系,也即前近代最早的世界貿易體系。從鴉片戰爭以后,傳統的世界貿易秩序開始為西方近代國際法為主導的世界貿易秩序所取代,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但其間蘊含的互通、平等、周濟的貿易精神,在現代依然有重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