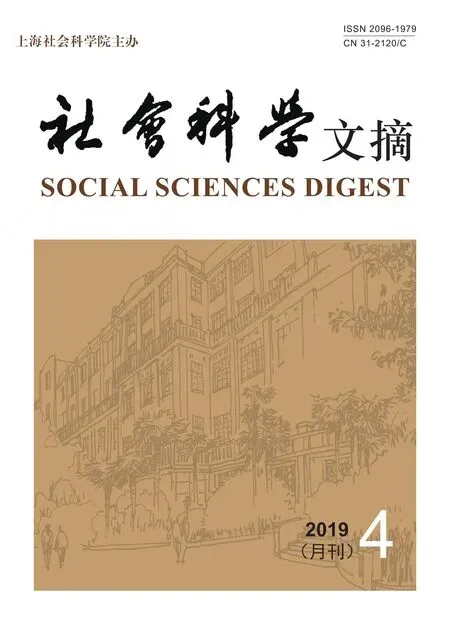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國是一個特別的目的地嗎?
本文關注的問題是,就美國對外直接投資而言,中國是否是一個特別的投資目的地?進一步地,在中國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和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中,為什么美國對中國的投資卻看似維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
促使我們思考這一問題的有四個背景性的因素。首先,在中國大陸的外資中,來自美國的資本并不突出。在2011—2015年的這五年里,來自美國的投資額平均為29億美元,占前十大投資來源地對中國大陸投資的比重平均為2.7%。其次,在美國對外投資中,中國所處的地位也不突出。依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EA)提供的信息,在2011—2015年的這五年里,按存量數據統計,中國位居第14位~第17位,所占的比重平均為1.4%。再次,如果美國對中國的投資看重的是市場,但美國對中國的投資增速卻滯后于中國的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也落后于整個外資流入的增速。在2011—2015年的這五年里,中國GDP的增速平均達到7.9%,人均GDP的增速平均達到7.3%,而美國對華投資的增速平均為-7.6%。最后,中國最近再度關注外資的重要性并頻密地調整外資政策,外資利用面臨新的機遇。美國是世界上對外投資最多的國家,中國是世界上吸收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與此不相稱的是,美國對中國的投資卻顯得相對不足。
在這些背景之下,本文通過跨國面板數據考察美國對外投資的動機,并跟蹤中國作為一個投資目的地,是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此基礎上,我們希望對上面提到的事實給出一些回應和解釋。與現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貢獻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針對2002—2012年156個國家的跨國非平衡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從樣本覆蓋面和時間跨度來說,這對已有文獻是一個改進。其二,跟蹤了中國作為投資目的地的特殊性,并挖掘了使得它有別于其他目的地的具體因素,包括市場規模、經濟發展水平、經濟增長、開放度,以及治理水平等。其三,進一步聚焦制造業,以初步把握美國對外投資的驅動因素在行業之間的差異性。我們在利用聯合國貿發會(UNCTAD)的FDI數據的基礎上,還利用了BEA的FDI數據。其四,我們在研究中關注了中國和印度,以考察兩個具有可比性的發展中國家在吸收來自美國的投資方面的異同。
文獻回顧
結合本文所關注的問題,我們對文獻進行了回顧。
從東道國社會和經濟環境考察影響FDI流入的因素的實證文獻有很多。例如Nunes等(2006)以15個拉丁美洲國家1991—1998年的宏觀數據為樣本,發現市場規模、基礎設施、經濟開放度對FDI流入具有促進作用,而通貨膨脹、工資水平會抑制FDI的流入,自然資源和私有化對于拉美國家吸收FDI沒有顯著影響。研究多個國家FDI流入的影響因素的文獻較多,而研究單一國家對多個目的地投資的影響因素的文獻則相對較少,文獻相對集中在美國這個FDI最大的輸出國上。Biglaiser和Staats(2010)利用微觀調查數據研究過去20年拉丁美洲的民主化進程對于來自美國的FDI的影響,結果發現產權保護、法律有效性以及高效的法律系統是美國公司在投資時最看重的。
有關美國對華投資的影響因素,也有一些學者進行了研究。徐康寧和王劍(2002)利用1983—2000年全國整體數據分析美國對華投資,他們發現主要因素是市場規模、政府的開放政策、跨國公司的前期資本存量和匯率。Du等(2008)利用1993—2001年6288家美國跨國公司對中國的投資數據,特別關注了制度因素的影響,結果發現知識產權保護良好、政府對商業活動干預少、政府腐敗程度低,以及合同執行力強的地方,可以吸收更多的來自美國的投資。
關于美國對華投資不足的因素,有學者發現,美國對華FDI投資總量偏少的外表下存在著結構性問題。蔣殿春和張慶昌(2011)基于美國跨國公司全球經營規模數據構建了行業面板,他們發現在控制了東道國市場規模、人均收入水平和貿易成本等因素之后,美國對華投資顯著低于模型的預測水平,但在制造業內,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卻高于應有水平,也就是說美國對華投資的主要阻礙在于服務業。Holmes等(2015)則把主要原因歸結于中國“以市場換技術”的政策,認為該政策抑制了投資意愿。作為一篇理論文章,該研究把重心更多地放在如何將“以市場換技術”政策引入到模型中,對于其他可能影響到FDI流入的因素的討論不夠充分,而這是本文想要完善的。
數據來源與變量選擇
基于現有文獻,本文利用地理距離、自然資源、基礎設施、通貨膨脹、貿易開放度、GDP、人均GDP、經濟增長率、治理水平、文化差異、人力資本等變量對經濟狀況、治理能力、稟賦條件這三方面因素進行控制。總體FDI凈流入數據來自UNCTAD,而制造業FDI凈流入數據和美國跨國公司經營數據則來自美國BEA。由于缺少服務業整體的FDI信息,在行業層面,我們聚焦制造業進行分析,并間接地對服務業做些討論。地理距離數據來自CEPII。治理水平的原始數據來自世界銀行的“世界治理指數(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數據庫,文化差異的原始數據來自“霍夫斯泰德國家文化(Geert Hofstede National Culture)”數據庫。其余變量均來自世界銀行WDI數據庫。
結合文獻,我們預計自然資源、基礎設施、貿易開放度、市場規模、人均GDP和經濟增長對FDI的流入有促進作用,地理距離、治理水平差異、文化差異和通貨膨脹率對于FDI的流入有著抑制作用。
本文使用的是非平衡的短面板數據,使用混合橫截面回歸方法。在實證檢驗中,還引入了一系列虛擬變量:Developed(目的國是發達國家時,該變量取1,否則取0)、Taxhaven(對于避稅天堂,該變量取1,否則取0)、FC(2008年及之后的年份該變量取1,否則取0)、China(投資目的地是中國時,該變量取1,否則取0)、India(投資目的地是印度時,該變量取1,否則取0)。
基準估計
我們首先針對總體樣本展開實證分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聚焦制造業樣本展開相應的實證研究。
(一)總體樣本
針對全樣本的估計,比較穩定的結論如下:市場規模、人均GDP、開放度和自然資源等四個變量,與美國投資顯著正相關;地理距離和治理水平差異等兩個變量,與美國投資顯著負相關。在啞變量中,金融危機和避稅天堂的系數分別顯著為負和顯著為正。在控制了這些因素之后,我們發現:與其他投資目的地相比,美國對中國的投資并沒有明顯偏離應有水平,美國對中國的投資大體上是現有變量可以解釋的;而與其他投資目的地相比,在控制了現有變量之后,美國對印度的投資有高于應有水平的部分證據。此外,美國與目的國的文化差異抑制了前者對后者的投資。
(二)制造業樣本
針對制造業樣本的估計,比較穩定的結論如下:市場規模和開放度等兩個變量,與美國制造業投資顯著正相關;地理距離、自然資源和治理水平差異等三個變量,與美國制造業投資顯著負相關。Developed、FC和Taxhaven等三個啞變量多不顯著。在控制了這些因素之后,我們發現:與其他投資目的地相比,美國對中國的制造業投資有高于應有水平的傾向;而與其他投資目的地相比,美國對印度的制造業投資沒有偏離應有水平。此外,與目的國的文化差異抑制了制造業投資,人力資本與投資顯著正相關。
從對總體和制造業樣本的估計結果可知,就美國對外投資而言:推動性因素包括市場規模、人均GDP水平、開放度等;制約性因素包括地理距離、治理水平差異、文化差異等。與其他投資目的地相比,從總量看,中國并不是特別的投資目的地。美國對中國的投資并沒有明顯偏離應有水平,現有變量大體上可以解釋美國對中國的投資。
拓展性分析
我們聚焦美資的重要影響因素,進一步考察中國作為投資目的國的特殊性。考慮到數據可得性,這里主要關注市場規模、人均GDP、經濟增長、開放度、治理水平差異等因素。
(一)總體樣本
對于全樣本,在模型設定中分別引入市場規模、人均GDP、經濟增長、開放度與China的交互項,四個交互項的估計系數都為正但均不顯著。進一步引入治理水平差異與China的交互項,交互項的估計系數為負但不顯著。單從交互項的符號看,似乎暗示:與其他投資目的地相比,市場規模、經濟發展水平、經濟增長、開放度對于中國吸引美資而言更為有力;而治理水平差異則可能是一個制約性的因素。
(二)制造業樣本
對于制造業樣本進行同樣的估計,我們發現,市場規模、人均GDP、經濟增長、開放度與China的交互項均正相關,只有治理水平差異與China的交互項負相關。這意味著,與其他投資目的地相比:市場規模、經濟發展水平、經濟增長、開放度對于制造業領域中國吸引美國的投資更為有力;而治理水平差異則相對地是一個制約性的因素。
結合兩組針對制造業回歸的結果可以知曉,在制造業領域,美國對中國投資高于應有水平的跡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歸因于市場規模、經濟發展水平、經濟增長和貿易開放度等的特殊吸引力。與此同時,治理水平差異則相對地是一個制約性的因素,這從一個側面說明,除了注意到中國在吸引美資方面的優勢之外,也要看到一些制約性因素的影響。
穩健性檢驗
具體包括:一是對FDI采用不同的度量辦法;二是對制造業進行細分。
(一)使用跨國公司經營數據代理美國對外投資
蔣殿春和張慶昌(2011)使用美國跨國公司1999-2007年在44個經濟體的總資產和總銷售額近似地代表美國對外投資的規模。我們效仿這一思路,用2002—2008年美國跨國公司總資產和總銷售額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實證分析。可以發現:總體樣本中,當被解釋變量為總資產時,相近的解釋變量的結果是接近的,如市場規模、人均GDP、經濟增長、開放度;China的系數在他們的文章中為負且顯著,在這里,絕大多數也為負,雖然多但不顯著。當被解釋變量為總銷售額時,估計結果與蔣殿春和張慶昌(2011)的結果對比:除人均GDP之外,相近的解釋變量的結果是接近的;最重要的是,China在他們的文章中,均為負且顯著,在這里,它也均為負且絕大多數顯著。
針對制造業樣本的回歸表明,在控制了相關變量之后,China的系數絕大多數為負但不顯著。這說明,如果用總資產和總銷售額代理美國對外投資,美國對華制造業投資沒有低于應有的水平。對比用總銷售額代理美國對外投資的總體和制造業樣本結果,說明如果美國對華投資偏低,原因很可能是服務業的美資相對不足所致。這一論斷與蔣殿春和張慶昌(2011)是相似的。
我們也同樣關注了印度的情況。在總體樣本,India的系數絕大多數為負,且在總銷售額為被解釋變量時絕大多數顯著。在制造業樣本中,India的系數均為負,且絕大多數顯著。對比全樣本和制造業樣本的結果,可以知道如果用總資產和總銷售額代表美國對外投資,美國對印度的投資整體偏低,而這基本上是由于美國對印度制造業投資偏低造成的。這一結果與中國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二)細分制造業
將制造業具有代表性的子行業作為樣本,進一步考察結果的穩健性。具體地,篩選出五個在投資存量中占比較大的制造業子行業,包括電腦和電子產品、食品加工、化學工業、機械設備和交通運輸設備。可以發現,在這五個子行業中,China的系數始終顯著為正,說明美國在這些制造業子行業的對華投資高于“應有”水平。
針對穩健性分析,我們有兩點小結:第一,使用跨國公司經營數據作為美資的代理變量,結果顯示,美國對華制造業投資并不低于應有水平,但對華服務業投資則相對不足,這與前面的結論和現有文獻的發現是一致的;第二,在中國,電腦和電子產品、食品加工業、化學工業、機械設備和交通運輸設備等五個代表性制造業的美資,高于應有水平,這為中國在制造業領域吸收美資所具有的優勢地位提供了更微觀的證據。
結論與政策含義
針對美國對華FDI看似偏低的現象,本文利用2002—2012年美國對156個國家的投資進行實證研究。通過基準估計和拓展分析,我們得到以下結論:其一,總體上看,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況下,美國對華投資并沒有偏離應有水平,大體上是現有變量可以解釋的;其二,如果局限于制造業,美國對華投資甚至有高于應有水平的部分證據;其三,市場規模、經濟發展水平、經濟增長率、開放度等因素對于美資的促進作用,在中國表現得更為突出,這是制造業吸引美資表現突出的微觀基礎。與此同時,治理水平的差異則相對地是一個制約性的因素;其四,與制造業吸引美資的成效不同,服務業在吸引美資方面的潛力可能還未充分釋放出來,這與印度的情況形成了對照。在穩健性檢驗中,通過對制造業進行細分,再次獲得在制造業美國對中國的投資并不低于應有水平的一些證據。以企業經營數據作為美資的另一種代理,我們得到了與蔣殿春和張慶春(2011)近似的結論,即如果美國對華投資不足,那應該是在服務業。
結合上述結論,就美國對華投資看似偏低的現象,我們有兩點解釋:一方面,人們可能只看到市場規模、經濟發展水平、經濟增長和開放度等引力因素,而忽略地理距離、治理水平和文化差異等制約性因素,形成美資流入偏低的“錯覺”;另一方面,與制造業相比,服務業利用美資的潛力還沒有充分釋放出來,對整體的美資利用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通過本研究,我們有三點政策建議:第一,繼續深化改革,挖掘經濟潛力,通過擴張市場規模、提高經濟發展水平、提升經濟增長率,以及擴大對外開放,維持和強化中國整體特別是制造業對美資的吸引力;第二,繼續改善營商環境,強化問責制,保持政治穩定,提升政府效率,提高監管質量和法治水平,充分展現吸引美資的“軟實力”;第三,繼續優化投資環境和政策設計,在維持制造業對美資的吸引力之外,加大服務業的開放,促使美國對中國的投資在結構上更為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