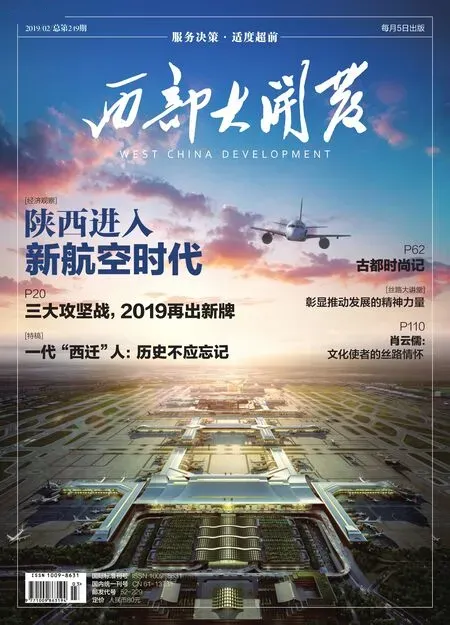下一個五年西咸新區如何繼續“新”下去?
文 / 貞觀 圖圖
1979年,袁庚在深圳蛇口搞“試管經濟”,是開發區的原始雛形;上世紀90年代初期先后成立的西安高新技術開發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是改革開放的代表成果之一;2000年之后,相繼有曲江新區、浐灞生態區、航天基地、航空基地、港務區等功能定位不一的城市新區相繼衍生出現;2014年1月,西咸新區獲國務院批準成為國家級新區。
每一個開發區或城市新區的出現,都承擔著不同的時代使命。這其間,西咸新區最為引人矚目。西咸新區作為國家級新區高調亮相,甫一問世,就被陜西上下寄于破題西咸一體化、打破行政體制藩籬的期望,更承擔著國家級新區探索改革、總結經驗、創新發展的全局性國家任務。
五年匆匆而過,作為“新區”立身的西咸新區,究竟“新”在何處? 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來陜視察的重要講話中,要求“發揮西咸新區作為國家創新城市發展方式試驗區的綜合功能”,接下來的時間里,它又將如何沿著“創新城市發展方式”的主題,繼續“新”下去?
破題行政區與開發區藩籬
2017年被稱為大西安元年。這一年西安市正式代管西咸新區,57.6萬居民享受同等戶籍待遇,機動車可換領陜A牌證,大西安建設進入了實質推進快車道。
與“實質”相對應的,是西、咸兩地在過往融合過程中的反復磨合。
以通勤在西安、咸陽兩地的普通人的一個感受來體會,距離20余公里的西安、咸陽兩地,在2002年12月18日簽署《西咸經濟發展一體化協議書》,直到14年后的2016年底才實現公交卡互刷。
而在這中間,從最早在陜西省發改委下的“西咸辦”;到2011年“西咸辦”改為“省直管”的西咸新區管委會;再到2017年初交由西安市代管,本質上都是在厘清橫在眼前的體制機制問題。
比如,由“西咸辦”變成“省直管”的西咸新區管委會,就是為了解決之前“由于受行政區劃分割、缺乏抓手等原因,一體化進展不快、力度不大,特別是西咸接合部建設步伐緩慢,沒有形成實質性、大規模的開發建設局面”,這在2011年出臺的《西咸新區總體規劃(2010-2020)》中有明確的描述。
說的再具體一些,在具體實施過程中,財稅分成、土地開發權益需要逐一明確,有省級層面土地指標傾斜的西咸新區,還需要獲得西安、咸陽兩市以及轄屬區縣、街鎮的配合。
有了西咸新區托管這一步,隨后在2017年4月的另一項舉動,加速破解了過往開發區與所在行政區之間的掣肘。西咸新區五個新城全面托管了咸陽市15個鄉鎮街道,而在更早的2010年,灃東新城的前身—灃渭新區就曾試點“區鎮聯動”,托管相應的社會事務。
這一模式后來被復制到老牌開發區高新區身上,2018年11月,雁塔、長安、鄠邑三個區的10個鎮(街)交由高新區托管,一舉解決了高新區因為無地可落的134個項目的“攔路虎”。未來,讓開發區承擔更多的社會事務,可能是體制改革的一個必然方向。
創新規劃發展理念
改革開放以來的開發區模式,多依賴各類產業園區帶動城市發展。這種模式迅速推動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擴大城市規模,以工業化帶動城市化,短時間內吸納了許多人口聚集在城市。
彼時的開發區以一種更為靈活、高效的管理體制,適應了區域發展的需求,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開發區也是地方經濟活力的重要表征。在西安,成立最早的高新區無疑最具代表性。高新區迄今是西安科技企業集聚度最高的區域,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體量占到全市三分之一以上,在西安各縣區和開發區中排在首位。
但這種以預期土地收益進行融資,推動城市迅速擴張的模式,短期內拉動了GDP的增長,卻使得城市邊際無節制的擴張,因此造成的“攤大餅”局面屢被詬病,重城市建設而輕環境保護的做法,也衍生出各種霧霾、堵車等城市病,使城市整體效率下滑。
無論反映到數據上,還是直觀感受上,曾經引領經濟增長的高新區逐漸顯得“傳統”,難以給人新意,雖然基數和占比還在,但增速已經被其他新興的開發區反超,尋找轉型路徑似乎迫在眉睫。
事實上,在如今西安周邊的開發區中,斷頭路、上學難、看病難、乘車難……等一系列公共服務問題,誠然有開發區體制上的問題,追根究底是原有的開發區模式已經不再能滿足新生的發展需求。
作為被賦予創新城市發展方式定位的國家級新區,提出的一個重要改變是,從過去的園區建設,轉向新的城市平臺建設。不再局限于基礎設施,而拓展到更為重要的人的聚集和融資環境的營造,由開發土地轉向開發人。
比如西咸新區打造了全國首個硬科技小鎮,致力于整合本地存量豐富的科技資源,實現與市場需求的有效對接,現已吸引了微軟、百度、阿里巴巴、清華紫光等300余家知名企業入駐,聚焦信息技術、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技術等主導產業。
之后隨著西工大無人機產業化基地、西部科技創新港等以高校為載體的創新平臺落成,將會帶來大批優質人才入駐,推動產城融合。
除了新興產業集聚,產城融合的細節還體現在,將城市生活半徑與就業半徑相結合,打造青年人才“5分鐘生活工作圈”,縮小通勤距離達到緩堵、提升生活品質等需求,這些更關注人本身的規劃已經在付諸實踐。
摸索歷史遺存保護與發展的新路徑
白居易有詩云:“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李白的一句“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道盡千古幽思。
五陵原,是漢代陵邑制的產物。漢時遷徙大量貴族官宦富豪,在帝陵周邊建起縣邑,短時間內聚集了充足的人力物力,經濟活躍,很快成為緊鄰長安城的衛星城邑。遺址區出土的許多生產工具以及地下水管道佐證了當時的人口殷盛。這類似今天的消費型都城副中心,疏散了相當部分的城市功能。
以五陵原為代表的漢帝陵群,如今被整體劃入西咸新區秦漢新城的板塊。秦漢新城位于涇渭兩河夾角,依渭河北岸狹長分布,總規劃面積302平方公里,其中的大遺址保護區104平方公里,產業發展以文化旅游、健康醫療領域為主。
最新公布的《秦漢新城分區規劃(2010-2020)》中,提及按照“生態為蘊、文化為魂、旅游為媒、創新為本”的思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必須要堅持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新城發展和遺址保護。對非建設用地的一條規劃原則是:確保新城生態環境、自然資源、歷史文化遺址及耕地得到有效保護,對歷史文化遺址的保護提及到一個明確的高度。
事實上如何處理好遺址保護和開發這個問題,是作為文明古都的西安一直需要考慮的,一不小心,就容易陷入過度開發的質疑。
去年10月,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先生在“首屆創新城市發展方式(西咸)國際論壇”發言談《文化在新城市中的作用》。他提到如今西咸新區所在區域,集中了唐以前中國最核心的文明,由此形成豐富的文化遺產。在歷史遺存的被動保護和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之間重新平衡,也是西咸新區需要探索的一個方向。
城市本身的經濟實力是基本要素,而擴大城市的影響力則離不開文化。而這個文化影響不能僅僅靠營銷和制造輿論強行輸出,真正的文化影響力需要將自身的價值觀念,傳播為可以被接受的文化產業和產品。兩三個月前,秦漢新城邀請英國編劇團隊打造了舞臺劇《我的小伙伴》,嘗試借秦始皇這個IP傳遞出不同于以往的價值,求變求新的意圖顯而易見。
新軸線帶來的大西安新格局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西安共編制了四次城市總體規劃,從中可以梳理出城市格局的發展軌跡。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建設中,西安主城區一直以渭河為北界,在鐘樓為中心的三環以內發展。市區面積從131平方公里增長到500平方公里左右,人口從120萬增長到千萬規模,城市“擴容”成為迫切需求。
2014年西安啟動修改第四輪城市總體規劃,對城市規模及增長邊界做出調整。兩年后“按照‘一軸兩城’的思路,實施北跨渭河發展戰略”的表述被寫入西安“十三五”規劃綱要。“沿河而治”變成“以河為軸”,隨著規劃中的地鐵線告成,將進一步拉近西咸兩地的距離。
西安的城市格局一直延續“中軸+方城”的“中”字格局。隨著西咸一體化推動,建立城市組團格局,由特大城市—中等組團城市—鎮—村落形成的市鎮體系,誕生了以灃河、渭河交匯處為原點,以秦嶺為南緣,以九嵕山為北緣,以渭河為東西軸的新軸線。
來自新加坡的城市規劃大師劉太格,曾受邀參與大西安規劃。關于對城市規模再次擴大的疑問,他這樣打比方,如果把北京比作一個人的身體,裝上五六個人的體重,城市就會有問題。他在規劃中強調將一部分城市功能分攤出去,這樣鐘擺式的交通壓力就會減小,解決擁堵和人員消耗的問題。
2018年2月7日發布的《關中平原城市群發展規劃》,明確提出建設西安國家中心城市,其中提到關中平原城市群要強化西安服務輻射功能,加快培育發展軸帶和增長極點,構建“一圈一軸三帶”的總體格局,提高空間發展凝聚力。
加上對“一帶一路”倡議進行積極響應后,西安的城市定位、規劃重心,已經不再局限于一城之中,而上升到了更高的戰略層面,這其中包括向西開放的重要樞紐、西部大開發的新引擎和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的范例。
從城市更新到新區新城,到大都市圈,到中國新的開放格局的構建,如何把戰略資源轉化為經濟增長,以西咸新區為核心的關中城市群需要走出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