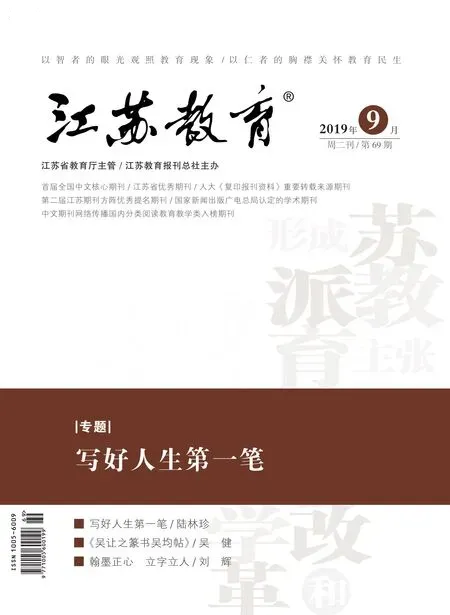真 體(下)
辛 塵 閆 帥
進入唐代,真體之“法”得到了空前的重視。上至太宗皇帝大力向社會推廣王羲之“新體”書法,推行書法教育政策,并在科舉取士中強調“楷法遒美”,向社會立“法”;下至文人士大夫竭力總結真體結字之“法”、用筆之“法”,可以說,在唐代朝野上下,崇尚真體之“法”的研究和總結,由此構建了一個法度嚴謹?shù)恼骟w世界。
初唐真體書藝的主要代表為歐、虞、褚、薛四家。活動于陳、隋之間的歐陽詢與虞世南,進入唐代已經年過花甲,因此,他們的真體在唐以前就已成熟,從他們的真體書法中尚且可窺見南北方的差異性。歐陽詢真體點畫凌厲,結體緊密,強調間架結構,大有北魏真體之風;虞世南作為南朝二王真體書藝嫡系傳人智永的弟子,其真體點畫精巧,講求韻律。歐虞兩人真體書法一剛一柔,代表了南北兩種不同的書風,正如張懷瓘所總結:“歐若猛將深入,時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辭。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
而其后真正將南北真體書風進行有機融合,開唐代真體書藝風氣的還要數(shù)褚遂良。在褚遂良的真體書藝中,既繼承南方真體強調點畫顧盼、點畫精巧的用筆特征,又保留了北方真體注重結體寬博開張、寬綽有余的傳統(tǒng)。確切地說,褚遂良真體真正反映了南北書法的融合。而作為褚遂良書法的傳人,薛稷更是秉承了其筆法特征,以此形成了南北兼容的風格特征。

圖1 顏真卿《顏氏家廟碑》(局部)
顏真卿、柳公權作為褚遂良之后真體書藝的杰出代表,無疑是唐楷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這種成熟是指“顏柳”真體有別于初唐以來的真體形象,對真體之“法”進一步挖掘,將唐代真體書藝法度嚴謹推向了無以復加的境地(見下頁圖1)。這種法度嚴謹具體的表現(xiàn)是:真體點畫形象越來越得到重視,每一個筆畫(尤其是在筆畫的兩端)修飾的效果更加明顯,在結體上嚴謹完備、成熟穩(wěn)固。而在“顏柳”之間又相區(qū)別,呈現(xiàn)迥然不同的“法”與“意”。顏真卿真體用筆厚重,豐筋遒勁;結體寬博,內舒外緊,透露出雄渾、博大、方正的風格特征;這種真體書風與盛唐社會高度繁榮,豪邁奔放的時代旋律相合拍。柳公權則身處已漸沒落的晚唐社會,其真體雖上接盛中唐,但已不復雍容的氣度,其真體表現(xiàn)的是一種剛正堅挺、孤傲瘦硬的“意”,是一種用筆平直、中宮收緊的“法”。因此,透過“顏柳”真體書藝,我們既看到不同的“法”,也透過“法”體會到個體與時代精神在書法中表現(xiàn)的“意”。
經過唐人的不懈努力,真體的發(fā)展總體上呈現(xiàn)出三種不同的形態(tài):以魏晉鍾王為代表的小字真體形態(tài);以北魏洛陽時期為代表的魏碑體形態(tài);以及以唐代“歐虞褚薛”和“顏柳”為代表的唐楷形態(tài)。這三種形態(tài)成為宋元明清書法家取法的淵源,并且在不同時期對這三種真體形態(tài)的取法各不相同。大致來講,宋、元、明三代,魏晉鍾王小字真體形態(tài)以及唐楷形態(tài)成為書法家主要取法對象;而到了清代,久被忽略的魏碑體被文人士大夫重新重視,并且納入書法藝術取法當中。因此,我們從“法”與“意”的角度來看,宋元明清真體書藝宗前人之“法”,同時受時代與個體影響,表現(xiàn)出各具時代特性的真體之“意”。
在盛產真體書法家的唐代,顏真卿在真體書藝領域并非是無可匹敵的,然而在宋代,顏真卿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一躍成為宋代真體書法家取法的對象。這是因為,比起唐人重“法”,宋代文人士大夫更加注重書法中表現(xiàn)的一種由書寫者道德節(jié)操、心性情感等共同構成的“意”。從這一角度來看,顏真卿為人剛正不阿、忠貞不渝的品德與其真體書法雄厚寬博的風格互為表里,這種特征更符合宋人的書法審美標準。

圖2 蔡襄《澄心堂帖》
蔡襄作為北宋學習顏真卿真體書藝的代表,其“學顏”更側重于“顏”的形體,與“顏”的寬博與雄渾不同,蔡襄真體小字用筆精勁,更多了幾分“安逸”(見下頁圖2),表現(xiàn)出了文人士大夫閑雅靜穆之“意”。另一位宋代真體書法家蘇軾,其點畫肥厚,行筆俊邁,不過多拘泥點畫修飾,體勢上寬博欹側。這種“法”透露出的是一種豪邁與不羈不經意之“意”,印證了他自己所說:“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宋徽宗趙佶無疑是北宋真體書法家中比較另類的,其真體學薛稷,點畫拋筋露骨,鋒芒畢露,透露出一種瘦硬與爽利,這種書法被人們稱之為“痩金書”。除此之外,宋代書法家的真體楷書書藝可謂乏善可陳。一方面,在唐代真體楷書高峰之下,宋人顯得對真體楷書缺乏良好的訓練與研究;另一方面,在宋人看來,比起真體行草書,真體楷書似乎更多的是“法”,而難以表達自己內心的“意”。
宋人“尚意”,對“意”的過分強調造成了“法”的缺失,最終導致書法的“意”也是一種毫無根據(jù)的粗糙與率意。因此,元代趙孟頫的出現(xiàn)似乎更加符合書史的邏輯,其大力向社會呼吁“復古”,無疑是對南宋以來“法”的缺失的彌補,是對書法秩序的一次重要調整。對于真體,趙孟頫更注重觀照“法”,注重從魏晉二王書法汲取法則。透過趙孟頫的真體書法,更多看到了其對魏晉二王筆法的繼承,其真體小字點畫精巧,結構緊密,意態(tài)古雅;真體大字則用筆一拓直下,融入行書筆意,點畫映帶連貫,結體方正平穩(wěn),透露出一種既靈動又沉穩(wěn)的“意”。元代書法家的真體書藝莫不受趙孟頫影響,遵從魏晉、崇尚古雅。這種復古書風直至明初依舊延續(xù)不絕,并且走向極端工致的“臺閣體”。
客觀地說,過于注重點畫精巧、工致,結體的工穩(wěn),以此追求雍容端莊,恰恰忽略了對個人意趣的表達。這種重“法”輕“意”的現(xiàn)象在明中期有所改觀,“吳門四家”的出現(xiàn)重新賦予了真體活生生的藝術生命。在“吳門四家”中,祝允明、文徵明、王寵皆善真體并以小楷稱能。其中,祝允明真體取法鍾王,用筆樸厚,結體偏扁,古樸厚拙;文徵明真體點畫精巧,用筆細勁,結體疏密勻稱,透露一種清勁與優(yōu)雅;王寵真體小楷得力鍾繇、虞世南,用筆遒勁,結體舒朗、空靈,氣息高古典雅。總體來看,吳門書家在學習前人真體法則的基礎上,多注重將自己的“意”貫穿到真體之中,并借真體表現(xiàn)自己優(yōu)雅、閑適的意趣。其后,晚明書家越來越重視對自己“意”與“個性”的表達。董其昌真體糅合多家,進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真體書法藝術風貌,用筆精到,結體精密略帶欹側,章法空靈、多有留白,值得一提的是在用墨上濃淡相間,整體營造出一種秀潤、淡雅、空靈的“意”。黃道周真體小字取法鍾王,點畫方折峻峭,結體方扁,表現(xiàn)出一種倔強不屈的“意”。綜合來看明代真體書法,明前期真體“法”重于“意”,到了中期書法家越來越注重將自己的個性、意趣融入真體書法中,以此形成了明中后期真體書法家之間迥乎不同的“意”。
清中葉,在金石學的帶動下,久未被關注的碑版石刻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學者尋碑訪碑,以碑考訂經史。正是在這種新型學術風氣的影響下,在書法藝術領域掀起了一場碑學運動。而真體書藝作為這場碑學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最突出的表現(xiàn)是,對久被忽視的北朝魏碑體書法重新以藝術立場的發(fā)掘,以此形成了獨特的清代碑派真體書法藝術。
在清代書法家眼中,“魏碑無不佳者,雖窮鄉(xiāng)兒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異態(tài)”。正是基于對魏碑書法的這種批評觀點,清人努力去學習魏碑,并竭力總結出了一套關于魏碑創(chuàng)作的法則。從北朝魏碑真體的表現(xiàn)方式來看,北朝魏碑多為刀刻加工,加之長時間的風雨侵蝕,形成了點畫斑駁、筆道泐損的效果,因此呈現(xiàn)出一種樸拙、厚重的自然物理之美;而清代真體書法家發(fā)覺到了這種碑刻所帶來的獨特趣味,在創(chuàng)作中反復實驗,總結出了一套關于魏碑的創(chuàng)作“法則”。如包世臣所進行的總結,“北朝人書,落筆峻而結體莊和,行墨澀而取勢排宕。萬毫齊力故能峻;五指齊力故能澀”。所以,就“法”的一面來講,用筆的“遲澀”“鋪毫”,以及結體的“莊和”成為清人從北朝魏碑真體中所總結的技法原理。另外,在工具上,清人采用了長鋒羊毫以及生宣作為真體創(chuàng)作的物質載體,以祈求行筆的遲澀與筆道的斑駁。
清代魏碑書法家努力師法北朝魏碑真體書藝,并非是停留在對北碑的繼承上,而是通過對北碑的借鑒從而尋求自己獨特的真體風格,建立屬于自己的一套真體的“法”與“意”,從這個角度來看,清代魏碑書法家是以自己的審美趣味對北朝魏碑體的一次重新建構。具體到清代不同魏碑體書法家,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他們在魏碑中的不同探索,以及表現(xiàn)出的不同的“法”與“意”。何紹基取法北朝魏碑真體,引入篆隸筆意,并以自己獨特的“回腕”之法,形成了遒勁古厚的風格;張裕釗真體追求碑刻效果,在結體上追求方正,在筆畫的轉折以及鉤挑中,有意的加入方折等用筆,形成外方內圓的奇特效果,營造出一種硬朗、蓄勢待發(fā)的意態(tài);趙之謙則宗法諸多北碑,其真體用筆峻峭,行筆上果敢并富有節(jié)奏,結字上欹側活潑,以此形成了獨具一格的真體面貌。而其后,清代魏碑真體書法家過多注重營造自己獨特的“法”,以求形成自己獨特的真體風格,這使得清代魏碑書法創(chuàng)作逐漸走向衰落。李瑞清作為最典型的代表,其魏碑書法采用篆書用筆,并在用筆上有意加入顫抖,以表現(xiàn)出碑刻的斑駁,但是這種嘗試使得其真體稍顯做作。因此,在魏碑書法的創(chuàng)作中,如果一味地以“法”來造“意”,最終形成的是“刻意”與“故意”,本末倒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