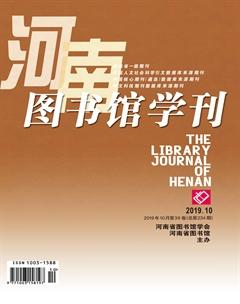唐代辨偽釋例
孫新梅
關鍵詞:唐代;辨偽;柳宗元;釋智升;劉知己
摘 要:唐代的辨偽較之兩漢、魏晉有了很大發展,這一時期涌現了一批著名的辨偽學者,他們對四部典籍進行深入考辨,并且取得了重要成果。孔穎達、顏師古、長孫無忌、劉知幾、釋道世、釋智升、柳宗元等人是其代表,這其中又以劉知幾的《史通》與釋智升的《開元釋教錄》涉于辨偽者最具典型意義。文章以劉知幾、釋智升、柳宗元為例,探討了唐代的辨偽成就。
中圖分類號:G25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1588(2019)10-0138-03
隋唐是經歷了五胡亂華和南北朝之后,形成的兩個大一統王朝,唐代又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唐代學者在辨偽方面已取得了諸多進步。中晚唐出現的劉知幾和釋智升兩個辨偽學者,更是我國辨偽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1 劉知幾《史通》之辨偽
劉知幾(661—721),唐代著名史學家、辨偽學家。劉氏所著《史通》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史學理論專著,全書主要包括史學理論和史學批評兩個方面。前者是關于史書體例、編纂方法、作史原則的論述,后者是關于史書得失、史事正誤的考訂。
1.1 《史通》之《疑古篇》
《疑古篇》主要是針對《尚書》的懷疑,認為古圣人、古帝王的賢德功績大多是后人粉飾的結果。云:“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推者難詳,缺漏無補。遂令后來學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聾瞽。今故訐其疑事,以著于篇。凡有十條,列之于后。”劉知幾臚列《堯典》《舜典》《湯誓》《微子之命》《金縢》等篇中的說法,逐一進行駁斥。茲舉二例。云:“蓋《虞書》之美放勛也,云‘克明俊德。而陸賈《新語》又曰:‘堯、舜之人,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造奇說也。案《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謂之‘元‘凱。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不才子,謂之‘渾沌‘窮奇‘梼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兇,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云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以比三族,俱稱‘四兇”而堯亦不能去。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愚共貫。且《論語》有云: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彌驗堯時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謂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劉氏以堯不用賢者八元、八凱,而又不懲罰四惡,質疑堯哪里具有超人的美德。又云:“《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孔氏《注》曰:‘堯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案《汲冢瑣語》云:‘舜放堯于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為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授為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為證者矣,而猶有所未睹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勛之子為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古有奸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劉氏以諸書記載不一,而質疑堯禪位于舜的真實性。他還提出了辨識偽說的方法:“今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參而會之,以相研核。”取各家之說,參核異同,判別是非,這是比較科學的類比法。劉氏還分析了近古之史與遠古之史的區別,以及遠古之書對先圣帝王溢美的原因,云:“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約不類,固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備,事罕甄擇。使夫學者睹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參;觀一主之才,而賢愚殆半。至于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也,略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近古史書記載較詳,對于人和事不論好壞全部記下,便于后人知道這些人和事的好壞兩個方面。遠古史書所記多為梗概,書史者對于心目中的好君主,就帶著頌揚的態度記錄他們的豐功偉績,同時不惜為其隱惡。
1.2 《史通》之《惑經篇》
《惑經篇》認為《春秋》因襲舊文,體例并不完善,非孔子先定義例而后作,不應受到世人的過分推崇。劉知幾在審查《春秋》文義時,提出了十二點疑問。此茲舉二例。云:“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為人;杞伯以夷禮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后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為齊、鄭及楚,國有弒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夫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凡在含識,皆知恥懼。茍欺而可免,則誰不愿然?且官為正卿,反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弒,躬為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凝脂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一也。”劉氏列舉《春秋》不能秉筆直書,記事使用多重標準的諸多例子,而質疑《春秋》的體例。又云:“案齊乞野幕之戮,事起陽生;楚比乾溪之縊,禍由觀從。而《春秋》捐其首謀,舍其親弒,亦何異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及。必如是,則邾之閽者私憾射姑,以其君卞急而好潔,可行欺以激怒,遂傾瓶水以沃庭,俾廢壚而爛卒。斯亦罪之大者,奚不書弒乎?其所未諭二也。”劉氏繼續舉證了《春秋》記事沒有做到不虛美不隱惡。他還考察了世人對于《春秋》溢美的來源,并指出每個人面對史書都要有自己的判斷,云:“考茲眾美,征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語曰:‘眾善之,必察焉。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尋世之言《春秋》者,得非睹眾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者乎?”這些溢美之辭,基本上是由儒家學者傳授相承的,為了神化孔子,他們在宣講時就會言過其實。
2 劉知幾辨《孝經》鄭玄注之偽
開元七年三月,唐玄宗敕群儒討論《孝經》鄭注與孔傳諸書之長短。劉知幾于四月七日上《孝經老子注易傳議》申明了自己的觀點。他提出了《孝經》非鄭玄之注的十二條證據。《唐會要》卷七十七《論經義》:“謹按今俗所傳《孝經》,題曰鄭氏注。爰自近古,皆云鄭即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至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群臣,共論經義。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自齊、梁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為非玄所注,請不藏于秘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于時。魏、齊則立于學官,著在律令。盡由膚俗無識,故致斯訛舛。然則《孝經》非玄所注,其驗十有二條。據鄭君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為袁譚所逼,來至元城,注《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魏晉朝賢,辨論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引《孝經》之注,其驗十二也。凡此證驗,易為考核。而世之學者,不覺其非,乘彼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于世。觀夫言語鄙陋,固不可示彼后來,傳諸不朽。”同時,劉知幾也對《孝經》孔傳做了評價,比較了鄭注與孔傳的優劣,云:“至如《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其詳正,無俟商榷,而曠代亡逸,不復流行。至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士王孝逸于京市陳人處,置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更此書無兼本,難可憑依,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劭以為此書經文盡在,正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于學官,良可惜也。然則孔、鄭二家,云泥致隔,今綸音發問,校其短長。愚謂行孔廢鄭,于義為允。”后人皆重劉氏此說,宋邢昺《孝經御制序疏》照錄此文,清阮元在《孝經注疏校勘記序》中說:“鄭注之偽,唐劉知幾辨之甚詳。”
3 釋智升《開元釋教錄》之辨疑偽經
釋智升,唐代高僧,生平不詳。唐玄宗開元間居長安崇福寺,于開元十八年撰成《開元釋教錄》,該書多辨疑經與偽經。釋智升的《開元釋教錄》在佛經目錄中地位甚高,后世評價謂之精嚴。智升在篇首闡述了目錄對于辨偽的重要性,云:“夫目錄之興也,蓋所以別真偽、明是非,記人代之古今,標卷部之多少,摭拾遺漏,刪夷駢贅。欲使正教綸理金言有緒,提綱舉要歷然可觀也。”
3.1 《疑惑再詳錄》
《開元錄》卷十八之上為《疑惑再詳錄》,記載疑偽待考的經書,云:“疑惑錄者,自梵經東闡年將七百,教有興廢時復遷移,先后翻傳卷將萬計。部帙既廣尋閱難周,定錄之人隨聞便上,而不細尋宗旨理或疑焉。今恐真偽交參是非根涉,故為別錄以示將來,庶明達高人重為詳定。”此錄記載尚待考定的經典共十四部,凡十九卷,即《毗羅三昧經》二卷、《決定罪福經》一卷、《慧定普遍國土神通菩薩經》一卷、《救護身命濟人病苦厄經》一卷、《最妙勝定經》一卷、《觀世音三昧經》一卷、《清凈法行經》一卷、《五百梵志經》一卷、《法社經》二卷、《凈度三昧經》三卷、《益意經》二卷、《優婁頻經》一卷、《凈土盂蘭盆經》一卷、《三廚經》一卷。其于《五百梵志經》下注云:“右《毗羅三昧經》下八部九卷,古舊錄中皆編偽妄,大周刊定附入正經。尋閱宗徒理多乖舛,論量義句頗涉凡情,且附疑科難從正錄……仍俟諸賢共詳真偽。”于《凈土盂蘭盆經》下注云:“右一經新舊之錄皆未曾載,時俗傳行將為正典,細尋文句亦涉人情,事須審詳且附疑錄。”
3.2 《偽妄亂真錄》
《開元錄》卷十八之下為《偽妄亂真錄》,云:“偽經者,邪見所造以亂真經者也,自大師韜影向二千年。魔教競興正法衰損,自有頑愚之輩惡見迷心,偽造諸經誑惑流俗,邪言亂正可不哀哉!今恐真偽相參,是非一概,譬夫昆山寶玉與瓦石而同流,贍部真金共鉛鐵而齊價,今為件別,真偽可分,庶涇渭殊流無貽后患。”《偽妄錄》登記偽經三百九十二部,凡一千零五十五卷。此三百余部中智升本人辨其偽者僅三十七部,“從《佛名經》下三十七部五十四卷,承前諸錄皆未曾載,今《開元新錄》搜集編上”。智升在《偽妄錄》中借鑒了許多前人的成果,他毫不掠美,一一表出。如東晉道安的《綜理眾經目錄》:“右《定行三昧經》下二十五部二十八卷,苻秦沙門彌天釋道安錄中偽疑經。”
對于一些抄輯眾經而別有題名的經書,智升采取了詳細說明、附于偽經的做法,這是一種不欲侵犯原作者著作權的非常審慎的態度。例如,智升于《佛法有六義第一應知經》《六通無礙六根凈業義門經》下云:“右二部二卷,梁僧祐錄云‘齊武帝時比丘釋法愿抄集經義所出,雖弘經義異于偽造,然既立名號則別成部卷,懼后代疑亂,故明注于錄。”于《佛所制名數經》下云:“右一部五卷,梁僧祐錄云‘齊武帝時比丘釋王宗所撰,抄集眾經有似數林,但題稱佛制,懼亂名實,故注于錄。”
4 柳宗元辨七部子書之偽
柳宗元(773—819),不僅是一位文學家,還是第一個對子書進行系統辨偽的人。雖然他辨識的偽書數量不多,但他的主要貢獻在于使用了豐富的辨偽方法,如考察稱謂的方式、考鏡源流的方式等,以及對于后世宋高似孫、明宋濂等人的影響。
《辯列子》:“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四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后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后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于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于利,禍不得逮乎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后,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柳宗元以著者早于書中所載,辨《列子》之偽。同時,他分析了劉向致誤的原因,即劉向將魯穆公誤作了鄭穆公。柳氏還能客觀看待偽書的價值,評價《列子》“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提醒讀者在使用時要慎重一些。除《辯列子》外,柳宗元還有《辯文子》《論語辯(上篇)》《辯鬼谷子》《辯晏子春秋》《辯亢倉子》《辯鹖冠子》等辨偽著作,這些辨偽著作都充分展現了柳宗元的辨偽精神。
5 結語
唐代的韓愈也是一個頗具疑古精神的人,他在《答李翊書》中言需“識古書之正偽”。對于這個觀點,清代的閻若璩甚是膺服,閻氏云:“嗚呼!事莫大于好古,學莫善于正訛。韓昌黎以識古書之正偽為年之進,豈欺我哉!”辨偽學在經歷了先秦至于隋唐這個漫長時期的積累與鋪墊后,到了宋代就轟轟烈烈地發展起來了。
參考文獻:
[1] 浦起龍.史通通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354-386.
[2] 王溥.唐會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663-1665.
[3] 李隆基,注.邢昺,疏.孝經注疏[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21.
[4] 釋智升.開元釋教錄[M].北京:中華書局,1992:1-398.
[5] 劉真倫,岳珍.韓愈文集彙校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0:700.
[6]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1.
[7] 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9:107-108.
(編校:崔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