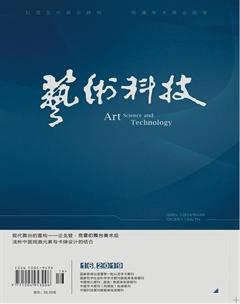無人駕駛汽車知識產權問題研究
摘 要:本文在現行知識產權制度框架下探討無人駕駛汽車相關客體的知識產權問題,為無人駕駛汽車企業保護相關客體提供法律路徑,提升企業在該領域的競爭力,進而促進無人駕駛汽車產業的發展。
關鍵詞:無人駕駛;著作權;專利權
無人駕駛汽車的出現打破了固有的“有人駕駛”的出行方式,對交通這一產業形態帶來了顛覆式的影響。其通過人工智能、雷達、路徑導航系統、監控設備、GPS定位系統等協作實現“無人駕駛”的目的。無人駕駛汽車作為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技術科學領域,人工智能所具有的創造性、結果不可預測性、自主性、智能性、進化性、信息交互性等特征,以及無人駕駛汽車的出現與發展給包括倫理標準、公共規則、法律規范在內的社會管理體制帶來了一系列的挑戰。人工智能系統的創造性和智能性,挑戰了傳統知識產權法律中的主客體之分。就無人駕駛的知識產權法律相關問題而言,主要體現在著作權、專利權、壟斷與不正當競爭等方面,目前整體來說擔憂甚于期待,紛爭多于共識,空白大于已知。
1 無人駕駛汽車與著作權
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第3條規定:著作權法所稱“作品”,包括“(七)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地圖、示意圖等圖形作品和模型作品”,無人駕駛汽車相關的設計圖、示意圖等圖形、模型作品是著作權法保護客體,按照已有法律的規定可確定著作權人身份及其享有的權利。而無人駕駛汽車的著作權問題主要是指其生成物的知識產權客體范圍。
著作權的保護范圍是以與創作者的思想表現形式相關聯的形式而存在的。其中,思想表現形式是著作權理論中最根本的基礎概念,其在文學藝術領域與科學創作領域的具象化即為作品。判斷是否為法律意義上的作品應當具備獨創性與可復制性兩個要件。無人駕駛汽車生成的路線、應急方案與文學藝術領域、科學創作領域之間的聯系較少,其性質更偏向于解決問題的技術方案。
路線與應急方案事實上是固定的,無人駕駛汽車只是在算法系統和數據分析過程中選擇最優解,無法完全擺脫人類預設的算法,有別于形式、種類、內容豐富無法預測的文學藝術創作。長期以來,著作權被認為是人格主義范疇內的權利,也就是說整個著作權法的保護體系都是圍繞著人類智力加以構建的,那么站在這一角度上考量,也就只有人的智力活動才能被稱為“創作”活動。在“猴子自拍照”版權登記案中,美國版權局就強調,“對于機器產生的作品,因不存在任何創造性輸入或者人類作者的直接干預,僅通過自動或隨機的機械方式產生的作品,版權局也當然不會登記”,如此意旨為只有人類創作的作品才能獲得著作權保護。按照這一思路,即便無人駕駛汽車生成的路線與應急方案在某種程度上符合獨創性(原創性)、復制性的要求,但仍然不能獲得著作權法保護。甚至由于其不具備人類作者的人格屬性,根本就無須再進一步考慮創造性和獨創性問題。因此,無人駕駛汽車生成物,包括但不限于生成的路線圖與應急方案,均不屬于作品,其“可版權性”存疑。
2 無人駕駛汽車與專利權
無人駕駛汽車技術作為知識革命中最具代表性與影響力的時代技術之一,通過專利權保護應對其發展過程中的不可預測性與潛在的不可逆性是必然的長遠的理性選擇。
當下已獲授權的與無人駕駛汽車相關的專利權利要求書涉及的范圍往往較廣,導致這類專利在侵權認定上具有其特殊性,實施全部技術行為往往需要多個主體彼此協作共同完成,單一主體、單一節點的實施大概率不會構成侵權行為或僅能牽強地適用間接侵權。例如,因提供無人駕駛汽車圖紙的行為不屬于對專利產品的制造,設計圖又無法與產品本身畫上等號,單純的提供行為也無法被“專利產品的使用、許諾銷售、銷售行為”囊括之內。那么,根據現行專利法的規定,其就不屬于直接侵權,不僅增加了專利權人的舉證難度,還不利于保護專利權人完整的專利權。
無人駕駛汽車產業化過程中,需要多個主體共同完成,在云計算、大數據等相關技術提升運算速度、降低運行成本的同時,為提供海量的數據資源以供計算、分析,創新更智能化的算法模型,傳統的商業運行模式已不再適用。在無人駕駛汽車商業化的產業鏈中,主要存在著平臺提供商、系統集成商、服務提供商、應用開發商,以及用戶五大主體,專利侵權行為一旦產生,就可能侵犯多個專利權人的專利權,也有可能發生多主體共同意思表示共同進行直接侵權行為,與一般的直接侵權相比,其具有特殊性。
關于間接侵權行為,我國專利法雖暫無明確規定,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中指出,“明知有關產品系專門用于實施專利的材料、設備、零部件、中間物等,未經專利權人許可,為生產經營目的將該產品提供給他人實施了侵權專利權的行為,權利人主張該提供者的行為屬于《侵權責任法》第九條規定的幫助他人實施侵權行為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而“明知有關產品、方法被授予專利權,未經專利權人許可,為生產經營目的積極誘導他人實施了侵權專利權的行為”,則屬于“教唆他人實施侵權行為”,應當與行為人承擔連帶責任。
法律規范如此規定,事實上是考慮到在實踐中間接侵權人與最終生產侵犯專利權產品的侵權人之間存在不具有共同意思聯絡的可能,亦不具備共同過錯。然而,因間接侵權人明知其提供的零部件等僅能適用于生產專利產品,即其提供產品是直接侵權行為的專用品,或在他人直接侵權行為中扮演著積極誘導角色的,但仍然向直接侵權人提供實施的主觀惡意,將此行為納入《侵權責任法》的規制范圍內,要求間接侵權人承擔連帶責任具有合理性。
3 無人駕駛汽車與商標權
當前我國研發無人駕駛汽車相關技術的領域主要有各大高等理工院校、傳統汽車及零部件制造商、互聯網資本巨頭三大參與主體。當然,在這三大主體中,互聯網企業以其強大的科研優勢與雄厚的資金實力在市場布局方面占據了一席之地。據不完全數據統計,我國以無人駕駛汽車技術為主要經營范圍的公司共計26家,融資規模已超80億元。
多個公司的聯合發展是無人駕駛發展領域的總體趨勢,無人駕駛汽車實現產業化后,按照我國現行有效的商標法規定,企業可通過注冊、使用獲得商標權,在無特別規定的情況下,企業之間可通過協商在量產的無人駕駛汽車上使用原有的商標,也可另行申請商標,企業對于商標問題有極高的自由度。
但考慮到無人駕駛汽車的技術尚不成熟,交通責任事故頻發,且造成了嚴重的后果,是否需強制性地使用證明商標?無人駕駛汽車行業協議組織注冊并控制相關證明商標,履行監督職能,待行業專家排除可能風險、驗收合格后,可在無人駕駛汽車上使用這一證明商標,用以證明車輛的質量與安全指數。
綜上所述,區別對待無人駕駛汽車領域的知識產權主體、客體、權利歸屬等內容,承認無人駕駛汽車生成技術方案的可專利性,否定無人駕駛汽車自身的主體資格,將無人駕駛汽車的決策理性控制在人類手中,而非冰冷的程序決策處理中。無論無人駕駛汽車技術發展程度如何,其仍然是作為機器或工具存在的,人類對于機器/工具的絕對控制力是人類文明社會的基礎。即便具有法律規則意識、倫理道德觀念的自然人主體在形成相關決策時,受到主觀情感的影響,無法直接作出最經濟的選擇,但為了保障人工智能立法的核心價值——安全,這也是必須作出的取舍。
就無人駕駛汽車的知識產權法規制而言,若是等待技術成果及技術效應完全顯現,再以此為基礎構建法律制度,法律的滯后性將進一步凸顯,有可能導致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有心無力”。因此,我們在立足于原有保護法律體系的基礎上,應合理擴大適用范圍,明確行業準入門檻和行業技術標準,依靠行業慣例、行業自律,重解有關規范,創建部分新制度。
參考文獻:
[1] 謝明遠,白碩.自動駕駛專利技術分析[J].河南科技,2017(14):57-58.
[2] 朱雪忠,張廣偉.人工智能產生的技術成果可專利性及其權利歸屬研究[J].情報雜志,2018(2):69-75.
[3] 曹越.無人駕駛技術對現有法律制度的影響研究[J].南海法學,2018,2(04):115-124.
作者簡介:余佳賽(1995—),女,浙江義烏人,碩士,研究方向:知識產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