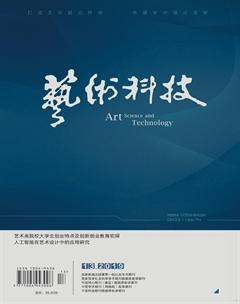丘禾嘉歷史評價探析
摘 要:丘禾嘉作為明末抗擊清軍的重要將領,《明史》有傳,深入研究這一貴定歷史文化名人,對于深入系統(tǒng)地研究貴定陽寶山的人文脊梁有重要支撐作用。《明史》中對其“忠義激發(fā),危不顧身”的評價,基本概括了丘禾嘉的人格風貌,關鍵時刻的“危不顧身”,使得崇禎皇帝對其“倚為長城”。在具體的軍事部署、軍政方略上,丘禾嘉可能與孫承宗等先輩存在差異,但這種差異更多的是政見不同,而非為求差異而差異的有意為之。因此,丘禾嘉與孫承宗的政見軍略之爭,并不妨礙兩位成為明末遼東危局中的關鍵擔當人物。
關鍵詞:丘禾嘉;抗清戰(zhàn)爭;陽寶山
1 丘氏兄弟與陽寶山
丘禾實(1570—1614),字有秋,登之,號鶴峰,明朝新添衛(wèi)(今貴州貴定人)。萬歷廿六年(1598年)進士,官至右春坊右庶子。與其弟丘禾嘉(崇禎時官至遼東巡撫兼統(tǒng)山海關諸處)攻書于此。萬歷年間,陽寶山已經(jīng)是士子們敬仰的佛教圣地,丘禾實賦詩《冬日登臨陽寶山假宿僧舍二律》:“晚宿芙蓉第一峰,醒來寒氣動塵第。天門早射扶桑影,虛谷猶傳子夜鐘。自有野猿能獻果,攜將筇竹恐成龍。前生知否浮邱是,已覺無生分外濃。”相比其兄的詩作才情,丘禾嘉更擅長的是兵戎戰(zhàn)場爭勝,并因此成為明末遼東戰(zhàn)場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丘禾嘉,字獻之,一字有谷,號少鶴。其軍事生涯開始于貴州,在平定奢安之亂中有功于朝廷,供職于貴州巡撫蔡復一軍中。“丘禾嘉,貴州新添衛(wèi)人。舉萬歷四十一年鄉(xiāng)試,好談兵。天啟時,安邦彥反,捐資助器,協(xié)擒其黨何中蔚。選祁門教諭,以貴州巡撫蔡復一請,遷翰林待詔,參復一軍。”[1]
所謂允文允武,丘氏兄弟的研究值得著力挖掘。地靈人杰的陽寶山,既培養(yǎng)了大批悲天憫人、佛學精湛的僧才,更孕育了積極入世、文韜武略的丘氏兄弟,入世與出世的品格同時集中在這樣一座名山上,實在難能可貴。丘氏兄弟與陽寶山的因緣頗深。在此攻讀時,兄弟二人曾流連忘返。“方余登洞時,余弟好捷甚。凡先余上下者再,不恃僮,又數(shù)數(shù)代僮掖余。余既下,則鼓余涉泉視石門,余辭不能,則褰裳獨往。久之出,謂余曰:‘門內(nèi)方丈余,更有重門,其中若明若暗,若泉若洲,且重門上,累累若有所屬,殆龍蛇之類乎?弟又前視,泉中一物,長尺有咫,麟甲皆具。余恐真龍也,挽俱出。然弟猶憾,不以火竟云。出洞已晡時。相與就壺觴,然意水所從來,不勝豪舉。因復從左山索之,復得一洞,深入無內(nèi),履其旁,則聞聲如吼,稍入,則聞聲如雷。深入而后,乃知為澎湃聲。有坎巉巖,下臨無際。則渟泓一潭也。余不敢入,第聞之僮若此,因名之曰‘雷鳴。乃余弟索奇無已,仍援石下視建瓴處,則當小洞。下有尾閭,為潭所泄,水三迭,如珠簾云。此洞去憑虛洞百余步,仍處高,然水不下泄,而旁穿為瀑布,乃余所改路,經(jīng)旁穿之上,石生如梁,小洞當余路旁,雖有聲,然不令人見險。噫嘻,水亦有靈,避余憑虛之勝,又避余雷鳴之險,造化之密,亦靈怪矣哉!此外巖洞迭出,在在現(xiàn)奇,時方誅茅,不及盡索而日暮矣,因為興盡之歸,姑記之。” [2]
可見,丘氏兄弟攻讀詩書于此,修身養(yǎng)性于此,涵養(yǎng)胸襟于此,陽寶山的名山品格已經(jīng)深深浸潤在丘氏兄弟人格氣象之中。陽寶山上王陽明心學的傳播痕跡也顯著可見。“雖然,山之靈,固人心之所為靈也。”[2]“如諸君言,則人心之靈,固不必余疏也。彼向者一念觸發(fā),旋獲善果。”[2]
2 丘禾嘉的抗清事業(yè)
執(zhí)政初期的崇禎頗有中興之君的氣象,面對內(nèi)憂外患的嚴峻局勢,不拘一格選用人才,尤其是軍事人才,丘禾嘉依靠自己的軍事方略與實戰(zhàn)考驗取得了朝廷的信任與器重。“崇禎元年有薦其知兵者,命條上方略。帝稱善,即授兵部職方主事。三年正月,薊遼總督梁廷棟入主中樞,銜總理馬世龍違節(jié)制,命禾嘉監(jiān)紀其軍。時永平四城失守,樞輔孫承宗在關門,聲息阻絕。薊遼總督張鳳翼未至,而順天巡撫方大任老病不能軍,惟禾嘉議通關門聲援,率軍入開平。二月,大清兵來攻,禾嘉力拒守,乃引去。已,分略古治鄉(xiāng),禾嘉令副將何可綱、張洪謨、金國奇、劉光祚等迎戰(zhàn),抵灤州。甫還,而大清兵復攻牛門、水門,又督參將曹文詔等迎戰(zhàn),抵遵化而返。無何,四城皆復。”[1]這一戰(zhàn)役充分體現(xiàn)了丘禾嘉的軍事才華與“忠義激發(fā),危不顧身”,丘禾嘉也因此得到了當時兵部尚書梁廷棟的器重。
明清遼東爭局中,大凌城的修筑是明遼東決策者的一個重大集體決斷,丘禾嘉、孫承宗基本觀點是一致的,只是戰(zhàn)術方略不同。
“會禾嘉訐祖大壽,大壽亦發(fā)其贓私。承宗不欲以武將去文臣,抑使弗奏,密聞于朝,請改禾嘉他職。四年五月命調(diào)南京太仆卿,以孫榖代。榖未至,部檄促城甚急。大壽以兵四千據(jù)其地,發(fā)班軍萬四千人筑之,護以石砫土兵萬人。禾嘉往視之,條九議以上。工垂成,廷棟罷去。廷議大凌荒遠不當城,撤班軍赴薊,責撫鎮(zhèn)矯舉,令回奏。禾嘉懼,盡撤防兵,留班軍萬人,輸糧萬石濟之。”
面對“廷議”的指責,丘禾嘉一方面“盡撤防兵”,同時卻“留班軍萬人,輸糧萬石濟之。”可以隱約窺見,丘禾嘉既要應對來自“廷議”的壓力,做做樣子,因而班軍只撤退了四千人,同時對于修筑大凌河城池又難以割舍,因而采取了變通的措施。這種模棱兩可的變通措施觸及了清朝的根本戰(zhàn)略。
清廷一方皇太極認為明朝一旦在江東地區(qū)修筑起堅固有效的防御工事,那就更不會理會后金的議和要求了,鑒于這個判斷,他一定要破壞迂東地區(qū)明軍的戰(zhàn)略體系,只有后金對明朝保持強大的軍事優(yōu)勢,議和才有實現(xiàn)的可能。基于這個目的,此次出征依然嚴格約束士兵,不得肆意殺掠。后金軍隊包圍了大凌河后,向城內(nèi)官民發(fā)出書信,再次希望他們可以將后金方面的意圖稟報崇禎皇帝。
“大凌糧盡食人馬。大清屢移書招之,大壽許諾,獨副將可綱不從。十月二十七日,大壽殺可綱,與副將張存仁等三十九人投誓書約降。是夕出見,以妻子在錦州,請設計誘降錦州諸將,而留諸子于大清。禾嘉聞大凌城炮聲,謂大壽得脫,與襄及中官李明臣、高起潛發(fā)兵往迎。適大壽偽逃還,遂俱入錦州。大凌城人民商旅三萬有奇,僅存三之一,悉為大清所有,城亦被毀。十一月六日,大清復攻杏山。明日攻中左所。城上用炮擊,乃退。大壽入錦州,未得間,而禾嘉知其納款狀,具疏聞于朝。因初奏大壽突圍出,前后不讎,引罪請死。于是言官交劾,嚴旨飭禾嘉。而帝于大壽欲羈縻之也,弗罪也。”[1]
實事求是地講,崇禎帝仍然羈縻祖大壽,是惜其才,而對于“前后不讎”的丘禾嘉,崇禎是基本信任的,因此,才有了隨后的“禾嘉仍以僉都御史巡撫山海、永平”[1]任命的下達。值得注意的是,“禾嘉請為監(jiān)視中官設標兵。御史宋賢詆其諂附中人,帝怒,貶賢三秩”。[1]多疑猜忌的崇禎如此袒護丘禾嘉,可見丘禾嘉在崇禎心目中的分量。這一事件也是朝堂政治的反映,“1631年,發(fā)生了另一個政治上的不祥之兆。10月初,中官再次被派往北部邊境監(jiān)視軍隊,這種做法在1627年崇禎皇帝即位時本已取消。皇帝的改變主意,反映出他對文武官員愈來愈不滿意,并想有他自己的消息來源。朝廷里經(jīng)常不斷地鉤心斗角,可能使他感到太監(jiān)更有用,因為他們直接對他負責”。[3]
盡管如此,政見上的不同使得丘禾嘉終究難以與孫承宗派勢力和睦相處,這也造成了兩位忠義之臣的歷史悲劇。“禾嘉持論每與承宗異,不為所喜,時有詆諆。既遭喪敗,廷論益不容,遂堅以疾請。五年四月詔許還京,以楊嗣昌代。令其妻代陳病狀,乃命歸田,未出都卒。”兩位明朝重臣的意見不合集中體現(xiàn)在大凌河之戰(zhàn)中遲遲不能統(tǒng)一意見,據(jù)孫承宗方面的說法:“臣(承宗自稱)欲檄撤凌之兵以援凌,撫臣曰不敢;臣欲馬步合營前進,撫臣曰不如用奇;臣欲以騎集錦,以步向凌,撫臣欲分四路;撫臣奉中樞堅壁之指,又不肯明言,持兩端觀望,屢易師期。宋偉不附撫臣,則主進;吳襄奉中樞而附撫臣,則主不進。”承宗命刻日誓師,違令者斬,禾嘉責其“過嚴”。[4]
此處,所謂丘禾嘉“奉中樞堅壁之指,又不肯明言”顯然系誤解。否則難以解釋丘禾嘉“心懼”而撤防兵一說。面對孫承宗乃議以糧散軍,委城而去,勿使資敵的提議,丘禾嘉不以為然,并爭取到了祖大壽兄弟的支持。丘禾嘉“與祖大壽及其弟大弼,縱馬上城東望,并嘆道:孫經(jīng)略當年,以樞輔守邊,有支持袁崇煥欲守寧遠之勇氣;今卻欲委此大好城池丟棄,難道今無如袁崇煥之人乎?抑人官高而膽自薄耶?祖大弼聞言,目視其兄;祖大壽見狀,亦正視其弟。于是,祖大壽、祖大弼兄弟二人,愿率四千精兵,與萬余戍兵,共守此城”。[5]閻崇年先生所引用的這段材料很有參考價值,提供了很多隱含信息:其一,丘禾嘉爭取到了祖大壽兄弟,意欲在大凌河城重現(xiàn)當年袁崇煥寧遠大捷的經(jīng)驗,再次依靠“憑堅城以用大炮”的戰(zhàn)術擊敗后金軍隊;其二,丘禾嘉與孫承宗的矛盾主要是軍事方略的不同,具體而言,丘禾嘉認為孫承宗“官高而膽自薄”,而孫承宗認為丘禾嘉是犯孤軍深入的軍事冒險主義;其三,結合幾方面的材料,孫承宗指責丘禾嘉“不敢”“不進”與修筑大凌河時丘的積極進攻不怕冒險的意見顯然并不相同,與戰(zhàn)后“移駐松山,圖再舉”的行為也不相符,再結合丘禾嘉此時實際上已經(jīng)被任命為南京太仆卿,丘禾嘉在此場戰(zhàn)役中所能夠行使的軍事權力與需要承擔的軍事責任顯然沒有孫承宗所言之大。
3 丘禾嘉的歷史評價再探
崇禎初政,力圖復遼。明朝與后金在遼西爭局,時勢所趨,不可避免。明軍在大凌河城已經(jīng)三毀基址上筑城,受到后金的密切注視。明朝修復已毀的大凌河城,成為大凌河之戰(zhàn)的直接導因。
明遼東巡撫畢自肅在寧遠兵變中遇害后,明廷廢除了遼東巡撫。明兵部尚書梁廷棟舉薦丘禾嘉為遼東巡撫。修復大凌河城的動議由孫承宗提議,并同梁廷棟、丘禾嘉等有直接關系。《明史·孫承宗傳》記載:
禾嘉巡撫遼東,議復取廣寧、義州、右屯三城。承宗言廣寧道遠,當先據(jù)右屯,筑城大凌河,以漸而進。兵部尚書梁廷棟主之,遂以七月興工。
可見,此時明廷軍政方略的基本方向是戰(zhàn)略進攻,這需要聯(lián)系明清總體的攻守形勢而言。需要注意的是,“1629年12月開始的關內(nèi)戰(zhàn)役,不僅導致袁崇煥的被捕與被殺,而且導致他從前的幾個支持者的辭職”。[3]換句話說,袁崇煥及其支持者原先所用的“憑堅城以用大炮”的積極防御戰(zhàn)略已經(jīng)被“以漸而進”的積極進攻戰(zhàn)略改變。但是,生性猶豫多疑的崇禎皇帝并不是徹底地改變戰(zhàn)略,“這種逆轉(zhuǎn)并不意味著東林集團在朝廷已經(jīng)失去一切影響。在這個時期,崇禎皇帝顯然想在真正的或傳聞的東林支持者和他們的反對者之間搞平衡”。[3]這樣,新提拔上來的輔臣勢必在軍政方略上有所改變,“1630年2月,當北直隸的軍事危機達到頂點時,皇帝任命了三名官員為輔臣,其中兩人與東林有關系”。[3]但是,這種改變又不可能徹底。廟堂之上謀算制衡的政治博弈,決定了戰(zhàn)場之上軍事官員戰(zhàn)略的左右搖擺。更糟糕的是,朝堂之上的黨爭傳遞到對清前線,則成了在筑大凌河城工程中巡撫丘禾嘉訐告總兵祖大壽,大壽也揭發(fā)禾嘉贓私的鬧劇。我們看到,“工垂成,廷棟罷去。廷議大凌荒遠不當城,撤班軍赴薊,責撫鎮(zhèn)矯舉,令回奏。禾嘉懼,盡撤防兵,留班軍萬人,輸糧萬石濟之”。[1]這種既不像戰(zhàn),又不像和,亦不像守的混沌戰(zhàn)略,打破了明清之間的遼東防線上的平衡,“在1631年9月初皇太極包圍新筑的大凌城之前,東北邊境這時相當安靜,大凌城是明要塞錦州北邊的一個戰(zhàn)略要哨,在山海關東北125英里”,[3]且明軍并無充分的應對方案。
孫承宗御關外以弊關內(nèi),逐步推進,最后恢復全遼的戰(zhàn)略思想,取得了遼東戰(zhàn)場長期對峙并有所恢復的局面。[6]但是,在接連遭遇兩次攻堅失敗之后,后金政權顯然在考慮新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其一,“后金軍同明遼軍作戰(zhàn),騎兵攻堅破,都是速戰(zhàn)速決,長期圍城攻堅,自大凌河城始”。[5]其二,后金同明軍的大凌河之戰(zhàn),皇太極第一次使用紅衣大炮,努爾哈赤與皇太極兩次攻城挫敗,使得后金軍認識到必須擁有紅衣大炮,而明軍對后金軍武器裝備上的進步認識不足。“以是久圍大凌河,克成厥功者,皆因上創(chuàng)造紅衣大將軍炮故也。”[7]
明廷在戰(zhàn)與守之間搖擺不定,朝堂之上的博弈嚴重影響了前線軍事的指揮統(tǒng)一,而對手后金軍隊則實施了大規(guī)模的軍事變革,以圍城打援替代速戰(zhàn)攻城,并使用了紅衣大炮這一新的軍事武器,以變革了的軍事方略替代不變的明廷方略,未戰(zhàn)已見高下。
4 結語
“明世舉于鄉(xiāng)而仕至巡撫者,隆慶朝止海瑞,萬歷朝張守中、艾穆。莊烈帝破格求才,得十人:丘民仰、宋一鶴、何騰蛟、張亮以忠義著,劉可訓以武功聞,劉應遇、孫元化、徐起元皆以勤勞致位,而陳新甲官最顯。贊曰:危亂之世,未嘗乏才,顧往往不盡其用。用矣,或掣其肘而驅(qū)之必死。若是者,人實為之,要之亦天意也。盧象升在莊烈帝時,豈非不世之才,乃困抑之以至死,何耶!至忠義激發(fā),危不顧身,若劉之綸、丘民仰之徒,又相與俱盡,則天意可知矣。”[1]
《明史》中對于丘禾嘉“忠義激發(fā),危不顧身”的評價,基本概括了丘禾嘉的人格風貌,我們注意到,相比盧象升等人的“不世之才”,劉可訓等人的“以武功聞”“以勤勞致位”,陳新甲的“官最顯”,丘禾嘉的綜合評價是“以忠義著”,關鍵時刻的“危不顧身”,使得崇禎皇帝對其“倚為長城”。換句話講,在具體的軍事部署、軍政方略上,丘禾嘉可能與孫承宗等先輩存在差異,但這種差異更多的是政見不同,而非為求差異而差異的有意為之。因此,丘禾嘉與孫承宗的政見軍略之爭,并不妨礙兩位成為明末危局中的關鍵擔當人物。
參考文獻:
[1] 貴州歷史文獻研究會.二十四史貴州史料輯錄[M].貴州民族出版社,2001:656-659.
[2] 郭子章(明).趙平略點校《黔記》[M].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244-246.
[3] 牟復禮(美),崔瑞德(英).劍橋中國明代史(上卷)(1368-1644年)[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596,598-599.
[4] 余三樂.明末黨爭中的孫承宗[J].史學集刊,1989(02).
[5] 閻崇年.論大凌河之戰(zhàn)[J].清史研究,2003(1).
[6] 孔騏驥.孫承宗的軍事思想略論[J].軍事歷史研究,1989(1).
[7] 清太宗實錄(卷十)[M].中華書局影印本,1985.
作者簡介:欒成斌(1982—),男,歷史地理學博士,貴州大學歷史與民族文化學院教師,貴州省社科院黔學研究院研究員,貴州大學中華傳統(tǒng)文化與貴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研究方向:歷史經(jīng)濟地理,貴州區(qū)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