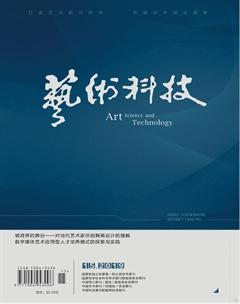“守祠人”的前世今生
摘 要: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變革,傳統的宗族祠堂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發生了不同的變化,具體體現在建筑形制、空間格局、運行管理、文化內涵等方面。而本文將以“人”為主體,展現被時代所遺忘,曾經以看守祠堂為工作的一群人的生活,并且試圖通過他們生活和習俗的變化反映時代的變遷。
關鍵詞:“守祠人”;生活與習俗;變遷
芝英鎮位于浙江省永康市,自明清以來該地區形成了規模宏大的應氏祠堂群落,因此,芝英流傳著“芝英馱(大),祠堂多”的民諺。在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普查人員發現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芝英鎮范圍內,保存著民國年間的81座祠堂,截止普查結束保存完整的祠堂有52座,而且都是應氏祠堂。如此之多的祠堂,在世代管理和運行的過程中曾產生過一個特殊的工作——“看守祠堂”,因而“守祠人”不僅僅是應氏祠堂變遷的見證者,還是時代變遷的見證者。
1 “守祠人”的名稱
自古以來,對于“看守祠堂的人”就沒有明確的定義,本文稱其為“守祠人”是根據芝英人的叫法,指的是守護祠堂的人,負責祠堂的雜務,例如,燒飯、打掃、開門、關門等事務。
從文獻資料來看,古往今來有關“守祠人”的研究十分匱乏,并沒有一個專門的著作談論到“守祠人”,只是零零散散地出現在宗譜之上,例如,在芝英“應氏家規二十條”中,將“建祠宇”列為首條,并且明確規定,“命一人處守之,兼責以司香燭,時灑掃,供祀事役使焉。”由此可見,按照家規,芝英祠堂大都有“守祠人”。例如,大宗祠堂、用大公祠等。江蘇宜興任氏大宗祠,“立宗子以主稞獻,宗長以定名分,宗正以秉權衡,宗相以揆禮義,宗直以資風議,宗史以掌薄版,宗課以管錢名,宗干以充干辦。還有一些職員以及‘守祠人等雜役,分掌族內事。”宜興任氏大宗祠提出“守祠人”這一名稱,并將其明確歸為雜役一類。
2 “守祠人”的來源
關于“守祠人”的來源,常建華將“守祠人”歸為特定地區的賤民,并指出其在浙江地區與媒婆、轎夫、戲子、樂人等同屬于墮民、丐戶一類。關于墮民和丐戶的來源,書中給出了多種說法,包括“籍沒的犯官家屬”說、“宋代罪俘之遺”說、“元朝蒙古人之后”說等。其來源眾說紛紜,觀點不一,并且各種來源傳說的真實性還需進一步證實。
芝英“守祠人”主要有以下兩種來源:一是周邊貧民,遷居于此;二是省內難民,逃難于此。一個王姓“守祠人”說,他們家祖上是來自距離芝英不遠的胡庫鎮黃泥坑。孫氏“守祠人”最早是來自芝英鎮臨近的古山鎮孫宅村。最早來到芝英的原因是因為家里很窮,而芝英作為集鎮中心比周圍的鎮子富裕很多,又由于應氏祠堂眾多,需要有人看管,于是爺爺輩干起了看守祠堂的工作。由此可知,有一部分來到芝英的“守祠人“,是芝英鎮附近其他鎮上的人,大都是因為他們家庭貧苦,而芝英當時富裕,為應氏看守祠堂能使他們獲得住所和田地,維持他們的生計。此外,還有一部分“守祠人”來自浙江其他地方。家住思文公祠旁邊的陳爺爺祖上也是“守祠人”,祖上陳阿玉是從紹興逃難來到芝英,逃什么難不太清楚,但是后來就定居在芝英,之后世代守護著思文公祠。概括來說,大多芝英的“守祠人”祖上都是來自浙江省境內,尤其是芝英鎮附近地區。
此外,可發現芝英的“守祠人”多是“非”應氏的外姓人。“芝英歷史文化研究會”的一個應氏老爺爺說:“以前守祠、唱戲、抬轎都是下等人做的事情,例如當地民俗信仰活動——八月十三的‘打羅漢唱戲,我們以前都是請外地的外姓人,去方巖廟會抬轎的轎夫也是外姓人來做,我們應氏的人是不做這種事情的”。①在調查過程中發現,許多“守祠人”的后代也不愿意提起祖先為應氏守祠的事情,只是說以前就住在祠堂旁邊。后來王爺爺說:“古代人有小姓人一說,小姓人是比大姓人低人一等的,舊時應氏宗族給小姓人立有規矩,嫁娶不能坐花轎、穿旗袍、戴鳳冠;辦酒席不能講排場,新媳婦過門三天要向村里大姓叩拜,方承認其家媳婦,一般不能同大姓通婚。”②
“守祠人”的工作特殊,加之作為“小姓”人群,其銘刻在人心中的印象就是一個地位低下的群體,不僅表現在應氏的外部認同上,還體現在“守祠人”對自身的內部認知上。如同岳永逸對北京天橋藝人的描述,“守祠人”也必須要從原有的生活世界、社會空間中脫離出來,融入一個新的生活世界、社會空間中,拋棄前者的秩序、規則,遵循后者的文化邏輯與理念并實踐。
3 “守祠人”的生活與習俗
3.1 “門衛”
按照應氏家規,芝英祠堂都有“守祠人”,并且為其安排住所。“守祠人”大都住在祠堂旁邊的房子里,與守祠人住房相連的是祠堂的倉房、燒飯的伙房等,有時候會統稱“伙房”。據孫爺爺說,他現在住的房子就是以前天言公祠的“伙房”。思文公祠的“守祠人”陳爺爺一家,自來到芝英就世代住在思文公祠旁邊的小四合院內。芝英其他許多祠堂都建有“伙房”,據《芝英應氏宗譜》記載,“大宗祠堂外,西邊有伙房和守祠人住房,大門偏西圍墻,有小門通往伙房”。
新中國成立后,1950年永康開始土地改革,土改主要完成了永康縣土地、房屋、山場、雜地等的重新分配,且主要原則是“地主、常會、族產、廟產沒收,富農出租部分征收,中農不動”,1951年4月,全縣有59435戶農戶領到了土地房產證。據村民說,土改時,祠堂變成了集體財產,許多祠堂分給私人居住或者歸為村里集體財產,有的甚至做了廠房。雖然許多祠堂已被損壞,有的甚至不存在了,但是“守祠人”依然居住在祠堂旁邊的房子里,只是房子再也不是從前祠堂的“伙房”,而是“守祠人”自己私人的房子了。
3.2 “管理員”
祠堂的大門需要“守祠人”看守,看守祠堂除了白天開祠堂門,晚上關祠堂門外,還要負責祠堂的日常灑掃。孫爺爺說:“以前天言公祠里面住有兩個應氏的老頭,因為年紀大了,也沒有后代,就住在祠堂里,但是祠堂的日常管理事務,兩個老頭也不曾承擔。解放前,爺爺和爸爸都幫著看守祠堂,負責日常管理工作。例如,谷子放在祠堂里,每個房頭都有自己的糧倉,為了防止被盜,晚上需要鎖門。或者祠堂議決宗族大事、祭祀、開倉等事情的時候,就把祠堂打開。”
1937年抗戰爆發,為安置浙西難民,1938年,芝英許多祠堂成為難民制造工廠,如天言公祠、天成公祠、小宗祠堂等。“大躍進”時期,秋收晚上割麥子沒有火把照明,村民就燒靈牌來當火把。后來集體化時期,祠堂變成生產隊的集體財產,由各個生產隊自己管理,也就不需要守祠了。
3.3 “廚師”
芝英應氏宗譜中記載,“祠堂會負責收租、祭祀。置有碗、碟、桌等物品,可隨時啟用。”祠堂在舉行祭祀活動的時候,“守祠人”就需要去幫忙燒飯,準備祭祀的供品等。后來祠堂沒有了祭祀活動,但祠堂有其他事情,“守祠人”也幫忙燒飯。孫爺爺說,每個祠堂都有自己的族產,收租是祠堂理事會自己管理,他父親主要是負責給理事會等燒飯,雖不給父親工錢,但是幫祠堂燒飯的當天,孫爺爺他們全家都會在祠堂里吃飯。③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土地改革對房屋等財產的劃分,許多祠堂成為私人財產,祠堂的祭祀、議決大事、儲糧備荒的功能逐漸消失,祠堂沒有活動舉辦,自然就不需要“守祠人”幫祠堂做飯了。
隨著時代的變遷,祠堂的功能也發生著變化,由最初的祭祀場所,逐漸變成私人居住場所,而最初依靠祠堂生活的這一特殊群體,他們的生活也隨著祠堂的變化而變化。由以前管理祠堂事務,到看守祠堂,再到僅僅是住在曾經是祠堂的房子里,“守祠人”的“前世”與“今生”的變化也反映著中國社會的變遷。
注釋:①本段敘述整理自芝英二村應子賢老人口述。
②本段敘述整理自芝英二村王明錢老人口述。
③本段敘述整理自芝英一村孫炳奎老人口述。
參考文獻:
[1] 經君建.清代社會的賤民等級[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2009:165-167.
[2] 岳永逸.近代北京天橋藝人的來源及認同[M].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48.
[3] 永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永康市志[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4] 芝英應氏宗譜(2014年重修本)[Z].
[5] 古山鎮孫氏宗譜(2011年重修本)[Z].
作者簡介:曹洪蘭(1994—),女,安徽六安人,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民俗學專業研究生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