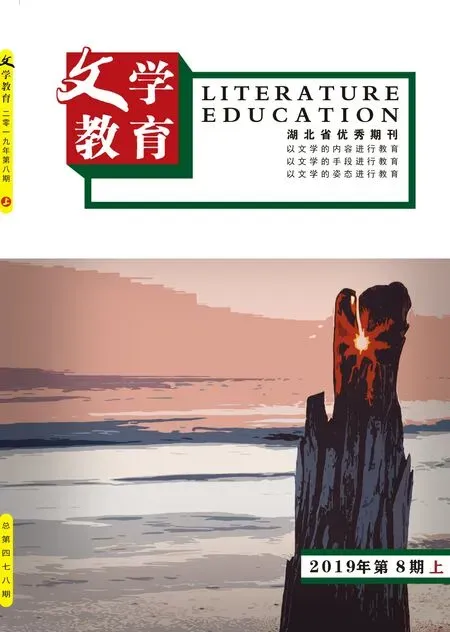宮本百合子《伸子》的生態女性主義解讀
王延紅
宮本百合子在日本近現代文學史上有著重要地位,是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抵抗文學的先鋒,也是日本婦女解放運動的重要活動家。17歲發表處女作《貧窮的人們》,被稱為“天才少女”而備受關注,戰后初期進步的日本知識人更對她致以神明般的崇敬。她一生創作頗豐,在她1951年逝世后出版的全集里,收入了84篇小說、697篇評論和散文等。其小說大都取材于作家的親身經歷,并且一直關注女性解放、婦女問題、戰爭的影響等,《伸子》即是以作家第一次失敗的婚姻經歷寫成的“自傳體”小說。
《伸子》最初連載于日本雜志《改造》上,1928年以單行本形式發行,發行單行本時稍有改動。因當時日本正處于軍國主義統治時期,是日本的白色恐怖時期,所以《伸子》在發表當時并未引起重視,直到戰后才被發現其價值,為廣大讀者喜愛。歷來關于《伸子》的研究都集中于小說中伸子的女性形象、女性意識、進步意識或從女性主義、社會性別、敘事學等角度研究,但是細讀《伸子》文本后,筆者發現小說的思想內涵與生態女性主義的主張有很多共同之處,所以本文將從生態女性主義這一新的視角深入研究。
一.生態女性主義
生態女性主義這一術語,是致力于環境保護的生態運動和力圖消滅性別差異、提高女性社會地位的婦女解放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最初是法國女性主義者弗朗西絲娃·德·奧波妮于1974年,在她的《女性主義·毀滅》中第一次提出了這一概念。該理論在上世紀90年代得到重要發展,但是國內還未引起關注。以“生態女性主義”作為關鍵詞、主題、篇名在中國知網進行檢索,發現在2007年、2008年之后,中國掀起了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熱潮。中國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涉及多個方面,如生態女性主義的理論介紹、在中國的傳播、研究述評、學科交叉研究、文本解讀等,其中應用最廣的當屬用該理論對文學作品進行解讀。
生態女性主義自誕生之初就是探索“女性受壓抑和自然被破壞之間的關聯”的思想運動,它強調“女性”和“自然”之間的天然聯系。所以,該理論把男權社會對自然的壓迫和對女性的歧視聯系起來,反對人類中心論和男性中心論,反對那些導致剝削、統治、攻擊性的價值觀,實質上就是反對西方社會的“二元對立”結構體系。生態批評和女性主義發展到今日,它們所關懷的對象都已不僅僅是自然或女性,而是包括了所有二元論中的弱勢一方:自然、女性、東方、有色人種、被剝削階級等等[1]。在本文中,我們將從生態女性主義的角度,深刻探討《伸子》文本對“男權中心社會”的解構,揭示女性悲劇的社會根源。
二.“伸子”的女性形象
《伸子》是宮本百合子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小說女主人公伸子為擺脫母親的控制和追求獨立自由的生活,隨父前往美國留學,不久在美國與一個大她十五歲的男子自由戀愛并結婚,結婚后的婚姻生活并未像她所想像的那樣自由并使夫妻雙方得到成長,因此四年后伸子毅然提出了離婚。這是基于作家的親身經歷寫成的一部自傳體小說,主要向我們展示了一名年輕的女性,為追求獨立自由的生活、完成自我成長所經歷的崎嶇道路。
作為佐佐家的長女的伸子,對兄弟姐妹的愛不言而喻。例如,從美國剛回到家的伸子,見到母親就急忙詢問剛出生的妹妹的情況,面對久別重逢的弟弟妹妹,她激動不已。之后,留在日本國內的伸子,與弟弟妹妹們的交往更為頻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與弟弟們之間的交往,可以看到伸子對弟弟們成長的關心、弟弟們對她的依賴。比如,弟弟興奮地和姐姐講培養仙客來的種種;在伸子與娘家決裂而搬出去居住后,與弟弟妹妹們的交往也未斷絕;弟弟和一郎因戀愛的煩惱而向姐姐伸子敞開心扉。但是,盡管姐弟情深,伸子在婚姻問題上并未被封建的守舊思想所束縛,不會為了家族利益選擇丈夫。
作為女兒,伸子對父母有著骨肉親情,但同樣她自立意識很強,不會被父母左右。她之所以與父親遠渡重洋前往美國留學,主要目的就是“找個能按自己的理想來生活的機會”[2]35,與父親一起前往美國留學是她自立的第一步。因為伸子的母親多計代個性很強,又把自己人生中未能完成的的希望強加于伸子身上,所以如果不從父母的身邊逃離出來,她就必然會受到母親的限制,沒有行動的自由。關于戀愛對象,伸子不僅沒有找一個讓父母覺得體面的、“門當戶對”的人,反而與一個大她十幾歲、一無所有的窮留學生戀愛并結婚。雖然知道這與父母心目中的理想女婿有巨大的差距,但是伸子為了維護獨立自主的生活,她“自己不打算后退。哪怕到了最不好的情況,成了終生感情上不和的原因。”[2]69可見其自立的決心之強烈。在伸子與丈夫佃分別回國并與伸子的父母同住之后,雙方間的矛盾沖突開始顯現出來了。母親把對佃的不滿幾乎都轉嫁到伸子身上,母親的強勢和不原諒人的性格,最后終于激起了伸子的反抗。養子事件和之后的作品事件,伸子都堅守自己的立場,不屈服于母親,養子事件的結果是伸子夫婦從娘家搬了出來,作品事件則導致伸子與父母徹底決裂。由此可見,伸子個性之強烈,與父母對抗之激烈。
作為妻子,伸子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社會所頌揚的“賢妻良母”。求婚時,伸子就明確提出“不放棄事業”和“暫時不要孩子”,這在近百年后社會已經有相當進步的今天看來,也不是每個女性都可以說出口并且能夠堅持做到的。婚后的伸子,也是可以隨心想睡到什么時候就什么時候,也不會被家務纏身,可以從事自己想做的寫作事業。總之,即便是已經結婚的伸子,她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活法生活,繼續工作,不生孩子,在經濟上和精神上都保持著獨立。但是,隨著日子的長久,尤其是和母親的幾次沖突,伸子慢慢發現丈夫的虛偽、偽善、氣量狹小、自甘平庸,這與一直追求積極人生、更豐富的自我發展的伸子顯然是格格不入的。她覺得“在自己面前逐漸展開的是什么樣的道路呢?不就是一條消滅一個女人作人的道路嗎?”[2]217,雖然伸子也嘗試修復夫妻間關系,但是多次努力后反而發現丈夫更加虛偽的一面,最終伸子選擇了離婚。
如上所述,不管是作為“女兒”的伸子還是作為“妻子”的伸子,她始終都沒有放棄自我,迷失自我,而是為了實現自我,勇敢的以一位“女斗士”的姿態反抗父母和丈夫代表的封建家庭。
三.對“家父長制”的反抗
伸子所處的時代正是大正時期,當時日本正處于半封建社會,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大正民主主義風潮席卷至文化的各個領域,但是在家庭關系中“家父長制”仍然占主導地位,具有絕對權威。在小說中,父親的出場并不多,因為父親整日忙于事業,表面上好像母親主導著家中的一切事務。但是,從“在晚上或什么時候,雙親在悄悄地談著什么話的當兒,伸子無心之中走了進去,他們馬上就會沉默起來”[2]110,“我和你爸爸也一再商量過,反正你是離不開他的,我們的意思,倒不如爽性把佃招贅作養子吧。”[2]135,136在因養子事件和母親沖突升級,父親喊出“好,滾出去!你舍棄得了父母的話,我也就算丟了一個孩子。好,永遠給我滾出去!”[2]144等可以看出,伸子的父母始終是統一戰線的,母親只是父親的“代言人”。
關于伸子的自主結婚,澤田章子曾評論道:“百合子的結婚,說起來是旅行時的事情,而且也未得到父母的同意。如果是現如今,倒怎么都會有的,但是在大正時代中期,結婚是‘家’與‘家’之間,憑媒妁之言的習慣根深蒂固的時代,所以真的是非常大膽的結婚。這里也可以看出百合子不畏世俗、堅持自己想法的生活方式。(筆者譯)”[3]47。確實,雖然當時的日本已經走上了近代化的國家道路,但是社會的方方面面,封建陋習特別是“家父長制”下的“家”制度,還是頑固地存在著。
對于自己的娘家,伸子反抗了“父權”,對于她和佃的家,她同樣挑戰了“夫權”。按照日本的家父長制,結婚后,伸子的丈夫佃成為伸子的家長。但是,在婚前伸子就明確提出“婚后繼續工作”和“暫時不生孩子”。在那個時代,“丈夫是天,違背天意會受到懲罰”,特別是“生育”自古以來被看作是女性的義務。伸子拒絕生育這一點,和社會生態女性主義的主張是一致的。社會生態女性主義是生態女性主義的一個分支,該理論否認女性“天生”具有關懷和生育的特性。這種直接將“生育”和“女性”的關聯剝離的主張,是對男權統治社會的直接宣戰,它否認了女性是“生育的工具”,宣誓了女性在“生育權”方面的話語權。伸子在結婚后也并沒有像其他的家庭主婦那樣照顧丈夫的飲食起居,她會睡懶覺,也不必做家務,甚至還經常丟下丈夫去旅行。這些都與當時家父長制的要求是完全不相容的。
對于伸子同時又是現實生活中的百合子這種向兩個“家”反抗的行動,正如日本文藝評論家本多秋五在《宮本百合子—其生涯和作品—》一文中指出:“從去美國游學到前往蘇維埃,從19歲到28歲的十年間,可以看作是宮本百合子作家生活的第二期。(中略)這段時期,通過結婚打破父母的家的秩序而逃離,更作為從事文學工作的一個女人破壞了自己的家庭,從雙重意義上可以說是描寫‘破家女’的自身體驗的時期。”,“女斗士”百合子用實際行動反抗了家父長制。
四.對男尊女卑思想的批判與反抗
按照生態女性主義的觀點,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沒有上下高低之分,沒有貴賤之分,所有生命是一個相互聯系的網,相互關聯。生態女性主義的實踐在本質上是反等級制的,她們意識到,要徹底消除女性壓迫,就要消除等級制度。[4]55但是,一直以來的社會觀念,都是男性居于上位,女性是下位的、從屬的“他者”。日本自古就是典型的男尊女卑、男權至上的社會結構,反映在教育上,則是對女性實行“賢妻良母式”的教育。不管是日本政府1890年公布的“舊民法”還是1898年完成并沿用至今的日本“新民法”——《明治民法》,都從法律上保證了男性的特權和對女性的控制權。“舊民法”和明治民法都規定了戶主及家族、婚姻、親子、親權、監護、親族會、撫養義務等項內容,基本精神在于確認和維護以男性為中心的封建家族制度,規定“戶主是一家之長”,強調戶主在家族中的統治地位;輕視家族成員的個人人格和權利。在婚姻關系上規定了夫權,確認了夫妻間的不平等關系。妻從屬于夫,行為能力受到限制。在繼承制度上,兩部法典都將日本封建社會的家督繼承制度保留了下來,沿用封建時期固有的戶主權利和義務的繼承,由此使日本傳統的封建繼承制度得以延續。[5]93
《明治民法》第十四條至第十八條,直接將妻與未成年人、禁治產人并列為無能力人。被視為“無能力人”的女性,其家庭地位、社會地位之低下及活動范圍之狹窄可想而知。關于女性離婚權,《明治民法》第813條規定,妻子只有在丈夫犯奸淫罪并被判刑的情況下,才可以提出離婚。但是反之,丈夫只要發現妻子與人通奸,就可以立即提出離婚。關于日本女性的離婚,在21世紀的今天,也是異常艱難的。新華網2015年12月17日轉載《文匯報》的一篇報道《男性氏族傳統仍具強大生命力》一文中就提到,日本最高法院在處理“日本女性在離婚后六個月內不得再婚的《民法》規定是否違反憲法”的民事訴訟時,最終裁決“禁止時間超出100天的部分違憲”。在社會文明如此進步的今天,日本的女性自主離婚竟還有如此限制,更不用說百余年前伸子所處的時代了。世界經濟論壇2014年發布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顯示,在男女平等程度上日本排在第105位,可見日本社會男女不平等制度的社會根源之深、之頑固。《明治民法》通過立法的手段,將舊民法中受到一定削弱的戶主權,在新民法中得到加強,實質上是將男尊女卑的思想法制化。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熱情奔放、向往自由的伸子,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向這種男尊女卑、夫尊妻卑的不平等制度發起了反抗。她顛覆了“妻子=母親的女性作為‘賢妻良母’主內、丈夫=父親主外”的“男權中心”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規范,在自己的小家庭內部實現了一定程度上的男女平等。正如本多秋五所述,百合子就是“一支箭”,她向當時的男尊女卑的社會射出了反抗之箭。
五.結語
縱觀百合子的一生,自“伸子”時代以來,作家的女性意識愈來愈強烈,個人的人生經歷也促使作家在思想上日漸成熟,最終走上了社會主義革命這一正確的道路。作家“人生三部曲”小說的女主公伸子,也一直在尋找事業和家庭的平衡,伸子所苦苦追尋的答案,生態女性主義者已經給出了解答。女性要想獲得真正的平等與個人人格的全面發展,只有通過建立一個平等、多元的兩性和諧社會才能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