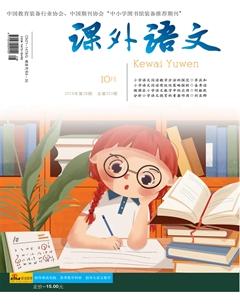讀解《邊城》的詩學價值
【摘要】沈從文的《邊城》是一部杰作,也是現代詩化小說集大成者。全書運用多個有濃重抒情意味的意象和似斷實續的敘事方式營造出詩意盎然的效果。本文擬探討讀者的詩意追尋過程,并分析《邊城》的詩學價值。
【關鍵詞】《邊城》;意象;敘事方式;詩學價值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中國是一個古老的詩的國度,其悠久的詩歌傳統對《邊城》這類詩化小說形成的影響不言而喻,更對中國讀者的讀解過程和審美旨趣影響頗深。接受詩歌話語,中國讀者從“言不盡意”“立象盡意”導引出追求“象外之象”的欣賞旨趣和詩意追尋法式。本文將從“立象盡意”、敘事方式、感受邏輯三個方面探討中國讀者閱讀《邊城》的詩意追尋過程,并分析其在修辭接受方面的詩學價值。
一、立象盡意
“言意之辯”是語言學和詩學的雙重話題。與言意之辯相表里的主體進入對象的方式,在修辭接受和文本讀解的詩意追尋方面體現出某種同構性。從莊子的“言不盡意”觀到孔子的“言以足志”說再到《易傳》的“立象盡意”論,中國的接受者漸漸穿越修辭活動兩極走近表達者。最終,孔穎達、陳骙用“象”填補了“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的語言空位。
凡《易》者,象也,以物象明人事,若詩之比興。
——孔穎達《周易正義》
《易》之有象,以盡其意;《詩》之有比,以達其情。
——陳骙《文則》
這里的象,不是自然物象,而是人格化的自然超越了現實化的自然之后,進入主體的心理幻象,是滲透了主體藝術經驗的審美符號。劉勰也在詩學意義上提出“意象”概念,把意象定為一種運思單位。他說“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至此,一個言、象、意三位一體的闡釋機制在詩學范疇上建立。表達者通過“象”來盡“意”,接受者也通過“象”來追尋“意”。
《邊城》一書飽含了碾坊、渡船、白塔等意象。這些意象的構成既有象征又有抒情,它們或者延長了小說的視景,或者暗示了人事的內在蘊含,從而擴大了小說的藝術表現空間。在《邊城》里,翠翠是著墨最多的一個人物,也是具有濃重理想色彩的一個意象。沈從文寫作《邊城》本意是要體現“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顯然,翠翠就是這種人生形式的象征,“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而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人又那么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在沈從文的筆下,翠翠幾乎是完美的。從這些優美的文字里,我們仿佛已瞧見那個溫柔明慧的小姑娘從盈盈翠影中走來。然而,翠翠不僅是完美人生形式的象征,更寄托著作家改造民族、社會的理想。他曾說,“在《邊城》題記上,且趁提起一個問題,即擬將‘過去和‘當前對照,所謂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可能從什么方面著手。”渡船和碾坊也是小說中的一對重要意象。渡船狹小破舊一如翠翠窮困的家境,而碾坊壯麗貴重一如團總家厚實的背景和強大的權勢。二者孰弱孰強幾乎是一眼分明,“但一個撐渡船的若想有那座碾坊,那簡直是不可能的妄想。”翠翠的愛情在如碾坊般強大的封建買辦婚姻重壓下做著艱苦的掙扎。而渡船與碾坊的幾度交鋒也隨著老船夫的突然離世而終止。翠翠身上濃重的理想主義色彩還是沒有戰勝這全部事變中的悲劇因子。最終,翠翠只能在渡口孤寂地等待儺送的歸來。然而,“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
象征本只是作品意象的一個構成因素。然而作家巧妙地在作品中融入自己的人生感慨并使這種感慨在性質上與具體意象相吻合,從而使意象本身也成為一種象征。《邊城》里翠翠天真活潑美麗明慧,本該是天使一樣無憂無慮的人兒卻透著一種莫名的孤獨感。老船工憨厚質樸,為人也熱情大方,本該是安然頤養天年的老人卻在關系寶貝孫女幸福的時刻被人誤解、猜忌甚至利用,最終含恨撒手西去。這兩個意象在作家最初營造的美麗祥和的氛圍里透出些許的悲涼。聯系歷史事實和作家的生平經歷我們可以了解到:湘西少數民族特別是苗族被長期視作“野蠻人”,他們歷代遭遇著被歧視、壓迫甚至屠殺的命運;沈從文作為有苗族血統的“鄉下人”在都市里感受到了壓抑,這種壓抑和人物所隱現的悲涼相契合,將作品憂傷、無奈的情感推上一個高峰。作品中流淌著的這股情緒是中國接受者走近表達者的階梯,更是接受者追尋“象外之象”的通道。“它表現受過長期壓迫而又富于幻象和敏感的少數民族在心坎里那一道沉郁隱痛,翠翠似顯出從文自己在這方面的性格……它不僅唱出了少數民族的心聲,也唱出了舊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聲。”越過作品的意象,作者自己的人生寄托也隱隱顯現。
《邊城》的意象是具體可感的,它們是茶峒這幅山水畫里的一個個物景,美麗而流露著淡淡的哀愁。然而這些意象也是一個個媒介。在作為媒介的作品人物的內心圖景上,疊印著湘西少數民族長期被壓迫和作者自身心靈受壓抑的歷史內容。通過把握這一個個意象所契合的人生情緒,讀者驀然回首,便發現那一個個獨立的意象漸漸模糊,而一個新的容納著各種情緒各種人生的意象漸漸淡出畫卷,漸漸明晰。
二、感受邏輯
修辭接受是接受主體介入對象的方式,在中國人對修辭話語的體驗和領會中,存在著三個明顯特征:悟性思維、平面拓展的思維和身心融入的思維。中國人平面拓展的思維方式為修辭接受中的秘響旁通活動提供了基礎。中國人的思考,感受勝過邏輯、意會勝過言傳,甚至可以“不求甚解”。中國是孔孟老莊的故鄉而不是柏拉圖、黑格爾、維特根斯坦、巴赫金的搖籃,它決定了中國人的思考在本質上仍然是感受多于思辨。
在敘事話語中,西方讀者受重視義理分析的語言哲學影響,注重話語的事理邏輯。而中國讀者從“立象盡意”出發,注重話語的感受邏輯,認同敘事話語貴“斷”而不貴“續”。《藝概》云:“章法不難于續,而難于斷。先秦文善斷,所以高不易攀。”由此可見,文本敘事話語的魅力就在于斷處而有接續感。在對《邊城》的讀解中,讀者也可以通過把握作家獨特的敘事方式而體驗這種“似斷實連”的審美感受。
《邊城》一共二十一節,每一節是一個故事,每一節自成首尾,然而通觀全篇,所有故事又似乎一氣呵成。因此有人稱贊《邊城》“每一節是一首詩,連起來成一首長詩;又像是二十一幅彩畫連成的畫卷”。仔細閱讀文本后我們發現,每一節的結尾或者引起下一節的話題,或者照應前一節的內容,或者與其他節的結尾和開頭構成故事發展的一條脈絡。在論及《邊城》的結尾時,汪曾祺說:湯顯祖評董解元《西廂記》,論及戲曲收尾,說“尾”有兩種,一種是“度尾”一種是“煞尾”。“度尾”如畫舫笙歌,從遠地來過近地,又向遠處去;“煞尾”如駿馬收韁,忽然停住,寸步不移。他說得很好,收尾不外這兩種。《邊城》各章的收尾,兩種兼見。
例如在《邊城》十二節的末尾,大老和二老決定“到那些月光照及的高崖上去,遵照當地習慣,很誠實與坦白去為一個‘初生之犢的黃花女唱歌”,“兩人便決定從當夜起始,來做這種為當地習慣說認可的競爭。”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翠翠的愛情似乎閃耀著明媚的曙光。在十三節的末尾,祖父和翠翠談起翠翠父母由唱歌而相愛的故事,并說“后來的事情長得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這種歌唱出了你”。我們似乎可以感到翠翠為歌而生,她也將經歷如歌般美麗的愛情。緊接著在十四節的開頭翠翠“夢中靈魂為一種美妙歌聲浮起來了,仿佛輕輕地各處飄著,上了白塔,下了菜園,到了船上,又復飛竄過懸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至此,象征翠翠愛情的虎耳草也出現了,與“大魚”相映成趣,讀者也能感受到翠翠內心的快樂。十五節末尾,翠翠自言自語“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祖父所唱的歌就是那晚上聽來的歌”。這兒的歌聲儼然使祖孫倆沉浸在翠翠越來越明朗的愛情帶來的喜悅中。最后一次唱歌出現在小說的結尾“可是那個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夢里為歌聲把靈魂浮起來的年輕人,還不曾回到茶峒來”。從十二節到最后一節,“唱歌”在小說的首尾共出現五次,連成了一條翠翠的愛情主線。翠翠的愛情由開始兄弟倆為她唱歌而充滿了希望到結局“可是那個在月下唱歌的年輕人還不曾回到茶峒來”。讀者通過把握各節的“斷”處,發掘出“唱歌”所暗含的愛情脈絡,從而打通審美通道體會作家運筆的妙處(如畫舫笙歌,從遠地來過近地,又向遠處去)。
與這類“似斷實續”的敘事方式相呼應的是中國接受者對周邦彥“詞斷意連”的贊賞和對書法藝術“筆斷勢連”的推崇。憑著得天獨厚的感受邏輯,中國接受者將作家預埋的一個個“斷”處進行審美續接,從而跨越修辭活動兩極,最大程度地接近表達者。
三、結語
由“立象盡意”連及的對于感受邏輯的偏重,使中國人對詩歌情有獨鐘。因而《邊城》濃郁的詩性也特別能激發中國接受者的審美思維。通過把握小說中翠翠、白塔、渡船等有濃重抒情意味的意象,中國接受者在詩意追尋過程中由事物返回精神,由具體的意象體悟出一種新的文化之“象”,從而產生“超以象外,得其環中”的詩性讀解。中國接受者在以詩讀詩的過程中,在體驗《邊城》詩美的輝煌瞬間,敞開了自己也重建了自己。
參考文獻
[1]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
[2]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M].香港:友聯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
[3]沈從文.沈從文文集(第十卷)[M].廣州:花城出版社,1983.
[4]譚學純,唐躍,朱玲.接受修辭學[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
[5]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6]沈從文.沈從文選集(第五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7]凌宇.從邊城走向世界[M].北京:生活·讀者·新知三聯書店,1985.
[8]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M].香港:香港昭明出版有限公司,1980.
作者簡介:馮芳,女,1985年生,福建省三明市人,碩士研究生,中學一級,研究方向為中學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