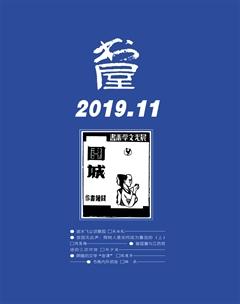偷盜火種
趙剛
人是靠思想站起來的,個人的認知升級,社會的繁榮進步,不是因為掌握了某種技能,而是汲取了優秀的思想。
——叔本華
一
1943年7月,納粹占領下的立陶宛的維爾納。
離開了維爾納大學圖書館,施默克·卡其金斯基向家中快步走去。自從納粹德國占領波蘭后,這個城市中所有的猶太人都被集中到由納粹黨衛軍和當地警察看守的聚居區。
按照德國占領軍的禁令,猶太人每天必須按時回到自己居住的聚居區,而且晚上八點之后不準上街。如果需要購買商品,也只能在下午的兩個小時里去指定的商店。購買商品需要特別的票證,按照規定,猶太人不準購買肥皂、香煙、肉類、雞蛋、魚、糖、奶酪、酒、發酵粉甚至蘋果、橘子和蔬菜。只要在猶太人家中搜出這些“違禁品”,例如,搜出一包香煙,收藏者就會被逮捕。猶太孩子哪怕吃了一個雞蛋或是一個蘋果,就是違法,就是犯罪。施默克的朋友柳芭·萊溫斯基,就是因為被搜出藏在身上的一小袋豆子,就被黨衛軍用鞭子狠狠地教訓了一頓。這還算是最輕的懲罰。
不久,施默克就發現情況有些不對頭,遠遠望去,等候回家的人群已經排到離聚居區大門兩個街區遠的地方。施默克默默地排到了隊尾,聽見前面有人悄聲說,今天在大門口進行人身盤查的是黨衛軍二級小隊的隊長布魯諾·基特爾。
“今天誰在門口檢查?”這是一個關涉生死的問題。
黨衛軍小隊長基特爾是一個年輕、高挑、皮膚黝黑的男人,據說還是一個訓練有素的音樂家。可誰也不會想到,在他那張英俊的臉龐背后,竟然有一顆極其冷酷的殺手的心。他時常會進入猶太人聚居區巡查,有時會攔下一個人,掏出一支香煙,問道:“有火嗎?”只要被問者點頭,基特爾就立刻掏出手槍,朝那個人頭上砰的一槍,然后殘忍地一笑,轉身而去。
今天基特爾坐鎮督查,守衛在猶太人聚居區的黨衛軍和警察格外賣力,比平時更加嚴格。不遠處傳來因私藏食物而被毆打的慘叫聲,施默克身邊的工人們立即動手將藏在自己衣服里的土豆、面包、蔬菜、香煙掏出來扔在路邊,還有幾盒火柴也滾到了街上。有的人一邊掏,一邊暗示施默克,趕緊將身上的東西處理掉。
扔,還是不扔?對于施默克來說,就如同哈姆雷特的生死獨白:“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
施默克明白,如果被抓住,等待他的只能是就地正法。因為他藏的東西,絕非身邊人那么簡單,只是一般的違禁物,他所藏的恰恰是納粹德國夢寐以求的東西。為此,希特勒指派專人從柏林趕赴維爾納。來人是一位神職人員——天主教牧師,名叫約翰內斯·波爾:四十一歲,博士。他曾經在耶路撒冷東方學院進行過高級《圣經》研究,熟練地掌握了希伯來語和現代希伯來語。作為猶太人文物專家,他加入了納粹德國文化寶藏劫掠機構——羅森堡國家指導總部(ERR)。
ERR是希特勒專門成立負責掠奪整個歐洲的文化財產的機構。1940年成立后不久,它就開始在法國大肆掠奪屬于猶太人的書籍和藝術品。不久,ERR更加肆無忌憚地把魔爪伸向國家博物館以及各種私人藏書庫,尤其是猶太人的宗教書籍、歷史檔案、著作手稿和歷史文化文件,原因不言而喻:這些是猶太研究的重要資源。借用納粹研究機構自己的話說,利用這些資源不僅可以研究“猶太人的墮落”,將迫害、滅絕猶太人的行為詭辯成“合理的科學術語”,而且一旦獲取了猶太人的這些稀有的歷史書籍和文物,就可以將此作為從精神和智力上鎮壓、摧毀猶太人的重要工具。
到達維爾納后,約翰內斯·波爾便馬不停蹄地開展工作。他首先下令抓捕當地大學的知名教授和圖書館負責人,在黨衛軍和蓋世太保的看押下,命令他們與ERR工作人員一起洗劫維爾納的研究所、圖書館、博物館以及當地猶太人引以為驕傲與榮耀的大猶太會堂,搶奪走各種珍貴的書籍、資料、手稿和《妥拉》書卷、王冠,并且還從猶太人聚居區內調集四十名囚犯作為苦工,編成不同的勞工小組(他們自稱為“紙張小隊”),負責分類、挑選、打包、運輸書籍及文物。這些猶太人每天都在維爾納大學灰色的禮堂里,在堆積如山的書堆中痛苦不堪地勞作。
施默克身上藏匿的違禁物正是一套被猶太人稱為圣物的《妥拉》。它是用猶太人最古老的希伯來文寫成的《舊約圣經》,它是猶太教經典中最重要的部分,同時也是公元前6世紀以前唯一的一部希伯來法律匯編,并作為猶太國的國家法律規范。
施默克所攜帶的《妥拉》是一件古版珍品,為防止損害,施默克像對待嬰兒一樣將它們貼身包在身上,外面再穿上襯衣,套上夾克。
在通向檢查點的隊伍中,施默克掃了一下身邊,絕大多數人面黃肌瘦,像他這樣高大并略顯臃腫的身材實在是太顯眼了!如果不立即丟掉《妥拉》,肯定會被黨衛軍一眼看出來。
施默克心情非常復雜,作為一名波蘭共產黨的地下黨員,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他從來沒有進過猶太教堂,更不用說讀過《妥拉》,而現在他卻要冒著生命危險保護這些宗教書籍。他明白這些書籍的重要性,就像他對自己的工友所說:“這些寶藏是我們的未來。對于現在的我們來說也許不重要,但對于那些能幸存的人來說很重要。”
“扔了吧,全都扔掉吧!”身邊開始有人低聲催促他。施默克此時反倒鎮靜下來。他清楚,現在絕不能丟掉這些書籍,保護這批書,這不僅是他的使命,而且是他作為“紙張小隊”隊長的責任。如果此刻丟掉這些書籍,德國人肯定會根據書中的書票及印章,順藤摸瓜地找到他的小隊。按照基特爾的脾氣,極有可能會處死整個小隊成員。施默克暗自下定決心,一旦被查出來,自己將與隨身攜帶的書共存亡。
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一步一步,義無反顧。突然,隊伍加快了行進速度,人群開始騷動。原來,基特爾和幾名黨衛軍覺得搜查工作繁復無趣,有些索然寡味,于是便打道回府了。德國人一走,當地警察也就懈怠了,放松了檢查,人們開始紛紛涌進聚居區大門。
施默克長舒了一口氣,隨著人流進入了聚居區。然后拐進一個街角,悄悄地潛入了猶太人聚居區地下深處的秘密地堡,將隨身書籍藏入地堡中的金屬鐵桶中。離開地堡時,施默克望著金屬鐵桶中裝滿的各種書籍、手稿、文件、宗教文物……默默地叨念:“我們的世界與地堡一樣漆黑,但在那即將到來的光明未來,這些文化寶藏一定會大放異彩。”
這僅僅是施默克和他的“紙張小隊”戰斗歷程中的一天。明天,又將繼續新的戰斗。
以上就是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猶太神學院歷史學教授大衛·E.費什曼在《偷書人》一書中所記述的在二戰期間,猶太平民在生死未卜的困境下如何愛書、讀書、護書的故事;如何冒著生命危險,從納粹手中搶救自己民族文化遺產的故事。這是一段黑暗歷史中鮮為人知的史實,是在強權和暴力下一個弱小民族如何捍衛自己民族文化與尊嚴的英雄交響曲。《偷書人》這部書,不僅榮獲2017年美國國家猶太人圖書獎,而且被翻譯成英、意、荷、葡、捷克、立陶宛語等,在全球發行。
二
在耶路撒冷有一條不足十英尺寬的小巷,環繞著一面巨大而不規則的石墻。這些石頭就是所羅門圣殿的花崗巖遺跡、猶太人的精神中心——哭墻,猶太教兩千年來哀慟自己流亡的象征性燈塔。雖然僅僅是一面長約五十米、高約十八米的殘垣斷壁,卻承載著猶太民族的全部希望,成為猶太民族兩千年來流離失所的精神家園,是猶太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猶太人相信它的上方就是上帝,千百年來,流落在世界各個角落的猶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時,便會來到這面石墻前低聲禱告,哭訴流亡之苦。
哭訴只是一種情感的宣泄,如何復興猶太文明,則一直是猶太民族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標。猶太哲學家邁蒙尼德說:即使叫花子也要研讀《圣經》。雖然猶太人研究《圣經》是出于宗教信仰,但卻使得猶太民族因此形成讀書的傳統。根據歷史考證,早在中世紀,猶太人就已經基本上消滅了文盲,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其他民族都不曾達到的。
猶太人有著獨特的知識觀和崇智主義,盡管一開始這種觀念帶有神學的傾向。《舊約圣經》教誨猶太人要“以智慧立地,以聰明定天”,只有知識“會使你走在世界的前列”。猶太民族領受了對神的契約,雖經歷史上三次大流散,但這種崇智主義理念卻在自身所遭受的苦難中得到了強化與升華。這種強化與升華深深地扎根在猶太人的心底,融進了猶太民族的血液中,成為他們獨有的傳統——對知識的尊重,對知識分子的尊重。由此,他們被稱為“書的民族”。通過書籍,猶太人踏上尋求智慧的道路;通過書籍,猶太人聚集了生命的力量;通過書籍,猶太人為自己及后代子孫在數千年的浪跡漂泊中,在虎狼環伺的險境下,建造了民族的“諾亞方舟”,豎起了前進的征帆。書的生命即是猶太民族的生命。書不朽,從而“書的民族”不朽!
無數劫難磨礪著猶太人對書的虔敬與赤誠。公元二世紀,羅馬,殉道者佳寧·本·塔丁被投入烈焰之時仍坦然自若,他手持“律法之卷”——《妥拉》鎮定地說:羊皮紙為烈焰吞噬了,但銘寫其上的文字將在天國匯聚一起,得到重生。
在古代的猶太社會,凡精通猶太法典者皆不必繳稅,因為社會公認他們為智慧付出了心血,對民族做出了貢獻。即使在日常生活中,猶太人對書籍、對知識也畏威懷德:家中若有書櫥,一定要擺放在床頭,表示敬意。猶太人的墓園中也常常放有書本,猶太人認為,生命雖有結束之日,但求知卻永無止境。
猶太文化不滅,其精神便永存;猶太書籍長留,其傳統便繼承。
“欲要亡其國,必先亡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國際學術界已經形成了一個基本共識:單就一個民族來說語言文字的中斷就足以導致該民族文化的斷裂。也就是說,當一種文化的載體——語言發生質的變化后,那么,這一文化與原先意義上的文化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例如,從文化學的角度出發,今天的埃及文化已不能算是古埃及文化的延續,當今的希臘文化也很難說是古希臘文化的延伸。盡管這些民族仍居住在這同一地區,但無論是他們的信仰、習俗,還是社會形態、生活方式到使用的文字等都已經不同于他們的先人。
現實就是如此殘酷,一旦希特勒滅絕猶太文化的計劃得逞,猶太人的書籍以及語言文字遭到毀滅,猶太民族將會遭受滅頂之災,整個猶太文明的發展進程就將中斷,猶太人賴以生存的文化也就會遭受歷史上曾經盛極一時、燦爛無比的蘇美爾、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等文明一樣的下場,僅僅留存于人類的記憶和典籍里。
三
如何利用反猶樹立自己的權威,打出一片天地,希特勒早在1924年被以“叛國罪”關押在蘭茨貝格監獄時,就已萌生想法。他曾幻想要創造一部杰作,一部自己的代表作,向世人展現自己的卓越思想。在七號牢房中,他用向看守借來的一臺老式打字機,用顫抖的雙手,在鍵盤上不停地敲打著,最后寫下了“四年半的抗爭:反對謊言、愚蠢和懦弱”的文稿,也就是后來那本聲名狼藉的“納粹黨圣經”——《我的奮斗》。
希特勒認為,哲學是德國文化的標志。在德國傳統中,哲學的地位顯赫,它被稱為國家文化成就的巔峰。康德、黑格爾和尼采等思想家對于德國人來說,就如同莎士比亞和狄更斯之于英國人,或者托馬斯·杰斐遜和馬克·吐溫之于美國人那樣神圣。“希特勒有一種強烈欲望,想要讓所有德國人信服……他必須把哲學主題收歸己有,沒有多久便開始幻想自己是個偉大的思想家。事實上,他很快就會以‘哲學領袖自居。”
1933年希特勒上臺,既然攫取了德國最高的政治地位,他也就自認為成了德國人民的“哲學領袖”,于是“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也就順理成章。要實現這個目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對信仰、言論、出版的自由實行全面壓制,對一切不符合納粹利益的書籍統統以“消滅墮落文化”的名義徹底清除、銷毀。尤其對猶太文化中最基本的精神——思辨精神,希特勒深惡痛絕。
猶太文化是一個多樣性的統一體。它從未要求思想和信仰上的整齊劃一,唯一強調的是對一些共同基本原則的篤信和遵行。正因如此,才會有“三個猶太人,就有四種想法”的說法。因此,允許不同意見的出現在猶太文化中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而這種觀念自然對希特勒的極權構成極大的威脅。
以“哲學領袖”自居的希特勒自然深諳這些道理,其中的底層邏輯就是他要以自己的學說統治精神世界,就絕對不允許猶太文化繼續存在。
二戰期間,納粹的鐵蹄蹂躪了歐洲二十個國家,在掠奪各國物質財富的同時,還摧毀了這些國家原有的規模不等的四百六十九座圖書館三百余萬冊藏書。這還不包括被納粹屠殺的一百五十余萬個猶太家庭的藏書。若是兩者相加,被焚毀的書籍數目相當驚人。僅1938年的“水晶之夜”當晚,就有數以百計的猶太教堂連同成千上萬冊的書籍、稿本被焚為灰燼。德國的一千三百余座猶太教堂,到1945年納粹戰敗時僅存數座。在號稱“立陶宛的耶路撒冷”的維爾納,納粹對猶太文化的大肆劫掠與毀滅更加令人發指,他們將幾十萬件的猶太文化寶藏盜運回德國,以研究如何消滅掉這個種族,同時又將逾百萬的猶太書籍、手稿、文件、圖片、海報、膠片送進焚燒爐和造紙廠銷毀。納粹對猶太文化的褻瀆恣行無忌,他們將猶太人視為圣物的《妥拉》當作垃圾送到當地皮革工廠,用這些羊皮紙修補德軍士兵的軍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