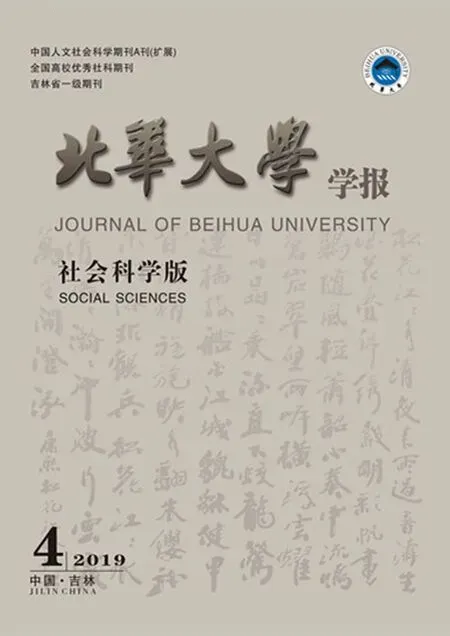棲居在思中
——論王蒙微型小說問句敘事修辭范式
李 娟
王蒙是個善于從日常微小事件中思考社會、思考人生、思考人性的作家,“思”對他而言不是單純的思考,而是超越思考的生命存在形態,他在《我的人生哲學》序中寫道:“駕駛著你的人生之船,做一次明朗的航行吧。”[1]3如何讓人生“明朗”?如何從蕪雜的生活中找到一條通明之路?為尋求答案,王蒙微型小說創作指向了“思”——一種敘事修辭方式。海德格爾曾說:“沉思執著于追問。追問乃通向答案之途。”[2]王蒙在多層面、多視角的“思”中不斷追問生活,觀照世事,解剖人性。他在“思”中引領讀者走出迷惘,走向“明朗”。
有“思”就有“問”,在王蒙微型小說中,問句是文本敘事修辭的一道風景線:有單句問、對話問、鋪排問;有無疑而問,有有疑而問;有真摯的問,有譏諷的問;有黑色幽默的問,有充滿玄幻的問;有小至柴米油鹽的問,有大至宇宙天地的問……這些“執著”的問共同構建了文本的敘事范式。王蒙說:“微型小說必須有自己的敘事邏輯和敘事語言。”[3]191他認為,微型小說“微到了沒有說教的余地,沒有打扮的余地,沒有貼膏藥、穿靴戴帽的余地。”[3]191由此可見,在微型小說方寸之地中,如何駕馭敘事語言,如何建構最優化的敘事范式,對作家來說都是極大的考驗。面對這種考驗,王蒙卻能獨辟蹊徑,借由一事一問,窺見大千世界。一事,說的是日常生活之事,如何說?梁漱溟先生認為:“生活即是某范圍內的‘事的相續’。”[4]2王蒙微型小說取材于日常生活,說的都是雞毛蒜皮、不登大雅之堂的小事。如果說微型小說篇幅短為“微”,其小之又小、甚至被人忽視的日常瑣事也是“微”。但是,“微”于王蒙看來,也自成一個世界,他說:“不論多微,仍然有自己的天地,自己的空間,自己的明暗與節奏,自己的概述與‘詳述’的方法與變化。”[3]191微型小說在敘事策略上自有機樞,“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當把一件小事又一件小事串接在一起時,就構筑出一個大世界,這就是王蒙微型小說的敘事邏輯。小說中,這一邏輯又以修辭化的“問”呈現,“我們問之不已——追尋不已。一問即有一答——自己所為的答,問不已答不已,所以‘事’之涌出不已。因此生活就成了無已的‘相續’。”[4]2-3梁漱溟先生這番話道出了“問”與“事”之間的關聯,“事”可生“問”,“問”又可生“事”,如此生生不息,氣象萬千。探究王蒙微型小說的敘事修辭范式就從這“問”開始。
一、問答式敘事修辭
問答式是文本對話雙方展開的一問一答彼此互動的敘事修辭范式。通過問答,小說人物就進入了一個修辭交際場。其中問者,即交際者,是指“在某場或某次人際交往、人際應酬或人際互動活動中占據主導或主動地位的一方”[5]3。他會基于自己的交際動機發問。答者,即受交際者,指交際活動中“居于被動地位的一方”[5]4,他是否能領會交際者的意圖而準確回答,并使雙方達成默契?這關涉到交際雙方的交際背景、認知心理、個性行為等影響因素。這些因素具有不可預知性,這不可預知決定了問答式敘事修辭在表達上將存在信息差,信息差是“言語交際過程中編碼與解碼處于不平衡、不等值的狀態”[6]。在現實交際中,如果交際者與受交際者在語義信息傳遞中出現不等值的情況,那么,就不能達成預期的交際效果。但是,在小說里,問答敘事修辭存在的信息差恰恰成為文本建構的優勢,因為交際者與受交際者表達的不對位,就有了對作品解讀的多種可能,進而作家與讀者之間也有更多的碰撞,由此,讀者將慢慢領悟文本修辭意圖,從而實現作家的創作愿望。這里以作品《考問》為例。
老王的孫子整天問老王:“爺爺,你整天寫什么呢?”
老王說:“我在寫信呀。”
孫子問:“寫信干什么?”
老王說:“把一些事告訴別人。”
孫子問:“干嗎要把事兒告訴別人呢?”
老王說:“有些想法想讓別人知道,想讓別人理解,想讓別人同情。”
孫子問:“干嗎要讓人理解讓人同情讓人知道呢?”
老王說:“誰也不知道你不理解你不同情你,你會覺得很悶很慌的呀。”
孫子問:“那您干嗎悶得慌呀?”
老王說:“一個人,不悶得慌嗎?”
孫子問:“干嗎說是一個人呀?到處都是人哪。”
老王說:“雖說到處都是人,可他們與我關心的不是一碼事兒啊。”
孫子問:“干嗎要跟您關心一樣的事兒啊?”
老王想,孫子大概新學會了“干嗎”一詞,拿著它練造句呢。[12]331
首先分析文本的敘事角色。《考問》是發生在爺孫倆之間的一次對話,爺爺年長,閱歷豐富,對社會有一定的認識;孫子年幼,童稚懵懂,好奇心強,對社會認知單純無雜念,飽有人類初始的干凈與自然。閱歷、年齡的差異,決定了角色認知的差異和話語交際信息傳遞的差異。在上述對話中,如果把孫子換成大人,將問不出那些看似幼稚甚至覺得無聊的問題。恰是孫子孩童的角色身份,讓他擁有強烈的好奇心。美國著名批評家尼爾·波茲曼說:“已知的世界和尚未知的世界是通過好奇心來連接的。但好奇心大半發生在兒童世界和成人世界是分離的,兒童必須通過提問尋求進入成人世界的情況下。”[7]在好奇心的驅策下,孫子對問題有了刨根到底的追問,一次次追問,一次次逼近人性的真相,逼近成人世界中自我迷失的可悲。王蒙真是高妙,他把小說的思想玄機隱藏在孫子的追問中。可以說,孫子的角色也是人性認知的一種隱喻。孫子代表了童年,童年飽有人性的真與美。《圣經》說:“你們如果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子,就一定不得進天國。”人生就是一次返璞歸真的旅程,“干嗎要讓人理解讓人同情讓人知道呢?”“那您干嗎悶得慌呀?”“干嗎要跟您關心一樣的事兒啊?”孩童本真的思維讓成人照見了被世俗化的自我,這就是爺孫倆對話的意義所在。從這個維度看,小說表層敘事角色的不平衡,在深層意義上就達成了平衡,當文本的信息差被消解時,小說的內在意蘊就凸顯了。
其次分析文本的敘事表達。在王蒙微型小說中,問答式敘事貼近日常,自然素樸,凝練極簡。我們看《考問》:“爺爺,你整天寫什么呢?”“我在寫信呀。”“寫信干什么?”“把一些事告訴別人。”……爺孫倆的對話極其簡單,極其樸素,再平凡再日常不過了,類似這樣的話語表達比比皆是。我們再看另一篇《極致》:
一個年輕人問老王:“您氣急了,想干什么?”
“想笑。”老王回答。
“您高興到極點,想干什么?”年輕人又問。
“想死。”老王回答。
“您恨極了想殺人嗎?”
“恨極了,恨極了想吃一客高級冰淇淋。”
“您愛到極點呢,您愛到極點會有什么愿望?”
老王于是閉上眼睛,用手示意,令那個提問題的人退去。[12]121-122
《極致》的表達自然隨心、精簡至極。小說主人公老王的回答不加渲染,沒有拐彎抹角,沒有華麗的辭藻,其字句里彌散的禪宗意味,給讀者留下許多回想的空間。我們知道,世間許多事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那如何意會?王蒙曾說過:“靠了悟,靠感覺,靠直覺,靠聯想。”[1]57所以,王蒙在微型小說創作時,注重通過文本去啟發讀者領悟。啟悟首先從敘事表達開始,越接近口語,越素樸真實;越接近自然,越隨心天成;越凝練簡潔,越意味悠長,這也契合了禪宗話語的表達特征,“禪宗應答,往往以少勝多。在他們看來,以不答為答,以少答為答,可以隨便聽者馳騁想象,答得越少,規定性越小。”[8]由此可知,敘事語言愈簡潔,就愈能給讀者留出空間去揣摩、思考、領悟。當然,極簡的表達需言簡而意豐,非言簡而意空。品讀王蒙微型小說,其問答式敘事修辭極富禪宗意味:“您氣急了,想干什么?”“想笑。”“您高興到極點,想干什么?”“想死。”(《極致》) “那您干嗎悶得慌呀?” “一個人,不悶得慌嗎?”(《考問》)“你說的是什么歌?”“我忘了。”(《老歌》) “那你干嗎老問我干嗎呢?”“我不問您干嗎,您讓我干嗎呢?”(《反問》)王蒙在小說人物的一問一答中給讀者制造一個個禪機,讓讀者在看似不平衡的修辭表象下去尋找內在的平衡,從而達實現對世事的領悟和自我的飛升。
二、懸念式敘事修辭
懸念式是指文本為激活讀者期待、參與心理而發問的敘事修辭范式。微型小說因篇幅短小,其敘事容量不能與中長篇小說同日而語,這就給微型小說創作帶來極大的挑戰,如何在有限的文字里把一個場景、一個事件講述得精彩動人,發人深思?這就需要靈活、巧妙、多變的情節構思。構思越精巧,越能體現微型小說獨特的審美趣味和藝術力量。王蒙微型小說創作重視敘事的內在機理,他認為,小說的敘事必須是有意義的,哪怕是微型小說,雖然只是生活的某個場景、某個瞬間,也是“一種機智,一種敏感”[3]192,甚至是“一種智慧”[3]192。他會帶著讀者“像觀賞一個風景點一樣地去‘穿行’一個故事。”[3]201可以說,他的每一篇微型小說都是一個別樣的風景點,他善于利用問句設置多變的敘事懸念,以此喚起讀者的文本參與意識和自我反思意識。王蒙微型小說的懸念設置主要有以下三種情形:
一是篇首懸念。篇首懸念出現在文本開頭。如《快樂與不快樂》的開篇:老王老了以后常常問自己:什么是快樂?什么是不快樂呢?《年紀》的開篇:老王和朋友們討論年紀究竟意味著什么?《談天》的開篇:老王星期六深夜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里的一個女聲一上來就說:“哎,老同學,你猜猜我是誰?”……從敘事修辭策略講,篇首懸念在故事的引入上有先聲奪人的效果,一個問句,就把讀者的好奇心理與期待心理引逗起來,作者的“思”境被打開,塵封的經驗被喚醒,到底“什么是快樂?什么是不快樂呢?”我們看看作品《快樂與不快樂》:
老王老了以后常常問自己:什么是快樂?什么是不快樂呢?
老王還愛問,誰有權力判斷一個人——比如他老王,該不該快樂呢?一個人的快樂權是屬于他自己還是屬于某個新出爐的哲學博士呢?
老王還想,一個悲憤的人是不是有權力要求旁人一定要和他一樣地痛不欲生呢?
一個快樂的人是不是須要為世界上乃至他的身邊還有不快樂的人而慚愧,而受到良心的責備呢?
老王給一位老朋友打電話,互致問候,當老王說到自己去了桂林,逛了漓江和七星巖之后,朋友埋怨道:“瞧你還玩呢,我這里,一家子住院……”
老王慚愧無地,覺得是自己太輕狂了,這么大歲數了,你就忍了算啦,還快樂什么?
……[12]102
在懸念的激發下,作家與作者因一個“快樂”的主題被系聯在一起。“快樂”是生活交際的一個高頻詞,《現代漢語詞典》對“快樂”的解釋是:感到幸福和滿意。什么會讓我們感到幸福和滿意呢?我們常常在節日時向親人朋友問候“快樂”,“快樂”成了人與人交際中最美好的祝愿,其樂融融,豈不快哉?我們的先哲孔子在《論語》一開篇就說“樂”:“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說”通“悅”,就是快樂的意思。孔子重視“樂”,這是儒家倡導的一種精神境界,也是人生的第一要義。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中也如是說“樂”:“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與宇宙天地同樂,何等遼闊,何等暢達的“樂”!“樂”是人生的終極追求,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常常會有“不快樂”的羈絆,人生因此有了矛盾、沖突與煩惱。王蒙是機智的,他在一開篇就設置兩個對立的懸念,這種雙線并行的修辭策略,可引發讀者對問題有更深入全面的認知與思考,《快樂與不快樂》在篇首借由“問”為文本提供一個引發讀者關注的敘事主題,進而“設身處地地進入作者的思境和視界”,并“重建一種可以兼容相反解讀的客觀意義領域。”[9]這個開放的意義領域,激活了讀者的心理參與,當文本第一瞬間進入視野時,讀者會有一個短暫的思考停留,他也會在內心問自己:我們常常說快樂,為什么我不曾思考過?到底什么是快樂?不快樂的體驗也常有,我們是否找尋過其中的緣由?日子如流水一般消逝,我們可曾好好思考過生活的意義?帶著期待與思考,在品讀下文時,讀者的經驗與作者的經驗就會慢慢融合,并最終獲得自己對“快樂”與“不快樂”的價值判斷。王蒙是睿智的,他運用懸念這一敘事修辭策略,開篇發問,以問促思,層層導入,水到渠成地引導讀者反思人生。
二是篇中懸念。篇中懸念出現在文本中間部分。其作用與篇首懸念不同,篇中懸念注重敘事結構的銜接,注重敘事氣氛的營造與烘托,微型小說雖然情節單純,但恰切運用懸念,也一樣可以獲得出奇制勝的修辭效果。就以《電梯》為例。
老王上電梯,發現一個陌生的青年。
青年先老王下了電梯。他問電梯工:“誰?”
電梯工答:“不知道。”
他是誰呢?
你管他是誰呢?
如果他是小偷呢?恐怖分子呢?
如果他不是呢?如果他只是一個客人,某個住戶的新成員,或者人壽保險推銷員……呢?
有物業,有保安,有電梯工,有110、112、派出所、武警……他們都會負擔起保衛居民的責任的,老王如果不是吃飽了撐的,何必操心陌生人是誰呢?
然而他還是忍不住想:“他是誰呢?”
……
他覺得自己的腦子亂了,癡了,呆了,病了。他有點驚慌 。
這時太太讓他到物業管理處繳納水電煤氣保安與清潔費用,他的腦子一下子就清醒了。[12]230-231
“他是誰呢?”從這個懸念開始,我們的心理預期就指向了一個明確答案,可小說結尾出人意料,沒有給出“他是誰”的答案,而是巧妙地把筆鋒一轉:太太叫去交各種費用,主人公老王一下子清醒了。原來“他是誰”只是老王無端的臆想。《電梯》顛覆了傳統情節的敘事模式,文本沒有關于“他”的具體事件、經過、結尾,沒有讀者所期待的邏輯結果。文本的懸念都是在老王一次次的臆想中產生,我們看第一次臆想:“他是誰?”這是警覺,是好奇,一個陌生人出現,總想知道他是誰?對于這一懸念,老王淡然化解了:“你管他是誰呢?”可老王沒有釋然,他的意識里又萌生出第二次臆想:“如果他是小偷呢?恐怖分子呢?”老王不安,老王擔心,他可以想象出小偷入室行竊的場景,想象恐怖分子屠戮的畫面,老王的擔心也許有道理,中國不是有句老話——“防人之心不可無”嗎?有備無患總是好。但是,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老王對社會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老王不能確定自己的判斷準確否,萬一想錯了呢?于是老王又制造出第三次臆想:如果他不是呢?老王在臆想的世界里糾纏著,對抗著,撕裂著。他試圖找到答案,可終究找不到答案。太太一聲呼喚,終于驚醒了“夢中人”,老王頓時由臆想之境進入現實之境,故事戛然而止,留給了讀者余韻悠長的思考:一切煩惱由心造,放下雜念,放下憂慮,身心自然輕松愉悅。《電梯》巧妙利用主人公的幻象制造懸念,巧妙置換虛實時空,在逆轉讀者的心理預期中收獲出其不意的修辭效果。
三是篇末懸念。篇末懸念在小說結尾。如:“當然,老王的作品不僅被剪切和轉移了,也被粘貼和展示了。要不,你們說,老王的小說跑到哪兒去了呢?”(《剪切》)“這怎么可能呢?難道我傻了嗎?這個洞到底是什么時候出現的呢?他覺得難以理解。”(《冷風》)“老王不懂,這究竟意味這什么?哪里都是熟人,哪兒都是熟事兒,跟誰都有過交往,與大家都有緣分,什么人和事都與記憶有關……吉乎兇乎?喜乎悲乎?欣慰乎?失落乎?”(《不期而遇》)篇末懸念敘事修辭要依托上文語境,同時,也要依托讀者的想象、聯想、推理等心理機制。從敘事策略看,篇末懸念延展了文本的敘事空間,也打開了讀者的心理空間。以小說《約會》為例。
老王與多年不見的老朋友約好十五日到郊外一家公園會面,老王十分激動。結果他記錯成十四日,提前一天就到達了那座公園等了一個小時。等了半天,老友沒來,老王悻悻地回了家。
回家翻了翻日記本,明白是自己記錯了時間,不免嘆息自己糊涂。
接著他猶豫起來了,第二天還去不去呢?再跑一趟,花上幾個小時,太過分了,見老朋友固然重要,跑兩次郊區沒有必要。故人相會,無非是那一點心意,那點心意頭一天已經表達出來了,再跑郊區反而有點多余。如果不去呢,也顯得有點荒謬,在錯誤的時間去了,并以此為理由拒絕在正確的時間去赴約,又不符合邏輯。
那么,去不去呢?[12]264
《約會》的巧妙就在結尾的懸念,如果沒有結尾懸念,這個故事就黯然失色。小說情節很簡單:老王因記錯和朋友約會的時間,白跑了一趟,那么,在約定的時間里去見朋友還是不去?作家沒有給出答案,而是留下一個懸念讓讀者解開。在懸念語境里,讀者的身份發生了轉變,由原來文外的旁觀者變為文內敘事的參與者,小說未完結的故事需在讀者的想象、聯想、分析、判斷中完成。那么,如何完成呢?我們先對主人公老王的猶豫作個分析,老王在白跑一趟之后,內心也作了一番斗爭,思考結果是:第一,路遠,不想再跑一趟且不必要。第二,老友相會貴在心意,心意到了情誼也就到了,不用特意再跑一趟。從情感層面說,老王的兩個理由不無道理。王蒙說:“人的感情其實也是一個或一組雜多的統一,是相悖而又相成的整體,感情也需要一個合理的架構、合理的分布、合理的配置。”[1]159老王對自己的猶豫選擇了“合理的架構”,他認為,感情貴在情,“故人相會,無非是那一點心意”,只要誠意傳達了,其他的便都是浮云。王蒙在《“友誼不必友誼”》一文中說:“友誼永遠是雙向的自然而然的,不需要表白也不需要證明的,不需要培養也不需要經營的。”[1]212-213小說主人公老王的思想就是作家王蒙的折射,老王的感情邏輯也讓我們反思:注重裝飾的友情,是真友情嗎?友情的本質是什么?可是,人是復雜的,是理性與感性結合的高級物種。因為與朋友有約定,所以,老王在情感上說服了自己,卻不能在理性上說服自己,與故人有約定,豈能違約?雖然約定只是口頭的,但也是有效力的,如果人際交往都要變成白紙黑字的契約,那朋友也失去存在的意義,所以老王是否守約成了解開問題密碼的關鍵?而作家把這個關鍵拋給了讀者,讀者要依據自己的經驗、認知來續接故事,那么,讀者會作出什么樣的選擇?也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因為每一個讀者都有自己的友情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去還是不去呢?”從另一個層面上也給讀者一個警示:當理性與感性發生沖突時,我們該如何面對?如何抉擇?一個沒有結果的懸念給予了讀者更大的思考空間,這是王蒙的智慧,他把敘事權交給讀者,讓讀者在判斷、選擇中領悟人生的真諦。
三、激問式敘事修辭
激問式是指運用激問建構文本的敘事修辭范式。激問是設問的一種。什么是設問?陳望道先生在《修辭學發凡》這樣表述:“胸中早有定見,話中故意設問的,名叫設問。這種設問,共分兩類:(一)是為提醒下文而問的,我們稱為提問,這種設問必定有答案在它的下文;(二)是為激發本意而問的,我們稱之為激問,這種設問必定有答案在它的反面。”[10]基于陳望道先生的界定,復旦大學吳禮權教授對激問的心理機制作了進一步闡釋,他認為,激問是“表達者在某種激情狀態下意欲凸顯自己的某種情意并希望接受者與自己達成情感上的共鳴,是表達者有意識地強化接受者注意的產物”[11]114。因此,激問修辭備受王蒙青睞,它可以洋洋灑灑、一瀉千里,也可以一語中的、發人深省,還可以委婉針砭、潤物無聲。在王蒙微型小說中,激問敘事修辭主要有以下兩種方式:
一是單句激問。單句激問主要用于文本結尾,其修辭效果的生成需依附上下文語境,上文語境是文內語境,它是激問的鋪墊,下文語境是讀者參構的語境,是激問的目的指向。激問鏈接上下文語境,拓展了文本敘事視界,在這個視界中,讀者可以直視內心,思考反省。以《秋與夏》為例。
老王發表感想說,他最喜歡的季節是秋天,秋高氣爽,頭腦清晰,果實成熟,植被斑斕,治學求知,事半功倍,讀書散步旅行回憶思考勵志感懷……無不相宜。
他引用名人名例說,俄羅斯偉大詩人普希金最喜歡的就是秋天,許多文藝大家都是秋天出生的。
而現在,老了老了,老王更喜歡的是夏天,草木蔥郁,鳥蟲歡騰,雷雨云電,紅霞彩虹,生命舒展,血液沸騰,盡情暢快,臉色彤彤,衣裳甚少,腳步甚輕,彈琴長嘯,如虎如龍,風、雨、日光,浴遍身心,天人合一,天下太平……嗚呼,從喜秋到戀夏,不亦宜乎!
同伴說:“那是因為你們家安裝了海爾或海信或春蘭牌空調。”
老王沒了脾氣,人文精神失落到這步田地,您還說什么呢?[12]128
“老王沒了脾氣,人文精神失落到這步田地,您還說什么呢?”小說結尾的激問表達的意思在其反面:人文精神失落到這步田地,沒什么可說的!作家不用陳述句式表達,而用激問的方式來表達,其敘事修辭效果顯而易見:首先,激問在表達作家情感上比陳述句來得強烈;其次,激問在引發讀者思考方面也比陳述句有力;再次,激問的敘事延展度比陳述句廣。另外,激問在具有表達優勢的同時,給予讀者的心靈沖擊也更大。在科技迅猛發展的今天,手機、電腦、空調、電視以及各種電子產品正慢慢吞噬著人們的情懷:一機在手,同桌吃飯可以不言不語,交流的樂趣少了;打開電視,世界景象盡在眼里,出游的樂趣少了;打開空調,四季溫度自由掌控,享受風雨日光的樂趣少了……時代在進步,人的精神世界卻變得荒蕪,許多人可以沒有書,沒有“草木蔥郁,鳥蟲歡騰,雷雨云電,紅霞彩虹”,可不能沒有手機,一部手機,讓多少人忘記了抬頭仰望天空飄飛的云朵,讓多少人忘記了駐足欣賞花開花落……“人文精神失落到這步田地,您還能說什么呢?”當個人的體驗與作家體驗融合時,我們讀出了激問背后的酸楚、無奈、失落,也讀出了作家的憂患:該如何拯救失落的人文精神?我們需要反思,需要從更多的作品中反思:“于是老王不再考慮時機,干脆胡亂買上一個用吧。他想,難道最好的時機不就是現在嗎?”(《時機》)“老王不明白,故事,不都是人‘瞎編’的嗎,怎么別人編則可,他編就不行呢?”(《故事(又一)》)“但是老王還是覺得老趙挺可愛,起碼是挺樂觀挺吉利,你只要不過分相信他的話,他不是既令自己愉快又令旁人愉快嗎?”(《吹牛》)每一次激問都凝結著作家對生活的思索,這些思索將指引我們走上“明朗”之途,去找尋失落的初心。
二是鋪排激問。鋪排激問是三句或三句以上激問句的并置使用。從語言上看,鋪排激問可以使表達語脈貫通,一氣呵成,更具沖擊力與感染力;從表意上看,鋪排激問可加強敘事的情感張力,給讀者更多思考與回想的空間。例如:
(1)老王窮追不舍,他問:“難道說,瓜子是自己飛過來的?是床縫里長出來的?是氣功大師發功用意念移動過來的?要不就是大便里夾帶的了?”(《瓜子》)
(2)老王思前想后,不明就里:此之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乎?此之謂說易行難乎?此說明他老王只能當幕僚不能當首長乎?此說明他老王是思想者不是實行者乎?此說明他下起棋來患得患失,思想包袱太重,影響正常發揮,而支起招來天馬行空,智慧超常乎?(《智慧》)
(3)老王想問:沒有特殊收入,你就不預留一些醫療費用了嗎?你不準備改善一下住房條件了嗎?你不考慮其他的天災人禍了嗎?你的親友對于你這樣舉家游歐洲,就沒有什么看法嗎?您不認為您的愛國主義有什么問題嗎?去不去歐洲當真有那么重要嗎?不喝法國干紅而喝二鍋頭,不吃荷蘭芝士(干酪)而吃北京麻豆腐,不買德國望遠鏡而聚精會神地看電視特寫鏡頭,究竟有何不可?心理醫生是否認為您的心理平衡沒有出現什么問題呢?(《舉家出游》)
例(1)連用四句激問,例(2)連用五句激問,例(3)連用八句激問,層層鋪排,氣勢豪邁,震人心魄,發人深省。激問在語勢上的緊逼緊問,加快了文本的敘事節奏,伴隨著快節奏的意識流動,讀者的思維也被激活,與作家一起追蹤迷惑的人生問題:“老王在床上發現了一粒醬瓜子。老王奇怪,他從來沒有吃過瓜子……他太太聲明說絕對沒有在老王的床上吃過瓜子。”(《瓜子》)于是就是有了例(1)戲謔滑稽的窮追不舍以及窮追不舍后的頓悟。例(2)老王的思前想后緣起他“退休以后,時有空閑,便也下起象棋來。他是逢棋必輸,百戰百敗。然而,當他觀別人之戰的時候,常常是一目了然,洞悉全局,胸有成竹,妙招出人意料。”(《智慧》)老王對此感到納悶,不明就里,一連串的激問噴涌而出,他極盡可能搜索答案,似在反思自己,更是在譏諷人性。例(3)豪邁的鋪排,句句直指現實,小說主人公老王其貌不揚的同學老霍舉家歐洲游,在各國購買的“洋貨很有些光彩奪目,老霍一家子也顯得有點得意洋洋。” “老王旁敲側擊,東問西詰,左顧右盼,陰陽五行,無非是想弄清老霍為何能出巨資出國旅游。”(《舉家出游》)老王的一個個困惑真實地反映出中國人傳統的生活思維,要未雨綢繆,要居安思危,要安居樂業,要知足常樂……盡管老王疑惑重重,挖空心思,但他“各種問題涌到嘴邊,卻一個也沒有說出來”。(《舉家出游》)小說結尾一個反轉,全然顛覆了上文的鋪陳敘事,這巧妙的一筆讓我們幡然醒悟:要好好審視當下生活,審視內心缺失的精神追求。這就是鋪排激問的敘事修辭力量。
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問句敘事修辭是作家王蒙創作的文學存在,他以自己的“思”喚醒讀者的“思”,在“思”中,“光明的智慧和智慧的光明將永遠陪伴!”[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