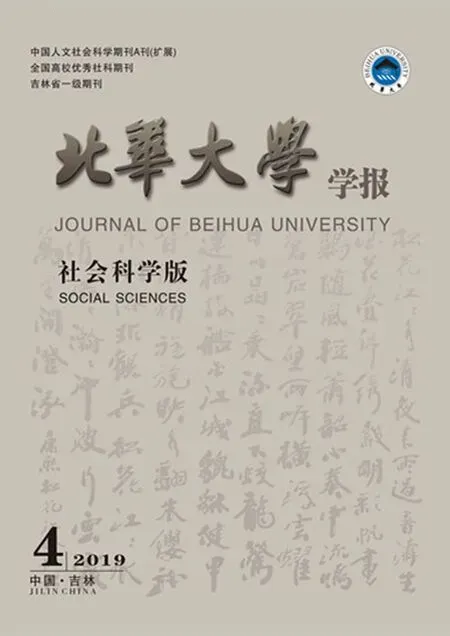中美民事判決承認與執行中的互惠原則
劉寧元 閆 飛
外國法院判決的承認與執行問題關乎涉外民事關系的法人及自然人主體能否最終實現判決內容,是整個國際民事訴訟程序的歸宿。[1]
根據國際法的主權原則,外國法院做出的司法裁判并不當然地在內國發生同等法律效力。因此,外國判決[注]本文的研討范圍僅限于外國法院做出的判決、裁定在內國司法機關得以承認與執行的問題,并不展開討論外國法院做出的判決與裁定在國內申請承認與執行的程序中可能存在的細微差別,因此文中出現的外國法院做出的“判決”通常指代相應的“判決與裁定”。在內國的承認與執行需要依賴國際間的司法協助。除了純粹依據國內法執行外國法院的判決之外,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的實現主要通過國際條約或根據互惠原則進行。通過國際條約承認與執行外國法院判決相對穩定、可期待性高。旨在實現此目的的國際條約較早便已經出現,早期有1869年法國和瑞士簽訂的司法協助條約,[2]1928年拉丁美洲國家制訂的布斯達曼特國際私法典之專門規定,1932年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哥本哈根公約,1961年,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三國簽訂了有關執行判決的多邊條約等,[3]盡管如此,當今世界并沒有一個洲際層面關于外國法院判決承認與執行的國際公約。最接近這個目標的是1971年2月1日《關于承認與執行外國民事和商事判決的海牙公約》(Convention of 1 February 1971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但因其締約方很少,該公約無法發揮預期作用。
因此,互惠原則成為國際法實現外國法院承認與執行的重點方向。互惠原則是一項歷史悠久的國際法原則,其擁有豐富的理論研究成果,相關理論學說可以追溯到國際公法及國際私法理論之始。盡管如此,從實踐領域關于互惠關系認定的案例卻乏善可陳,中國法院更是鮮有相關公布案例。在本世紀第一個10年之前,中美之間甚至沒有任何承認對方法院民商事判決的成功案例。
2017年6月30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互惠原則裁定承認和執行一項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高等法院做出的金錢給付判決,該案是中國法院承認與執行美國法院民事判決[注]本文不討論中國《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544條中當事人向中國法院申請承認外國法院做出的發生法律效力的離婚判決的特殊情況,因此不對離婚判決司法協助案例進行列舉。的“第一案”。該案中,人民法院認定中美之間存在互惠關系并據此最終裁定承認并執行美國法院判決。中國法院在該案中認定互惠關系存在的關鍵原因是2011年3月29日美國法院曾首次承認中國法院做出的民商事判決。其后,2017年10月27日美國法院再次承認中國法院民商事判決。[注]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Central District of California,QinrongQiu v.Hongying Zhang et al.,CV 17-0546-JFW(JEM).從上述3個案例中能否推定互惠原則已經在中美之間順利適用?該問題需要從互惠原則基本理論以及具體實踐案例的法律分析中具體研討。
一、互惠原則基本問題
(一)互惠原則的概念
現代意義上的互惠(reciprocity)一詞普遍用于商業、外交及社會領域。互惠原則,也稱互惠關系原則,早在薩維尼的“法律關系本座說”中就有體現。薩維尼從各國民族和個人的利益實現角度出發,認為應當采取互惠原則處理各國間的法律關系。胡伯的“國際禮讓說”認為在其本國主權及臣民的利益不受損害的前提下,應當相互尊重各自國家的法律及其域外效力。[4]
盡管互惠原則是國際法中歷史相對悠久的一項原則,針對該原則的是,是否應當被外國法院判決承認與執行領域采納的問題,理論爭議長期以來并未停止,這也是其無法成為被世界各國所普遍采納的原則的主要原因。根據各國對互惠原則的采納態度之程度,各國的立法模式有:完全采納、部分采納和不采納三種。完全采納互惠原則立法模式的國家以日本、中國臺灣地區、美國少部分州等為代表,其特征是對于外國法院的判決不區分外國判決的具體類型而根據互惠實踐進行承認與執行。部分采納則以德國、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為代表,從原則上大部分采納互惠原則,但是在承認與執行一些特殊領域的民事判決時則不以互惠關系的存在為承認與執行的前提,特別是婚姻關系的人身關系部分,中國的立法模式也采取類似做法。不采納互惠原則的立法模式以法國、美國大多數州為代表,其主要受到互惠原則批判理論的影響。互惠原則的批判原理由美國富勒法官在希爾頓案中較早提出,其認為互惠與報復并無本質區別,應當由政府采取而不是法院。
誠如前文,美國大多數州已經摒棄了通過互惠原則承認與執行外國法院判決的立法,其背后的原理是從美國的角度看,除非根據美國簽訂的國際條約,使美國公民在海外面對潛在的不公正審判是對美國無益的。[5]美國統一法委員會(Uniform Law Commission)在其前身美國統一州法律委員會(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 State Laws)1962年版本的基礎上于2005年頒布了改版《承認外國金錢判決統一法(Uniform Foreign Money-Judgments Recognition Act,UFMJRA)》,[6]《承認外國金錢判決統一法》系統性地規定了外國法院判決承認與執行,盡管《承認外國金錢判決統一法》并未納入互惠原則或禮讓原則(doctrine of comity),但是明確了美國法院承認與執行外國法院判決的原則,例如承認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保留原則等。[7]截至2017年,美國21個州及哥倫比亞特區使用《承認外國金錢判決統一法(2005)》,其他12個州及維京群島內《承認外國金錢判決統一法(1962)》生效。
(二)互惠原則應用原理——以國際法制為始,以國內法制為終
前文提及,外國民事判決承認與執行的問題屬于國際司法協助的范疇,然而當互惠原則成為促成此類國際司法協助得以落實的法律依據時,則通常以國際法制為始,以國內法制為終,[注]本文所指稱的國際法制包括國際條約、國際慣例、國際法一般原則等明確具體的國際法淵源,國內法制是指主權國家的國內法律制度。其具有顯著的國際私法特征。例如根據中國《民事訴訟法》第281、282條之規定,在處理外國法院判決承認與執行申請或請求時,人民法院應當首先依照中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進行審查,這里的國際條約即國際法制的范疇;其次按照互惠原則進行審查,因此,落實到實踐中的互惠原則其本質還是中國國內法所規定的一項原則。
盡管互惠原則在外國法院判決承認與執行實踐的國際法理論體系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其具體實踐操作卻乏善可陳。因為互惠承認外國法院的判決最終需要落實到國內法治范疇,為了實現真正的雙邊互惠原則適用,則相對雙方國家從立法模式上應當采取同樣(至少可比相近)的立法模式。從下文將要分析的中美案例中,中美兩國的法律制度和司法體系大相徑庭,其兩國間相互采取互惠原則進行判決承認與執行的司法借助從邏輯上看很難穩定成立,極有可能出現“單邊互惠”的情況。
二、中美相互承認與執行民商事判決實踐案例
(一)湖北三聯案[注]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Central District of California.D.C.No.2:06-cv-01798-FMC-SS.Florence-Marie Cooper,District Judge,Presiding.——美國法院承認與執行中國民商事判決首例
1.案情要述[注]Hubei Gezhouba Sanlian Indus.Co.v.Robinson Heli-copter Co.,2009 U.S.Dist.LEXIS 62782 (C.D.Cal.,July 21,2009)
1995年3月14日,湖北葛洲壩三聯公司(HUBEI GEZHOUBA SANLIAN INDUSTRIAL,CO.,LTD.,下稱“三聯公司”)其前身與湖北平湖旅游船公司(HUBEI PINGHU CRUISE CO.,下稱“平湖公司”)于美國洛杉磯高等法院(Los Angeles Superior Court)起訴美國羅賓遜直升機公司(ROBINSON HELICOPTER COMPANY,INC.,下稱“羅賓遜公司”),訴稱羅賓遜公司生產的R-44型號直升機于1994年3月22日墜入中國長江,并主張羅賓遜公司根據過失、嚴格責任及違反默示擔保而承擔原告的經濟損失。在洛杉磯高等法院案件中,法院在獲得羅賓遜公司同意時效中止并遵守中國法院判決的前提下,支持其主張美國法院是本案不方便法院(forum non convenience)的動議(motion),并終止美國案件的審理。
2001年1月14日,三聯公司、平湖公司以羅賓遜公司為被告向中國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訴請與美國洛杉磯高等法院類似。該案經過漫長的送達過程[注]中國與美國都是《關于向國外送達民事或商事司法文書和司法外文書公約(海牙送達公約)》的締約國。于2004年3月25日開庭審理。被告羅賓遜公司并未采取審核措施參與庭審,亦未向法庭提出延期審理。經過當事人舉證及法院調取證據,三人合議庭于2004年12月10日對本案做出一審判決,判決主要認定:本案訴訟相關文件已經依法送達,該法院有管轄權,羅賓遜公司因其產品生產缺陷應當承擔墜機事故責任,并判定被告賠償兩原告造成的經濟損失。判決做出后于2004年4月20日送達。在2005年5月11日,羅賓遜公司致信中國司法部反對(object)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判決但并未提出上訴或延期上訴,判決(下稱“中國法院判決”)生效。
2006年3月24日,三聯公司、平湖公司仍以羅賓遜公司為被告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中區地區法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Central District of California)請求根據并入原《加州民事訴訟法(California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Sections)》的《承認外國金錢判決統一法》執行中國法院判決。2007年3月22日,美國地區法院做出簡易判決(summary judgment)支持被告主張,及本案于原告在中國起訴前已過訴訟時效。
2008年7月22日,針對初審法院的判決,原告訴至美國上訴法院,美國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Ninth Circuit)認定本案不受訴訟時效限制,理由是:其一,在1994年案件中,因被告同意時效中止為條件(condition)而認定了美國洛杉磯高等法院為該案的不方便法院,加利福尼亞州訴訟原地中止(forum non convenience stay of the California State Action remained in place)。其二,法院沒有理由據以認定執行中國法院判決會違反加利福尼亞州針對失效請求的公共秩序(California’s public policy against stale claims)。該案發回初審法院審理。
2009年7月21日,發回重審的案件經加利福尼亞州中區地區法院重新審理判決承認并執行中國法院判決。其一,中國法院判決案件的送達程序符合《海牙送達公約》。其二,中國一審法院判決根據《中國民事訴訟法》規定在上訴期過后成為終局、決定性和可執行的中國法下的判決。其三,中國法院判決沒有《承認外國金錢判決統一法》規定的例外情況。
盡管其后羅賓遜公司再次向美國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提起上訴,2011年3月29日,該法院仍然維持了初審法院的判決,承認執行中國法院判決。
2.法律分析
在美國法視角下,主要有兩種“外國”判決。第一類是美國一州針對美國其他州的判決而言,這類判決根據《美國聯邦憲法》的第4條得到承認與執行,不是本文研究的范疇。第二類是我們通常討論的來自美國之外的國家之法院做出的判決,其承認與執行的司法、立法及學術討論實際上始于1895年格雷法官(Justice Gray)在Hilton v.Guyot案中的意見。盡管沒有統一的承認與執行外國法院判決的立法,但是誠如前文提及《承認外國金錢判決統一法》已被美國大多數州的立法所采納而編入(codify)其法律體系。
除了申請承認與執行判決標的類型必須是給予或拒絕金錢給付義務之外,從本案最終判決中,美國法院在審查是否應當承認外國法院判決時主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1)程序公正,即各方當事人是否獲得了妥善的司法程序權利。具體到本案,加利福尼亞中區地區法院重點考察了本案的送達是否符合《海牙送達公約》的要求。(2)管轄權適格,即做出待執行判決的外國法院是否就該案擁有管轄權。本案有一項突出的特點在于其最初是在美國法院開始的,美國相關法院根據當事人的申請和不方便法院原則中止了其案件審理,并待有管轄權的“方便法院”即中國法院審理。在審理承認執行案件的過程中,美國法院仍然再次按照美國法對中國法院判決做出的法院擁有事項管轄權(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和屬人管轄權(personal jurisdiction)進行了再次確認。(3)外國法院判決效力。首先,美國法院考慮判決做出與生效是否符合《中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其次,美國法院同時關注該中國法院判決是否是針對該事項唯一的生效判決。(4)公共政策(publicpolicy)。在本案的審判詞中可以窺見,針對公共政策,法官并不是一概而論地推演,而是例如“加利福尼亞州針對失效請求的公共秩序(California’s public policy against stale claims)”這樣細化的具體方面的公共秩序問題。(5)非欺詐取得。本案不涉及相關情況。
值得一提的是,本案的全過程中對于執行中國法院判決是否符合互惠原則并未論及,亦未分析中美兩國之間在金錢給付判決或民事判決的互惠關系。同時,雙方當事人也未就互惠問題進行舉證或者抗辯,其原因在于作為裁判依據的《承認外國金錢判決統一法》已經取消了互惠的要求,同時美國采納大多數州也取消了互惠的規定。[7]與此同時,如果美國法院需要在裁判申請執行外國法院判決的案件中納入互惠原則,則鑒于中美之間尚無(除確認離婚案件)“第一案”,且中國當前的立法將互惠關系存在作為承認與執行外國判決的原則,則從邏輯上看中美之間將永遠無法通過互惠原則實現判決的相互承認與執行。
綜上,美國法院可以被認為是單純根據其國內法所做出的裁判,并不考慮判決法院的所屬國的任何法院的實踐歷史。從本案的美國司法實踐看,其并沒有從主觀上考慮到中美之間民事判決相互承認的“互惠關系”因素,然而該判決作為“美國法院承認中國法院民事判決首案”卻成為其后中國法院相關案例認定中美兩國在該領域互惠關系的決定性因素。
(二)劉某案——中國法院承認與執行美國民商事判決首例
1.案情要述[注]中華人民共和國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2015)鄂武漢中民商外初字第00026號。
中國籍公民劉某與陶某于2013年9月22日通過簽訂1份“股權轉讓協議”的形式擬將陶某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注冊成立的Jiajia Management Inc.之50%股權轉讓給劉某,協議簽訂地點為美國。協議簽訂后,劉某分多次通過銀行轉賬的形式向陶某及其丈夫童某匯款。后劉某以陶某、童某二人利用虛假股權轉讓獲取其錢款為由,于2014年7月17日向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高等法院提起訴訟。該案經過委托送達及公告送達相關法律文書,并于2015年7月24日做出缺席判決支持劉某訴訟請求,判令陶某、童某退還已經收取的錢款并支付相應利息及費用。劉某于美國辦理了后續的判決登記手續(下稱“美國法院判決”)。
2015年10月19日,劉某以陶某、童某為被申請人在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承認與執行美國法院判決議案,依照《中國民事訴訟法》組成合議庭并于2015、2016年分別組成聽證會對本案進行審查。2017年6月30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1)作為被申請人財產所在地和經常居住地法院,其對本案有管轄權。(2)申請人提供的美國法院判決符合申請和執行外國法院判決的形式要件。(3)美國法院判決“已經證實”美國有承認和執行我國法院民事判決的先例存在,并據此認定兩國相互承認執行民事判決的互惠關系。(4)美國法院判決內容因其系針對商事合同關系做出的,并不違反中國法律的基本原則或者國家主權、安全、社會公共利益。(5)該案經過合法傳喚及送達。(6)該案系司法協助案件,因此不對申請人與被申請人商事合同糾紛的實體問題進行審理。(7)申請人主張的超出美國法院判決之外的金錢給付內容不屬于申請承認與執行外國法院案件審理的范疇,不予支持。據此,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承認并執行美國法院判決。
2.法律分析
在劉某案之前,中國司法實踐中并沒有在國際條約之外單獨適用互惠原則承認與執行的案例。從早前中國法院拒絕承認與執行外國法院民事判決的案例中,可以窺見互惠原則的適用實踐,即互惠關系的消極認定。在五味晃案中,日本公民五味晃向中國法院申請執行日本法院做出的金錢判決,該案經過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并上請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6月獲得最高院復函,復函確認“我國(中國)與日本國之間……未建立相應的互惠關系”,最終執行申請被駁回。在本案中盡管沒有具體分析據以認定中日兩國之間沒有互惠關系的原因,日本國法院亦未有承認中國法院民事判決的司法實踐可能是其中的關鍵因素。然而本案中并沒有能夠體現在互惠關系認定中事實證據所發揮的作用,因為關鍵因素“未建立互惠關系”并非通過當事人舉證或者人民法院查證認定,而是直接由上級/最高級法院做出認定。這個審判邏輯在2003年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受理的一起申請承認與執行德國法院判決案件中得以沿用。
在劉某案的審理中,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并沒有如審理五味晃案的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一樣請示上級人民法院,轉而直接通過當事人舉證的其他美國案件判決即認定中美之間存在互惠關系,其中可以推出判斷,即根據目前的實踐,中國法院對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互惠關系認定是事實問題的認定。
其一,以客觀事實存在為基礎。在互惠關系認定的理論觀點中,長期以來有相對狹義的事實互惠關系認定和相對廣義的法律互惠關系認定的學說法律上的互惠,顧名思義是指通過外國法查明手段考察外國法律與本國法律是否存在互惠,具體考察方式有兩種:第一,外國法律是否與中國法律就同樣的問題有相同或類似規定;第二,假設相同案件在外國法院提請承認與執行,是否可以根據該國法律獲得支持。在劉某案中,(從公布的判決書上看)人民法院并沒有對美國法律進行美國法查明,亦未進行任何推演。因此可以推斷目前中國的司法實踐對于互惠關系的認定是客觀事實認定,即以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中國法院判決的客觀存在為觸發因素。
其二,以審判庭認定為依據。五味晃案中,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并沒有直接對互惠關系問題進行定性,而劉某案中,(根據公開的審判材料)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本案的合議庭是獨立進行判斷的,是獨立行使審判權的體現。由此可見,審判庭將是否存在互惠關系的問題作為一項事實問題進行審理,而不是作為一項法律解釋問題而需要進行司法解釋。
其三,非法律互惠的邏輯。如果從法律互惠角度出發,結合按照劉某案的認定邏輯,美國多數州的法律自始“惠”于中國且普遍“惠”于世界各國的,因為其并未將中國法院存在承認與執行美國法院判決作為其審查承認與執行申請或請求的前置條件。由此可以得出,當前中國法院對于互惠關系的認定以事實為基礎,而非法律假設。
三、認定互惠關系的實踐批判
中美之間的判決承認與執行實踐在近年來相對豐富,湖北三聯案、劉某案以及2017年10月27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中區地區法院再次承認中國法院做出的生效判決,似乎已經形成了一個中美民商事判決相互承認與執行的實踐“閉環”。劉某案處于中美判決相互承認與執行的邏輯中心點,因此也成為中美“互惠”相互承認對方判決的關鍵案例。假設中國法律不采納互惠原則,則中美兩國各自判決在對方國家的承認執行將純粹采取個案審理的原則依據其各自國內相關法律進行裁判,“互惠”的邏輯結構無從談起。
然而,在關鍵案件劉某案的裁定書中,僅有一句相關審判詞,即“經審查,申請人提交的證據已證實美國有承認和執行我國法院民事判決的先例存在,可以認定雙方之間存在相互承認和執行民事判決的互惠關系”。[8]人民法院將“有……先例存在”作為認定互惠關系的充分且自足的條件。如果按照該案審判邏輯,當美國任何一個國內法院有承認和執行我國法院民事判決的判例即可構成互惠關系的認定條件。很遺憾其中并未有深入地分析互惠關系的認定過程以及考慮的因素,筆者認為,在以下方面應當進一步批判性地思考。
(一)單邊或雙邊
單邊或雙邊的問題具體而言是:采納互惠原則本身是否作為認定互惠的條件?互惠原則所認定的互惠關系應當是相互做出且得以反復實踐復制的,這一論點可以從前文引述的薩維尼“法律關系本座說”中窺見一斑,這種互惠最終的落腳點是共同/各自利益的實現,即如果這種反復實踐的循環無從期待,則互惠關系只能是單邊的。
考察互惠原則的價值,應當首先解決“惠”的表意,從司法實踐上看,一國司法機關應當根據其所賴以擁有管轄權的法律體系行使審判權,本身不存在自身的意思表達。而一國法院所屬的國家也不應當通過民事司法判決的形式來進行意思表達。如果該國立法上采納互惠原則,則其前提假設必定是,當相對國依其適用的法律做出一項判決后,則該國必須相應地做出“惠”的表示。那么,如果對方國家本身并不采納互惠原則,則互惠無法雙邊地實現。
具體回歸到美國的情況,誠如前文所述,美國大多數州并不采納互惠原則,湖北三聯案判決承認與執行的加利福尼亞州即為其中之一,這代表中國法院對于美國法院判決的承認與執行并不會作為該州法院審理來自中國法院判決的承認與執行案件中考量的因素,即中美互惠是單邊的。
(二)整體或部分
從互惠關系推定的角度上看,劉某案忽略了部分與整體的關系,即將美國某個法院的判決視為該國司法“惠”的意思表示,而反致“回饋”于美國整體。美國是聯邦制國家,其個州民商事法律制度不盡相同,甚至存在沖突,聯邦與個州的司法體系更不盡相同,中美之間討論互惠原則的運用應當深入討論其互惠關系的認定范圍,作為認定依據的案例來源及其代表性以及未來美國反向實踐的可期待穩定性。
正因為如此,有學者曾經提出應當參照韓國的實踐做法,即按照對美國以各州為對象考察并認定互惠關系。[2]回歸中美實踐,不難發現一個“巧合”,即目前的3個案例中相互承認與執行的案件判決僅在中國的湖北省與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之間,盡管根據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詞可以初步認為其互惠關系的認定是基于中美兩國之間,而非兩國的部分與部分、整體與部分或部分與整體之間的,但是由于其并沒有針對這個問題進行查明或認定,在出現其他地區案例之前,互惠關系的認定范圍仍然存在不確定性。
(三)一貫或中斷
對于互惠關系的認定,應當同時研討互惠關系中斷的可能性。因為美國不是采納互惠原則作為外國法院民事判決承認與執行的國家,如果其法院后續出現拒絕承認或執行中國法院判決的情況,中國法院是否在后續繼續認為互惠關系存在?
如果傾向前者,這意味著互惠關系一旦建立,且無法中斷,這種可能性不符合互惠原則的基本原理。如果傾向后者,則外國判決承認與執行案件的被申請人可以嘗試以此抗辯。如果抗辯發生,中國法院并無從判斷美國法院的拒絕承認與執行案件的原因,然而由于美國不采納互惠原則,美國法院不存在“不互惠”的拒絕承認與執行,只存在根據美國法拒絕承認與執行的情形。在耗費了大量的司法資源進行美國法調研后,其結論也似乎只能是拒絕承認與執行的裁定。
四、結語
綜上,中美之間在民商事判決相互承認與執行的問題上,存在客觀上的相互承認與執行案例,中國法院已經存在認定中美之間互惠關系的生效裁定,而美國做出承認與執行的依據中并未包涵互惠原則,中美之間的互惠關系實際上是單邊互惠。中美之間針對對方法院做出的民商事判決是單向互惠地進行的。涉及相關問題的公布案例仍然較少,中美互惠關系認定的實踐發展有待后續案例進一步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