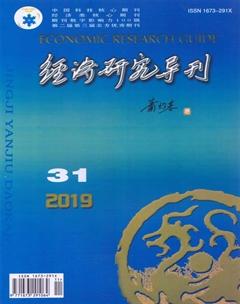行政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的有限性原則
王曉杰
摘 要:行政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制度是2014年修訂的行政訴訟法新規定的法律制度,行政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的范圍、審判方式及審查對象都應遵循有限性原則。行政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只能審查被訴行政行為“依據”的規范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第一批行政規范性文件附帶典型案例中確立審查對象是規范性文件的具體條款,對行政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做了進一步的限縮,但該限縮有待商榷。
關鍵詞:行政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有限性原則
中圖分類號:D925?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19)31-0198-02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發布了第一批行政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典型案例,其中“毛愛梅、祝洪興訴浙江省江山市賀村鎮人民政府行政強制及行政賠償案”(以下簡稱“毛愛梅案”),確立了行政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對象的有限性原則,明確了可以附帶審查的是作為行政行為依據的規范性文件的具體條款。對此,筆者持不同的意見,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的確應遵循有限性原則,審查作為行政行為依據的規范性文件,而不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附帶提起訴訟的所有規范性文件。但審查對象是否應限制為所訴規范性文件的具體條款?筆者認為,這樣的限制違反了立法本意。對行政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的有限性原則的內涵進行討論,有助于解決訴訟實踐中的難題,更好地保護行政相對人對行政規范性文件提起附帶審查的權利。
一、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的有限性原則
《行政訴訟法》第53條確立了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制度。該條規定了行政訴訟原告認為行政行為所依據的國務院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制定的規范性文件不合法的,在對行政行為提起訴訟時,具有一并請求對該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的權利。該條款中對規范性文件的司法審查做出了限定:一是附帶審查而非單獨審查,不能單獨對規范性文件提起訴訟;二是法院只能審查行政行為“依據”的規范性文件;三是必須是原告請求審查的文件,而不能是原告未提起審查請求的文件。這是立法對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案件司法審查范圍的限制性規定,是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有限性原則的具體內容。
二、規范性文件附帶審判方式的有限性
《行政訴訟法》第64條則進一步體現了附帶審查的審查方式的有限性原則。法院經審查認為規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為認定行政行為合法的依據,并向制定機關提出具體的處理建議。法院并未獲得對不合法的行政規范性文件的變更權或撤銷權、廢止權。立法本意并不是授權在司法審查中直接改變規范性文件的效力,而是通過審查行政行為的依據來監督行政行為的違法。如果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僅以被訴規范性文件為依據,則該行政行為依據不合法而構成違法;但如存在其他上位法作為行政行為合法的依據,行政規范性文件的違法并不能影響行政行為的合法性。
根據相關《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的規定,法院認為行政規范性文件不合法的,應當在判決書說理部分指明該文件不合法并闡釋理由,而不是在判據書主文部分認定規范性文件不合法。立法本意是在審查行政行為合法性的目標下,審理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可以發現,行政訴訟法規定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的立法目的是阻卻不合法的規范性文件在個案中的效力,即通過認定被訴行政行為的依據不合法來監督行政行為是否合法。
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制度可以預防由于法院直接援引規范性文件判定行政行為合法而侵害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早在新《行政訴訟法》規定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制度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即通過司法解釋、會議紀要等文件逐步創制了法院對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司法審查的規范。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若干解釋》)第62條規定,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判文書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規章及其他規范性文件。該條規定法院對規范性文件是否“合法有效”的判斷權,并在判斷為合法有效的前提下“引用”。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于審理行政案件適用法律規范問題的座談會紀要》中規定,法院經審查認為被訴行政行為依據的應用解釋和其他規范性文件合法、有效并合理、適當,在認定被訴行政行為合法性時應承認其效力;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理由中對具體應用解釋和其他規范性文件是否合法、有效或適當進行評價。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裁判文書引用法律、法規等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規定》中規定,經審查認定為合法有效的(規范性文件),可以作為裁判說理的依據。該條明確了“審查認定”權及在裁判文書說理部分的引用權限。但是前述三文件所規定的規范性文件的審查權都是在原告并未提起對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的前提下,法院可以審查并引用規范性文件。前述兩部司法解釋產生了續造法律規范的效應,有的法院僅將之理解為賦予人民法院對規范性文件的司法審查權而未按照司法解釋的指引規范用權,于是在行政案件的司法審判活動中出現了人民法院未經審查就將行政規范性文件作為裁判依據予以適用的情形。余軍教授等撰文指出,自2000年《若干解釋》施行以來,截至2015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一共公布14個典型案例涉及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審查,共涉及20個行政規范性文件,法院對其中14個行政規范性文件未經審查就將其作為裁判依據予以適用,占所涉行政規范性文件總數的70%。這種不規范地行使行政規范性文件司法審查權的行為,既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的規定,也不符合相關司法解釋的規范。2014年修訂的新行政訴訟法所確立的附帶審查規范性文件有限性原則有效地對前述司法權行使不規范的問題起到“治亂”作用。未經審查并在判決書說理部分論證合法有效的,不得作為認定行政行為合法的依據。原告只要提出對規范性文件的附帶審查的,人民法院必須在判決書說理部分做出認定并釋明理由,原告通過依法行使訴權可以預防法院未經審查直接援引規范性文件判定行政行為合法而侵害行政相對的人的合法權益的情形發生。行政機關依據不合法的規范性文件做出多個行政行為的,原告只對部分行政行為提起訴訟并一并請求審查行政規范性文件的,經法院審查確認該文件不合法,將阻卻該文件適用于起訴的行政相對人所訴爭的具體行政行為,但并不影響該文件在其他行政行為中的效力。通過訴訟,人民法院只能改變被訴行政行為的效力,而并不能改變規范性文件本身的效力,這是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制度有限性原則在法律規范中的核心體現。
三、行政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對象的有限性
行政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的對象是有限的,僅限于被訴行政行為依據的行政規范性文件。這是由于規范性文件司法審查“附帶”性所決定的“有限性”,更是由于行政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制度的立法目的所決定的”有限性”。何為“依據”?對其認識將決定附帶審查對象有限性原則在司法審查中的具體適用。該討論涉及以下兩種情形:第一種,被訴行政行為在相關法律文書中明確援引了被訴行政規范性文件的。這種情況下,法院的審查對象十分清晰,就是行政機關援引的行政規范性文件。第二種,由于行政機關違法,根本未制作相關法律文書或制作的法律文書中未援引任何法律規范,那原告只能根據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內容來判斷行政機關依據某規范性文件做出了行政行為,但原告將面臨舉證難的問題。因此,法院審慎適用附帶審查對象有限性原則就顯得特別重要。在行政機關未制作法律文書的情況下,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內容與行政行為之間具有法律上的“因果聯系”應當是將行政規范性文件納入審查對象的核心判斷標準。具體包含以下幾種情況:一是規范性文件的制定主體違法。從規范性文件內容所涉行政管理權看,制定主體沒有規范性文件制定權,該文件違法與原告的合法權益具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二是規范性文件的主要內容違法上位法,在上位法之外限制行政相對人的權利或在上位法之外給行政相對人增設義務,該文件違法決定行政行為違法,與原告合法權益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三是規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違法,該文件違法決定行政行為違法,因此文件全文與原告合法權益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針對以上三種情況,法院都應對規范性文件整體審查,而不能僅僅審查規范性文件的相關條款。
“毛愛梅案”判決書指出,原告請求一并審查行政規范性文件,經原告當庭明確系認為該文件第3條第3款不合法,而該條款內容是對生豬退養相關補助的規定,非鎮政府實施強制拆除行為的法律依據,決定不予審查。在毛愛梅案典型案例發布中,最高人民法院的王振宇法官在新聞報道中指出附帶審查對象是“作為被訴行政行為依據的規范性文件的相關條款”。根據司法解釋,對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審查包括了制定主體、制定程序、文件內容等方面是否合法。因此,從立法本意看,不應當將規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審查局限在訴爭條款上。在行政機關未制作文書或未援引法律規范的情況下,假如由于當事人法律技術能力不足,會對規范性文件與行政行為之間有因果聯系的具體條款認識不清。法院應當通過審查,確認有因果聯系的條款為行政行為的“依據”并進行合法性審查。假如發生原告由于法律知識的不足,對與行政行為有因果關系的條款判斷錯誤,但行政機關系依據被訴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其他條款做出了行政行為。此時,法院應當行使釋明權,闡明行政行為所依據的條款,被告違法不做出書面決定的不利后果不應當由原告承擔。在典型判例中確認附帶審查的對象為規范性文件的具體條款,屬于對公民訴權加以限制,對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對象的進一步限制,應當有上位法為依據。“毛愛梅案”法院實踐與制度規范之間產生了明顯的沖突,在上位法之外的過度限制缺乏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