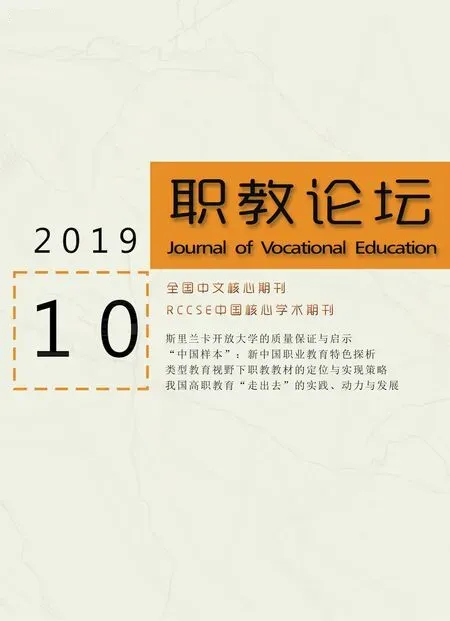TPACK框架下高職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的調查分析
□謝 燕 張棟棟
隨著教育信息化的持續推進和職業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入,高職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作為信息技術與高職教育深度整合的重要關鍵環節,受到普遍關注和重視。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國發〔2014〕19 號)提出:加強現代信息技術應用能力培訓,將現代信息技術應用能力作為教師評聘考核的重要依據。《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國發〔2019〕4 號)指出:要適應“互聯網+職業教育”發展需求,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改進教學方式方法。信息化教學能力是教師以促進學生綜合能力的發展為目的,利用信息技術,整合教學資源,從事教學活動,完成教學任務的綜合能力[1]。本研究擬從高職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現狀調查出發,分析當前高職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水平并提出相應對策建議。
TPACK 框架(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and Content Knowledge)是美國學者Mishra 和Koehler在2005年提出的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法知識,由技術知識(TK)、教學法知識(PK)和學科知識(CK)三類知識要素和四類復合要素組成(如圖1),強調技術、教學法和學科知識的融合、實踐與動態發展[2]。這一理論已被國內外普遍認可為教師開展信息化教學的必備框架。

圖1 TPACK 框架圖
基于上述框架,本研究從信息化教學意識與態度出發,抽取與信息技術相關的四項要素:高職教師信息技術(TK)、信息化教學知識(TPK)、信息化學科知識(TCK)、信息化學科教學法知識(TPACK),對高職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進行調研分析。
一、研究設計
1.研究對象。本研究選取常州、南京、無錫、淮安、蘇州、揚州、泰州、鹽城、徐州、連云港、南通等江蘇省內13 個城市在職高職教師和學生為調查對象,采用抽樣調查的方法,自2018年6月至2018年9月,通過問卷星進行在線問卷發放,系統自動采集篩選數據,回收高職教師的有效問卷134 份、高職學生的有效問卷659 份。調查樣本基本覆蓋高職教師不同性別、年齡、學歷、教齡、職稱、任教類別等多個方面(見表1)。
2.研究工具。本研究選擇黃東明在Archambault和Crippen[3]針對美國在線教師培養設計開發的基于TPACK 框架的量表為設計基礎,借鑒我國《中小學教師信息技術應用能力標準》(試行)(教師廳函[2014]7 號),經提煉要點,從信息技術融入教學意識、教學知識、學科知識、學科教學法知識四個維度制定調查問卷。通過小范圍試測,依據項目分析修改后,利用SPSS 軟件進行信效度檢驗,最終形成調研問卷。問卷包括三個部分,包括個人基本信息、TPACK 各要素測量、信息化環境與教學能力培訓,其中,TPACK 各要素內容問題采用李克特五點量表法設計,選項為完全同意、同意、不確定、不同意、完全不同意,對應得分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分值越高,說明該題對應能力越強。

表1 高職教師調查樣本基本信息統計

表2 問卷的信度檢驗
3.信度與效度檢驗。通過在線SPSS 對本研究量表信效度檢驗,Cronbach α 系數介于0~1 之間,數值越大,表明量表的內部一致性越高,結果顯示問卷總體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40(見表2),信度較好。通過教學督導的調研結果計算效度,KMO 值以0.5 位分界,值越接近1,表明效度越高,本問卷KMO值為0.924,表明本量表效度良好。
4.研究過程。研究選取20 名教師進行試測,對問卷中不恰當的題目予以刪除或修改后確定問卷。依托江蘇省教師培訓、校本培訓和學生管理平臺,面向江蘇省內13 個城市的高職教師和學生通過問卷星發放、收集問卷并進行數據在線統計。
二、調研結果統計與分析
1.描述性統計分析。為了解目前高職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的總體情況,對高職教師信息化教學意識與態度、信息技術(TK)、信息化教學知識(TPK)、信息化學科知識(TCK)、信息化學科教學法知識(TPACK)的均值進行比較分析,結果如表3。
結果顯示,五個維度的得分情況為信息化教學意識與態度>信息化學科知識(TCK)>信息化教學知識(TPK)>信息化學科教學法知識(TPACK)>信息技術(TK)。整體來看,信息化教學意識與態度得分最高,說明絕對多數教師認可信息技術應用于高職教學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信息技術與教學法知識的融合三個維度均得分較低,得分最低的信息技術(TK)標準差最高,說明上述五個維度中,教師的技術與教學融合的能力發展不平衡,不同教師的信息技術的認識情況有較大差異。

表3 高職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4 不同性別的高職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方差齊性分析結果

表5 不同年齡的高職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方差齊性分析結果
2.高職教師在不同性別、年齡、學歷、教齡、職稱、任教類別下信息化教學能力差異分析。對不同性別、年齡、學歷、教齡、職稱、任教類別的高職教師的信息化教學能力進行方差齊性檢驗,方差分析結果顯示P<0.05,說明教師的信息化教學能力在α=0.05 水平上存在顯著性差異,結果如表4至表9。
結果顯示,不同性別教師對信息化教學意識與態度存在顯著差異,女性在這一維度上測得的平均值均高于男性,標準差顯示女性在這一認知上個體差異較男性小,這與李志琛有關數學教師信息技術素養的調查研究結果一致[4]。
結果顯示,不同年齡高職教師在信息化教學意識與態度、信息技術(TK)、信息化學科知識(TCK)、信息化教學知識 (TPK)、信息化學科教學法知識(TPACK)五個維度8 個指標上均存在顯著差異,總體來看,不同年齡高職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呈現兩頭低、中間高的趨勢,年齡在30 歲以下和51-55 歲的教師分別有3 項和4 項指標的均值最低,31-40歲有5 項指標的均值最高。說明新手教師雖然信息技術(TK)水平不低,但其整合教學與學科的能力還有待提高;51-55 歲教師雖然教學經驗豐富,整合信息技術于教學與學科的能力不低,但在信息化教學意識與態度和信息技術(TK)得分較低,說明他們更接受傳統的教學方式,信息技術水平較低。高職院校應重點發揮31-40 歲這一中間骨干力量,關注30 歲以下教師群體整合信息技術的能力和51-55 歲教師的信息化教學意識和信息技術能力的培訓。
對不同學歷的高職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進行方差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學歷在信息技術(TK)3個指標上存在顯著差異,學歷越高,信息技術(TK)能力越高,博士學歷的高職教師信息技術(TK)能力最高。這與韓錫斌有關中國高校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調查研究結論一致[5]。
結果顯示,不同教齡高職教師在信息技術(TK)、信息化教學知識(TPK)、信息化學科教學法知識(TPACK)三個維度8 個指標上均存在顯著差異,總體來看,教齡在11-20年的高職教師有5 項指標的均值最高,其他組別均只有1 項指標均值最高,說明教齡在11-20年的高職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最強,這點與不同年齡的高職教師的調研結果一致;教齡在30年以上的高職教師有7 項指標的均值最低,說明這一特殊群體在信息技術(TK)、信息化教學知識(TPK)和信息化學科教學法知識(TPACK)上無法與年輕教師媲美,中老年教師容易出現信息技術的應用能力較低、整合信息技術于教學和學科的能力較低,他們往往需要付出更多時間和精力準備信息化教學設計。這與李雨潛對師范大學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的調研分析結果一致[6]。

表6 不同學歷的高職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方差分析結果

表7 不同教齡的高職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方差齊性分析結果
結果顯示,不同職稱高職教師在信息技術(TK)、信息化學科教學法知識(TPACK)兩個維度4個指標上存在顯著差異,總體來看,隨著職稱等級越高,教師的信息技術(TK)能力遞減,剛入職尚未評聘職稱的新教師的信息技術水平最高。
結果顯示,不同任教類別的高職教師在信息技術(TK)、信息化學科知識(TCK)、信息化教學知識(TPK)、信息化學科教學法知識(TPACK)四個維度10 個指標上存在顯著差異,從均值來看,不同任教類別教師的得分情況為專業平臺課教師>專業方向課教師>文化基礎課教師,專業平臺課教師的標準差總體最小,說明專業平臺課高職教師的信息化教學能力相對最高,且個體認識情況差異最小。

表8 不同職稱的高職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方差齊性分析結果

表9 不同任教類別的高職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方差齊性分析結果
3.教師和學生對高職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差異分析。對高職教師和學生關于高職教師的信息化教學能力調研結果進行t 檢驗,結果顯示P<0.05,說明教師的信息化教學能力在α=0.05 水平上存在顯著性差異,結果如表10。

表10 教師和學生對高職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t 檢驗分析結果
結果顯示,教師和學生在信息化教學意識與態度、信息技術(TK)、信息化學科知識(TCK)、信息化教學知識(TPK)、信息化學科教學法知識(TPACK)五個維度29 個指標上存在顯著差異,從均值來看,學生在其中26 項指標上測得的均值高于教師自評,說明學生總體對教師的信息化教學能力認可度高于教師自評。
三、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高職教師的信息化教學意識與態度較高,信息技術得分較低,受這一短板所限,高職教師的信息化技術與教學和學科的整合與運用能力相對較低。
2.高職教師隨性別、年齡、學歷、教齡、職稱、任教類別不同,其信息化教學能力有不同程度差異。從存在顯著差異的TPACK 維度來看,其影響程度順序依次為年齡>任教類別>教齡>職稱>性別=學歷;從存在顯著差異的指標數量來看,其影響程度順序依次為任教類別>年齡=教齡>職稱=性別>學歷。由于年齡與教齡存在一定相關性,任教類別、年齡、教齡對高職教師的信息化教學能力影響最大,學歷的影響最小。從各影響因素來看,女性高職教師的信息化教學意識與態度要高于男性,31-40 歲和教齡在11-20年的高職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最強,教齡在30年以上的高職教師更難適應信息化教學要求,博士學歷的高職教師信息技術水平較高,專業平臺課教師的信息化教學能力總體較強。
3.學生對高職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的認可度整體高于教師自評。
(二)建議
1.彌補短板,加大高職教師信息技術培訓力度。在職培訓是高職教師的信息技術培訓的主渠道之一,結合教師對培訓形式的調研結果,84.33%的高職教師選擇基于案例的互動式培訓,因此,應著重應用基于案例和“教學做合一”的培訓形式,此外,校際觀摩(58.96%)、專家講座(56.72%)、教師研討交流(48.51%)、遠程學習(36.57%)和校本培訓(35.07%)等其他形式可作為有效補充。
2.分層培訓,提升培訓在不同群體中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根據不同因素的影響程度,建議根據教師的任教類別、教齡和年齡等開展分層培訓,發揮信息化骨干教師的傳幫帶作用,帶動30 歲以下青年教師和文化基礎課教師的信息化教學能力,著重提升男性高職教師的信息化教學意識,提升信息化教學能力培訓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3.排除阻礙,打通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提升通道。針對阻礙教師實施信息化教學的調研,前三大因素分別為:76.12%的教師認為信息化教學準備時間長,增加教師備課負擔;69.40%的教師認為自身信息技術技能水平不高;65.67%認為工作壓力大或忙,缺乏精力。建議從制度建設和培訓平臺兩大途徑入手,一方面,完善信息化教學激勵制度,從工作量計算、先進獎勵等方面促進教師主動開展信息化教學;另一方面,針對信息技術不足的情況,搭建多樣化的培訓平臺。
4.打造師生共同體,構建良好的信息化教學生態。構建良好的信息化教學生態需要高職師生的共同努力,主動適應信息化時代教學方式的變革需求,形成知識、技能、能力共生共長的信息化教學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