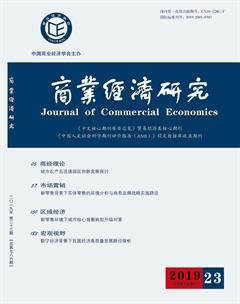基于跨境電商的區域外貿企業集群創新路徑研究



基金項目: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課題“基于跨境電商的江蘇外貿企業集群創新模式研究”(2018SJA1455);江蘇省教育廳“青藍工程”資助項目(蘇教師[2018]1號)
中圖分類號:F724? ?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面對經濟環境、貿易政策、要素成本壓力,傳統外貿增長乏力,而融合“互聯網+貿易+智能制造”的跨境電商逆勢而上,如何依托跨境電商實現外貿轉型升級成為各界關注焦點。本研究基于協同創新理論與集群創新網絡模型構建外貿企業跨境電商集群創新模型與假設,運用結構方程模型檢驗蘇州外貿企業跨境電商集群創新現狀,針對集群創新互聯網化、創新資源、創新環境對集群品牌效應與溢出效應影響不顯著等問題制定對策,助推“蘇州制造”嵌入全球價值鏈高端環節。
關鍵詞:跨境電商? ?外貿企業? ?集群創新? ?路徑
研究框架
(一)外貿企業跨境電商集群創新概述
企業集群創新是將生產企業、關聯企業、服務機構等主體置于開放系統,依托系統內人、財、物、信息等資源的優勢互補,實現集群技術、品牌、商業模式創新,有效克服個體創新難以承擔的成本或風險。
跨境電商是推進外貿互聯網化,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模式,專業外貿企業和制造型外貿企業是其兩大核心主體,專業外貿企業是協調生產、制造、目標市場的中介組織,制造型外貿企業則是自主從事進出口業務的生產制造企業。基于跨境電商的外貿企業集群一般遵循流程創新、產品創新、功能創新、鏈條升級的邏輯實現價值鏈攀升(見圖1)。
(二)建立基于跨境電商的外貿企業集群創新影響關系模型
基于跨境電商外貿企業集群創新動因研究未系統開展,但有關“集群創新動因”已有一定積累。周國程(2010)認為企業集群創新受企業、政府、市場、技術、環境等影響;曹瑄瑋等(2016)指出集群技術、專業化、創新能力是集群創新的動因;馮朝軍(2017)提出競合效應、市場拉力、政府推力、文化是集群創新驅動力;李海東、張純(2018)從針對陶瓷業創建產業根植性、社會資本、創新網絡與集群創新的關系模型;劉霞等(2019)提出行業環境、政策環境對集群創新影響。
建立影響關系模型。基于已有研究成果,企業集群創新動因可概括為集群創新能力、創新載體、創新資源、創新環境及制度機制等;同時,針對跨境電商特性將集群創新效應分為規模、品牌與溢出效應。借鑒Haken(1975)的協同創新理論,Gnyawali,Sivastava(2013)的集群創新網絡模型,將政、行、企、校等主體置于開放系統,構建基于跨境電商的外貿企業集群創新模型(見圖2)。
設計觀測變量。本研究設計了集群創新水平、互聯網化、創新資源等8個潛變量,其中模型左側為外生潛變量,右側為內生潛變量。為系統測度模型中各因素交互作用,將潛變量轉化為觀測變量(見表1)。
建立關系假設。基于跨境電商外貿企業集群創新影響要素既相互獨立又互相影響,其演化過程就是一個動態自組織過程,基于此,本研究設計了15個假設(見表2)。
(三)問卷設計與數據采集
設計問卷。根據關系模型設計“基于跨境電商的蘇州外貿企業集群創新現狀的問卷”,從集群創新水平、互聯網化、創新資源、創新環境、協同機制五維度量度各因素對集群創新的影響;從規模效應、品牌效應、溢出效應三維度細化創新成效,用李克特量表表示,由“1”-“5”依次表示“很不重要”-“十分重要”五個程度。
樣本概況。本次調研歷時三個月時間(2019年4月-2019年6月),通過企業走訪、論壇交流、電子郵件等方式,以蘇州外貿企業為調研對象,向蘇州沃金網絡、昆山世碩、太倉阿爾派等企業發放問卷200份,回收180份,其中有效問卷172份,有效回收率95.56%,樣本信息見表3。
本次調研以蘇州專業外貿企業與制造型外貿企業為主(占比80.24%),蘇州市區樣本比重最高,為61.63%,其次來自昆山與太倉;其中,300人及以下的樣本主要源自專業外貿企業,300-2000人的樣本主要源自制造型外貿企業。所有樣本均開展跨境電商業務,其中B2C模式比重最高,占比46.51%。專業外貿企業與跨境電商平臺、服務企業較好協同,但與高校、科研院所協同度較低,與行業協會協同比重低于50%;而制造型外貿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協同比重高于專業外貿企業,但與行業協會協同度較低。
(四)數據信度與效度檢驗
問卷信度檢驗。運用SPSS20.0檢驗采集數據,31個觀測變量均值3.4,說明數據較集中;偏度與偏度標準誤比值、峰度與峰度標準誤比值均小于2,說明數據呈正態分布。由于本調研為一次性調研,采用Cronbachs α檢驗量表信度。通過計算,量表整體Cronbachs α=0.912,說明問卷具較高可靠性,各分量表中除F2、F4稍低于0.7(基本接受)外,其余都大于0.7,說明各觀測變量與潛變量具較高一致性。
問卷效度檢驗。運用SPSS20.0檢驗量表結構效度,獲得KMO=0.875(良好水平),Bartlett=4327.365,P=0.000,說明觀測變量中存在共同因素,適合做因子分析,獲得特征值大于1的累積因子貢獻率63.592%,除A6、B5無規律分布外,其余變量因子載荷均大于0.500,即六成以上可用8個公共因子表示,量表通過效度檢驗。問卷量表的信度、效度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實證分析
(一)建立結構方程模型
在問卷信效度檢驗后,本研究使用AMOS20.0建立結構方程模型驗證蘇州外貿企業集群創新各因子間的關系與交互影響程度。用○表示潛變量,□表示觀測變量,構建原始結構方程模型M0(見圖3)。
M0中各擬合度指標計算結果為:X2/df=2.778(參考值<3.0),TLI=0.889(參考值≥0.9),CFI=0.978(參考值≥0.9),RMSEA=0.017(參考值≤0.08)。其中,TLI未通過檢驗,說明模型擬合不夠好,須調整。由圖3可知,集群互聯網化與集群品牌效應,集群創新資源、集群創新環境與集群溢出效應這三條路徑系數低于0.2,刪除這三條路徑,重建結構方程模型M1,運行結果如圖4所示,M1中各擬合度指標通過檢驗(X2/df=2.689,TLI=0.902,CFI=0.980,RMSEA=0.014),說明M1擬合良好,各路徑驗證結果見表5。
(二)檢驗結果分析
由表5可知,在10%顯著性水平,前期構建的15個假設中,僅H4b未通過檢驗;變量A6、B5在信度檢驗中刪除,未參與結構方程模型驗證;而假設H2b、H3c、H4c由于路徑系數過低,在驗證中被剔除。由此說明,基于跨境電商的蘇州外貿企業集群創新水平、協同機制對三個集群創新效應均有顯著正向影響;集群互聯網化對集群規模效應、品牌效應產生顯著正向影響;集群創新資源與環境對集群規模效應、溢出效應產生顯著正向影響。
現狀分析
(一)基于跨境電商的蘇州外貿企業集群創新成效分析
蘇州外貿企業跨境電商集群創新規模效應凸顯。模型左側所有因素對集群規模效應產生正向顯著影響,影響程度排名前三的分別是集群創新資源、創新水平與互聯網化。首先,集群創新資源是影響規模效應最顯著的因素,系數0.58,說明人、財、技術、信息等資源共享利于集群規模效應發揮;其次,集群創新水平是影響規模效應的第二大因素,系數0.52,說明蘇州外貿企業跨境電商集群根據國際市場需求研發新產品、開發新市場、探索新模式,有助提升集群規模效應;再次,集群互聯網化與規模效應路徑系數0.48,說明依托蘇州網絡高覆蓋率和強勁網絡交易活力,能凸顯規模效應。
蘇州外貿企業跨境電商集群創新品牌效應初現。集群互聯網化、創新資源與協同機制對蘇州外貿企業品牌效應產生顯著影響。其中,集群創新水平對品牌效應影響最顯著,系數0.52,說明蘇州企業開始提升產品品質、創新品牌,探索國際化品牌營銷模式,增強品牌影響力。集群協同機制對品牌效應影響位居第二,在品牌培育與激勵機制推動下,企業能有效提升集群品牌效應,推進“蘇州制造”進入價值鏈中高端環節。集群創新資源是影響品牌效應的第三大因素,依托蘇州制造業雄厚的人、財、技術、信息等資源基礎,對打造產品、企業與區位品牌產生積極作用。
蘇州外貿企業跨境電商集群溢出效應有所展現。集群協同機制、創新水平、互聯網化對溢出效應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其中,集群協同機制對蘇州外貿企業集群創新溢出效應影響最顯著,系數0.48,說明健全集群交互機制、資源整合機制、誠信保障機制,能更好實現資源整合、員工流動并衍生新企業;集群創新水平對蘇州外貿企業集群溢出效應影響位居第二,系數0.44,說明集群企業在推進產品、工藝、技術、商業模式、品牌等集群創新中,利于衍生新型外貿企業;集群互聯網化對溢出效應影響位列第三,說明集群互聯網化作為集群創新工具,在資源整合與員工流動中發揮重要作用。
(二)基于跨境電商的蘇州外貿企業集群創新問題
集群互聯網化作用尚未充分發揮。蘇州的專業外貿企業與行業協會協同較高,但與科研院所、高校的集群創新較低;而蘇州的制造型外貿企業剛好相反,說明集群的互聯網化水平影響集群效應發揮;同時,多數外貿企業將跨境電商集群作為進出口載體,多基于技術、產品、流程創新,但圍繞品牌的協同創新并未系統推進,并未凸顯“蘇州制造”在國際市場上的品牌影響力。
集群創新資源不夠充分。蘇州的外貿企業多為松散型家族式小微企業,個體很難爭取創新資金,在集群創新中也未能凸顯依托集群爭取創新資金;同時,由于蘇州外貿企業整體規模小、實力弱、薪資低,很難吸引具有國際視野的高層次跨境電商人才,集群內外人員流動性不強;再次,受資金、技術、人才限制,集群創新衍生新企業頻率較低,影響集群創新力。
集群創新環境不盡完善。蘇州政府雖然制定政策培育網谷、金楓、兩岸和商等跨境電商產業園,但由于集群規模小、創新能力弱,不少集群對國際經貿趨勢、供需環境認知度不高;部分企業雖在空間上形成集群,卻較少推進集群內產品、流程、技術、商業模式、品牌的協同創新;另外,由于集群創新氛圍營造不夠濃厚,使集群資源共享、員工流動及衍生新企業成效不夠顯著,影響了集群活力。
結論與展望
(一)結論
通過模型構建、假設設定、結構方程驗證,針對蘇州外貿企業跨境電商集群創新的問題,精準制定對策。首先,發揮蘇州外貿企業集群互聯網化水平,通過集群主體間協同,打造產品品牌、企業品牌和區位品牌,提升“蘇州制造”國際影響力;其次,豐富集群創新資源,發揮集群創新主體競合作用,推進集群資源交互整合、人才流動,新企業衍生,提升集群創新活力;再次,優化集群創新環境,通過氛圍營造、政策支撐、信息共享等推進集群的外貿形勢認知水平,依托集群內技術、人才、信息整合,發揮集群溢出效應。
(二)展望
本次調研樣本容量還不夠大,可能無法反映蘇州外貿企業概況,后期還須擴大樣本容量,以便更全面反映蘇州外貿企業跨境電商集群創新的真實情況。另外,本研究所設計模型中的五大因子對三大集群效應影響是單向度的,尚未分析三大集群效應對五大因子的反向影響,以及因子間的交互作用。在后續研究中,還須進一步分析因子間、效應間的交互作用,以便更精準把握蘇州外貿企業跨境電商集群創新動力,制定政策提升集群創新效應,形成蘇州跨境電商生態圈,提升“蘇州制造”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參考文獻:
1.李芳,楊麗華,梁含悅.我國跨境電商與產業集群協同發展的機理與路徑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19(2)
2.周芳.區域跨境電商產業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9,33(1)
3.周芳.產業競爭力視閾下區域跨境電商發展路徑研究[J].商業經濟研究,2018(19)
4.劉霞,夏曾玉,張亞男.不確定環境下本地與跨區域網絡對集群企業創新影響研究[J].科研管理,2019(6)
5.Haken,H.Cooperative phenomena in systems far from thermal equilibrium and in nonphysical systems[J].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1975,47(1)
6.Gnyawali,D. R.,Srivastava,M.K.Complementary effects of clusters and networks on firm innovation:A conceptual model[J].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2013,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