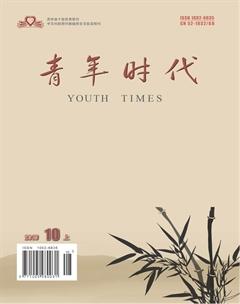家庭暴力的法律救濟
周星文
摘 要:家暴的現象層出不窮,而法律則是受害者賴以反抗的利器,雖然我國制定了諸如強制報告制度、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公安的告誡書制度等來對受害者予以救濟,但法律規定的制度仍存在諸多問題,這把“利器”還有待磨煉。例如,在家庭暴力中,立法應當彌補立法技術的缺陷、在證明責任上可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則、受害人在行使正方防衛時可適當突破刑法所規定的成立要件、建立并完善家庭暴力公益訴訟制度、完善行政救濟嚴格執法等各。
關鍵詞:家庭暴力;遺棄;虐待;正當防衛;法律救濟
一、家庭暴力司法現狀
我國針對家庭暴力立法歷經了20年的變遷,基本上形成了以憲法為根據,以婚姻法、民法通則、繼承法、刑法、婦女權益保護法及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為依托的眾星拱月般較為完善的法律體系。時間在變,法律也在變,法律作為上層建筑,需要不斷適應這個變化的社會,隨著“家庭暴力”愈演愈烈,《反家庭暴力法》顯露真身,并于2016年3月1日起施行。它進一步明確了家庭暴力的概念,并擴大了主體范圍,將共同生活的非家庭成員也納入進來,有許多進步之處,但它仍然比較年輕,仍有許多改進的空間。《反家庭暴力法》的進步也促使我們有必要更加深入的研究、探討我國現階段的家庭暴力現象。與其他暴力相比,家庭暴力具有普遍性、對象的親密性、隱蔽性、突發性、形式的多樣性及反復性等特征。《反家庭暴力法》已經實施了三年,在這三年里它針對家庭暴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也在司法實踐中逐漸顯現出立法、執法等各方面的不足[1]。
二、現階段立法、執法上存在的不足
縱觀立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我國對家庭暴力方面的立法實屬有限,規定的基本上是一些原則性的東西,寥寥數字便可概括,可操作性不強,沒有針對性,法律條文較為抽象、空泛、分散。這就直接導致在執法過程中各機構的相互推諉,沒能將失職者追責到位,從而加劇家庭暴力的發生。
(一)立法籠統,法律之間銜接不到位
一是《反家庭暴力法》與《婚姻法》的調整對象大都相同,但是在某些相關內容上存在矛盾,如《反家庭暴力法》的第13條和《婚姻法》的第43條相比,兩者表述不一[2]。二是《反家庭暴力法》中許多內容與其他法律法規相重復,如其第37條規定“家庭暴力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與《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以及《刑法》的相關規定如出一轍,實乃浪費立法資源。三是非規范性條款大量存在,立法過于籠統,原則性大于實用性,可操作程度低[3]。部分規范性弱的條款,削弱了法律的規范效力,不具有規范的功能,僅限于表明法律的態度。四是法律之間銜接不到位,刑法救濟不足。
(二)家庭暴力案件取證困難,證據規則不明
家庭暴力作為一種特殊案件,出于傳統觀念的影響受害人往往不愿意向外界提及,即使公安機關介入也不愿意積極配合;暴力發生時在場的見證人與雙方關系都較為親密,所以也不愿出庭作證,這就造成了取證的困難性。再者,大部分家庭暴力案件一般都是民事案件,少有上升為刑事案件,而按照民訴中“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就很不利于保護受害者,而法律卻沒有對家庭暴力這一特殊案件規定是否可以采取特殊的證據獲取手段,是否可以適用特殊的舉證規則。
(三)傳統的正當防衛制度難以適用于家庭暴力
正當防衛是法律賦予普通公民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的一項權利,是法律鼓勵公民對自己合法權益的保護。但是正當防衛具有嚴格的限制條件,在時間上,需要有不法侵害的發生,在限度上反抗的手段和程度要合理。但是家庭暴力中,通常是強者壓制弱者,而弱者幾乎沒有相當的力量與之抗衡,故此只能采取極端做法來維護自身安全。而出于隱蔽性的特點、舉證的原則,反抗者很難證明自己沒有防衛過當,從司法實踐來看,一般都需要承擔一定的刑事責任。如此,正當防衛對于家庭暴力便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
(四)訴訟制度流于形式
首先,家庭暴力頻頻發生,很大程度上在于施暴者受到懲罰的幾率太低。按照我國《婚姻法》第45條的規定,針對家庭暴力案件是自訴和公訴并存的,但是由于刑法中并沒有設定專門的家庭暴力罪名,而且前文提及的家庭內部成員基于家庭關系社會輿論等各種原因不會提起自訴,這就使得公訴的規定也流于形式。其次,在自訴中,對未成年人的訴權保護不夠。《反家庭暴力法》中規定在家庭暴力中,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從我國民法規定來看,未成年人是不具有訴訟行為能力的,需要監護人代理起訴。但是在他們遭受家庭暴力的情況下,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往往就是施暴者,他們怎么可能會去法院起訴呢?孩子的自訴權該如何保障?
三、家庭暴力法律規制的完善
(一)制定規范性條款,填補立法空白
首先,在立法技術上,各地方民俗不同風情各異,地方性立法可以“因地制宜”“對癥下藥”見效更好。其次,在立法技術上,盡量避免重復、矛盾、非規范性立法較多的問題,重復雖然能起到一個強調的作用,但是能制定出更多新的、具體的、行之有效的法律規范才具有突破性,否則只會固步自封。最后,在刑法的立法上,刑法中應當制定專門的家庭暴力罪,以與《婚姻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反家庭暴力法》等緊密銜接,將介于一般性家庭暴力行為與構成刑法上暴力犯罪的行為之間的暴力行為納入到刑法保護的范疇,防止出現法律的斷層、真空地帶,結束籠統套用諸如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遺棄罪等罪名的局面。如此規定,可以提高對各種暴力刑事處罰的力度,使家庭暴力得到應有的救濟。
(二)關于家庭暴力的證明規則問題
在司法實踐中,家庭暴力認定為犯罪的概率很低,勝訴率更低。盡管法律明確了公安機關的出警記錄、告誡書及傷情鑒定意見能作為家庭暴力的有效證據,但還是仍有改善的空間。一方面,不僅是公安機關的搜集的證據,受害人和其他機構、個人、組織提供的證據也應當納入進來;基于家庭暴力的特殊性,應該給受害人搜集證據時更多的空間、更大的權限;在能夠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鏈,能夠滿足“高度蓋然性”的標準,就應當認定為家庭暴力成立的有效證據。此外,基于對家暴中弱勢群體的保護,也可以考慮在審理案件過程中嚴格依據民事訴訟的一般規定———“誰主張,誰舉證”原則,讓家庭暴力受害人來承擔主要證明責任[4]。
(三)適用正當防衛時的適當突破
由于家庭暴力具有循環性的特點,在家庭中,家人之間親密的生活,受害人能夠很準確地預感到下一輪家暴的發生。在此情況下,法律應當允許家暴的受害人提前防衛,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家暴的發生,造成不必要的傷害。還可以將“受虐婦女綜合癥”引入正當防衛制度。“受虐婦女綜合癥”是指在婚姻家庭中受到同居者長期的暴力傷害,從而在心理上產生了一種無助感。這使得她們對施暴者的暴力行為會有激烈的反應,而他們的行為結果是具有合理性的。作為可采證據,“受虐婦女綜合癥”最早見于加拿大的司法實踐,現在美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都引入了該理論,認定婦女“以暴制暴”屬于正當防衛。
(四)建立家庭暴力公益訴訟制度,并設立專門的家事法庭
我國的公益訴訟制度涉及民事公益訴訟和行政公益訴訟,但是在民事公益訴訟中并沒有建立家庭暴力公益訴訟制度。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借鑒外國經驗。例如,在美國,檢察總長、婦女聯合組織甚至與案件當事人無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個人,對于其有一定證據證明的家庭暴力行為均有權提起公益訴訟,以保護被侵害者的身心健康及其合法權益。在我國,既然《反家庭暴力法》已經規定了居委會、村委會、社會組織等有義務對家暴行為予以制止和報告,那么在家庭暴力自訴難的問題上,我們何也不建立此種制度,賦予一定社會組織,尤其是公益組織以原告資格保護相關群體的合法權益。
(五)關于人生安全保護令制度的完善
《反家庭暴力法》規定的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無疑是該法律的一大亮點,民事保護令制度的引用彰顯了法律對弱勢群體人身健康的尊重以及生活質量的關注[5]。基于前文已經提及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作為一項新引入的制度,各方面還有待完善。主要是完善配套機制,確保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有效實施:出臺配套司法解釋,對各基層人民法院處理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案件進行引導;適當擴大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申請范圍;構建起多層次的處罰體系,不只局限于現階段的訓誡、罰款和拘留之類的處罰。
四、結語
家庭是孩子成長的搖籃,是夫妻守望的愛巢,是家人溫暖的依靠。這個世界暴力充斥的地方已經太多,莫讓家庭也淪為暴力的重災區!落實反家暴法必須雙管齊下。既要加大宣傳力度,增強受害者的維權意識,讓施暴者及時受到法律的制裁,又要完善法院、公安、婦聯等單位的溝通協調機制,提高執法力度。良好的立法是成功的一半,但真要讓反家暴法發揮更好的作用仍然任重道遠。
參考文獻:
[1]姜佩杉.反家暴法實施三周年:亮利劍 鑄強盾 繪藍圖[N].人民法院報,2019-03-01.
[2]周國平.《反家庭暴力法》亟須解決的幾個問題——對《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的分析[J].婦女研究論叢,2015(2).
[3]湯敏.淺談我國《家庭暴力法》的不足之處[J].法制博覽,2016(6).
[4]吳卓,錢仁偉.我國家庭暴力法律救濟問題研究[J].黑龍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6(3).
[5]宋炳華.論家庭暴力防治中之民事保護令制度[J].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