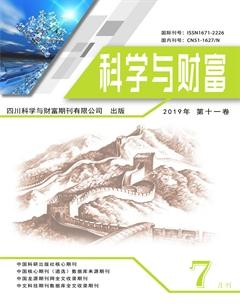關于浙江省各博物館互動體驗服務現(xiàn)狀的調查研究
毛芳玲 劉鴻霖
一、調研背景
我國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淀,也擁有著大批藏有珍貴藝術品的博物館。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新時代文化建設的基本方略。對于文化事業(yè)和文化產業(yè)的發(fā)展,十九大提出了“加強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理念。同時,國家文物局發(fā)布了“砥礪奮進 輝煌五年—黨的十八大以來符合國情的文物保護利用之路新成就”的文章,展示了推進文物合理適度利用的努力,讓文物活起來,更好的讓文化傳承融入經濟發(fā)展,是符合國情的文物保護利用之路的必經之路。
二、互動體驗的概念
隨著博物館教育理念的不斷發(fā)展,博物館教育逐漸脫離利用藏品、文字說明、輔助展品等靜態(tài)展示對觀眾進行教育的被動模式。對于現(xiàn)代博物館而言,即便是以信息技術和多媒體技術為支撐的動態(tài)展示也不能完全滿足博物館教育的需求。展覽圍繞主題運用各種多媒體技術手段設計的教學情境,鼓勵觀眾動手動腦參與展先將觀眾被動的參觀過程變成了一個在體驗參與中探索、欣賞、發(fā)現(xiàn)和思考的雙向傳播學習模式。
(一)體驗
所謂體驗是指通過實踐來認識周圍的事物。博物館學家約翰佛克(John Falk)將參觀行為全過程定義為博物館體驗(Museum Experience),他指出博物館體驗并非單向的,而是個人條件、社會條件、環(huán)境條件共同構成的互動的體驗模式(lntemcrive Experience Mode)。換言之,觀眾的博物館體驗不僅僅是觀眾與展覽互動后的結果,也是觀眾個人與社會條件、博物館環(huán)境條件共同建構的成果。當觀眾步入博物館開始選擇性地參觀展覽,互相討論問題,嘗試對他們所看到的東西予以個人化理解并賦予其意義時,觀眾選擇參觀的展品就會被加入到己的博物館體驗中。博物館體驗展示通過3D、4D環(huán)幕影院、模擬場景、數(shù)字沙盤和虛擬世界等體驗方式刺激觀眾的視覺、聽覺和觸覺,創(chuàng)造一個能調動觀眾新奇感與興奮感的環(huán)境條件,幫助觀眾尤其是首次參觀博物館的觀眾將展覽訊息群組化,有效提升觀眾對展覽的理解力,同時還能鼓勵觀眾團體之間的交流與互動。
(二)互動
目前各博物館常見的互動形式主要有博物館教育部門主辦的各類藝術作、文化實踐活動以及以多媒體科技為核心的各類人機互動游戲等。博物館展覽的互動性不僅僅來自于圍繞展品設計的各種形式的開放式互動展示,也來自于啟發(fā)觀眾想象力的陳列文本,成功的互動展覽給觀眾帶來的不是“眼球運動”,也不僅僅是娛樂性質的“肢體運動”而是“心腦運動”。互動展覽不要求觀眾記住展品的年代、質地或者涵義,鼓勵觀眾在動手參與的同時讓大腦也活動起來,使他們在參觀過程中興味盎然,實現(xiàn)博物館教育功能的最大化。
三、省內博物館互動體驗發(fā)展現(xiàn)狀
浙江省第十四次黨代會作出了“兩個高水平”“六個浙江”“四個強省”的重要部署,其中,“文化浙江”作為“六個浙江”之一,為浙江省文化建設賦予了新使命、指明了新方向。而博物館行業(yè)是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陣地,責無旁貸地肩負著實現(xiàn)文化遺產公益性價值的重任,但由于主觀意識的影響和客觀條件的制約,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博物館在發(fā)展中遇到的問題日益顯現(xiàn)。要解決在發(fā)展中遇到的各種問題,需要用創(chuàng)新思維去看待,從全球化的視角去分析解決存在的問題。
浙江博物館數(shù)量眾多,相關的配套產業(yè)發(fā)展卻后勁不足。大多數(shù)博物館的展出有著過于學術化,缺乏互動性的短處,且僅限于進行傳統(tǒng)展覽,并不注重交流互動區(qū)的設置,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民眾與博物館之間的交流。同時研究民間傳統(tǒng)策展企業(yè)與博物館合作的幾個案例后,可以發(fā)現(xiàn)此類企業(yè)的經營活動的思路傳統(tǒng)、配套技術滯后、缺乏針對性與創(chuàng)新性,策劃的展會往往觀感單一且僅局限于視覺等問題都降低了博物館的可觀賞性與人流量。根據(jù)我們對博物館館眾進行的調查結果:認為展覽過于枯燥的人群高達54.16%,認為交流活動區(qū)的設計有待提升的占72.34%。各博物館普遍存在互動體驗發(fā)展欠缺的問題。
四、博物館發(fā)展趨勢
(一)功能演進,角色轉換,融入當代生活
博物館最早的功能是王權對勝利的陳列,直到文藝復興之后,才逐步成為對公眾開放的非營利常設機構,此后由政府、基金會和個人進行支持,開始謀求擴大在公眾當中的影響力。隨著博物館自身的演進和公眾需求的改變,早期以收藏為核心的“神廟”功能逐步淡化,讓位于吸引公眾參與、學習和討論的“公共論壇”功能,同時周邊文創(chuàng)、智慧服務等功能建成產業(yè),更進一步融入日常生活。
目前,中國博物館正在經歷著“以物為本”向“以人為本”的觀念轉變,博物館做為公共文化服務機構的屬性不斷強化,工作重點不再是博物館的可及性,而是調整博物館與公眾之間的關系,更好地滿足公眾教育和文化消費方面的需求。為此,越來越多的博物館開始轉換角色,放下身段,以服務者的姿態(tài),為公眾提供更加豐富的文化產品。博物館在未來社會城市發(fā)展和公共文化服務的作用會越來越大,博物館將成為城市發(fā)展的新文化勢力。
(二)技術驅動,創(chuàng)新變革,構筑新型平臺
近年來,作為傳承社會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和創(chuàng)造性表達的風向標,博物館以增強觀眾體驗為導向,實現(xiàn)了運營模式與移動應用、社交網絡的緊密結合,形成了以博物館業(yè)務需求為核心,用創(chuàng)新科技手段整合線上線下活動的新型博物館生長模式。
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在談“十三五”文物科技工作時指出,當前文物博物館事業(yè)發(fā)展面臨一些亟待突破的瓶頸問題:
一是對于文物的價值認知能力有限,難以全面、系統(tǒng)挖掘和深刻闡釋文物的多元價值,難以講好“中國故事”;二是對于文物保護的能力有限,在瀕危文物的搶救性保護和更大范圍的文物預防性保護方面,都有大量難題尚未突破,需求復雜而巨大,技術手段卻十分有限、單一;三是對于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能力有限,,難以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公共文化需求,急需通過創(chuàng)新管理理念和技術,突破裝備革新,來提高文物保護利用的質量與效果。
從長遠看,文物博物館事業(yè)不僅在維系國家記憶、涵養(yǎng)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彰顯文化自信和擴大國家文化影響力等方面發(fā)揮更為重要的作用,也將在培育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促進產業(yè)結構調整方面具有極大的潛力和空間,急需通過科技創(chuàng)新與體制機制創(chuàng)新的“雙輪驅動”,來優(yōu)化發(fā)展方式,進一步提高文物工作的公共服務能力,提升文物工作的影響力。
觀眾是博物館展陳對象的主體。 娛樂經濟和休閑文化的出現(xiàn)使得博物館的主 要職能完全由收藏轉移到教育上來,觀眾期盼在博物館得到信息更希望得到娛樂。同時公眾考古學提出考古學知識大眾化理念,作為考古學成果展示平臺的博物館,必須為考古資料的展示與復原提供了新的展示手段和方法,讓觀眾成為博 物館陳列的參與者而非旁觀者。隨著互聯(lián)網為代表傳媒高科技的發(fā)展,網絡數(shù)字 化博物館迅速發(fā)展,多媒體技術的成熟,促成各種互動展示手段日趨多樣。這一階段的展示是立體多維的、互動的。他們的需求直接關系到博物館建設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