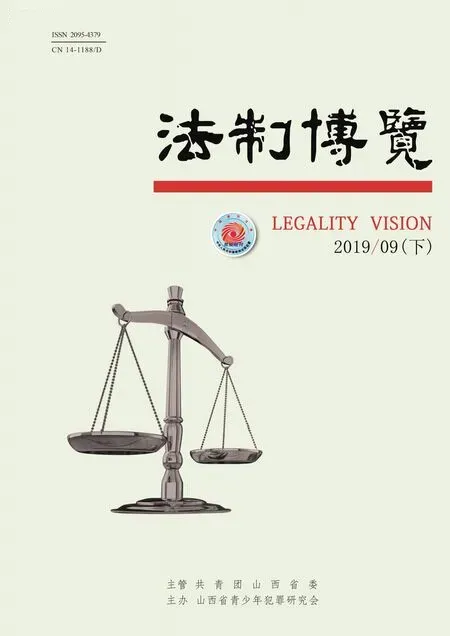淺析不動產交易中的欺詐法律問題
李春平
中共甘南州委黨校,甘肅 甘南藏族自治州 747000
一、案例分析
案例一:某市某區房地產商于房屋出售廣告及社區建設示意圖上標注小區內有游泳池及附近在建設施(超市、健身中心等),劉某是該地區有名的健身達人,見小區規劃范圍內有游泳池,遂購置該社區三套房產,購房款及其他尾款總額達470多萬元。入住小區后,三年內小區及附近所有設施建設完成,唯獨未見規劃方案中小區內游泳池。遂訴至法院,請求判令被告開發商返還購房款及其他尾款470多萬元。
案例二:因工作需要需長期停留于廣州東莞的張先生欲在東莞商業街附近購置一套房產,中介劉某于網絡渠道獲取到張先生購房信息,遂將商業區東北部一處老宅介紹給張先生,張先生以相對實惠的價格(略低于市場價10%)購入,后聽鄰居議論說該老宅中曾有人自殺,張先生遂以中介劉某向其隱瞞宅中死過人這一事實,以隱瞞和欺詐的行為使其錯誤購買房屋,請求判令劉某返還購房款并進行精神損害賠償。
上述兩個案例是真實發生的,法院對于兩個案件也給予了不同的判決。案例一中,劉某的請求得到實現,法院以開發商虛假宣傳使劉某產生錯誤的認知,而錯誤的處理了自己的財產,認為開發商的行為構成欺詐。而案例二中,張先生的請求并未得到實現,法院駁回了張先生的請求,法院認為中介的行為并未構成欺詐,僅僅是未完全履行告知義務,并未使張先生產生錯誤認識而錯誤處分其財產。
二、不動產買賣中欺詐行為分析
對上述兩個案例進行分析,不難發現現階段我國法律實務中對不動產買賣欺詐的認定過程和依據。雖然案例一中的劉某和案例二中的張先生均在意思表示上出現誤差,但是開發商和中介的行為卻是截然不同的性質。
在案例一中,開發商的行為可以明確認定為不動產買賣中的欺詐行為。首先,開發商明確指出小區內有游泳池,而實際未進行游泳池建設,這屬于虛假宣傳。其次,開發商未告知業主具體的開發計劃,劉某明確表示其因為小區內有游泳池而購置房產時,開發商應當告知其是否真的準備進行游泳池修建,具有隱瞞的故意。而劉某購置房產的最直接原因是,因為其熱愛健身,小區內有游泳池而其有此項需求,換句話說,劉某購房時的意思表示是購買具有游泳池的小區房產,而并非單純的房產。即產生了這樣的法律后果,開發商和劉某之間的房屋買賣合同中存在錯誤的意思表示,劉某以為其購買了帶有游泳池的小區的三套房產,而開發商以為劉某僅購買了三套房產。兩者在意思表示上不同,依據《合同法》的相關解釋,開發商和劉某的房屋買賣合同屬于一種可撤銷的合同,這個合同是可以自始無效的,從合同的規范、不同產買賣中的意思表示均可以解釋案例一中的不動產買賣是一種具有欺詐性質的交易行為。
反觀案例二,案例二則較為簡單,其不具備意思表示上的錯誤,張先生并未指出其要購買一套“沒有死過人”的老宅,法律上也并未規定死過人的房屋不可買賣。死過人的房子不適合買賣僅僅是出于“迷信”傾向的說法,換句話說宅子里是否死過人并不影響中介對外表達“出售房屋”的意思。而張先生的交易需求極為簡單,“因工作需要,停留住房”,其對房屋沒有額外的功能性需求,因此中介出售的死過人的老宅是完全滿足張先生購房需求的意思表示,雙方在意思表示上具有一致性。而中介違背的僅僅是未將房屋內死過人的事實告訴當事人,侵犯了當事人的知情權,并未對當事人的其他權利產生侵害。同時在該次房屋交易行為中,合同的主要權利義務是房屋買賣,而告知房屋內的往事屬于從義務,并非主義務,因此中介的行為并不會影響不動產交易的主義務的履行。同時,事實中中介已經意識到房屋內死過人而“不吉利”,因此以低于市場10%的差價賣個張先生,雖然具有故意隱瞞的行為,但是在這里并不能認定為故意欺詐,使當事人作出錯誤的意思表示。但是中介劉某終究是隱瞞了房屋內死過人的事實,屬于侵犯張先生的知情權,但是在主合同義務“不動產交易”的行為中,這一行為無傷大雅,并不會對合同效力產生影響,這也是案例二中法院駁回張先生請求的原因。
三、不動產交易欺詐行為的定性
從上述兩個案例的分析中不難看出,不動產交易欺詐與房屋買賣合同效力具有直接關系,一旦認定為欺詐那么房屋買賣合同效力將會受到影響,合同無效或效力待定。
根據相關法律實務和《城鎮房屋買賣租賃解釋》對不動產交易欺詐行為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首先,該行為的主體一定是不動產交易,就是說買賣合同的主義務一定是房屋的過戶登記,而不是其他。換句話說,比如買游泳池送房屋,那么簽訂的是游泳池的交易合同,而送的房屋是從義務,并非主義務,即使房屋的價值遠超游泳池。舉個例子來說,游泳池旁邊有A、B兩棟房屋,買游泳池送B房屋,但當事人以為是送A房屋而簽訂買賣合同,此時的行為并不會構成不動產交易中的欺詐,因為房屋的過戶并非該合同的主義務。
其次,該行為的客體一定是侵犯了購房人的知情權,使雙方在意思表示上存在實際差別,購房人的錯誤認知而處分其財產,且另一方充分知情,具有故意隱瞞或故意引導購房人錯誤處分財產的行為。最常見的就是房屋的虛假宣傳,當然還有故意隱瞞行為。比如劣質工程當做優質工程出售,故意對外宣稱房屋處于“黃金地段(與實際不符)”等,以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使購房人產生錯誤認知,做出了意思不符的明示。
最后,根據《刑法》與《民法》、《合同法》的相關規定,欺詐行為具有故意。在不動產交易欺詐中,一方一定是故意誘導另一方作出錯誤的意思表示,使購房人產生一種意識上的錯覺,認為實際與心中所想相符,而作出一致的意思表示(盡管這種意思表示與實際不符,但當事人認為相符),就是說銷售方、開發商或中介具有欺詐故意,行為可以是作為或不作為的形式。
在論述了主體、客體和行為要件后,為了構成完整的民事侵權行為,那么還需要有結果要件,即損害結果的發生。即使在簽合同前最后一秒,當事人意識到受到欺詐而不簽不動產交易合同,也不能稱為交易欺詐,或者說未這種情況僅僅稱為未完成的交易,甚至不具備法律效力。只有買賣實際完成,欺詐目的實際達到,購房人法益受到實際損害,才能稱之為不動產交易欺詐行為。此時,主觀上欺詐的目的與客觀上錯誤認識后的交易行為相符,此時才能從法律上定性為不動產交易欺詐行為。
四、規避不動產交易欺詐的方法
(一)完善立法
在法治社會,立法先行,司法隨后,只有完善立法,才能在探索中不斷完善行為。關于不動產交易的立法較多,但是相對龐雜,在實際的法律實務中處理此類不動產交易欺詐糾紛,有時會引用《合同法》、《民法》、《物權法》或《城鎮房屋租賃合同解釋》等,現階段對于此類欺詐行為沒有直接的法律定性和定義,實際處理過程中多參考民法或刑法中關于欺詐的解釋進行解釋,這實際上是法律的空缺,我們缺少一部處理不動產交易的特殊法律。
(二)規范不動產交易市場
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動產交易受到市場特征的影響,具有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特點。以房地產交易最為典型,“購房托”就是很典型的一個例子,群眾購房過程中很容易受到“托”的影響。此外還有房地產市場的虛假宣傳,如同本文中的案例一,這些因素都是引起當事人產生錯誤意思表示的重要原因。此外,國內還一度出現“房熱”現象(城鎮房屋價格虛高,但是這并非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法律問題,更傾向于行政問題、經濟杠桿失調),我國不動產交易市場亟待規范。
(三)群眾法律意識的培養
在現實生活中不動產交易的欺詐行為有時還會表現在合同條款的“咬文嚼字”上,如格式條款等。雖然法律明確規定,格式條款未履行提醒告知義務可以撤銷合同效力,但是不同產與一般交易不同,商品房涉及到的標的額較高,另一方面很多群眾雖然受到欺詐,但是實際損害仍處于可以“忍受”的范圍內,其選擇息事寧人,這是助長國內不動產交易市場亂象的重要因素。這種情況并非市場管理的缺失、法律制度的缺陷,而是群眾法律意識淡薄的結果。同時這種法律意識淡薄,會使當事人在交易過程中未嚴格按照謹慎性原則進行考慮,很容易在另一方誘導下產生錯誤意思表示而受到欺詐。這種欺詐與其說是被動的欺詐,不如說是主動的疏忽大意。正所謂“蒼蠅不叮無縫蛋”的道理,若所有人均遵循嚴謹性行事,那么不動產交易欺詐糾紛的發生率將會顯著降低。
(四)行政力量的干預
不動產的存在需要諸多要素作為憑依,因此如果想要單純依靠法律力量來規避不動產交易欺詐的社會風險難度較高,需要以政府市場管理為主導的行政力量干預,尤其是加強對開放商或銷售商虛假宣傳的懲罰力度,嚴格約束廣告宣傳行為等。或通過行政指導力量,引導群眾正確審視不動產交易。此外,行政力量不應當是不動產交易中的中堅力量,其應當是立于民(民生)、承于法(法律)、明于情(實情)的群眾生活指導力量。在此基礎上結合法律力量,不斷規范不動產交易市場,保護不動產交易安全,這也是解決民生問題的一個重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