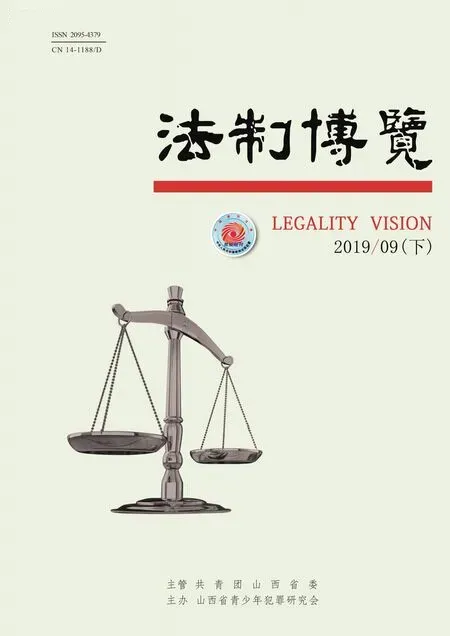違約責任中的精神損害賠償
劉 余
江蘇知南貞律師事務所,江蘇 常熟 215500
通常,我們在對損害進行劃分時會將其分為“財產損害”和“非財產損害”。前者具有財產上的價值,可以簡單地用金錢加以計算。后者也稱精神損害,以精神痛苦為主,包括肉體上的痛苦。傳統民法中,精神損害賠償請求只能在侵權之訴中提起,對于僅因違約而導致的精神損害,受害人是無法提起訴訟以獲得救濟的。在日益重視人權的今天,我們是否能考慮突破傳統,將精神損害賠償也納入到違約責任中,從而給予民事主體更全面的保護呢?本文將對這一問題進行簡要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國外的有關判例和做法
英國早期對于違約導致的精神損害是不予賠償的,并且一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后,英國判例才開始突破限制,開始對違約精神損害給于救濟,翟維斯訴天鵝旅游公司(Jarvis v.Swans Tours Ltd)一案便是一個典型。該案的主審法官丹寧勛爵認為:“在適當的案件中,在合同法上可以對當事人精神上遭受的痛苦授予損害賠償。這方面的一個例子就是度假合同,或者提供休閑娛樂和享受的合同。”[1]
美國先后兩次發表的合同法重述是對判例的總結概括。1933年發表的《第一次合同法重述》明確:“除非特殊情況,法院對違約所致的精神賠償不予支持。”而1981年發表的《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353條規定及其解釋延續了第一次的規定,即僅在非常情況下支持違約精神損害賠償。
法國在對于是否認可合同精神損害責任的判例上,最初表現的比較消極,之后的判例則越來越傾向于認可并支持違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
德國民法典第253條明確規定:“非財產上之損害者,除有法律規定外,始得請求以金錢賠償之。”前期的判例礙于法律無規定,不承認違約案件中的精神損害賠償。直到1956年的海上旅行享受一案才有所突破。德國在1979年修訂民法典時,增訂了旅游契約,明確規定了旅游契約的精神損害賠償以及精神損害賠償的額度。[2]
通過以上幾個代表性國家的判例和做法,我們可以看出:幾個代表國家(不論是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對于“違約損害賠償中也應當包括精神損害賠償”均在不同程度上進行了認可。同時,該做法得到了日本、瑞士、澳大利亞等國的追隨,也得到了國際公約的認可,違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已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重視。
二、理論上的合理性
怎樣更好地確立違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法律地位,使其成為“有本之木”,首先要從理論上為其尋找基礎依據。
(一)全部賠償理論。即“因違約方的違約使受害人遭受的全部損失都應當由違約方負賠償責任。完全賠償是對受害人的利益實行全面、充分保護的有效措施。”[3]在此,由于違約責任實行的是無過錯責任,故賠償的范圍取決于違約行為所造成的客觀損害,而與違約方的主觀過錯程度無關。
(二)預期利益理論。預期利益是合同當事人主觀上可以預見的,對合同的期待價值。預期利益的保護,目的在于使合同當事人能夠得到如合同得以正常履行情況下的利益。而對于那些目的在于“獲得安寧和愉悅”或目的在于“擺脫痛苦和煩惱”的合同中,預期利益實際上就是守約方在合同履行后所應處的精神狀態。因此,法律對這種精神損害的救濟,正是對預期利益的保護。這種預期利益雖具有主觀性,但計算和證明困難完全可以通過法律技術來解決。
(三)統一保護理論。該理論認為合同義務包括主給付義務和附屬義務,對二者要加以統一的保護,而附屬義務又分為從給付義務和保護義務。盡管在以“獲得精神愉悅或擺脫痛苦”為目的的合同中,因違約所造成的精神損害已經是對主合同義務的違反,但其實是主合同義務與保護義務的重合。因此在因違約導致精神損害的情況下,都可以看作是對保護義務的違反,與主合同義務的違反一樣,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造成的損失要給予賠償。[4]
綜合上述觀點,違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與現有的民法理論并不相沖突,具有理論上的合理性。
三、立法上的必要性
法律之所以拒絕給予精神損害以物質賠償,是出于對人格商品化和濫訴的擔憂以及精神損害難以金錢量化的考慮。但隨著人們對人格利益的重視,出現了給精神損害以物質賠償的迫切需要。法國1804年民法典實現了精神損害賠償由否定到肯定的轉變。損害不僅包括財產上的損害、侵害人身權的損害,還包括了精神損害。在1900年《德國民法典》中,提出了非財產損害的概念,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對人格權的法律保護進行了明確,因此被視為“現代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起源。”[5]人是一切價值的終極來源,人的價值與尊嚴、精神世界的安寧當然需要法律的保護。相應的,法律對于人的關懷和尊重也正從物質世界向精神世界擴展。因此,將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納入到違約賠償責任中,順應了現代法律發展的趨勢。
四、違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在我國適用的現狀
(一)在司法實踐中的操作
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有些法院在處理合同違約案件時,對當事人在訴訟中提出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是予以部分支持的。如“程某訴某婚慶服務社案”就是其中之一。該案案情為:程某(原告)與某婚慶服務社(被告)簽訂了婚慶一條龍服務合同,但被告并未按照合同約定準時提供彩車和化妝服務,而且由于被告的攝像機出現故障,導致婚禮過程中許多重要片段和場景未能通過錄像得以記錄。原告認為被告的違約行為對其造成了極大的精神損害,提起訴訟要求被告返還服務費200元并支付精神損害賠償金3000元。該案后經調解,由被告給付原告精神損害賠償費1600元。[6]
此外,還有羅某等訴某市殯葬管理處賠償案、馬某訴某市某美容院賠償案等案件中,法院均支持了當事人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但法院并沒有明確闡明精神損害賠償與所涉合同之間的關系,更多的是基于公平原則,或是通過調解結案,意義不大。
當然,實踐中也有許多否認違約精神損害賠償的案例,如戴某等訴某婚紗攝影公司案等。
(二)學界的爭論
我國民法理論界對于違約責任中是否包括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眾說紛紜,但主流觀點是持否定態度的。大多數學者認為合同責任是財產責任,而精神損害賠償責任屬于非財產責任,故在合同責任中不應當包括精神損害賠償,對于精神損害賠償的救濟只有在侵權責任中才能提出,(如,王利明教授的觀點[7])。但也有學者認為,在一定情況下應承認違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例如,有學者指出:既然我國《民法通則》中規定“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時,可以要求賠償損失”,那就等于說是承認精神損害賠償的。這些規定雖然是針對侵權行為而言,但并不意味著不能適用于某些違約行為。值得注意的是,現在支持違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學者有日益增多的趨勢。
(三)立法上的一些規定
我國現行的法律雖然沒有在違約責任中給予精神損害賠償以明確的規定,但在《民法通則》及《合同法》的相關法條中均明確規定了賠償損失是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的一種形式,不過并未界定“損失”的范圍。依立法者的理念,該損失應該是不包括精神損失的。隨著最高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的頒布施行,更加確定了我國現行法律僅對侵權導致的精神損害提供救濟,強調精神損害是由侵權行為引起的。
但在有的法律中卻并非涇渭分明,如《產品質量法》中規定的產品責任,就可以看作是侵權責任和合同責任兩者的競合。可以在提起的違約之訴中,要求對因產品缺陷引起的非財產損害進行賠償。《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規定經營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務造成人身傷害或人員死亡,經營者要支付殘疾賠償金或死亡賠償金。有關部門規章也規定對客運合同、醫療合同、勞動合同履行中發生的人身傷害或死亡要給予殘疾賠償金或死亡賠償金,而這些賠償金中就包括了對傷殘者和死者家屬的精神損害賠償等等。由此看出,立法上的不完善,導致司法實踐的不統一。
五、努力構建我國違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
對于我國違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建立,是否能考慮通過對《合同法》中的“損失”進行擴大性解釋,使其包括財產性損失和精神損失,來實現對違約精神損害的救濟。因為以上所說的“損失”未限定于財產性損失,只要不作縮小解釋,完全可以包括精神損失。合同法中既然規定了完全賠償原則,那么將“精神損失”納入“損失”之中也是題中之意。既然“侵權責任”和“違約責任”在民事責任體系中是處于同等地位的,那么為何前者中的“責任”既能包括財產損害又能包括精神損害賠償,而后者卻不能都包含呢?
總之,對于因違約行為給當事人造成精神損害的,能否在違約之訴中進行賠償,我國現行的法律中并沒有明確禁止。因此在民法典的總則中明確規定違約精神損害賠償的一般適用原則,同時規定適用的限定性條件,對于符合條件的精神損害給予違約損害賠償救濟也是可以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