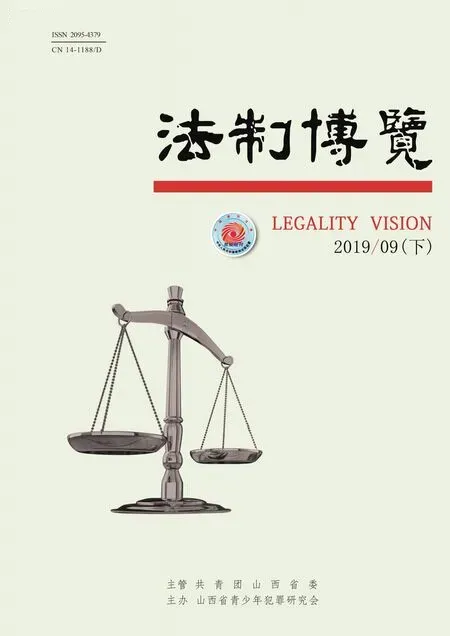居住權立法的制度構想
譚茹今
山東師范大學法學院,山東 濟南 250358
早在《關于在我國物權法中設置居住權的幾個問題》的文章中,錢明星教授就對居住權的特征、作用、歷史沿革和效力進行了表述,隨著社會主義法制不斷發展,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這項權利。學界對于是不是應該正式確立居住權的制度大致分為兩派,其中江平、申衛星等為代表的一派學者支持我國設立居住權制度,而梁慧星、房紹坤等學者們的觀點則是目前我國設立居住權是沒有意義的。
一、設立居住權的必要性
(一)解決老年人的住房問題
中國已開始邁進了老齡化社會,如何養老開始漸漸變為社會愈加在意的首要問題。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導致社會的醫療、養老體系雖然范圍較廣,但保障的力度卻較小,導致很多老年人在子女贍養不足且自身無法承擔日常生活的情況下,將自己的住房賣出變現以獲取一定的收入來承擔生活費用。
子女對于父母具有贍養義務,這是一項強制性規定,父母可以去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子女承擔責任。但這是一種相對缺少穩定性的債權,而且沒有監督的部門,所以實際操作相對較難。而居住權如果設立,其定性應為一種物權,其穩定強于贍養請求權,可以進一步提高老人最終獲得贍養而老有所養的概率。如果設立了居住權的制度,一方面可以保證老年人有最基礎的生活住處,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讓老人在將自己的房屋轉讓或贈與子女之時,仍然能夠保障自身能夠居住的權利。
(二)解決離婚后經濟困難一方的住房問題
根據《婚姻法》規定的是夫妻雙方的資產共有制度,準確來說是婚后所獲取的財物共同制,分別對于個人財物和夫妻共同財物進行了區分。一旦夫妻選擇結束婚姻關系,則只分割夫妻共同財物部分。如果夫妻一方個人的財力雄厚,婚后所得的共同擁有的部分較少,一旦離婚,則對于處于弱勢一方容易造成無法保證正常生活的嚴重困難。雖然婚姻法也規定了離婚時如果其中一個存在生活困苦的現象,另一個應從個人資產中給予部分補助。但應幫助到一個什么樣的程度,也就是應如何幫助才稱得上適當,這個在司法實踐中是很難進行界定的。如果明確規定了居住權的制度,則可以解決上述問題,在離婚訴訟中可以判決為離婚后生活較為困難的一方設立居住權,但其實所有權還在另一方手中。實際上,在物權法制定之前,最高院的司法解釋就已經對居住權進行了規定,但因為物權法并沒有進行規定,而使得該項司法解釋有些蒼白,沒有特定的法律地位,不具有物權法的效力而只能變為一種債權性的權利,效力較低。
(三)解決當下社會環境住房壓力大的問題
社會發展至今,租房居住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從法律上來講,房屋的租賃時建立在租賃合同之上的權利,不具備物權那樣的絕對穩定性,而居住權制度則提供了另外一種選擇的方式,對于那些無經濟能力購買商品房而又不愿意租房居住的人來說,可以通過購買房屋的居住權予以解決。
二、設立居住權的可行性
對于設立居住權的支持觀點,筆者在本文中不再贅述,以下僅對學界的反對觀點進行統一概述:
一是居住權制度不適用于我國的法律體系。居住權的概念產生于地役權與人役權的二元模式,而我國并沒有對地役權和人役權進行約定的區分,因此設立居住權的法律基礎在我國法治背景之下并不能合理存在。
二是居住權與我國固有的社會基礎之間的沖突。我國對于家庭依附觀和社會的基本倫理都很重視,而居住權制度存在的意義是為了改變西方國家的繼承關系和不太緊密的家庭親屬關系,因此移植居住權制度進入我國社會法制,肯能會造成“水土不服”與我國人文大環境等社會基礎產生沖突。
三是居住權將對作為所有權的物權產生限制。一旦搭建了居住權的基本內涵,相當于在房屋的所有權之下由存在了另一項權利,這樣極大限制了其所有權人對于所有物的處分權利,附著于房屋之上的居住權將極大地增加該不動產的封閉性,削減了房屋作為物的流通性。
筆者認為,居住權的家庭倫理屬性已慢慢喪失,當代社會已經將其由固定的人占有和使用特定房屋的一項權利轉變成了居住人對于全部或其中一些的房屋享有的占有或使用的權利。居住權的人役權屬性已漸漸被改變,在這種前提之下,我們是否還需要堅持居住權的人役權屬性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了。
對于居住權是否可能構成限制房屋所有權轉讓的限制性因素,在筆者看來,并非一定如此。居住權本身具有可轉讓的屬性,可以通過轉讓該項權利而使權利人獲得收益。且如今學界對于居住權的定義,倫理色彩已逐漸剝離,居住權的使用范圍也不僅僅局限于家庭婚姻關系,居住權人可以根據自身情況靈活選擇是否轉移部分或全部權利和利益。如果所有權人轉讓的是所有權,則可同居住權的權利人達成一致意見,在轉讓所有權的同時將房屋之上附著的居住權一并處分,從而并不影響房屋轉讓的靈活性和有效性。
居住權應定義為一種物權,比之債權則更加直接,這種直接體現在居住權人可以直接對其享有居住權的房屋進行支配,這種支配是絕對的、排他的,而居住權的這種絕對性屬性,其賦予物之上的物權保護,能夠實現物利用價值的最大化。
三、居住權的制度設計
(一)居住權的主體設計
根據當前學界關于居住權的討論,大體上將居住權分為房屋使用權、出租權、物上請求權和房屋轉讓時得以優先行使的優先購買權。下面筆者將分別進行解釋說明:
1.使用權。居住權人擁有的為了自身生活所需而使用房屋不動產的全部或部分的利益,該權利應遵循合理原則。所謂合理即居住權既要充分安排好權利人的生活所需,即保障其與房屋所有權人包括但不限于家庭成員的其他分子與其共同居住,并享有該房屋之上附著的其他物權。但同時,又要對居住權予以限制,不能對該權利作擴大化解釋,不得侵害房屋所有權人的合法權益。
2.出租權。能夠受到居住權保護者,往往都因為經濟實力較弱而無力購買一套不動產的所有權,居住權允許出租,則能緩解租住者的經濟負擔。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居住權的權利人和所居住房屋的所有權人往往具備親屬關系,如果打破這種親屬關系,可能會喪失居住權人和房屋所有權人之間的信任基礎,因此,允許居住權人將對于房屋不動產享有的居住權對外出租,應以不損害房屋所有權人的合法權利為限。
3.物上請求權,該權利在民法上的定義及當權利利益受到損失時,受到損失的人享有要求損害人排除妨害、消除危險、停止侵害、恢復原狀的權利。物上請求權是物權所具有的固有屬性,因此該權利無需多言,應列為居住權的基本權利。
4.優先購買權。在居住權制度下設立優先購買權,在權利人對外轉讓該不動產的所有權利時,在給出的相同經濟利益的條件下應允許該房屋之上附著的居住權的權利人享有首先得到該不動產所有權的權利。并且該項設定應為物權上排位優先的權利,其效力還應高于擁有債權屬性的租賃權。
(二)居住權的取得和消滅
對于居住權是如何獲得的,可以參照傳統物權的獲得方式,分為依法律取得或者依雙方合意取得。法定獲得即根據相關法律的具體內容或根據法官的文書取得,而意定獲得則包括實行轉讓、贈與或遺囑等方式獲取。而居住權的消滅方式則應按照傳統物權的消滅方式作同等定義,權利人死亡、權利人拋棄、撤銷等。
四、結語
事實上,居住權的內涵外延其實早已超越了居住的基本范疇,逐漸演變成了以占有、使用為基本內容的一項投資性權利,而不再是單純的居住屬性。結合國情現狀,我國的立法方向就是要構建多方面供給、多道路救濟、租房和購房雙管齊下的住房制度,讓廣大人民群眾做到住有所居。因此,居住權的確立對于我國國情而言富有極大的現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