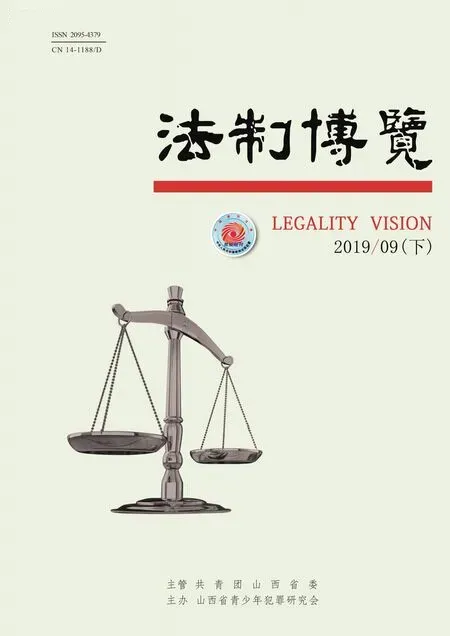未成年人監護制度之思考
趙飛雪 陳春輝
北京市京師(哈爾濱)律師事務所,黑龍江 哈爾濱 150090
監護是保護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合法權益,彌補其民事行為能力不足,協助其通過民事法律行為事先自身利益的法律制度。然而我國監護制度立法起步較晚,水平落后。未開始著手編纂民法典時,我國成年人監護制度立法體現在《民法通則》第二章中,未成年人監護制度除在《民法通則》中有所規定外,在《婚姻法修正案》、《未成年人保護法》、《收養法》、《義務教育法》等法律中均有所體現。此種立法模式具有諸多不足之處。首先,此種立法是一種廣義監護,并未區分親權與監護,兩者的性質不同、權利主體范圍不同、權利內容與范圍不同、采取的立法原則不同、產生的原因亦不同[1]。模糊區分親權與監護使得同樣作為監護人,父母基于親緣關系需要承擔更為特殊的權利與義務;其次,《民法通則》并未對監護制度進行系統的、整體的規范[1],僅僅將監護歸于民事主體制度,然而監護法律關系旨在通過調整監護人與被監護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從而實現監護人與被監護人之間的利益平衡。將監護制度放入民事主體部分規定顯然忽視了監護制度的人身性以及其與婚姻、家庭和親屬密不可分的特性,將監護規定于民事主體制度中,會使內容比較單一空洞,缺乏可操作性。在實踐中出現無法解決的情況時,需要通過其他法律或者司法解釋予以補充,具有滯后性。
現代監護制度應當以保護被監護人的合法權益為首要目標,各國早已不再將監護完全歸屬于私法自治的法律領域,而是由公立機關承擔更多的監護職責,通過專設國家機構對監護進行監督。因此,民法典的編纂應當從體系與結構等多方面調整、完善監護體系。首先,監護體系應當以被監護人的利益為本位,符合被監護人最佳利益原則,既堅持人格平等,也堅持實質平等。其次,監護制度應當以社會化、公法化為導向[2]。對于國家公權力機關、社會機構介入監護的限度,學者們具有不同的觀點。有的人認為,父母應當不再作為未成年人的監護職責主體,而是作為國家強制賦予的責任替代者和義務履行者。父母受國家的監督和輔助,在父母不能履行這一職責時,國家應當擔負起實際責任[3]。有的人則認為,父母監護基于親子關系,仍屬于私法領域,不能完全摒棄私法自治。公權力介入監護應當符合比例原則。雖然親子關系在立法上的趨勢是私法公法化,但仍應當明確公權力的介入必須以謙抑的態度保持一定限度,盡量采取替代性措施,不使子女簡單輕易地脫離親權(父母責任)[4]。
筆者對現代監護制度本位選擇以及職能轉變的思想持認可態度,人權至上的今天,未成年人作為弱勢一方,以其利益為首要保護對象是毫無疑問的。只是,在公權力介入監護的限度這一問題上,筆者更為認可后者的觀點。“老牛舐犢”、“羊羔跪乳”、“烏鴉反哺”這些典故自古以來便指導世人親情是最為牢固的感情。父母的照管義務應當來自于親權(父母責任)。親權(父母責任)是基于血緣關系而自然產生的,法律應當對其予以確認。親權(父母責任)對未成年人權利的保護理應處于第一順位,優先于其他任何權力(包括公權力)。在親權(父母責任)可以充分保證未成年人利益時,便無需通過監護制度另行保護。相反,如果將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照管歸屬于國家公權力的授權,則十分不利于中華家庭文化與倫理道德的傳承。公權力機關與社會機構應當作為監督者與輔助者,在依親權(父母責任)無法切實合理保護未成年人權利時,得以依國際人權公約、憲法之精神,為保護未成年人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參與權而成為監護職責主體。
因此,筆者認為,民法典關于未成年人監護制度的制定應當借鑒大陸法系各國民法體例,依據《民法總則》“以家庭監護為基礎,社會監護為補充,國家監護為兜底”的原則性規定,將婚姻與家庭單獨成立一編,適用親權(父母責任)與監護二元結構。同時,立法者需要在私法自治與公法干預之間找到平衡點,兩者合力保證未成年人平穩、健康成長,實現保護未成年人利益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