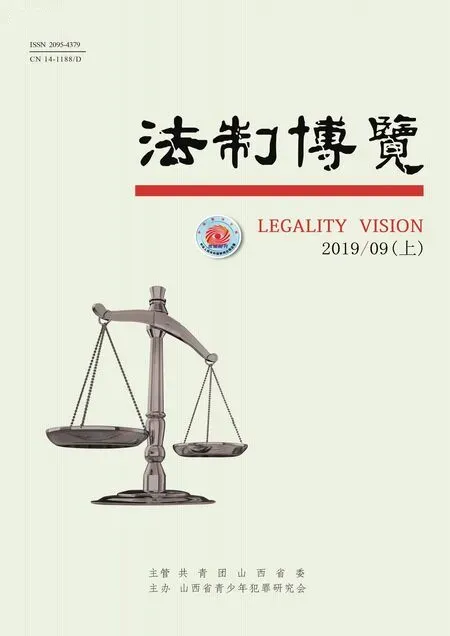淺析見義勇為的法律保護
巢金飛
渤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遼寧 錦州 121000
一、法律視角下的見義勇為
當前社會視角下的見義勇為,充滿了道德的光芒,為世人所推崇。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若是遇到不義之事消極旁觀,為人們所不齒、為道德所譴責。見義勇為之人皆是道德高尚的,道德要求我們遇到不平事要勇敢站出來,救人于危難。法律是冰,道德似火,雖然存在諸多差距,但其本質是一樣的,不能得到道德認同的法律被視為惡法。道德要求我們應樂于助人,當見義勇為,為除出人們的后顧之憂,法律著重保護見義勇為行為人的利益。
(一)見義勇為的法律構成
從民法基本理論來看,見義勇為是一種不以成立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為目的事實行為。見義勇為是一種救助行為,具有強烈的利他主義色彩,“義”強調行為的道德性、“勇”強調行為的主動性。見義勇為是指在沒有法定或約定義務的自然人,在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遭受到侵害時,不顧自身利益,勇敢相助的行為。所以,其構成要件有三:(1)主體是自然人;自然人見義勇為不以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為前提,未成年人亦可成為見義勇為的主體;(2)沒有法定或約定的義務;(3)為維護他人利益。救助人在實施見義勇為行為時,是具有保護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不受侵害為前提的主觀意思所做出的救助行為,是一種利他的行為,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如果為了保護自身權益而作為同時也保護了他人的利益,同樣也構成見義勇為。
(二)見義勇為與無因管理的區別與聯系
無因管理與見義勇為的關系極為密切。兩者是一般性與特殊性的關系。一般認為,無因管理的構成要件有:(1)管理人沒有法定或約定的義務;(2)管理人要有為本人管理的意思;(3)管理人需要實施管理本人事物的行為,且該行為不得違反本人明知或可推知的意思。而實踐中的無因管理事例大多可以稱之為見義勇為。
見義勇為與無因管理有很多的共通之處,兩者主體上都以行為人都沒有相關的法律義務與特殊義務為前提,都不要求行為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①;主觀方面都有保護保護國家、社會、集體或他人利益的意思。在這兩個方面,見義勇為與無因管理的內涵是基本一致的。
見義勇為相對于無因管理又具有特殊性。就見義勇為行為特點而言,見義勇為可能會涉及侵權人、受益人和見義勇為行為人等三方主體,但是絕大多數的無因管理只涉及管理人和本人兩方主體;見義勇為往往發生在情況緊急的條件下,多表現為受助人正在遭受侵害或者處于危難中,而一般的無因管理無需具備情況緊迫的條件;見義勇為行為人在實施救助行為的過程中可能遭受人身損害和財產損失,且可能存在損害受助人或者無辜第三人的利益②,而一般的無因管理很少會涉及人身損害,更多表現為在管理過程中所支出的必要費用。
二、法律對見義勇為的保護
(一)受益人補償
在實踐中,行為人實施了見義勇為的行為,在這個過程中遭受到了人身損害或者財產損失而尋求法律援助,在此種情況之下,法院大多適用無因管理相關法律規定,判決由利益關聯方對見義勇為行為人給予適當補償。即由受益人補償或侵害人賠償見義勇為行為人的損失。
無因管理與見義勇為存在共性,在一般情況下,《民法總則》中關于無因管理的相關規定可以類推適用見義勇為產生的法律問題。《民法總則》第121條和183條確立的受益人補償規則,與《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中規定的:“救助人實施救助行為致使自身利益受損,在沒有侵權人、不能確定侵權人或侵權人缺乏賠償能力時,救助人可以請求受益人根據收益多少來給予適當補償”相呼應,由此我們可以推出,當見義勇為行為人實施求助行為致使自身或他人利益受損,在存在侵害人的情況下,侵害人賠償該損失為第一順位,只有在沒有或不能確認侵害人,又或是侵害人不足以賠償損失的情況下,才由受益人適當補償,受益人補償則是第二順位。法律條文中“適當”一詞在司法實踐具有相當大的活性,基本依賴與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法官在個案中,在選擇“適當”數額時通常考慮的因素有:見義勇為行為人因見義勇為遭受的損失;受益人在見義勇為行為人的救助下挽回的損失數;受益人的經濟狀況等因素,綜合考量以適當確定數額。③在存在侵害人的情況下,見義勇為行為人的損失在大多數情況下由侵害人承擔,只有在侵害人的經濟狀況不足以彌補見義勇為行為人損失的前提下,才能適用公平原則,由受益人適當補償。
(二)責任豁免
由于見義勇為與無因管理存在共性與個性差異,實踐中,一律適用無因管理的相關法律規定有時難以有效解決見義勇為產生的法律問題。因為在實踐之中,存在見義勇為行為人因救助行為的不當造成被救助者或者無關第三人的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失。在這種情形下,顯然無法適用無因管理的規定,而在以往司法實踐中,由于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法官只能依照《侵權責任法》的相關規定,判決見義勇為行為人承擔賠償損失的責任。
為應對道德滑坡的窘境,有效維護見義勇為行為人的利益,《民法總則》第184條應運而生,因見義勇為而造成受助人或者無關第三人人身或財產損失的,行為人不承擔賠償責任,由此見義勇為致害的問題得到了有效的解決。當人們在遇到他人危困之時,可以毫無顧慮的見義勇為,對他人施予援手,不用再擔心“惹禍上身”。《民法總則》正式頒布之后,有學者對這條規定持否定態度,認為不應當排除見義勇為行為人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損害的情況。筆者認為,就這條的立法目的而言,是為了挽救道德滑坡,以弘揚社會正氣,傳播正能量。而在《民法總則》草案中,并沒有排除故意或過失承擔責任的情況,但在正式頒布的條文中刪除了“故意或過失”的相關內容,體現了公眾迫切要求以立法形式對道德滑坡的社會進行防治的要求,讓人們對于見義勇為不再存在任何顧慮,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法律對于見義勇為行為人的傾斜保護,彰顯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價值追求。
三、結語
道德是感性的,法律是理性的。兩者看似截然對立,但其本質是相通的。就像是冰與水一般,雖然表現形式不一樣,但本質是一樣的。見義勇為在道德受世人推崇,法律就當對其給予相應的保護,以維護法律與道德的內在統一。在挽救社會道德滑坡,弘揚社會正氣,法律就當發揮其導向作用,維護見義勇為人的合法權益,以傳播社會正能量。
[ 注 釋 ]
①李金國.論共同侵權行為之“共同性”的認定標準[D].中國政法大學碩士論文,2017.
②賀光輝.見義勇為行為法律保護之不足與完善[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7,25(3):133-144.
③侯新啟.見義勇為的法律救濟與保障[D].貴州大學碩士論文,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