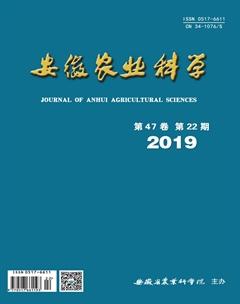政府主導的農地流轉對農戶收入影響效應研究
柯為民
摘要?基于武漢、鄂州2市的農戶調研數據,分析政府主導下的農地流轉對不同兼業程度轉出戶家庭收入的影響。研究發現政府主導的流轉會降低純農戶與 Ⅰ 兼農戶的農業收入,提高 Ⅱ 兼農戶的農業收入;流轉還會提高 Ⅱ 兼農戶的非農收入,而對純農戶與 Ⅰ 兼農戶家庭非農收入影響不明顯;最終政府主導下的流轉使得純農戶和 Ⅰ 兼農戶家庭總收入下降,Ⅱ 兼農戶家庭總收入上升。
關鍵詞?政府主導;農地流轉;兼業農戶;農戶收入
中圖分類號?S-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517-6611(2019)22-0261-05
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farmers in Wuhan and Ezhou,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led formland circulation on household income of different types of parttime farmers.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governmentled circulation will reduce parttime farmersⅠand pure farmers agricultural income and improve the agricultural income of parttime farmers Ⅱ; the transfer will increase the nonagricultural income of parttime farmers Ⅱ,while the impact on the nonagricultural income of parttime farmersⅠand pure farmers was not obvious; the transfer under the governmentled eventually makes parttime farmers ofⅠand pure farmers?total income decreased,and the total income of parttime farmers Ⅱincreased.
Key words?Governmentled;Farmland circulation;Parttime farmers;Household income
農地流轉不僅能解決當前中國農村土地利用細碎化及耕地撂荒問題,而且它還促進了農業結構調整和農民增收[1]。在農地自由流轉市場中,土地總是由低生產率的家庭流向高生產率的家庭,高生產率家庭通過轉入土地實現適度規模經營,從而促進家庭收入的增長,而低生產率的家庭通過轉出土地,實現勞動力向非農部門的轉移來促進家庭收入的增長[2-4]。然而對于轉出農戶來說,家庭非農收入與其轉出土地可能性存在相互促進的關系。如許恒周等[5]采取協整模型研究農民非農收入與農地流轉的關系,研究得出非農收入與農地流轉之間互為雙向因果關系。當前,我國的農地流轉的組織模式主要有自發流轉與政府主導流轉2種形式,不同組織形式的流轉對農戶家庭的收入影響也存在差異性。近年來不少學者對不同組織模式下的農地流轉與農戶收入的關系進行了研究。
在農戶自發流轉的研究方面,薛鳳蕊等[6]、李中[7]分別基于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的農戶調研數據和湖南邵陽市跟蹤調研數據,運用雙重差分模型(DID)研究農地流轉與農民收入的關系,他們的研究結論都顯示參與農地流轉的農戶家庭收入明顯增加。朱建軍等[8]基于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數據,運用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分析了農地流轉對我國農戶收入與收入分配的影響,研究結論顯示土地流轉增加了農戶收入,但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農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陳飛等[9]運用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和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中的農村家庭數據,分析農戶農地流轉決策行為并評價福利效應,研究發現轉出戶的凈收入效應大于轉入戶的凈收入效應。農戶自發流轉是在農戶理性決策下自主選擇的行為,理性行動者都會采取最優策略實現自身效益最大化,因此,自發流轉都能使轉入戶與轉出戶的家庭收入增加。
在政府主導流轉的研究方面,諸培新等[10]運用雙重差分模型(DID)對比分析政府主導型和農戶主導型農地流轉對農戶收入影響差異,結果顯示自發流轉的農戶家庭收入增加值相對于政府主導流轉的農戶家庭收入增加值更高。張建等[11]采用內生性處理回歸模型研究政府干預下農地流轉對農戶收入的影響,研究發現在政府干預下轉入戶家庭收入顯著增加,而轉出戶家庭收入增加不顯著。這兩項研究體現了政府主導的流轉與農戶自發流轉對家庭收入影響的差異性,但是他們的研究并沒有回答政府主導下流轉對轉出戶收入增加不顯著的原因,且對于不同類型的農戶,在政府主導的流轉下,轉出土地對其家庭收入的影響程度如何也可能是不一樣的。為此,筆者基于現有的研究,進一步探討政府主導下的農地流轉對不同類型轉出戶家庭收入的影響,即討論轉出面積對不同類型農戶家庭收入的影響效應,以期為政府主導的流轉獻言建策,最終實現政府高效行政、農戶收入增加、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目標。
1?理論分析
農戶家庭的收入由農業收入、非農收入與轉移性收入3部分組成。該研究的農業收入包括開展種植業所獲得的農業經營性收入與農地流轉租金收入;非農收入是指家庭成員提供勞動力而獲得的工資性收入以及進行商業經營所獲得的非農經營性收入。該研究只討論政府主導下的流轉,補貼發放的形式與標準統一制定,因此對轉移性收入不過多深究。
政府主導的流轉是在政府強制下進行統一集中連片流轉,政府代替農戶與用地主體談判、簽約[10],農戶農地流轉行為不會受農戶自身各方面因素的影響,農戶無法通過理性思考決定自己是否流轉土地或者流轉多大面積的土地。但是農戶作為家庭經濟活動的主體,其理性的行為邏輯是轉出土地后,合理的配置勞動力和生產要素等以實現產出高效化、就業完全化和收入最大化的目標[12]。在政府運用行政力量主導的農地流轉中,一些農業生產效率高的農戶也不得不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轉出土地,然而不同農戶家庭的農業勞動能力與非農勞動能力具有一定的差異性,因此,政府主導的農地流轉對不同類型農戶的家庭收入可能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1.1?政府主導的流轉對不同兼業轉出戶家庭農業收入的影響
農戶土地轉出后,經營土地面積減少,相應的資本與勞動力要素的投入也就減少,其種植收入減少,但是可以獲得農地租金。因此土地轉出對不同兼業程度農戶家庭農業收入的影響差異就取決于不同農戶家庭種植收入減少量與獲得租金的對比。在政府主導的流轉中,政府協商統一流轉租金,不同兼業戶轉出相同面積、同等質量的農地會獲得相同的土地租金。但是不同兼業戶其農業生產效率不同,因此在政府強制流轉過程中,不同兼業戶轉出相同面積的土地,其種植收入的損失存在差異。現有的主流觀點認為,農戶兼業使得農業被不同程度的副業化,降低了農業生產的效率。從農業生產效率分析,純農戶會花費最多的勞動時間在種植業上,其可以精耕細作以得到更多的產出,故其農業生產效率相對較高。而 Ⅰ 兼農戶與 Ⅱ 兼農戶花費在種植業上的勞動時間相對較少,耕作土地較為粗放,其農業生產率較低。故農戶兼業程度越高,其農業生產效率越低[13-14]。因此,不同類型農戶轉出土地后,Ⅱ 兼農戶家庭農業收入增長量最大(增長量有可能為負值),Ⅰ 兼農戶次之,純農戶家庭農業收入的增長量最小。
1.2?政府主導的流轉對不同兼業轉出戶家庭非農收入的影響
對于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純農戶而言,由于純農戶家庭長期從事農業生產,家庭內部的要素結構和人力資本更多的適用于農業生產方面[15],并且缺乏非農就業經驗,故其轉出土地后剩余勞動力難以轉移至非農部門。而對于兼業戶而言,兼業戶在農忙時期需要非農勞動力回鄉幫助進行農業生產[16],而當土地轉出后,經營土地面積的減少亦能夠減少非農就業人員回鄉進行農業生產的時間,實現農戶家庭非農收入的增長。另外,兼業戶家庭成員在非農工作中建立起來的社會資本和社會網絡將更加容易幫助原來在農業部門工作的剩余勞動力實現非農就業[17]。另一方面,在政府主導的農地流轉下,政府會通過加強農村勞動力非農職業培訓等舉措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就業能力,提高其找到非農工作的機會,從而提高農戶家庭的非農收入[10]。因此,綜合來看政府主導下農地流轉對純農戶收入增長效應難以判斷,但是會促進兼業戶家庭非農收入的增長。
1.3?政府主導的流轉對不同兼業轉出戶家庭總收入的影響
政府主導下的農地流轉對不同兼業轉出戶家庭總收入的影響取決于上述2種收入的綜合影響以及2種收入各自占總收入的比例。一般情況下,轉出戶非農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一般比較高,因此,政府主導的農地流轉對轉出戶總收入的影響方向與非農收入的影響方向一致。
2?數據來源、模型設定及變量選取
2.1?研究區概況與數據來源
武漢、鄂州2市作為武漢城市圈農村產權制度創新的試驗先導,2市率先分別于2009和2012年成立了農村綜合產權交易所(中心),農地流轉市場極其活躍,在農地流轉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經驗,是“1+8城市圈”農村產權交易市場平臺搭建的基礎。該研究使用的數據來自2015年7月針對2市典型地區農地流轉狀況的問卷調查,調查區域涉及武漢市江夏區安山鎮、五里界鎮,鄂州市鄂城區燕磯鎮、梁子湖區涂垴鎮共計26村,共發放問卷300份,回收有效問卷287份,問卷有效率為95.67%,其中轉出土地樣本253份,自發轉出的15份樣本,政府統一流轉的238份樣本,該研究所使用的數據為238份政府統一流轉樣本。樣本來源情況見表1。
2.2?模型的設定
農戶家庭的收入不僅受到農地流轉的影響,而且還會受到家庭特征以及外部市場環境的影響。該研究討論的是政府主導下的流轉,大部分農戶都是被動的流轉出土地,因此,可以直接用轉出的土地面積變量替代農地流轉變量來分析農地流轉對不用類型農戶家庭收入的影響。將政府主導下的流轉對農戶家庭收入影響的計量模型設定如下:
式中,Yk為被解釋變量——家庭收入,其中k=1,2,3分別表示家庭的農業收入、非農收入和家庭的總收入;S為關鍵解釋變量——土地轉出面積;Xi表示家庭層面的控制變量;Vi表示外部市場環境的控制變量;α0、α1、βi、γi為待估參數,ε為隨機誤差項。
2.3?變量選取及樣本描述性分析
2.3.1?農戶的類型描述。參照廖洪樂[18]的研究將農戶按照流轉前家庭勞動力的務農狀況及收入占比狀況分為3類農戶,其中純農戶為52戶,占比為21.85%,Ⅰ 兼農戶為137戶,占比為57.56%,Ⅱ 兼農戶為49戶,占比為20.59%。兼業戶占到調查農戶樣本的75%以上,說明農戶兼業在農村已經是普遍的現象,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兼業是因為農戶兼業是農戶獲得額外甚至主要收入的一個重要方式[19]。
2.3.2?農戶的家庭收入描述。主要研究農戶在農地流轉后家庭收入情況,一方面要體現農地流轉面積的變化導致家庭農業生產收入的變化,另一方面也要體現由于農地面積變化導致的農地流轉收益的變化,還應考慮農地經營面積的變化導致家庭剩余勞動力是否轉移非農就業,從而影響家庭非農收入的變化。因此,該研究的家庭收入包括家庭農業收入(農地流轉收益包括在農業收入內)、非農收入兩部分。不同類型農戶的家庭收入的描述性數據情況如表2所示。土地轉出后,Ⅱ 兼業戶的家庭收入最大,Ⅰ 兼農戶次之,純農戶收入最小,這說明農戶兼業提高了家庭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20]。
2.3.3?農戶收入影響模型解釋變量的選擇及描述性統計。該研究關鍵的解釋變量為農戶轉出土地面積,通過調研的問卷直接得出。其他控制變量包括家庭特征變量與外部市場環境特征變量。家庭特征變量主要包括以下2類。①人力資本變量。人力資本的數量與質量都會影響農戶的家庭收入,因此,在數量維度選取農戶家庭勞動力數量變量,在質量維度選取戶主年齡、戶主受教育年限、勞動力平均年齡、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等4個變量。②物質資本變量。這里主要研究農地流轉對農戶家庭收入的影響,因此,物質資本變量選取農戶家庭的農地資源稟賦變量,用家庭人均承包耕地面積來表示。在外部市場環境特征變量方面,選取家庭非農勞動力的占比表示外部市場對農戶家庭的非農就業影響,選取農戶家庭是否參加過非農就業培訓來表示外部市場對農戶家庭剩余勞動力非農就業的影響,另外還要選取地區控制變量控制由于自然、地理特征以及經濟發展狀況的不同對農戶家庭收入的影響。各變量的統計數據如表3所示。
從農戶家庭層面的特征變量看,人力資本方面,3類農戶家庭擁有的勞動力數量差距不大,家庭勞動力規模大約都為3個,但是純農戶勞動力的質量不高,戶主年齡與勞動力平均年齡偏大,戶主受教育年限與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對較少;而 Ⅱ 兼農戶勞動力質量是3農戶中最高的,其中戶主年齡比純農戶平均少10.86歲,勞動力平均年齡平均小8.80歲,戶主受教育年限與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別高2.19年與0.77年;Ⅰ 兼農戶勞動力質量都介于純農戶與 Ⅱ 兼農戶之間。再從物質資本變量看,純農戶在流轉土地之后家庭人均承包耕地的面積最多(0.098 hm2),Ⅰ 兼農戶次之(0.081 hm2),Ⅱ 兼農戶最少(0.072 hm2)。雖然純農戶在轉出土地后種植收入的損失量最大,但是純農戶流轉的土地面積最多,且剩余的土地面積也最多,故流轉前他們擁有最多的土地,這就是土地轉出后純農戶農業收入最高的原因。
從外部市場環境特征變量看,農戶兼業程度越高,其家庭非農勞動力占比越高。 而從是否參加過非農就業培訓看,Ⅱ 兼農戶參加過非農就業培訓的比例最高(達到了80%),Ⅰ 兼農戶參加非農就業培訓的比例為72%,而只有58%的純農戶參加過非農就業培訓。
3?結果與分析
該研究采用Stata1 2.0對式(1)進行估計。并且對引入回歸模型的自變量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自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值)均小于5,說明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各個模型參數的估計值及R2的統計值見表4。
3.1?農業收入模型的估計結果分析
轉出土地面積對3類農戶家庭農業收入都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即轉出土地面積越大,農戶家庭的農業收入越小。這也說明了政府主導的下的農地流轉會降低農戶家庭的農業收入,轉出土地面積對農戶家庭收入影響系數由大到小依次為純農戶、Ⅰ 兼農戶、Ⅱ 兼農戶,即在政府主導的流轉下,純農戶農業收入損失最大、Ⅰ 兼農戶次之、Ⅱ 兼農戶最小。這也證明了第二部分的理論分析,在政府主導下的流轉下,純農戶農業收入的增長量最小,Ⅰ 兼農戶次之,Ⅱ 兼農戶最大。
另外,一些控制變量也對農戶家庭的農業收入產生了顯著影響。其中,是否參加過非農培訓顯著負向影響純農戶與 Ⅰ 兼農戶家庭農業收入,而對 Ⅱ 兼農戶家庭農業收入影響不顯著,可能的原因是 Ⅱ 兼農戶非農就業水平已經很高,是否參加過非農就業培訓對他們的就業選擇不會產生太大影響,而對于純農戶與 Ⅰ 兼農戶來說,家庭非農就業水平不高,參加過非農就業培訓會一定程度上增加他們找到非農工作的概率,從而負向影響他們的農業收入。人均承包面積變量顯著正向影響3類農戶家庭農業收入,即人均承包面積越大,農戶家庭農業收入越大,這與前面的描述性分析結果一致。從地區變量看,武漢市 Ⅰ 兼農戶與 Ⅱ 兼農戶的農業收入相對于鄂州市更高,一方面是由于武漢市土地租金更高,另一方面是因為武漢市更發達,農業生產技術較先進。
3.2?非農收入模型的估計結果分析
轉出土地面積只對 Ⅱ 兼農戶家庭非農收入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對純農戶與 Ⅰ 兼農戶家庭非農收入的影響不顯著,但是影響方向為正。土地轉出后,Ⅱ 兼農戶非農收入增加的可能原因是該類農戶家庭非農勞動力從事農業的機會成本在土地轉出后直接轉化成了農戶家庭的非農收入,這也就證明了理論部分兼業農戶家庭在轉出土地后節約了非農勞動力回鄉幫助生產的勞動時間。轉出土地面積對純農戶家庭非農收入影響不顯著的原因可能是純農戶家庭結構與人力資本更適合農業生產,而當土地轉出后,剩余的勞動力比較難以實現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從而導致家庭非農收入變化不顯著。Ⅰ 兼農戶家庭勞動力已經實現高效的配置,適合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在轉出土地后也很難實現向非農產業的轉移,故其非農收入的變化也不顯著。
在家庭層面的控制變量中,家庭勞動力數量顯著正向影響3類農戶家庭非農收入,即家庭勞動力數量越多,農戶家庭非農收入越高。在外部市場特征變量中,是否參加過非農就業培訓也顯著正向影響3類農戶家庭非農收入,即參加過非農就業培訓的相對與未參加過非農培訓,其農業勞動力轉移至非農業的機會更大,故其家庭非農收入也就相對更高。另外,戶主年齡、戶主受教育年限、勞動力平均年齡、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家庭非農勞動力占比都對 Ⅰ 兼農戶家庭非農收入產生顯著影響,且影響方向也與預期一致,與Wan[21]的研究結果相吻合,戶主年齡越小、戶主受教育年限越長、勞動力平均年齡越小、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長以及家庭非農勞動力占比越高,農戶家庭非農收入越高。家庭人均承包土地面積顯著負向影響 Ⅰ 兼農戶與 Ⅱ 兼農戶家庭非農收入,這表明,人均承包土地面積越大,Ⅰ 兼農戶與 Ⅱ 兼農戶就會配置更多的勞動時間在農業勞動上,增加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導致家庭非農收入下降。
3.3?總收入模型的估計結果分析
轉出土地面積對純農戶與 Ⅰ 兼農戶家庭總收入產生了顯著負向影響,對 Ⅱ 兼農戶家庭總收入產生正向影響,且影響系數由大到小依次為純農戶、Ⅱ 兼農戶、Ⅰ 兼農戶。這表明,農戶在政府主導方式下轉出土地后,純農戶農業收入的減少量不能通過非農收入來填補,純農戶轉出土地后,有部分剩余勞動力未能實現就業,使得家庭總收入下降;Ⅰ 兼農戶農業收入的減少量比純農戶小,但是也不能通過非農收入來填補,原因可能是 Ⅰ 兼農戶在土地轉出后,剩余的都是些老年勞動力,這部分勞動力也很難轉移至非農產業,實現家庭非農收入的增長;而 Ⅱ 兼農戶農業收入的減少量最小,且其可以通過非農收入來填補,最終實現家庭總收入的增加,原因可能是Ⅱ兼業農戶家庭非農勞動力從事農業的機會成本在土地轉出后直接轉化成了農戶家庭的非農收入,最終實現了家庭總收入的增加。
另外,一些控制變量對農戶家庭總收入也產生了顯著影響。家庭勞動力數量、是否參加過非農就業培訓都顯著正向影響3類農戶家庭總受入,即家庭勞動力數量越多,參加過非農就業培訓的農戶家庭總收入更高。戶主年齡、人均承包耕地面積顯著影響 Ⅰ 兼農戶與 Ⅱ 兼農戶家庭總受入,戶主年齡越小、人均承包地面積越大,其家庭總收入越多。
4?結論與討論
在當前政府主導農地大規模流轉的背景下,農地流轉必定對農戶家庭勞動力的配置與農戶的家庭收入產生影響,農戶家庭都會根據家庭預期收益最大化原則針對轉出面積的不同合理配置家庭勞動力在農業與非農業的勞動時間[22]。研究表明,政府主導的農地流轉對不同類型農戶的家庭收入的影響效應存在差異。純農戶轉出土地后,土地租金不足以補償損失的農業經營性收入,導致純農戶農業收入下降,而非農收入變化不明顯,最終導致家庭總收入的下降。Ⅰ 兼農戶擁有最優配置的家庭勞動力結構,農業勞動力和非農勞動力達到了合理的分工,當轉出土地后,剩余的部分老年農業勞動力并未能轉移至非農產業,農業收入的損失也無法完全通過非農收入增加來補償,最終也使得 Ⅰ 兼農戶家庭的總收入有略微的下降。對于 Ⅱ 兼農戶來說,低效率的農業生產使得轉出土地后農戶家庭農業收入有了略微的下降,但是 Ⅱ 兼業戶的兼業機會成本也在轉出土地后直接轉化成了農戶家庭的非農收入,非農收入的增加量大于農業收入的損失量,最終導致農戶家庭總收入顯著增加。
該研究只是選擇中部2個市的樣本討論政府主導的農地流轉對不同類型農戶家庭收入的影響,得出的結論可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從該研究的分析也可以得出一些政策性啟示:政府主導下的流轉會降低純農戶與 Ⅰ 兼農戶家庭收入,因此,為了降低政府主導下的流轉對農戶家庭總收入的損失。政府應加強對農戶進行非農就業培訓,進一步發展非農經濟,提供更多的非農就業崗位,促進農戶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從而促進轉出土地農戶家庭非農收入的增長;另外政府在推進農地流轉過程中,對那些轉出土地后剩余老年勞動力得不到轉移的家庭要給予一定的養老補助。最終使得政府主導下的流轉能實現農戶滿意、政府高效行政、地方經濟得到最大化發展的目標。
參考文獻
[1] 張丁,萬蕾.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影響因素分析:基于2004年的15省(區)調查[J].中國農村經濟,2007(2):24-34.
[2] 冒佩華,徐驥.農地制度、土地經營權流轉與農民收入增長[J].管理世界,2015(5):63-74,88.
[3] 楊渝紅,歐名豪.土地經營規模、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與農民收入關系研究: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檢驗[J].資源科學,2009,31(2):310-316.
[4] 鐘甫寧,何軍.增加農民收入的關鍵:擴大非農就業機會[J].農業經濟問題,2007(1):62-70,112.
[5] 許恒周,郭玉燕.農民非農收入與農村土地流轉關系的協整分析:以江蘇省南京市為例[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1,21(6):61-66.
[6] 薛鳳蕊,喬光華,蘇日娜.土地流轉對農民收益的效果評價:基于DID模型分析[J].中國農村觀察,2011(2):36-42,86.
[7] 李中.農村土地流轉與農民收入:基于湖南邵陽市跟蹤調研數據的研究[J].經濟地理,2013,33(5):144-149.
[8] 朱建軍,胡繼連.農地流轉對我國農民收入分配的影響研究:基于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數據[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5(3):75-83,124.
[9] 陳飛,翟偉娟.農戶行為視角下農地流轉誘因及其福利效應研究[J].經濟研究,2015(10):163-177.
[10] 諸培新,張建,張志林.農地流轉對農戶收入影響研究:對政府主導與農戶主導型農地流轉的比較分析[J].中國土地科學,2015,29(11):70-77.
[11] 張建,諸培新,王敏.政府干預農地流轉:農戶收入及資源配置效率[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6,26(6):75-83.
[12] 張蘭,馮淑怡,陸華良,等.農地不同流轉去向對轉出戶收入的影響:來自江蘇省的證據[J].中國農村觀察,2017(5):116-129.
[13] 蔡基宏.關于農地規模與兼業程度對土地產出率影響爭議的一個解答:基于農戶模型的討論[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5(3):28-37.
[14] 陳曉紅.經濟發達地區農戶兼業及其因素分析:來自蘇州農村的實證調查[J].經濟與管理研究,2006(10):90-94.
[15] 劉鴻淵.農地集體流轉的農民收入增長效應研究:以政府主導下的農地流轉模式為例[J].農村經濟,2010(7):57-61.
[16] 賀振華.農戶兼業及其對農村土地流轉的影響:一個分析框架[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06,8(2):72-78.
[17] 張智勇.社會資本與農民工就業[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7(6):123-126.
[18] 廖洪樂.農戶兼業及其對農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影響[J].管理世界,2012(5):62-70,87.
[19] 蔡昉,王德文.經濟增長成分變化與農民收入源泉[J].管理世界,2005(5):77-83.
[20] 李明艷,陳利根,石曉平.非農就業與農戶土地利用行為實證分析:配置效應、兼業效應與投資效應——基于2005年江西省農戶調研數據[J].農業技術經濟,2010(3):41-51.
[21] WAN G H.Accounting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4,32(2):348-363.
[22] 游和遠,吳次芳.農地流轉、稟賦依賴與農村勞動力轉移[J].管理世界,2010(3):6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