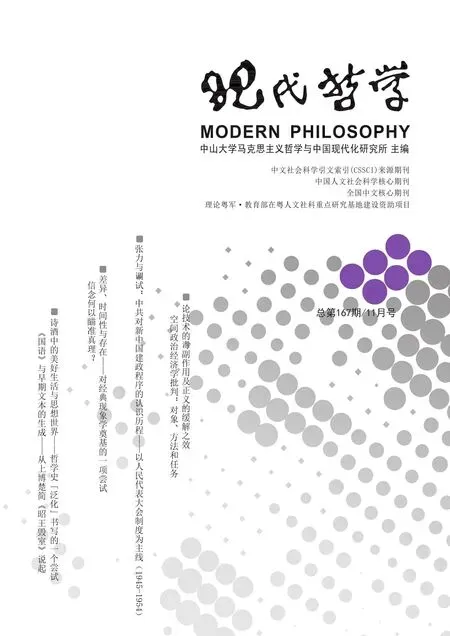論韋伯思想的“馬克思因素”
馬碧霄
在過去一百多年里,中外思想界對馬克斯·韋伯和馬克思的比較研究傾注了巨大熱情,既因為他們各自建構了一套系統性和開創性的現代思想,在深刻把握現代社會根本性問題的同時,還為現代社會科學的發展奠定了基本的思想框架和理論體系;也因為他們在思想上呈現出來的高度相似性和鮮明差異性,他們不僅名字相似,而且在研究對象、研究立場、研究廣度、研究深度等方面具有極強的可對比性。長期以來,學術界專注于韋伯與馬克思之間的異質性研究,更多是研究韋伯與馬克思在政治立場、理論觀點、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的差別。一方面,面對現代資本主義和現代社會這一共同的研究對象,韋伯和馬克思有著棋逢對手卻又針鋒相對的偉大理論成就;另一方面,這種差別正是20世紀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相互斗爭的立場體現,選擇為馬克思辯護還是為韋伯辯護,本就是現實的社會政治運動在思想上的真實呈現。事實上,作為“資產階級的馬克思”,韋伯與馬克思之間的差異,并沒有一般理解的那么“大”;而馬克思對韋伯思想的正面影響,也沒有一般理解的那么“小”。在思想史發展過程中,馬克思既是韋伯的“對手”,也是韋伯的“老師”。
作為德國統一后成長起來的第一代思想家,韋伯已經完全生活在一個深受馬克思影響的“后馬克思”世界里。在學術思想領域,馬克思為他提供了思想資源、理論視角、問題視域和研究對象;在社會現實領域,倍倍爾、李卜克內西、伯恩斯坦、考茨基等第二國際、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代表人物為他提供了政治實踐的經驗參照和批判對象。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世紀之交,作為馬克思恩格斯的“下一代人”和列寧的“同時代人”,韋伯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發生了復雜的同頻共振關系。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運動的變化,推動著韋伯思想的發展,使韋伯終其一生都在面對著“馬克思”;另一方面,韋伯思想的發展又反映出馬克思主義在那個時代存在的危機和問題,從而為20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興起埋下問題的線索和理論的伏筆。因此,我們今天既不能脫離馬克思去看待韋伯,也不能拋開韋伯去研究馬克思主義。在經過20世紀之交的思想關聯后,馬克思與韋伯、韋伯與馬克思主義之間已經產生了特殊的“同質性”思想譜系關系。實際上,“馬克思”就像一個幽靈,始終若隱若現地呈現在韋伯的思想之中。作為韋伯各階段思想形成的重要推手,“馬克思因素”在韋伯思想的不同階段發揮著不同作用。
一、早期:提供思想資源和理論視角
1883年,馬克思去世的時候,韋伯還只是一個19歲的學生。從現實生活看,他們之間并無交集;但從時代背景看,他們之間有著顯著差異,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馬克思生活在19世紀早期的“德國”,是神圣羅馬帝國瓦解后于1815年維也納會議上成立的德意志邦聯,是一個松散的邦國體制;而韋伯生活在19世紀晚期的“德國”,是1871年成立的德意志第二帝國,是在俾斯麥主導下、以普魯士為核心建立起來的強權國家。第二,馬克思生活在“落后”的德國,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都落后于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這也是馬克思在思想早期青睞青年黑格爾派的主要原因,即如何通過理性的制度批判使德國盡快擺脫落后的處境;韋伯則生活在“先進”的德國,德國在統一后的40年里實現了經濟騰飛,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強國。作為資本主義的后發強國,韋伯面臨的問題是德國如何在列強競爭的時代保持世界大國的地位。第三,馬克思生活在資本主義從早期走向興盛的時期,他既看到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的悲慘生活,也感受到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自由主義的黃金時期;韋伯生活在第二次工業革命后的資本主義發達時期,工人的生活有很大改善,但大工業社會的建立使官僚機器進一步扼殺自由,使自由主義面臨著普遍危機。第四,馬克思生活在“無階級意識”的時代,正是他首先為無產階級提供理論武器,使無產階級開始成為一個“階級”,實現了階級意識的啟蒙;而韋伯生活在“有階級意識”的時代,馬克思主義已經廣為流傳,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和工人運動已經成為政治舞臺上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韋伯在思想最初的形成階段曾經深受德國民族自由黨的家族傳統影響,但很快實現了對自由主義傳統的轉向。一方面,這與德國自由主義的特殊歷程有關。作為一種外來思潮,德國的自由主義者一開始試圖通過建立自由的憲政國家從而實現德意志國家的統一,但1848年法蘭克福議會的失敗,正式宣告了德國自由主義原有路線的失敗。隨著俾斯麥用鐵血政策實現德國的統一和崛起,德國自由主義隨之轉而擁護俾斯麥軍國體制,資產階級也試圖融入容克階級的政治體制。然而,在韋伯看來,俾斯麥的這種強權直接導致德國資產階級政治領導能力和資格的喪失。另一方面,自由主義無法回避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引發的政治運動。無論從歷史背景還是思想關系看,作為后人的韋伯都直接面對和繼承了馬克思留下來的思想遺產和從馬克思延續而來的時代問題。正如吉登斯指出的,“1848年發生的事件表現了馬克思與韋伯之間的直接歷史聯系。對于馬克思來說,事件的結果是他流亡英國,并且在思想上認清了具體闡明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體制的運動規律的重要性。在德國,1848年的失敗顯示了自由主義政治的不合時宜性,相反倒使俾斯麥的強權統治獲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功,這是韋伯整個思想形成的重要背景”(1)[英]安東尼·吉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郭忠華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第239頁。。在韋伯所處的時代,自由主義一邊受到德國現存體制的擠壓,一邊受到馬克思主義的沖擊,陷入理論和現實的雙重困境。正是從思考和應對自由主義的這一普遍危機出發,韋伯開始尋找自己的思想取向。
為了調和各階級的矛盾并改善工人階級的命運,德國于19世紀末建立了社會政策學會,通過采取介于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社會改良政策,承認工人階級的正當要求,避免工人階級采取革命行動。作為年輕一代的代表,韋伯與桑巴特、滕尼斯等人反對老一代成員把德意志國家理想化的做法,要求正確地對待馬克思。與老一代成員不同的是,韋伯這一代人熟悉馬克思的著作,認為資本主義及其階級沖突才是形成現代社會的根本動力,而現代社會只有在馬克思的理論框架中才能得到準確的理解,因此需要嚴肅對待馬克思。與馬克思最初的思想經歷相似,韋伯在思想起步的過程中也遭遇了自己的“物質利益難題”。通過研究德國東部地區的農業問題,韋伯發現東部地區的經濟變革已經摧毀了容克階級的統治基礎,并將進一步威脅德國政治體制的穩定。隨著德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相應而來的社會結構劇變,傳統的自由主義理論既不能理解、也不能解決經濟社會領域的問題和矛盾。正是在這一點,韋伯看出了自由主義的根本缺陷,并與之分道揚鑣。韋伯發現,德國自由主義在資本主義沖擊下遇到的危機,反映的正是自由主義在19世紀末存在的普遍危機,而造成這一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自身的發展,因此,“資本主義經濟系統的起源以及它對社會結構和政治組織的沖擊,就在他的社會學研究和政治思考中占據了核心地位”(2)[德]沃爾夫岡·J.蒙森:《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1890-1920》,閻克文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7頁。。
需要指出的是,韋伯在其思想形成的早期階段,正是借助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政治經濟學的視角,才從自由主義的傳統中脫身而出。和馬克思一樣,韋伯也是在遭遇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實矛盾后,轉而進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這一時期的韋伯,一方面延續了馬克思思想中最為重要的研究對象,即現代資本主義的起源、動力和進程,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概念,如階級、權力、斗爭、經濟、社會等,并在《易北河東部地區農業工人的處境:經濟發展趨勢與政治后果》(3)參見[德]馬克斯·韋伯:《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甘陽編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第37—80頁。一文中,大量使用了馬克思的這些專有名詞。正如威姆斯特所說的:“韋伯在1890年代是一個國民經濟學家,必須在一些細節中進行研究,才能發現什么才是他所特有的韋伯式方法,發現哪一個不是冠以另一個名字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形式。”(4)[英]山姆·威姆斯特:《理解韋伯》,童慶平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第1頁。在馬克思的啟發下,韋伯高度重視經濟因素對社會和政治變化的重要影響,他開始從現實而不是抽象的角度看待社會歷史的發展。與此同時,在新康德主義的影響下,韋伯也拒絕了馬克思對歷史變遷過程所做的辯證理解,尤其是對社會歷史做出類似自然科學的鐵的規律因果性解釋。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是由多個部分組成的整體,其形成和發展均是由多種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歷史的因果關系是多元的和復雜的,而不是單一的和線性的。實際上,這種多元和復雜本就是韋伯那個時代德國和西方社會的主要特點。19世紀末的德國正站在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保守主義的三岔路口,面對著相互沖突的不同階級、政黨與思潮,韋伯通過充分吸收、改造和整合不同的世界觀,最終形成自己的思想取向。在尋找思想取向的過程中,韋伯既借鑒了馬克思等不同思想的研究方法和理論視角,又保留了對這些思想觀點的異議,更為重要的是,他高度關注如何為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保守主義找到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共同基礎。正是在這一問題上,韋伯逐步走出早期的思想積累時期。
二、中期:成為揚棄對象和主要對手
1895年,韋伯在弗萊堡大學發表的就職演說《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被普遍認為是他思想正式形成的開端,也充分體現出他對馬克思思想的“揚棄”。一方面,韋伯承認斗爭是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最為普遍的狀態,也是最為根本的動力,但這種斗爭應體現為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斗爭,而不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的斗爭。在他看來,在人類為生存而進行的斗爭中,民族之間的差異和矛盾比階級之間的差異和矛盾更重要、更根本。另一方面,韋伯承認經濟權力的至關重要性,承認掌握經濟權力的階級同時也應該掌握政治權力,以及在政治權力背后的意識形態問題。與馬克思不同的是,韋伯認為經濟權力、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并不僅僅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關系,政治權力有其不同于經濟權力的特殊性和獨立性。從這兩個方面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韋伯既能夠熟練地運用馬克思的理論,也開始顯現出和馬克思觀點的顯著差異,并進一步實現了對馬克思的“發展”。韋伯不僅在馬克思已經得出成熟結論的問題領域中開辟出新的思想方向,并且通過借助和改造馬克思的概念體系,進一步構建具有自己特色的思想框架。實際上,韋伯對馬克思“階級斗爭”和“唯物史觀”兩方面理論做出的不同理解,正是他從事政治和學術雙重身份的最主要體現。在政治上,他需要重新闡釋自由主義,為資產階級提供應對階級斗爭的理論武器;在學術上,他需要重新建構社會歷史理論,用解釋社會學修正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決定論”。
在韋伯看來,隨著資本主義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原初那種誕生和維護自由主義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完全喪失了,傳統的自由主義所立足的社會基礎已經發生根本性的劇變。在新的政治、經濟、社會形勢面前,自啟蒙運動以來一直作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基礎的自然法理論已經崩潰,不能再為自由主義制度提供基本的依據和有效的辯護,這是自由主義在19世紀末遭遇普遍危機的真正根源。而且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自由主義遭遇的這場危機最終將危及自由本身。為了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維護自由制度,韋伯對自由主義進行重新闡釋,也就是把作為自由概念基礎的“抽象的理性個人”轉換為“現實的民族共同體”。通過這種概念內核的改造,韋伯消解了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基礎,把個人自由問題與民族國家問題有機結合起來,以民族主義作為自由主義新的內在支撐。在韋伯看來,對自由主義的這種改造除了能夠挽救個人自由的可能性,還能夠有效維護資本主義制度,應對階級斗爭的沖擊和挑戰。在馬克思主義“工人沒有祖國”的口號指導下,歐洲各國工人階級的政治運動呈現出跨越國界的國際主義特征,并力圖接管各國政權。為了維護德國資產階級的政治領導權,韋伯試圖用工人階級的民族屬性替換工人階級的階級屬性,以此轉換工人階級的運動方向。在韋伯看來,一國內部的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盡管存在階級對立,但雙方的利益與維護民族國家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此,資產階級只要能夠讓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充分獲益,就能引導并掌控工人階級的力量以確保穩固地掌握政治領導權,從而推行一種世界強國的對外政策,讓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在德國的海外擴張中共享利益。需要指出的是,韋伯在這一時期已經改變了“階級”概念在馬克思語境下的內涵,使“階級”從一種人類生存狀況的普遍抽象“下降”成為人類社會的身份群體之一。在韋伯看來,“民族”作為另一種真實的身份群體,能夠把一國之內的階級斗爭轉換成為國際舞臺上的民族斗爭。因此,資產階級只要用民族策略替代階級策略,就能有效瓦解工人階級革命的正當性, 使之成為能夠同時包容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保守主義的共同基礎。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對唯物史觀所做的經典表述,后來被簡單概括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使歷史唯物主義被簡化為“經濟決定論”。盡管馬克思恩格斯在世時一直反對這種理解,但在韋伯那個時代,歷史唯物主義確實被廣泛理解和傳播為一種“經濟決定論”。一方面,韋伯高度肯定馬克思對經濟結構與社會政治結構之間具有同構性的重要發現。韋伯對人類社會歷史變遷,尤其是資本主義的起源和運行方面的實證分析,無論是概念、論據還是結論,幾乎與馬克思保持高度一致。正如其夫人瑪麗安妮所說:“韋伯極為欽佩卡爾·馬克思的杰出工程,把探尋各種事件的經濟與技術成因看作是極富成效、的確是特別具有新意的啟發性原則,可以用來指導知識探索進入以往不為人知的全部領域。”(5)[德]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421頁。另一方面,韋伯也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論斷至少存在三個方面的概念不清晰:一是馬克思從未清晰地區分“經濟因素”“由經濟決定的因素”“與經濟相關的因素”,甚至沒有對“經濟因素”“技術因素”做出區分;二是馬克思沒有對經濟基礎如何“決定”上層建筑做出詳細說明,而更多的是使用一些描述性的詞語來表達這種關系,如“制約”“與之相適應的”“或快或慢的”“一目了然的”等;三是馬克思在上層建筑方面存在理論的空場,比如他對“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更多的是從生產關系而不是其他關系的角度做闡述,他沒有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生活(6)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曾把資產階級的國家制度作為他的研究計劃之一,但最終沒有進行專題的系統整理。、社會生活、精神生活等上層建筑結構進行細致地分析。因此,一方面,馬克思為韋伯提供了基本的理論視角,即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社會結構之間,物質利益和政治利益、意識形態利益之間,都具有緊密的相互關聯的同構性,韋伯接受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異化批判,也認為上層建筑絕不是形而上學意義上的獨立精神實體;另一方面,馬克思為韋伯提供“預留”的理論空地,正是在馬克思“不在場”的那些地方,韋伯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結構、社會結構和觀念結構進行系統性的分析和建構,并實質上回答了那些馬克思沒有來得及、也未曾回答的問題,從而進一步“拓寬”和“完善”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視域。正如里澤布羅特所說:“韋伯把他們自己理解成是在從一個批判的角度進一步發展馬克思,而不是在駁斥他。”(7)[英]山姆·威姆斯特:《理解韋伯》,童慶平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第45頁。
三、后期:呈現三種面相和思想交匯
韋伯沒有針對“馬克思”寫過系統和專題的研究著作,對于“馬克思”的評論大都分散在其著作的各個部分。直到1918年,在德國內外部政治形勢劇烈變化的沖擊下(8)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后成立了蘇維埃政權;1918年,德國戰敗后成立了魏瑪共和國,在之后幾年里與德國共產黨以及工人運動經歷了多次斗爭。,韋伯開設了一門以“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證批判”為主題的課程,并發表了一篇題為《社會主義》的論文。他在這一階段對“馬克思”的評價也表現出更加復雜的維度。按照吉登斯的說法,韋伯語境中的“馬克思”實際上包括三個層面,即馬克思本人、馬克思主義者、作為政黨意義的馬克思主義。在韋伯思想的后期甚至后韋伯的時代,他正是通過學術與政治兩種不同的方式與“馬克思”的三種不同面相進行對話。
從學術上看,韋伯對馬克思本人的評價要遠高于和他同時代的那些馬克思主義者。在韋伯看來,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堪稱一項最高等的學術成就。誰都不可能否認這一點,也沒有人會否認,因為沒有誰會相信這種否認,還因為懷著明凈的良心就不可能否認它”(9)[英]彼得·拉斯曼、羅納德·斯佩樂編:《韋伯政治著作選》,閻克文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年,第230頁。。而與他同時代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等,卻把馬克思的思想解讀為一種“社會分階段的自動進化論”,也就是“修正主義”。吉登斯認為,當韋伯使用“歷史唯物主義”這個術語時,批評的正是這些奉馬克思為鼻祖、卻對馬克思的思想進行庸俗化理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馬克思本人(10)[英]安東尼·吉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郭忠華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第246頁。。在韋伯看來,馬克思提供了一個未來社會的先知式預言,為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方向做出重大啟發,而這些“馬克思主義者”顯然背離了馬克思本人的思想,把馬克思的思想變成一種教條。
從政治上看,韋伯認為正是由于馬克思在社會形態變革的關鍵問題上沒有做出明確回答,尤其是在歷史進程的演進方面存在實證層面的空白,導致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走向兩個截然不同的政治實踐方向,一是堅持自動進化論的修正主義,其代表是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一是堅持災變崩潰論的激進主義,其代表是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在韋伯看來,無論是自動進化論帶來的冷靜預期,還是災變崩潰論帶來的激進革命,都無力面對資本主義進入發達的大工業階段后出現的新型官僚制機器;官僚制機器是現代社會最基本、也最有效的組織形態,無論是經濟組織、政治組織還是社會組織,都只是官僚制機器在不同領域的具體體現。在韋伯看來,這兩種馬克思主義即使能夠回答如何在經濟結構中通過掌握生產手段消滅私有制的經濟根源,也無法回答如何在社會和政治結構中通過掌握管理工具改變組織形態的支配關系。因此,韋伯判斷,這兩種方向不僅不能超越現代社會的組織形態,而且將在最高的理性程度上實現官僚制機器的完成。
需要指出的是,韋伯對“馬克思主義者”和“作為政黨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反而更接近馬克思本人的思想。蒙森指出,“韋伯比他本人愿意承認的更接近馬克思的方法論立場……他自己的社會學方法試圖在普遍歷史的背景下根據理想類型描述現代社會的重大發展趨勢,在很大程度上與馬克思的卓越概論是一致的”(11)[德]沃爾夫岡·J.蒙森:《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1890-1920》,第105頁。。事實上,韋伯對資本主義的理性化祛魅過程和官僚制建立的正面評價,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所取得的革命性歷史成就幾乎持有同樣結論;而韋伯對理性化社會結構導致的個人自由淪喪,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異化勞動的分析也高度類似。因此,韋伯的理性化問題和馬克思的異化問題在實質上面對的都是同一個問題,即資本主義條件下人的生存和自由問題。韋伯和馬克思的真正分歧在于,對于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他們選擇了不同的理論取向和實踐方案。正如洛維特所指出的(12)See Karl L?with, Max Weber and Karl Marx,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韋伯和馬克思之間存在的思想差異,歸根結底是兩人在存在論問題上具有不同的哲學基礎。從根本上說,韋伯站在存在主義的個人主義立場,而馬克思站在哲學人類學的人道主義立場,他們之間的這種差異實際上就是Essence和Existence的差異在當代的延續。因此,馬克思最終選擇了超越資本主義,要通過揚棄私有制,實現人在共同體中的解放;而韋伯最終選擇了維護資本主義,更加關注如何在發達的官僚制條件下維護個人的自由。
客觀地說,韋伯并不“仇視”或“敵對”馬克思。從個人的角度說,韋伯高度同情工人階級為了爭取有尊嚴的生活而進行的斗爭,始終認為要正視工人階級的力量并提升工人階級的社會政治地位,還常常認為自己應該加入工人階級的政黨。在他看來,只有能夠按照無產者的生活方式進行生活,也就是放棄對無產者勞動的依賴,才能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就這點而言,他比很多同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者”更像馬克思主義者。但從階級的角度來說,韋伯始終是一個具有資產階級自覺意識的擔綱者,這是他不能“同意”馬克思的政治目標的主要原因。韋伯對自由主義做出的民族主義式改造,就是為了消除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使工人階級在強化民族意識的過程中進一步建立起對資本主義的廣泛政治認同。韋伯對馬克思理論的掌握是精準的和到位的,所以他清楚地認識到物質利益在現實政治運動中的根本重要性。與此同時,當馬克思指出“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時,韋伯也進一步指出,由觀念所創造的世界圖像能夠對物質利益的軌道起到扳道岔的導向作用。韋伯清楚地認識到觀念利益對現實政治運動的方向影響性,而這在馬克思那里并沒有得到彰顯。作為資產階級的辯護者,韋伯沒有“回避”階級斗爭的問題,他坦誠政治斗爭的核心問題就是資產階級要爭奪政治領導權;他還進一步“發展”了階級斗爭的理論,使觀念利益和物質利益一樣成為政治領導權爭奪的主要陣地。正是在韋伯的啟發和刺激下,20世紀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和意識形態領導權等問題做出回答,并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延伸到資本主義的社會、文化、政治批判領域。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19-20世紀之交的復雜社會歷史背景下,韋伯在與馬克思的思想交匯中發展出一種特殊的因緣關系。一方面,馬克思在韋伯思想的源起和發展過程中起到領路人作用,使韋伯在思想取向、研究對象、問題視域、理論方法、基本觀點等方面批判性地“繼承”了馬克思,成為韋伯思想中必不可少的“馬克思因素”。另一方面,韋伯也在應對和批判“馬克思”的過程中“擴大”和“發展”了馬克思的理論,使那些原本在馬克思本人那里沒有得到回答的問題,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得到新的解答,從而進一步激發和呈現出馬克思思想的時代價值和生機活力。實際上,盡管韋伯與馬克思的階級立場分明、理論分歧顯著,但從現代思想的發展歷程看,他們之間的思想關聯程度是相當緊密和廣泛的。正如布萊恩·特納所指出的,“僵硬地把馬克思和韋伯隔離開來,已不再被當代學術界認可”(13)《馬克斯·韋伯社會學文集》,閻克文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頁。。可以說,在通往現代思想的道路上,韋伯正是由于“遭遇”了馬克思,才成長為我們所熟悉的那個“韋伯”。韋伯曾坦率地承認:“現代學者們,尤其是哲學家們的誠實性,可以從他對尼采及馬克思的態度中來衡量。要是誰不肯承認他自己作品中的重要部分,若非參考了這兩位作者的研究成果將無法完成的話,那么他在欺騙自己及他人。我們每個人今天在精神上所體會到的世界,已是一個深深受到尼采與馬克思影響的世界。”(14)[德]沃爾夫岡·施路赫特:《理性化與官僚化》,顧忠華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58頁。因此,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脫離馬克思去研究韋伯的思想內涵,抑或拋開韋伯去追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歷程,都已經成為不可能之事,也是不可取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