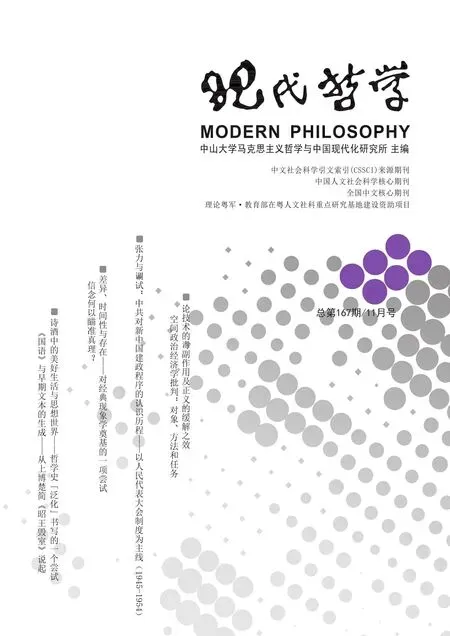王陽明良知說的道德動力問題*
陳曉杰
一、引言:“是非”與“好惡”
明末儒學的殿軍人物劉宗周對于王陽明的良知說有一個很著名的批評:“且所謂知善知惡,蓋從有善有惡而言者也。因有善有惡,而后知善知惡,是知為意奴也。良在何處?”(1)[明]劉宗周撰、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第2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17—318頁。也就是說,如果良知只是“有善有惡”之“意”發動以后能夠“知(意之)善知(意之)惡”之“知”,那就不能主宰“意”。這也就意味著,良知無法成為道德動力之根源。
對此批評,學界一般不以為然,認為王陽明的良知思想不僅包含“知善知惡”,還有“好善惡惡”之側面,而例證就是《傳習錄》卷下門人黃省曾所錄的一條:“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2)黑體字為筆者所加,下同。,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個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傳》288條(3)本文使用的王陽明著作版本為:陳榮捷:《傳習錄詳注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以下在引用時僅給出此版本中的條目編碼,記為“《傳》某某條”;[明]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學者通常認為,此條說明良知不僅是道德判斷原則,而且還“好善惡惡”,所以是“道德情感原則”。然而,至少有如下兩條理由讓我們懷疑上述文獻解讀的準確性:其一,將“是非”與“好惡”放在一起講良知,除了此條以外,只有“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傳》179條)一條;而在第179條中,此“是非”“好惡”確實應當是“是其是、非其非”“好善惡惡”之意,但此前提是“致良知”,換句話說,是良知已“致”之結果,而并未點明良知自身就含有“好善惡惡”之道德動力意。其二,學者介紹此條材料時大多不引用“又曰”的部分,“又曰”中言“是非”是個“大規矩”。對于“規矩”二字,王陽明曾數次使用,例如在回答顧東橋的書信中,針對顧東橋認為“舜不告而娶”這樣的“特例”必須“討論是非,以為制事之本”的觀點,王陽明提出反駁:“夫良知之于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于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傳》139條)節目時變不可勝窮,千變萬化,所以人不可能依循前例或者經典來進行應對,而必須訴諸天理之根源“良知”自身,良知自是“知是知非”,所以“是非”與“規矩”在此都表示良知自身作為道德判斷之根源與基準(這一點從王陽明早年提“心即理”就一貫如此),并無“道德動力”之含義。由此可知,“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并不足以證明王陽明的良知思想中必然有“好善惡惡”之道德動力義。
那么,良知思想究竟是否只是“知善知惡”之“知”呢?答案應當是否定的。只是如果我們要否定劉宗周的看法,首先必須將目光放到王陽明對于“良知”一詞的其他用法,以見良知應當含有更廣泛乃至普遍性的意義,一切善念均可歸入良知本體之發用來進行理解。說“應當”,意味著除零散的少數幾條材料外,從王陽明的良知思想只能通過間接推斷而得出“良知具有道德動力與自我實現”之意義,所以劉宗周的“誤解”完全情有可原。以下,本文將首先論述王陽明并非“是非之心”意義上的良知,并討論王陽明的良知思想何以會被“誤解”為只是“知是知非之心”;再進一步分析王陽明對“七情”以及“四端”的態度,并結合其晚年的“不著意思”之主張來進行分析。
二、“知者意之體”
眾所周知,王陽明思想與朱熹一樣,很大程度上都建立在對于《禮記·大學》的“八條目”之結構基礎上,王陽明論“心、意、知、物”,并以“意”為“心之所發”,也完全同于朱熹。然而至少有下面三條記錄,王陽明以“知”為“意之本體”:
A、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傳》6條)
B、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發,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大學古本旁釋》)
C、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后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傳》137條)
《大學古本旁釋》存在版本問題,也有究竟王陽明在改訂時是否加入后期“致良知”思想的爭議,但即便我們將材料B與A均歸入“早年未定之論”(《傳習錄》卷上的“知”字事實上也是“良知”之義),材料C雖未言“知是意之體”,但說良知“應感而動”、由此產生“意”,那顯然是說良知自己能夠產生“意”,此材料出自“答顧東橋書”,寫作時間為嘉靖四年(1525年)九月,所以王陽明的上述說法應當受到重視。
“本體”為宋明理學家所常用,而王陽明使用“本體”二字也不甚嚴格,至少有三層含義,即“體用論意義上之本體”“本然(應當)如此”“本質或本質屬性”。對“知是意之本體”這一命題,原則上也可以做出上述三種不同的解釋,但正如陳來所言,說“本然之意”相當于取消“意”與“知”的實質區別,說“本質”則良知變成類似于朱子學之“理”那樣的東西,無法發用(4)陳來:《有無之境》,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8頁。。根據材料C,我們可以暫且假設,上述材料A、B中的“體”應當以“體用”范疇來進行理解。良知本身可以發用,這似乎是不用多說的,然而在王陽明單提“致良知”宗旨以后,說良知之“用”一般意味著:不管有事無事或者有無私欲遮蔽,良知作為“知善知惡”之明鏡都能朗照,而“自知”此心之是非善惡,但此“用”或者“(自)知”以及比喻意義上的“照”顯然不同于王陽明放在“心意知物”下的作為發動的意念。本文將列舉四條不應歸入“知是知非”之意義的良知之“用”的用例,作為上述假設的佐證:
①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傳》8條)
②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無不是道。(《傳》165條)
③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于見聞,而亦不離于見聞……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傳》168條)
④“思曰睿。睿作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傳》169條)
材料②中,門人陸原靜認為“古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韓,范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見道者,果何在乎?”王陽明在回答中首先提出:“性一而已。仁義禮知,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所以,這里說的良知不是狹義的“知善知惡”之良知。材料③討論的是良知與“見聞之知”的關系,似乎可以歸入“外在經驗知識在良知之主導下發揮作用”的理解,但王陽明在回答中還提到“酬酢”,即廣義的交際應酬,那么此良知亦不限于知是非善惡。材料④將“思”歸入良知之發用,在此,“思”顯然也是廣義之“思”,則良知作為“體”亦當是廣義。不難發現,材料②③中“發用(見)”后面緊跟著“流行”二字(材料①中用“充塞流行”),更明確提示良知之發用是落實在“氣”的層面上說的。王陽明的“氣”概念并不很清晰,在很多情況下深受朱子學的影響,將“氣”視為對治或者需要加以限制的對象。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氣”是隨著至善之“性”或者“良知”說的情況下提到,就完全是正面積極意義,“流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被使用:“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傳》154條)“氣”在此是作為最高實體在現象界的顯現以及自我展開而言(就如同佛教說“法身”之“身”),所以上述材料中的良知之發用,都絕不可能僅僅限定為在人的心中作為一個判斷是非善惡之“明鏡”的朗照而已。
通過上述四則材料,本文想要證明的一個基本命題是:良知不僅“知善知惡”,而且可以應感(“見聞酬酢”)而產生意念(5)此處取“對外物的意念”之義,即“外感”。、思慮(6)此處取“不應物的情況下自應自感而產生的意念”之義,即“內感”。,并且此意念或思慮也不是停留在意識層面,而應當有自我實現之動力義。對此命題,讀者可能會馬上提出反駁:如果“意”是良知之所發,良知即是天理,是純粹至善,那么“意”豈非也是純粹至善?那么王陽明一生都堅持將“格物”之“格”解為“格其不正以歸于正”豈非完全落空?對此的回答是:王陽明確實自始至終堅持認為“意有善惡”,那么惡之意從何而來?自然只能是出自泛指意義上的“私欲”(不僅包括耳目口腹之欲,還有好名、好色等欲),王陽明說“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也主要是對治現實世界中的人內心所存在的反面之私欲而言,說“(良)知是意之本體”并不意味著一切“意”均發自良知或者說根源于良知(7)至于要問此私欲是否完全外在于良知或者另有獨立于良知之根源,則牽涉“根源惡”的問題。此問題與本文論旨并無直接關系,在此不贅。。更何況“格其不正以歸于正”的思路本身就存在問題,首先“其”究竟指什么,如先行研究所言,大多數情況下指主體自身發動的意念之不正,但少數情況下也似乎指向對于作為意念對象的“正”。我們姑且認為王陽明的意思就是“正念頭”,那么本來就“正”的念頭又何須要“正”?雖然王陽明曾說“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于正’,為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于正也”(《傳》317條),但如果王陽明確實如此認為,那他就是預設了現實狀態的人(圣人除外)在任何時候的意念都必定有不善之處,這事實上非常接近朱熹的路數,而與孟子乃至陸象山的“心學”路數——無論人在現實世界中如何汩沒于私欲,良知/本心都可能在任何時點下當下呈現——相去甚遠。“意”可以是從純粹至善之良知直接發出(這正是王龍溪在“天泉證道”中提出的“四無說”之義),即是說,直接從“心之本體/良知”縱貫地說“心意知物”(只是心/知、意、物而已)。
三、良知與四端之心
通過對于王陽明思想的全盤考察,我們確實可以找出一些良知作為發用之本體的話頭,由此做出以下合理的推斷:良知自身就能產生意念,當然也能產生情感乃至喜怒哀樂等情緒。那么,考察王陽明對于道德情感的論述就顯得非常有必要。眾所周知,宋明儒學對此的討論主要還是圍繞孟子所說的“四端之心”而展開,王陽明也不例外。
王陽明正面論及“四端之心”的材料,事實上在《傳習錄》中只有兩條:
⑤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于人也,謂之性。主于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傳》38條)
⑥“生之謂性”。“生”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氣即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即是性。即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傳》150條)
材料⑤,陸原靜問“四端之心”是否也是“性之表德”,王陽明答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也就是說“四端之心”與“四德”都是“性”的具體內容,又緊接著說“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意思是說“天帝命性心”等都是對于“性”的不同側面、性質的表述。那么,例如當中提到“心”就是有善有惡之心嗎?當然不能,此皆是從本源上說,所以“四端之心”也是從本源上說。對于天理之人間“道成肉身者”圣人而言,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當然是純粹至善的,這點無論是王陽明還是朱熹乃至任何宋明理學家都不會反對。材料⑥牽涉“生之謂性”以及“性”“氣”之關系問題不易理解,但對本文而言,重要的是如何理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這句,聯系“氣即是性,性即是氣”來看,似乎四端之心也被上提到“性”之高度,然而不要忘記“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前面有“若見得自性明白時”這個限定。王陽明與陸象山一樣,對于概念之分疏剖析甚不在意,喜從“一”與“合”來看待理學概念,在王陽明看來,學問思辨與工夫都需要“頭腦工夫”,在把握此頭腦或者“立言宗旨”的情況下,對于本體工夫、已發未發、心性理氣等概念都不需要做過多糾纏,“見得自性明白”就如同說“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氣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傳》146條)一樣,是站在悟道(良知)的高度來看待問題,所以就此而言,王陽明并未對四端乃至“氣”做全盤之肯定。材料⑥還說“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這種口吻完全可以原班不動套用到主張理氣心性情分立的朱熹那里,無非是說至善之“理/性”不可見,需通過“氣”之媒介方可在現象界顯現,“氣”在此只是工具,其本身之善惡乃至是否由“理/性”產生,則全未論及。
既然是從“頭腦=良知”或者“性一而已”的超越層面(也可以說是本然狀態)來理解四端之心,那么是否只有儒家之理想即“圣人”才可能如此呢?就如同孔子說“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朱熹會認為,凡人的心之所欲夾雜了大量私慮雜念,只有通過格物窮理與居敬的工夫達到圣人境界,人欲才會徹底消盡,此時“心”才與“理”達到“一”的狀態,心之所欲才自然不會逾越天理之規矩。但是,如果“四端之心”也必須由圣人的內心發動才能保證其純粹至善,那就意味著凡人無論當下有什么念頭或者感情,都不足以作為行為的依據。亦即是說,如果四端之心是作為工夫論之“效驗”,正如同朱熹說“理”作為“所當然而不容已之則”,那么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就無法作為人的道德動力或者情感而得到肯定,道德情感之意義就實際上被架空。反之,如果我們承認,即便是凡人也可能在某些情況下“良知未泯”,看到孺子將入于井就當下會生出惻隱之心,那么四端之心就可以成為“我為什么要做好事/不做壞事”的道德動力,從而促使人不斷地為善去惡,進行道德實踐。故此,若要使“上提”之四端之心真正成為道德動力,就必須承認此四端之心乃至良知,都可能在任何情況下全體呈現,此即港臺新儒家一直強調的“良知當下呈現”。對此命題,已經有很多先行研究與討論,在此僅舉出正反兩點以供思考:其一,王陽明后期強調“致良知”,此“致”字在《大學問》中釋為“致者,至也……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釋“知至”時曰“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似乎都暗示了這是一個趨向于“至極”的過程,然而如果這樣理解,那么“良知”就變成最終的目標和效驗,江右學派正是如此理解“良知”與“致良知”。王陽明反復強調其良知之宗旨是從千辛萬苦之磨練中得來,告誡學者不要將良知當作“光景”把玩,所以上述理解絕非無故。其二,王陽明又說“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傳》206條),“知猶水也,人之心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8)[明]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八《書朱守諧卷》,第277頁。。這里說“依著他(良知)”,乃至形象化地比喻“打開下方的缺口,水就會順流而下”,在理論上都已經預設了良知在當下存在或者全體呈現(即此“在”并非潛在意義或者可能性上的“存在”),人只需要依照當下呈現的良知判斷去切實做出相應的行動,就是“致良知”。通常所說“良知現成派”或者“王學左派”基本都如此理解,所以“致良知”的說法會被經常換成“依本體”或者“循其良知”(9)參見吳震:《陽明后學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六章《歐陽南野論》的第3節“循其良知”的相關介紹與分析。。至于王陽明本人究竟采取何種解釋,單從上述文本分析來看,是不會有定論的。
回到四端之心的主題。從材料⑤⑥來看,王陽明對于四端之心的態度并不明確。眾所周知,雖然孟子以四端之心來論證性善,但重點放在“惻隱之心”,此即以“惻隱之心”統攝四端,或者從“性”上說,是以“仁”統仁義禮智四德。王陽明雖然在五十歲以后多以“是非之心”論良知,但他對于“惻隱之心”以及“仁”也多有所提及。接下來將考察王陽明的“惻隱之心”、“仁”與良知說之間的關系。
⑦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傳》179條)
……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于深淵者……故夫揖讓談笑于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矣。(《傳》181條)
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于道路,而不暇于煖席者,寧以蘄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傳》182條)
材料⑦出自《答聶文蔚書》,內容是經常為學者所樂道的“萬物一體”論,其中第二段提到“惻隱之心”,第三段說孔子是“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很顯然是在從“一體”的角度說“仁=惻隱之心”。然而我們卻注意到,在整個無比真誠痛切、體現王陽明汲汲皇皇救世之精神的段落中有這樣一句:“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當然,我們可以為王陽明辯護,說在這里王陽明強調的是“知疾痛”,但是這個“知”顯然既不是一般認知意義上的“知”,也不是道德判斷意義上的“知”。這種通過身體感覺來講“萬物一體”,是出自北宋程顥,后又為其弟子謝上蔡所繼承,即“以覺訓仁”,卻被王陽明說成“是非之心”(更何況后面兩段里面王陽明自己都說這是“惻隱之心”“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就筆者之管見,這在宋明理學史上并無第二例。由此可見,王陽明以“是非之心”來理解良知的思維定式是多么強烈。再來看下面這則資料: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為二矣……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于孺子之身歟?抑在于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傳》135條)
這里討論的依然是《傳習錄》卷上就多次出現的“要完成一個道德行為,其‘理’應當求之于前言往行等外在之物,還是求之于我之本心”的問題。對于“孺子將入于井”,王陽明也同樣如此思考問題,“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材料①),邏輯上都是“對于某事,我的內心知道‘應當如何做’”,是以“是非之心”統攝一切。或許在王陽明看來,我知道應當惻隱(“知”)就意味著我一定會惻隱,乃至去救孩子(“能”),但這恐怕與孟子的本義還隔了一層。孟子給出的情境“乍見”,正是為了強調此情形之突發性與偶然性,人置身于其中的第一反應就是“怵惕惻隱之心”,這種“怵惕惻隱”的感情并非由一個“我知道應當惻隱”的“是非之心”所引導而發生,而應當就是我自己的良知在當下的呈現。如果要用“知/能”或者“知/行”進行區分,那么毋寧說人在很多情況下是“知/能”同時,甚至“能/行”中含“知”。王陽明對此并非全無體會,所以他才會在講“知行合一”時說人“知痛”是“必已自痛了方知痛”(《傳》5條),又說“持志如心痛”(《傳》25條),但始終沒有明確此中所蘊含的道德判斷、道德動力乃至執行的一體性。而糾纏于“知某某之理”,恐怕還是沒有徹底走出朱子學陰影的緣故。
再來看王陽明晚年所作《大學問》中的相關論述(10)由于引用篇幅較長,采用字母編號進行適當分段,以便討論。:
A.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
B.……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于欲,而未蔽于私之時也……是故茍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
C.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故止至善之于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于方圓也,尺度之于長短也,權衡之于輕重也。(11)[明]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二十六,第968—969頁。
段落A、B是王陽明解釋何為“(明)明德”的部分。王陽明認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精神的體現者“大人”,并非自己有意為之,而是“心之仁本若是”;在段落B中更是強調,即便是承載負面價值意義的“小人”,一旦沒有私欲之蒙蔽,就可能使得其自身的“一體之仁”有所發動而見孺子必起惻隱之心。由此可知,“明德”即是“(萬物一體之)仁”。而段落C看似簡單,實則無論在語句表達還是層次上都欠分明,但王陽明想說的,無非是以“至善”為“極則”,為“良知”,為“明德之本體”。“是而是焉,非而非焉”,以及“止至善之于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于方圓也”,則是將“至善”乃至“良知”放在王陽明所慣用的“知善知惡”的是非之心框架內來進行理解。歸納如下:心=仁=萬物一體=明德,良知=至善=知是知非=明德之本體
這里就出現某種非常怪異的現象,似乎見到孺子將入于井而必然會產生的惻隱之心(明德)是一回事,而作為“明德之本體”(此“本體”之義也極不明確)的良知,作為判定心之活動的法官而存在則是另一回事情。或者我們可以用下面這個圖式來幫助理解:
從以上幾條材料看,王陽明雖然對孟子所言“惻隱之心=仁”有非常精準的把握,但在論述中始終將良知定位在“知惻隱之心”“知吾身之疾痛”,強調良知是“靈昭不昧”的明鏡,給人會造成一種錯覺:似乎人看到孺子入井所產生的惻隱痛切之情乃至一系列行動是發自一個心,而良知只是在此心發動之后審視、判斷此心之發動是否合理的法官而已(12)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在極少數資料中找到王陽明良知說具有道德動力的解釋,例如《傳習錄》第189條“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因篇幅關系,本文無法具體展開,參見傅錫洪待出版的《“良知只是一個真誠惻怛”——王陽明晚年關于本體與工夫問題的一項論述》(《中道:中大哲學評論》第1輯,北京:商務印書館)。感謝作者將未刊稿賜予筆者拜讀。。
四、結 論
楊祖漢曾以對四端之心的不同把握與偏重來歸納陽明學的發展趨勢:“陽明之良知說,于知是知非處指點本心……此以知統四端,異于以往的‘以仁統四端’……由于陽明從朱子所言之格物致知用功而無所入,后悟知行合一之知,知即心即理,將朱子所言致知之知轉而為本心明覺之知,此知是即物而給出行動所根據的道德法則,由是而生相應的行動。”“龍溪以水鏡喻心,言本體自然無欲,則道德之直貫,似轉成了知性之橫攝。應物而自然之義甚顯,而自作主宰、奮發植立之義,便有不足。”(13)楊祖漢:《從良知學之發展看朱子思想的形態》,《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集刊》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41—142頁。其實,這種“應物自然之義甚顯,主宰奮發之義不足”的現象,在王陽明的思想中已經存在。
從早年開始,王陽明就非常重視“誠意”的問題,但對于“意”卻幾乎完全接受朱熹的界定即“意是心之所發”,“意”與“心”在此都落在經驗層面,故“有善有惡”。這就決定了王陽明對于“意”的基本態度:首先將“意”視為被審視與反省的對象。這是在對治的意義上說,就如同朱熹也重視“心”一樣,但在工夫論視域下的“心”無疑不是能給予全盤信任的對象,更不是性善之本體。所以即便提及“知是意之本體”,王陽明也從未就此做真正深入的展開,換言之,探討從純粹至善之良知直接縱貫而下的純化之“意”(或者反過來說,“意”作為良知自我實現之能量)。晚年“天泉證道”,王龍溪提出著名的四無說,王陽明對此評論道“此顏子 明道所不敢承當”(《傳》315條),則實際上幾乎就等于否定了常人可能直接從本體悟入的可能性。在王陽明看來,只有圣人才可能如此,常人對于“意”必須通過知善知惡之良知加以嚴厲審視,“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同上),如此“意”與“知”就判然如同兩物(14)說“判然”是因為王陽明必定不會承認“意”能在“知”外或者“心”外。,縱貫一致之“知意物”義自然就不顯了。
再從道德感情看,雖然四端之心被“上提”到與“天/命/性/心”等量齊觀的超越高度,但此四端之發動如果只有在圣人境地才純粹至善,則道德動力之義就被架空,四端之心必須如孟子那樣的“就我對其他人物之直接的心之感應上指證,以見此心即一性善而涵情之性情心”(15)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第76頁。,肯定即便是凡人、其良知或者本心在當下也可能全體呈現出來(而表現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如此才是“縱貫”而體現出道德動力與情感義。遺憾的是,王陽明對此并沒有做出明確抉擇。王陽明對于“惻隱之心”或者“萬物一體之仁”有很深的理解與體會,但在“拔本塞源論”等膾炙人口的作品中所體現的思想卻帶給人一種錯覺,似乎“惻隱之心=萬物一體之仁”是一回事,“良知=知是知非=知惻隱”是另一回事,或者說,道德情感(惻隱之心)與道德判斷(良知)在王陽明的良知說中并沒有得到充分整合,又形成了判然如同兩物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