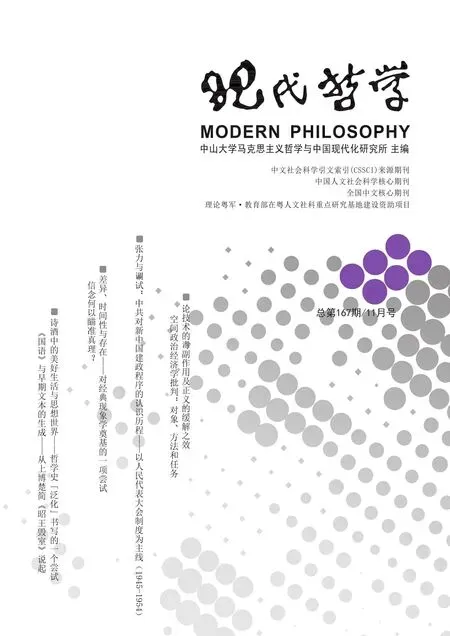勝軍比量與《增一阿含》
孫勁松
勝軍生為西印度蘇剌佗國人,著名的佛教居士。主要生活時代是公元七世紀,曾從賢愛、安慧等人學習因明、聲明及大小乘論,后追隨戒賢深研《瑜伽師地論》,博學廣聞、名重一時。據《大唐西域記》記載,勝軍“年漸七十,耽讀不倦。余藝捐廢,惟習佛經。策勵身心,不舍晝夜……年百歲矣,志業不衰”(1)[唐]玄奘撰、[唐]辯機編次、芮傳明譯注:《大唐西域記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6頁。。他在七十歲至百余歲的三十年中,常年在杖林山集徒講學,從學僧俗常達數百人。玄奘西游時,曾在其門下二年,學習《唯識決擇論》《瑜伽師地論》以及因明等方面之義理。
一、玄奘對勝軍比量的批評與修訂
玄奘翻譯了商羯羅主所造之《因明入正理論》,窺基對其進行注釋,成《因明入正理論疏》一書,世稱《因明大疏》。據該書記載,勝軍通過四十余年的深思熟慮,立一比量:“諸大乘經皆佛說(宗);兩俱極成、非諸佛語所不攝故(因);如《增一》等阿笈摩(喻)。”(2)[唐]窺基:《因明入正理論疏》卷中,高楠順次郎等編校:《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4卷,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部,1990年,第121頁。在當時“時久流行,無敢征詰”(3)同上,第121頁。。
這是典型的共比量三支量式,一般來說,“宗”由前陳、后陳(又稱“宗依”)組成;前陳與后陳需要立論者、敵對者共許,但由此二者所成的宗體則必須是立論者認可,敵對者不認可。此比量的核心論點(宗)“諸大乘經皆佛說”“諸大乘經”作為宗的“前陳”是大小乘人都承認的一個事實,“佛說”作為“后陳”所表達的佛陀曾經有所說法,也是一個大小乘人都承認的事實。但是前陳、后陳之間加了一個“皆”,變成“諸大乘經皆佛說”,就明顯成了大乘人認可、某些小乘宗派不認可的一個論點。
其“因”支用了“兩俱”“極成”四個字。所謂“兩俱”,就是論辯的敵我雙方都承認的前提條件;“極成”指至極的成就。“兩俱極成”就是敵我雙方都認可的、絲毫不容置疑的“前提”。因明作為論辯邏輯,立正破邪、戰勝對手是其目的。所以,因明家特別強調論辯前提的“兩俱極成”。而此論題兩俱的對象是“非佛語所不攝故”,意指不僅小乘佛教教理超越所有外道理論,大乘佛教也超越各種外道的理論,只有佛陀才能說出大乘佛教教理。其“喻”支則舉了《增一阿含經》作為例證(阿笈摩即“阿含”)。
玄奘到杖林山向勝軍求學期間,認為勝軍比量的“因支”犯了“兩俱不成”“隨一不成”“自不定”等過失。玄奘法師主要用小乘薩婆多部(說一切有部)以及該派別的代表作《阿毗達磨發智論》對勝軍的因支展開辯難。根據窺基《大疏》記載,玄奘展開質疑的角度如下:
1.勝軍比量犯有一分兩俱不成過。“且《發智論》薩婆多師自許佛說,亦余小乘及大乘者,兩俱極成非佛語所不攝,豈汝大乘許佛說耶?”(4)[唐]窺基:《因明入正理論疏》卷中,《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4卷,第121頁。玄奘指出,當時非常流行的小乘佛教流派薩婆多部自認為《發智論》的觀點是佛陀所說,但是大乘佛教和其它小乘派別都不許可這個說法。此時,大乘佛教與小乘薩婆多部在《發智論》是否“非佛語所不攝”的問題上已經存在分歧,這對大小乘“兩俱極成”說形成一個挑戰。玄奘進一步指出:“若以《發智》亦入宗中,違自教,‘因’犯一分兩俱不成。‘因’不在彼《發智》宗故。”(5)同上,第121頁。“兩俱不成”是“因十四過”之“四不成過”的第一過。指“因”不周遍于“宗”的“前陳”,而成為立論者、與問難者共不許之量。據《因明入正理論疏》記載,“兩俱不成過”又以“因”體與“宗”關系之程度而分為“全分”與“一分”。熊十力在《因明大疏刪注》中指出:“此極成非佛語所不攝之因,既對《發智論》無簡別,汝若立‘《大乘經》《發智論》者俱是佛說’以為宗者,此‘因’對小乘之許《發智》是佛說者而言,大乘但有違自教失,以大乘本不許《發智》是佛說。今成此宗,故違自教,若對小乘之不許《發智》是佛說者而言,此因即犯一分兩俱不成過,立敵共許此因,于宗中一分《大乘經》上有、一分《發智論》上無,故言一分兩俱不成也。”(6)熊十力:《因明大疏刪注》,蕭萐父主編:《熊十力全集》第1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55頁。在勝軍比量中,論辯的“問難方”若包含信奉《阿毗達磨發智論》薩婆多部,他們不承認大乘是佛說,大乘佛教也不承認《發智論》是佛說;但大乘與小乘的矛盾也不是全面性的,大乘佛教承認《四阿含》是佛說,小乘的某些派別也不完全否認大乘,所以說此命題可能導致一部分的“兩俱不成”,在因明學中稱為“一分兩俱不成”。
2.勝軍比量犯隨一不成過。玄奘認為:“又誰許大乘兩俱極成非佛語所不攝?是諸小乘及諸外道,兩俱極成非佛語所攝,唯大乘者許非彼攝。因犯‘隨一’。”(7)[唐]窺基:《因明入正理論疏》卷中,《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4卷,第121頁。玄奘指出,小乘和外道都認為大乘佛教不是“佛語”所能包含,除大乘佛教自身外,沒有哪個派別“兩俱、共許”大乘是佛說。所以,這一比量的“因”支犯有“隨一不成”的過失。“隨一不成”也是“因十四過”之“四不成過”的一種。指立論者與問難者的某一方以對方不承認之因(理由)來立“量”時所造成之過失。此一過誤復分為兩種情形:若立論者自身認可其因,而他方不予承認,稱為“他隨一不成過”;若立論者自身不認可其因,而他方予以承認,則稱“自隨一不成過”。此二過皆可因冠上簡別語而免除之,如“他隨一不成過”用“自許”之簡別語以作自比量,“自隨一不成過”用“汝許”之簡別語以作他比量,即不犯此過。玄奘認為,勝軍比量的“因支”所犯的是“隨一不成過”中的“他隨一不成過”,需要將此比量由“共比量”修訂為“自比量”,將“兩俱極成”修改為“自許極成”來避免過失。
3.勝軍比量犯有自不定過。玄奘認為:“因不在彼《發智》宗故,不以為宗,故有不定。小乘為不定言,為如自許《發智》,兩俱極成非佛語所不攝故,汝大乘教非佛語耶?為如《增一》等,兩俱極成非佛語所不攝故,汝大乘教并佛語耶?若立宗為如《發智》,‘極成非佛語所不攝’,薩婆多等便違自宗,自許是佛語故,故為不定言。為如自許《發智》‘極成非佛語所不攝’,彼大乘非佛語耶?以不定中亦有自、他及兩俱過,今與大乘為自不定故。”(8)[唐]窺基:《因明入正理論疏》卷中,《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4卷,第121頁。“不定過”是在因明論式中,具有因三相“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異品遍無性”(9)商羯羅主造、[唐]玄奘譯:《因明入正理論》,《大正新修大藏經》第32卷,第11頁。中之第一相,而缺后二相,所立之宗義不定所生之過失。
所謂“同品定有性”是表明因與宗后陳之關系。凡與“宗依”的后陳同類的,都稱為同品。所謂“定有性”是說宗的同品中必定具有因的性質,但并不需要同品都具有該性質,只要有些具有該性質即可。所以,只說“定有”,而不說“遍有”。勝軍比量的“后陳”是“佛說”,而“因”中“兩俱”二字含攝有“小乘薩婆多部”,但大乘及小乘其他宗派認為其并非“佛說”;同理,“小乘薩婆多部”也不同意“因”中“兩俱”二字含攝的“大乘”是“佛說”,這樣就不能具足“同品定有性”,就形成“不定”的過失。
“異品遍無性”指“宗”的異品須普遍沒有因的性質。所謂“異品”,亦即某物只要不具有“宗”的“前陳”所表述的性質,即可用來作為異品。異品分宗異品與因異品兩種,凡與“宗”的“前陳”相異的,叫做宗異品;凡與“因”相異的,叫因異品。由于“宗”的“前陳”的外延比因法大,所以凡與“宗前陳”相異的宗異品,也都是與因相異的因異品。所謂“遍無性”,是說所有的宗異品都與“因法”不發生關系,因為凡宗的異品應該都是因的異品。由于此異品遍無性是用來從反面制止因法之濫用,所以要求宗的異品必須全部不具有因法的性質;如果不是全部宗異品同時都是因異品,那就不能制止因法的濫用。在勝軍比量中,“大乘”作為“宗”的“前陳”,其異品可以說是“小乘各派別”,但是大乘佛教以及其他小乘教派認為“薩婆多部”理論與外道的“非佛語”相類,不在“非佛語所不攝”的范疇;反之,薩婆多部也認為大乘不在“非佛語所不攝”的范圍內。所以,勝軍比量也違反了“異品遍無性”,玄奘認為其犯了“自不定”小乘各派別的過失。
根據窺基《因明大疏》記載:“由此大師玄奘正彼勝軍因云:自許極成非佛語所不攝故,簡彼《發智》等非自許故,便無茲失。”(10)[唐]窺基:《因明入正理論疏》卷中,《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4卷,第121頁。將勝軍比量的“兩俱”改為“自許”,將“薩婆多部”等小乘宗派排除在外,以避免過失。玄奘修訂后的比量如下:“諸大乘經皆佛說(宗);自許極成、非諸佛語所不攝故(因);如《增一》等阿笈摩(喻)。”(11)同上,第121頁。
二、玄奘法師沒有注意到“喻支”是勝軍立論的關鍵
因明作為印度佛學以及各宗派、教派共同遵守的論辯邏輯,依立、敵雙方對所使用概念或判斷是否共許,其論式可以分成三種比量:自比量、他比量和共比量。一個沒有過失的共比量,必須是立、敵雙方共許;除宗體是立敵對諍的標的外,所使用的概念和因支、喻體都要得到雙方承認;既是真能立,又是真能破,功用最大。他比量限于破敵之論點,不申揚自宗。自比量只申揚自宗,限于詮釋自己的理論,無力破他。玄奘在運用“簡別”的方法,對勝軍經過四十多年深思熟慮而立的一個比量卻有過失加以辯難,將其共比量改為自比量。但玄奘的辯難過程沒有對“喻支”加以論述,筆者認為這個喻支恰恰是勝軍比量的關鍵。
窺基在書中引用《攝大乘論》所立的另外一個比量云:“諸大乘經皆是佛說(宗),一切皆不違補特伽羅無我理故(因),如《增一》等(喻)。”(12)同上,第121頁。。其喻支所用的是《增一阿含》等經,勝軍比量也是用《增一阿含》為喻支。那么,《增一阿含經》到底是一部什么經?里面有什么內容能支撐大乘是佛說的觀點?這成為一個核心問題。
《增一阿含經》是小乘佛教的基本經典,四部阿含之一。這部經典明確記載了佛教有“三乘”,信徒有聲聞部、緣覺部(辟支部)、佛部(菩薩部)等三部大眾,大乘法中的“六度”“菩薩”等詞語也頻繁出現,還記載有大乘佛教中廣泛出現的彌勒、文殊等事跡。
①如是《阿含增一》法,三乘教化無差別;佛經微妙極甚深,能除結使如流河。(13)[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卷1,《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卷,第550頁。
②以此功德、惠施彼人,使成無上正真之道。持此誓愿之福,施成三乘,使不中退。復持此八關齋法,用學佛道、辟支佛道、阿羅漢道。(14)[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卷38,《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卷,第757頁。
③今此眾中有四向、四得,及聲聞乘、辟支佛乘、佛乘。其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得三乘之道者,當從眾中求之。所以然者,三乘之道皆出乎眾。(15)[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卷45,《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卷,第792頁。
材料①已經出現“三乘”一詞。材料③明確指出佛教不僅是聲聞、緣覺二乘,還包括阿羅漢道(聲聞乘)、辟支佛道(緣覺乘)、佛道(佛乘、大乘),共計“三乘”。
《增一阿含經》還有大量關于菩薩、六度的記載。如,
④如來在世間,應行五事。云何為五?一者當轉法輪,二者當與父說法,三者當與母說法,四者當導凡夫人立菩薩行,五者當授菩薩別。(16)[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卷15,《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卷,,第622頁。
⑤若菩薩摩訶薩行四法本,具足六波羅蜜,疾成無上正真等正覺。(17)[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卷19,《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卷,第645頁。
材料④指出,佛在人間示現應該要做這五件事情,要建立菩薩行,讓佛弟子們遵循而修,并為諸菩薩受“記別”,即受記何時成佛。材料⑤記載了佛與彌勒菩薩的對話,這里出現大乘“六度”的概念,并提出大乘佛教修行的目標是“無上正真等正覺”。《增一阿含經》卷44,還有與大乘佛經相同的授記彌勒將來娑婆世界成佛的文字。可見,《增一阿含》作為小乘佛教尊奉的佛陀所說之根本經典,確實可以看到大乘佛教的只鱗片爪。這也正是勝軍等人反復引用《增一阿含》與小乘人論證大乘是佛說的關鍵原因。
現代學者對《增一阿含》的產生年代以及是否為佛說提出質疑。此質疑若成立,將對勝軍比量形成致命傷。一些學者提出大乘佛教是佛滅度后數百年間,為大乘佛教徒編創,并以此為根據,將《增一阿含》所涉及的大乘部分也列入后世“編造”的范圍。臺灣的印順法師說:“四部、四阿含的成立,是再結集的時代,部派還沒有分化的時代。”(18)釋印順:《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頁。他認為佛滅度后,第一次五百結集中只完成“雜藏”,而《長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都是佛陀入滅后一百年左右的第二次七百結集時才完成,這為偽造、摻假提供了可能。但是,即便是印順信奉的《雜藏》也指出四阿含在第一次結集中全部完成了。《雜藏》的《佛般泥洹經》卷二指出,佛陀涅磐后不久,“大迦葉賢圣眾,選羅漢得四十人,從阿難得四阿含,一阿含者六十疋素”(19)[西晉]白法祖譯:《佛般泥洹經》,《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卷,第175頁。。這說明四阿含都是在第一次結集完成的,并且都形成文字,記載在“疋素”之上。由此可知,印順等人的考證并不準確。另外,龍樹《大智度論》云:“佛滅度后,文殊尸利、彌勒諸大菩薩,亦將阿難集是摩訶衍(大乘)。又阿難知籌量眾生志業大小,是故不于聲聞人中說摩訶衍,說則錯亂,無所成辦。”(20)龍樹撰、[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5卷,第756頁。根據傳統說法,不僅四阿含為第一次結集形成,大乘經典的主要部分也應在佛陀滅度后不久,由大乘弟子另外結集而成。可見,勝軍比量的關鍵,不在因支,而在“喻支”。在勝軍生活的時代,各佛教教派都共許《增一阿含》是佛說,所以,勝軍比量以此為“喻支”并沒有問題。
三、勝軍因支“兩俱極成、非諸佛語所不攝故”并無重要過失
1.大乘經“非佛語所不攝”并無過失
“非佛語”與“佛語”的根本區別是什么?概言之,佛所語者是出世間法,而非佛語者都可以歸屬于有生有滅的世間法。所謂世間法可以分為三類:其一是有情世間,也稱眾生世間,指由五蘊假合而心識的一切有情生命,包括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各界的眾生;其二是器世間,也稱國土世間,指由地、水、火、風四大積聚而成的山河、大地、國土、家屋等,是一切眾生所居住的地方與空間,包括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其三是五陰世間,又名五蘊世間,即色、受、想、行、識之五陰,包含有情世間與器世間之全體。無論是有情世間、器世間還是五陰世間,都是遷流變化的現象世界,一切眾生皆有生壯老死,一切物質世界都有成住壞空,“五陰”定有聚散離合。佛教之前的各類宗教體驗,都不出六道輪回;一切世間的哲學、玄想、教義,都不出“世間”。
佛陀因眾生根器之不同,從淺至深施設三乘法教,都是出世間法。其先說聲聞法之八苦、四諦、四念處觀、八正道,后根據時節再說緣覺乘之十因緣法、十二因緣法。小乘僧眾依靠四圣諦、八正道、十二因緣理論來思維與觀行,明白緣起性空、緣起無我之理,明白緣起之法必歸于滅,其性必空,故知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之性空,由是體悟緣起性空之理,斷除我執、煩惱,不再受業力與無明牽制,達到證得阿羅漢四果、辟支佛果,斷我見與我執,舍壽而滅盡十八界法,由此而出離三界、“世間”,證小乘解脫之無余涅槃。然而,無余涅槃之本際為何?阿羅漢并不知曉。此無余涅槃若是絕對的“無”,就是“斷滅”論者,成了斷見外道;若是一個具體的“有”,必然落于三界的“世間法”,成為常見外道。所以,《阿含》中佛陀多處說明無余涅槃內有本際,《四阿含》常用“實際、我、如”甚至“阿賴耶”等代指真心本際。但此說都是略說,并非詳細解說,恐小乘眾生“執此為我”,反生羈絆。阿羅漢雖無實證無余涅盤之本際真心,然依佛圣教量的開示,確知“無余涅盤”非斷滅后,故可于內無恐怖、于外無恐怖而安住于其修證的境界。可見,小乘聲聞、緣覺之法以大乘法為根本而方便宣說,若離大乘法所宗的“真心實際”,小乘涅槃將無異于“斷滅見”。
真心的親證是在佛陀宣講般若、唯識系大乘經典時才詳細解說。小乘聲聞人雖于結集前亦曾參與二三轉法輪般若唯識諸會,因無實證,不得現觀驗證諸佛所說法要,唯能記憶一些名相,此亦是大乘經典中所說的“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21)[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大正新修大藏經》第8卷,第218頁。。此“本際、真心、阿賴耶”是“真際之有”,此“有”與“世間萬法之有”不在一個層面,而是作為所有世間萬有之體的“有”。近代學者見大乘佛教描述“真心體性”有“常樂我凈”之語,便說大乘佛教等同于印度外道“梵我”,可謂荒謬之極,此“我”非彼“我”,豈可混淆一談。“真心”“阿賴耶識”是三界萬法之所依,出世間與世間法不二,一切眾生本來常住涅槃, “心”與“三界萬法”如水與波之關系,三界萬法如夢幻泡影、生滅不息,但是其所依之“心”是不生不滅、不垢不凈的,只要契悟此心就可證知輪回只是表面現象,真心本不生滅、本來不入輪回。體證這個自性清凈之常住真心以后,還需要高桿進尺。如《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云:“有二法難可了知,謂自性清凈心,難可了知;彼心為煩惱所染,亦難了知。如此二法,汝及成就大法菩薩摩訶薩乃能聽受;諸余聲聞,唯信佛語。”(22)[唐]玄奘譯:《勝鬘獅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2卷,第222頁。證悟自心自性清凈只是“見道”,而自性清凈之心為煩惱所染,證悟自心之后仍需要反復體證五蘊十八界的空相(這是小乘修行的核心內容),生生世世廣修六度萬行,斷盡煩惱障習氣種子隨眠,以及所知障無量隨眠,圓滿具足一切種智的智慧功德,方能成就究竟佛道。可見,大乘佛法含攝小乘佛法,兩者都以“本心真我”作為理論基礎,都超越所有描述世間法的“非佛語”。
2.“兩俱極成”可以成立
《增一阿含》等小乘經典有明確的三乘、菩薩、六度等大乘名相的出現。勝軍運用“《增一》等阿笈摩”作為“喻支”,與小乘人辯說“大乘是佛說”。小乘教徒看到《阿含》確實記載有“聲聞、緣覺、佛乘”的三乘概念,雖然他們只能理解聲聞、緣覺的教義,但不會貿然否定大乘教義。而大乘佛教徒也承認聲聞、緣覺乘的經典是佛陀因機教化眾生所說。所以,大小乘根據《增一阿含》等經典的記載,共許大小乘“非佛語所不攝”是可以成立的,由此可以推出“大乘是佛說”的概念。
薩婆多部又稱“說一切有部”,約于佛滅后三百年出現,此派以迦濕彌羅國為中心,于健馱羅、中西印度及西域等地,曾盛極一時,玄奘西行印度期間,此派實力相當大。創始者為迦多衍尼子,著有《阿毗達磨發智論》,其主要教說為“三世實有,法體恒有”。“三世實有”指過去、未來與現在相同,皆有實體。“法體恒有”指色法、心法、心所有法、心不相應行法、無為法這五位(細分七十五法)均有實體。這一主張明顯誤解了佛陀在《阿含經》中滅盡十八界方入無余涅槃的教導,若“涅槃”與世間生滅法都是“實有”,則其“涅槃”必然不能脫離“三界”,是“假涅槃”,不能攝屬于佛陀所言之“出世間法”。薩婆多部認為佛教唯以八正道為正法輪之體,認為佛之說法中有無記語,將不利于自己的體系的佛陀言教說成“無記語”,而且說佛陀化緣盡時永入寂滅,將佛陀等同于其錯解的阿羅漢乃至斷滅論外道。玄奘作為通曉三藏的杰出法師,當然知道《發智論》的觀點誤解了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之教義,在辯難勝軍的論述中,明確指出大乘不承認《發智》的觀點是佛說。由此,我們可以為勝軍比量提出兩點辯護:
其一,從理上說,薩婆多部沒有真正宣揚佛陀的“出世間法”,并不能稱為嚴格意義的“小乘佛教團體”,自然不在“兩俱極成”的含攝范圍內。“佛教團體”的界定若沒有嚴格的標準,都由自己說了算,那么玄奘改成“自許極成”也會出問題。后世許多附佛外道及邪教都自稱是真正的“大乘佛法”,若把他們都算成“大乘佛教”,那么“自許極成”就將納入這些附佛外道的理論,同樣會落入玄奘責難的“兩俱不成”“隨一不成”“自不定”等過失。所以,玄奘用自己都認為是“非佛說”的教派作為佛教派別來辯難勝軍,有些牽強。
其二,即便承認“薩婆多部”是佛教團體,但“薩婆多部”也承認《增一阿含》的地位。玄奘在《成唯識論》卷三指出,“說一切有部《增一經》中,亦密意說此名阿賴耶,謂愛阿賴耶、樂阿賴耶、欣阿賴耶、喜阿賴耶”(23)護法等撰、[唐]玄奘譯:《成唯識論》,《大正新修大藏經》第31卷,第12頁。,還專門引用說一切有部所流傳的《增一阿含》,并且說此經有大乘經典的“阿賴耶”等名相。無著所撰《攝大乘論》也認為“聲聞乘中亦以異門密意,已說阿賴耶識。如彼《增一阿笈摩》說:世間眾生愛阿賴耶、樂阿賴耶、欣阿賴耶、喜阿賴耶”(24)無著撰、[唐]玄奘譯:《攝大乘論本》,《大正新修大藏經》第31卷,第134頁。。勝軍比量所引用的例證是《增一阿含經》,“經”的地位當然高于迦多衍尼子所造的《發智論》,即便其以《發智論》來辯難,也可以用《增一阿含》的論述讓其落到自相矛盾的境地。這可能才是勝軍比量“時久流行,無敢征詰”的關鍵原因。
《增一阿含》可以作為可信的小乘佛教經典,雖然在傳譯過程中有不同版本,但都記載了小乘人聽聞大乘法時紀錄的大乘名相,只是由于小乘人不能深刻領會大乘佛法,不能詳細記憶、背誦、記錄;但其中的大乘名相已經充分說明佛陀確實演說過大乘法。真正具信或實證聲聞解脫果的小乘信徒,可以據《增一阿含經》接受“大乘經是佛說”的觀點。從大乘經典看,大乘佛法含攝小乘佛法的內容,其范圍遠比小乘佛法深廣,真正的小乘圣者閱讀大乘經典之后,也不得不承認這些思想不是僅僅描述世間法的“非佛語”所能包含的,真正的大小乘信徒在此問題上可以“兩俱極成”,勝軍比量是可以成立的。另一方面,薩婆多部在當時信徒眾多,大家都認為其為“佛教”,而且其教理并非一無是處,其“五位七十五法”之說,經無著大師等修正為“五位百法”,對唯識理論的細化提供一定的思想資源。從當時印度佛教弘傳的事實情況看,玄奘以薩婆多部為假想敵,對勝軍比量進行修訂亦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