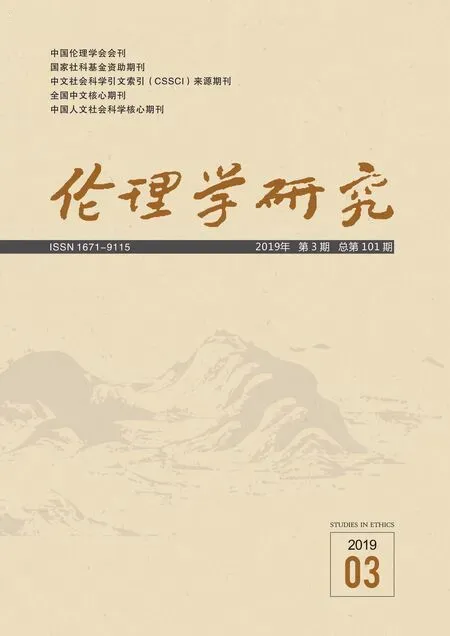文明共處的正義原則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
范寶舟,王嘉曦
資本擴張的殖民主義時代,刀與劍的血腥戰爭,使東方文明從屬于西方文明。美元統治下的霸權主義時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憑借對全球經濟規則的制定權,推行體現西方現代化、全球化價值觀的所謂“普世價值”。當今世界,盡管東西方之間你死我活的激烈博弈依然存在,但是,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的深入發展,以及人類面臨日益增多的共同挑戰,使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成為當代世界歷史進程不可抗拒的實踐維度。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使命相一致,我們必須徹底變革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時代文明間的畸形關系,構建與人類命運共同體要求相適應的文明共處的正義原則。
文明共處貫徹正義原則,是文明間實現相互理解和尊重的重要前提。文明間的相互理解和尊重,為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提供深層次的精神“黏合力”和不可或缺的精神自覺。文明共處正義原則既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內容,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要求。習近平科學把握當今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的時代節律,站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高度,創構了文明共處的正義原則,即,尊重文明多樣性、維護文明平等、注重文明共生共存。這一文明共處正義原則的創構,有力地駁斥了“文明沖突論”“文明優越論”“文明隔閡論”“文明威脅論”等錯誤思想;清晰地表達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過程中,文明間必須遵循包容、平等、共存等精神的核心內容;充分體現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方案的中國智慧,為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所不可或缺的文明間的相互理解提供可供遵循的實踐路徑。
一、尊重文明多樣性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文明多樣性表現為各民族、國家在語言、宗教信仰、藝術風格、風俗習慣、價值取向,以及生活方式上的差異性和獨特性。尊重文明多樣性,作為文明共處的正義原則,是對民族國家文明權利的根本保證。因為尊重文明多樣性,不僅是對文化殖民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破壞人類文明生態系統的一種否定,以及以商品經濟文化同質豐富多彩的人類文明的拒斥,更是對健康的人類文明生態系統的回歸。正如自然生態中的物種具有多樣性一樣,每一種文明都是人類社會生態系統中的一個“種”。文明作為人類社會生態系統的“物種”也必然具有多樣性。可見,人類文明多樣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尊重文明多樣性是文明共處實踐中維護文明正義的重要前提。習近平指出,“文明相處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1](P524)。對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言,尊重文明多樣性既是對人類共同體共同利益的根本維護,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活力源泉,促進差異性文明的相互作用,以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其一,尊重文明多樣性,促進文明多樣性發展,是對人類共同體利益的根本維護。從現存文明的價值來看,多樣性的文明,作為歷史的記憶,作為理解人類命運的密碼,作為我們探索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寶貴資源,都凝聚著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貢獻。文明作為人類精神的瑰寶都是人類擁有的共同財富。文明的多樣性存在,在于每一種文明都有其存在的歷史必然性、每一種文明都有其獨特魅力和深厚底蘊、每一種文明都是人類對世界的一種理解方式。習近平指出,“不同歷史和國情,不同民族和習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豐富多彩”[1](P544)。所以,一種文明的衰落乃至消失,都是人類共同體利益的巨大損失。從文明對人類面臨的現實問題的價值意蘊來看,人類歷史發展證明,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國家能夠自視其文明能夠掌握解決人類社會發展問題的全部真理。每一種文明都是在特定時代、特定區域對于其特定問題的回答,有其值得尊重的價值和智慧。即使是世界歷史進程進入到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期,各個民族國家遭遇到的問題依然有其特殊性。只有尊重文明的多樣性,才能發揮各民族、國家文明的積極作用,為各民族、國家找尋到適合其具體國情的解決發展問題的最佳辦法,從而促進人類共同體利益的實現。相反,以某一種文明為尊,企圖同化、改造、替代其他文明,在使人類大家庭喪失寶貴的文明財富的同時,也由于忽視了不同民族、國家的文化傳統、現實國情等等的差異性,而不利于各民族國家的發展,更不利于世界文明的共同發展。習近平指出,“不要看到別人的文明與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順眼,就要千方百計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圖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歷史反復證明,任何想用強制手段來解決文明差異的做法都不會成功,反而會給世界文明帶來災難”[2]。
其二,尊重文明多樣性,促進文明多樣性發展,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活力源泉。尊重文明多樣性,不僅能保證世界文明的多彩多姿,更是世界保持勃勃生機、具有活力的生動體現。文明多樣性是世界保持欣欣向榮的象征和標志。習近平指出,“應該維護各國各民族文明多樣性……這樣世界文明之園才能萬紫千紅、生機盎然”[2]。相反,習近平也指出,“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2500多個民族和多種宗教。如果只有一種生活方式,只有一種語言,只有一種音樂,只有一種服飾,那是不可想象的”[3](P262)。不僅如此,只有尊重文明的多樣性,才有可能把各個民族納入到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洪流中來,沿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求同存異,在文明間的辯證運動中,把多樣性文明的差異性和復雜性轉化為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斷向前發展的活力。一般來說,對文明差異性的尊重,可以讓一個民族、國家走出自身價值觀念的狹隘視野,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姿態,辯證對待其他文明的價值意蘊。可以說,文明包容性極強的社會,在與其他文明的交流共振中,自覺反思和改善自身而更加富有創新活力,經濟社會的發展則會動力十足。相反,保守性和排他性極強的社會,固守自身文明的差異性就會陷入原教旨主義的傲慢,排斥其他文明的差異性而陷入閉關自守的窠臼。由于固守文明的單一性,自身文明中的不足得不到反思,自身文明的優秀成分得不到激活。對傳統路徑的嚴重依賴,往往會讓“死人”抓住“活人”。閉關自守的文明盡管表面上看處于超穩狀態,實則往往是死氣沉沉,失去創新的活力,經濟社會的發展也就相對緩慢。相反,經濟社會繁榮發達的地區大多與文明多元共存的發達程度相關。歷史上,曾經輝煌一時的羅馬、西安、倫敦、紐約、香港等等莫不如此。可見,只有尊重多樣性文明,各種文明才會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活力源泉。
其三,尊重文明多樣性,促進文明多樣性發展,有利于在文明的相互作用中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文明多樣性帶來了文明之間的交流、碰撞甚至是沖突,即,文明之間的相互作用。文明之間的相互作用,一方面表現為文明之間的彼此欣賞、相互尊重、相互借鑒,以開放的心態吸收其他文明的優秀成分為我所用。這是一種主動積極的態度,彰顯了對多樣化文明的尊重和包容態度;另一方面表現為文明之間的彼此敵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先在邏輯預設,不僅產生文明間的相互排斥乃至對立,而且會導致文明間采取閉關自守、唯我獨尊,以至貶低、改造、征服其他文明的現象出現。這種相互作用,把文明的舞臺看作是各種力量彼此角逐較量的戰場。這是一種被動消極的態度,凸顯了對其他文明的傲慢和偏見。文明之間的這兩種形式的相互作用都是對立統一的體現。只不過前者以非對抗的形式呈現,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的自覺性的充分體現。后者以對抗的形式呈現,讓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付出更加沉重的代價。盡管如此,這種對抗性并不能阻止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前進的步伐。文明的相互作用,使得文明的多樣性不是一種僵死的存在,而是一種不斷發展著的、動態中的文明多樣性。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離不開多樣性文明之間的相互作用的推動。文明的相互作用,不會導致文明的同質化,反而通過吸收其他文明成果生成新的文明,從而不斷豐富世界文明的多樣性。習近平指出,“人類文明多樣性賦予這個世界姹紫嫣紅的色彩,多樣帶來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產生進步”[1](P524)。而且,“尊重各種文明,平等相待,互學互鑒,兼收并蓄,推動人類文明實現創造性發展”[1](P525)。
二、維護文明平等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維護文明平等就是尊重每一種文明的獨特性的意義,賦予每一種文明以等值地位,不把某些文明凌駕于其他文明之上。維護文明平等,作為文明共處的正義原則,既是尊重文明差異性的體現,也是保證差異性文明和諧共存的有效機制,更是能夠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文明相互理解的倫理環境。文明平等是對不同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文明間關系的重新審視。從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視域來審視的文明平等問題是與不同民族、國家文明應該受到同等的尊重和待遇聯系在一起的。習近平指出,“文明沒有高下、優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別”[1](P544)。所以,“要了解各種文明的真諦,必須秉持平等、謙虛的態度。如果居高臨下對待一種文明,不僅不能參透這種文明的奧妙,而且會與之格格不入”[3](P259)。當然,維護文明平等,不是文化相對主義所主張的無底線的泛多元論,因為不是任何文明都具有代表社會歷史前進方向的進步性。只有那些在各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切實推進了生產力發展、人的自由解放和社會進步的文明才具有平等性。同時,文明的平等性是相對的、具體的和歷史的,而不是抽象的、超越時空坐標的一種平等性。尤其是,文明的平等性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是在諸多文明的相互作用中所獲得的平等性。對腐朽的、倒退乃至反動的文明,如果不采取有理、有利和有節的斗爭,也就很難奢談有新生的、前進的和進步的文明的平等性。
其一,維護文明平等賦予每一種文明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都必須享有平等地位。任何一種進步的文明都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一員,都有其產生的歷史根據,都凝聚著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貢獻,要用平等的態度、一視同仁地承認他們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哪一種文明具有優越性或不具有優越性,不能把文明按照高低、優劣、貴賤,或第一、第二、第三……來做“差序格局”的結構排列。習近平指出,“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多姿多彩、各有千秋,沒有優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別”[4](P525)。因此,看待其他民族、國家的文明,既不能采取貶低和排斥的態度,也不能有文明同化的意念和企圖,更不能幻想把某一種文明上升為是可以統治世界、充任世界救世主的唯一的文明。文明平等性在于文明作為特定民族、國家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實踐產物,盡管不可能解決超越時空的問題,但畢竟是該民族、國家實踐智慧的結晶,其中,蘊含著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理解上的合理性。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中,盡管各民族、國家的文明都是從本民族、國家實際出發而形成的生活方式,以及對自身發展路徑進行深入思考的產物,但是,這種思考是歷史走向世界歷史過程中共同價值和各民族、國家特殊價值的辯證統一,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統一,從而形成具有各民族、國家特點的新生的文明。這種新生的文明恰恰是其他文明所不能,也是無法替代的。盡管其他文明在其本民族、國家發展中曾經起到過積極作用,但不能不看到這種積極作用的取得恰恰是由這個民族、國家的特定歷史條件所決定。超越這個條件則會是“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淮北則為枳”。因此,基于民族、國家特定文化傳統、特定的歷史使命,以及特定國情條件下產生的文明,如果它帶來這個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中都應當享有平等的地位。
其二,維護文明平等賦予每一種文明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的貢獻都是等值的。習近平指出,“各種人類文明在價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無是處的文明”[3](P259)。洛馬克斯認為,關于文明消失是因為該文明價值孱弱而被淘汰的達爾文進化論式的解讀,不僅反人類而且反科學。他指出,文明由于都具有同樣的表現和交流的作用,也就都具有同樣的價值。之所以如此,“因為它們豐富了使用它們的人民的生活”“因為每一種傳達系統(不管是語言、視覺的、音樂甚至食品)都包含著對自然和人類環境的重要發現”“因為每種文化都是一個有潛在力的寶藏,一個集體的創作,在無數世紀中傾注了一個分支的天才與智慧”[5]。湯因比針對文明,因為價值不同而不可比較,或者說,相對于自己的文明來說,其他文明根本就沒有價值,甚至是“非文明”的觀點,他認為,文明的價值是相對的。21個“文明社會”相對于原始社會而言,其文明成就是頗為可觀的,但是,“如果用任何一個理想的標準對它們全體加以衡量,就會發現它們做得遠遠不夠,它們之中沒有一個比其他社會更為高明。事實上,我們的21個社會可以在哲學上假定是共時與等值的”[6](P45)。對文明價值同等性的肯定,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時代對文明間關系的一種現代定位,體現了社會進步的趨勢和對歷史發展規律的遵循。這也是對殖民主義時代和霸權主義時代,關于文明間關系理解上的“種族中心主義”狹隘理解的一種超越。
其三,維護文明平等賦予每一種文明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的獨特性。維護文明平等必須超越文明優越論,不能用某一種文明作為標準、模式或理想,從外部去衡量和評判其他文明,而是要深入到該文明的內部,去審視其生成的社會實踐基礎,去看待其對該民族、國家的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所產生的積極作用。習近平指出,“本國本民族要珍惜和維護自己的思想文化,也要承認和尊重別國別民族的思想文化。每個國家、每個民族不分強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應該得到承認和尊重”[2]。所以,我們不能用今天的文明理念和文明樣式去審視傳統的文明理念和文明樣式,或者用美國的文明理念和文明樣式去審視非洲、亞洲的文明理念和文明樣式,或者用理想中的文明理念和文明樣式來審視不同民族、國家或不同時代現實的文明理念和文明樣式。同樣,相反也是如此。因為這恰恰是文明認知中教條主義或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體現。阿格尼絲·赫勒指出,“那些仍然在比較各種不同文化并把一個置于另一個之上的人們,除了證明他們采取了錯誤的立場外什么也證明不了。因為他們沒有做到僅僅從內部來看待各種文化,而是強加給它們一個外在的標準(外在于那個將因此而被貶至文化等級體系中一個較低層次的文化)”[7](P189-190)。
三、注重文明共生共存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文明共生共存意指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和相互借鑒的關系。它是歷史向世界歷史深度推進,尤其是當代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必然要求。當今世界,科學技術和產業發展的日新月異、國際分工體系的深刻變革,以及全球價值鏈的深度重塑等等,都賦予經濟全球化以全新的內涵。當代經濟全球化的這種深刻變革,把具有不同價值觀和文化傳統的國家民族的命運更加緊緊地聯系在一起。這在客觀上要求我們,對文明間關系不能再做非此即彼的沖突與對抗式的理解,而是要秉承包容精神做彼此依賴的共生共存式的理解。習近平指出,“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各國發展環環相扣,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協調合作是必然選擇”[8]。同時,全球性問題使人類面臨的威脅和挑戰,只有各國共同面對才能得到根本解決。人類越來越利益交融、安危與共。不同文明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都不可能成為一座文明孤島。因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要尊重文明多樣性、維護文明平等,更要注重文明的共生共存。
其一,注重文明共生共存,才能秉持包容精神,化解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的文明沖突。注重文明共生共存是秉持包容精神的根本保證。包容建立在對文明間相互依存、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關系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上,否則,包容就只能是為占領輿論制高點而做出的一種道德清談。道德清談式的包容是沒有實質內容、無助于化解文明沖突的形式主義。盡管文化多元化、文明多樣化是當今世界的顯著特點,然而,在它們日益頻繁的交流中,文化沖突、文明優越,乃至種族歧視的現象依然存在,究其根源,就是沒有深刻理解文明的共生共存關系。
建立在文明共生共存基礎上的包容,不僅尊重文明差異性存在的合法性,而且賦予每一種文明有表達自我訴求的權力,享有與其他文明平起平坐的待遇,從而實現文明之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誠如習近平指出的那樣,“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沖突’,就可以實現文明和諧”[3](P259-260)。不僅如此,文明的共生共存,有助于不同文明自覺把握世界歷史進程的節律,在不同文明的相互交往中,實現自身文明的“特殊性的普遍化”與世界文明的“普遍性的特殊化”的辯證統一。并且,文明的共生共存,不只是對不同文明價值的尊重,更是能夠對單一文明一統天下的企圖進行有效遏制,避免某一種文明的“一種聲音、一個調子”獨霸世界的現象出現。習近平指出,“推動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和平共處、和諧共生,不能唯我獨尊、貶低其他文明和民族。人類歷史告訴我們,企圖建立單一文明的一統天下,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4]。
其二,注重文明共生共存,才能開展文明間的平等對話,形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價值基礎。注重文明共生共存是開展文明間平等對話的前提和條件。沒有自覺的文明共生共存的清醒意識,往往會形成對其他文明的傲慢與偏見,拒絕文明間的交流互鑒。然而,誠如習近平指出的那樣,“歷史與現實都表明,傲慢與偏見是文明交流互鑒的最大障礙”[3](P259)。不僅如此,喪失文明共生共存的自覺意識,要么不切實際地認為自身文明具有超越時空的普世價值,并企圖以自身文明作為邏輯預設來改造其他文明;要么視自身文明為絕對優越,割裂與其他文明的交往而陷入孤立和隔絕狀態。原教旨主義就是典型體現。上述兩種態度都是對自身文明的盲目自大,而對自身文明的優點和弱點缺乏自覺的評價和認知,從而不僅不利于文明間的對話、溝通和理解,而且會加劇國家民族之間的裂痕、對立和沖突,給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造成巨大的障礙。
注重文明共生共存、促進文明間平等對話的自覺開展,不僅有助于我們發現不同價值體系的文明之間存在差異性的根本原因,避免由于對文明差異性的誤認而導致的矛盾沖突,而且有助于我們能夠從文明深處發現現有沖突的根源,從而對癥下藥,為解決現有沖突提供妥善和合理的方案。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增進文明間的平等對話,形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價值基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離不開人們對于涉及全球根本利益問題的共識。如果沒有共識,沒有共同價值為基礎,世界在面臨根本利益問題時就會是一盤散沙。盡管當今世界,參與全球交往的主體依然是民族和國家,并且每一個國家都有自身的特殊利益訴求,但是,這種特殊的利益訴求,有的又是與整個人類利益關聯在一起的。比如生態問題,盡管在世界氣候大會上,各個國家、地區之間在減排問題上為著自身利益爭論不休,但是“遏制氣候變暖,拯救地球家園,是全人類共同的使命”則是全球共識。不僅氣候問題如此,在當今世界經濟發展動能不足問題、國家以及網絡安全問題、恐怖主義問題、核威脅等等問題上也都是如此。所以,習近平指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1](P522)。
當然,共同價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更不能把普世價值混同于共同價值。普世價值總是賦予某一特定民族、國家的文明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泛化為全人類必須遵循的唯一具有合理性并具有普遍意義的文明。同時,共同價值的形成,文明的交流互鑒,也不是后現代主義者所標榜的是文化符號的自我繁衍、自我循環和自我復制的產物,而是在人類的實踐活動中,秉承文明共生共存的原則,實現不同文明之間相互溝通、相互理解、相互借鑒的結果。習近平指出,“對人類社會創造的各種文明……都應該采取學習借鑒的態度,都應該積極吸納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類創造的一切文明中的優秀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優秀文化精神弘揚起來”[2]。
其三,注重文明共生共存,才能摒棄零和博弈思維方式,形成不同文明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的共振效應。薩繆爾·亨廷頓預言,冷戰后的世界,“最可能逐步升級為更大規模的戰爭的地區沖突是那些來自不同文明的集團和國家之間的沖突。政治和經濟發展的主導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9](P8)。由此,他呼吁要加強西方文明內部之間的合作,以對抗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如果說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凸顯了對西方文明衰落的擔憂,那么弗蘭西斯·福山則信心滿滿地把西方價值體系看作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無論是亨廷頓還是福山,實則都是站在西方中心論的視角強調文明之間的沖突和對抗,并把西方文明作為其他文明效仿的普遍模式,實現其對世界秩序的重建。當前,特朗普要求世界其他國家秉承美國優先的原則,既是美國經濟霸權也是其文化霸權的當代體現。
然而,隨著當代經濟全球化的深度推進,當今世界不僅越來越呈現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形成為名副其實的“地球村”,而且政治多極化、信息社會化以及文化多元化帶來了全球治理體系的深刻變革。同時,人類面臨諸如經濟增長動能不足、恐怖主義肆掠、網絡安全危機、全球重大傳染性疾病困擾、全球氣候變暖、核威懾以及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等共同問題的威脅與挑戰,使得不同國家民族間的相互依存度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前所未有的增強。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不是某一個國家民族的“獨唱”,而是世界各國的“合唱”。習近平指出,“世界的前途命運必須由各國共同掌握”[1](P523)。
當代世界歷史進程的發展實踐,迫切要求我們要更加注重文明的共生共存,而不是強調文明間的沖突與對抗。注重文明的共生共存,一方面可以避免把其他文明看作是與自身文明相沖突和對抗的一種“他者”存在,從你死我活的絕對對立的思維中走出來,在文化自覺中把其他文明看作是謀求自身文明存在與發展的資源和條件。縱觀人類歷史發展,任何民族、國家在承先啟后、繼往開來中發展自己文明的同時,都是在文明的共生共存中、在或遠或近的意義上吸收和借鑒其他民族、國家的文明成果,汲取其他文明成果的滋養,從而保持自身文明持續不斷的創新動力。艾倫·洛馬克斯認為,即使是原始的或民間的文明也不是自我封閉的,而是與更大范圍或地區中的文明相聯系。他說,“文化不可能而且從來不是在隔絕中發展起來的,而是在那些既能保持獨立性而又允許非強加的外來影響的地方興起的”[5];另一方面可以正視文明間的分歧、求同存異,尤為重要的是,能夠理解和領會多元文明“和而不同、和實生物”的真諦,重新發現各種文明在應對全球性問題威脅和挑戰中的價值意蘊,從而自覺汲取不同文明中的智慧,形成不同文明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的共振效應。習近平指出,“我們應該從不同文明中尋求智慧、汲取營養,為人們提供精神支撐和心靈慰藉,攜手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各種挑戰”[3](P262)。不僅如此,世界文明的豐富和發展也正是在每一個民族、國家文明的你追我趕中形成的,從而帶來人類社會文明的整體進步。羅素指出:“不同文明的接觸,以往常常成為人類進步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學習希臘,阿拉伯學習羅馬,中世紀的歐洲學習阿拉伯,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學習東羅馬帝國。”[10](P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