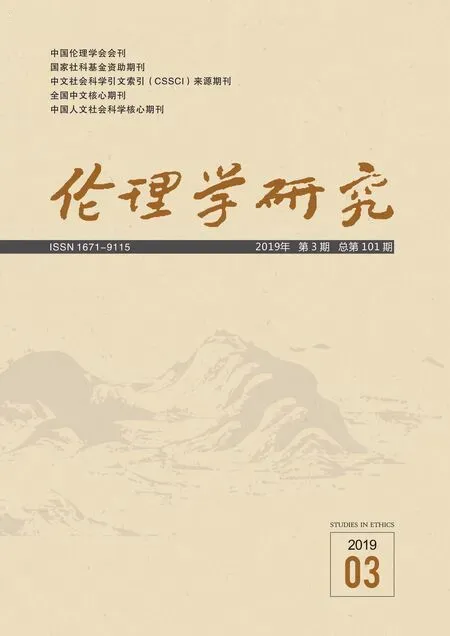共同體意識下的家國情懷論
張 軍
以公民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情感為基本內容的家國情懷培育是我國新時代思想道德建設的一個重要目標,尤其在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中要“開展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為重點的家國情懷教育……增強國家認同,培養愛國情感,樹立民族自信”[1]。但在國際交往不斷深化,全球化已成為歷史趨勢的今天,世界各國已經成為了一個相互依存、命運交錯的整體,構成了一種休戚與共的共生關系,習近平在多種國際場合呼吁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那么既要培育注重國家意識、民族情感的家國情懷,又要培養打破國界、關注人類整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體意識,這二者之間如何統一起來?這就意味著,新時代的家國情懷培育應該沖破傳統觀念的束縛,將之放置于關切人類整體利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背景下來考察,從共同體意識出發探尋家國情懷的時代境遇,發掘其存在的哲學根基,這是澄清其理論前提和劃定其實踐界限的可行路徑。同時,我們還應從學理層面厘清家國情懷的概念邊界,避免將其與其他情感混為一談,造成模糊的認識,產生不妥的行為。
一、家國情懷的內涵及其價值
家國情懷是在中國特有的文化環境下產生的社會意識,具有特定的民族和國家指向,因而具有獨特的內涵。“情懷”一詞,《漢語大辭典》中的釋義為:心情、情趣、猶胸懷;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釋義為:含有某種感情的心境;在《辭海》中的釋義為:心境、心情。綜合看來,情懷是指人對某物含有某種感情的心境,以及基于這種感情的對此物的包容與寬容的胸懷。因而,從語言學角度而言,家國情懷就是指人對與自己密切相關的集體如家庭和國家眷念與愛戴的心境,以及對其包涵與寬容的胸懷。
倫理學上的家國情懷是個人對于小至自己的家庭,大至自己所屬的國家的一種積極的思想意識,包含了人們對于家庭、社會、國家的一種情感認同和自覺擔當的意愿,反映的是個體與群體之間交織交融、休戚與共的關系,是對天下蒼生的仁愛之心,是對共同文化的認同,也是對普遍價值觀念的堅守與踐行。家國情懷在傳統文化中的生成基礎是中國傳統社會中“家國同構”的政治理念和“家國一體”的價值觀念。古人重視家庭與國家之間的辯證關系,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人生的價值取向。在當今時代,家國情懷是對于自身身份的認同,對于民族和國家的熱愛,對于民族文化的自信,以及對于維護國家尊嚴、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責任擔當意識。
家國情懷本質上是一種社會關系的精神化反映,是從情感方面對個體、家庭、國家、世界之間關系的道德評價,是道德認知、道德意志、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人格品質和道德行為習慣的綜合,體現為倫理個體道德動機的真實性和道德行為的自覺性和持續性。更深層次來看,家國情懷不僅僅是一種道德評價和道德規范,還是一種價值選擇和道德實踐,表現為倫理個體道德內化與道德行為自覺的統一,是一個知行合一、道德意識自覺與道德行為自控有機結合的過程。
新時代背景下的家國情懷從傳統文化中脫胎出來,與時代實踐緊密結合,被賦予重要的時代價值。
第一,家國情懷對培養人們正確的歷史觀具有重要價值。從唯物史觀來看,社會意識形態是具有繼承性的。恩格斯以哲學為例說明了這個問題,他說:“每一個時代的哲學作為分工的一個特定的領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驅傳給它而它便由此出發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為前提。”[2](P612)家國情懷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雖然在各個歷史時期有內容上的差異,但其核心內涵是一脈相承的。我國歷史上的諸多歷史文化名人,其深厚的家國情懷影響和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人為民族和國家利益舍身奮斗。家國情懷已經成為我國歷史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世界交往日益深入的今天,面對外來文化對本土文化的巨大沖擊,家國情懷能夠喚起人們重新審視自己民族和國家的歷史,對傳統進行反觀和揚棄,在反思歷史得失的過程中,堅定本土文化和傳統的獨特性,從而樹立正確的歷史觀。
第二,家國情懷對促進人們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具有現實價值。正確價值觀應該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思想前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思想基礎,二者融合統一而形成的科學的價值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3](P170)傳統文化中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樂精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意識,“家國一體”的整體情結等所體現出來的家國情懷對于正確的價值觀培養仍然有著不可小覷的意義和價值。在風云變幻的當今世界,面對各種社會思潮和社會現象,要做出正確的價值評判并非易事。家國情懷基于對自身民族和國家的忠實情感而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其本身就蘊含著個人與集體、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義利觀念,并且是個人與家庭、個人與國家、家庭與國家之間的一種利益取舍和價值取向,因而,家國情懷作為一定的價值標準能夠提供價值指引,有助于端正人們的價值觀念。
第三,家國情懷對促使人們樹立高尚的道德觀具有獨特價值。道德觀是人們在道德活動中產生的各種關系以及處理這些關系的基本準則,包含著行為的道德品格和價值。道德力量的發揮對于人高尚的道德情感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黑格爾說:“精神上的道德力量發揮了它的潛能,舉起了它的旗幟,于是我們的愛國熱情和正義感在現實中均得施展其威力和作用。”[4](P32)而家國情懷是一種崇高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行為的統一體,具有巨大的道德力量。《晏子春秋》中所謂“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就是一種基于家國情懷的道德觀。因此以家國情懷為出發點來引領人們的道德修養和道德評判,能夠促進人們的道德意識和道德水平的提升。
綜合來看,家國情懷作為精神理念、價值取向和道德規范,已經成為融入中華血脈中的文化基因,對中華民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家國情懷扎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今社會,家國情懷又呈現出重要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在繼承和弘揚傳統文化,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值得肯定和認可并大力弘揚和培育的人的精神意志。
二、家國情懷與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不能直接等同
家國情懷由于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而受到極大的推崇,這對于國家發展、民族振興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但是,對于家國情懷的弘揚及培育,其前提是要對家國情懷有正確的認識,要防止與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等意識混為一談,尤其有害的是將家國情懷等同于激進愛國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因此有必要對這些概念之間的關系加以厘清。
第一,家國情懷不能直接等同于愛國主義。人們很容易把家國情懷與愛國主義混為一談,這是因為二者都以對于祖國的深厚感情和責任擔當作為感情起點。但是二者卻有著明顯的差異。首先,二者概念內涵不同。家國情懷講究的是一種心境,是一種個人所包含的對家庭和國家愛戀情感的心境,其中雖然包含著愛國主義的因素,但還包含諸如共同體意識等其他因素;愛國主義是一種政治意識與道德規范,是愛國情感、愛國覺悟和愛國行為的統一。其次,二者所指相異。家國情懷的所指范圍更為寬泛,除了包含對民族和國家的深厚情感外,還含有濃厚鄉梓之情,它起于情感主體對于其所生所長的環境的一種物緣情結,表征為對故土家園諸多事物的眷念之情;愛國主義的所指主要集中于針對民族和國家文化認同和利益維護,既是道德要求也是政治原則和法律規范,因而對情感主體構成政治和道德上的雙重約束。最后,二者所適應的情感主體有別。家國情懷是在中國獨特的傳統文化中產生的,并已成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對其傳承和發展反映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歷史現實的有機融合,因而它具有獨特的中國歷史文化土壤,其情感主體僅限于中華民族;而愛國主義是一種大眾情感,其所適應的情感主體沒有限制,任何國家和民族的個體都能夠產生愛國主義的情感。
愛國主義圍繞國家利益這一中心來處理國家與個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強調國家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并在復雜的國際關系中捍衛自己國家利益。而且“愛國主義精神是國家凝聚力的精神核心,表現為它是國家凝聚力最堅實的精神支柱”[5],因而愛國主義對于凝聚人心、共同維護國家權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愛國主義是基于人的認識的一種情感,由于沒有統一的衡量標準而難以準確把握。如果過分強調國家利益的排他性,就會很容易陷入偏激的愛國主義情緒之中。激進的愛國主義以個人的激情和沖動為基礎,是一種基于感性認識的情感宣泄,不能顧及語言和行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這種情緒會滋生出魯莽的、盲目的、不顧后果的行為,甚至被某些別有用心的個人或集團所利用來達到其特定的目的,是十分有害的。家國情懷中所包含著的愛國主義情愫是一種去偏激化的理性的愛國主義。
第二,家國情懷有別于民族主義。人們也容易將家國情懷和民族主義混為一談。民族主義是一種特定人群對其所屬民族帶有特殊情感的思想意識形態。美國學者漢斯·科恩認為,民族主義“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應被認為是一種思想狀態……在這一思想狀態中,體現了個人對于民族國家的高度的忠誠”[6](P10-11)。民族主義從本民族情感出發,自覺維護本民族的利益、地位和尊嚴,從性質上來看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并帶有一定的封閉性。家國情懷雖然包含著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但是與民族主義又不能同日而語。首先,二者的連接載體不同。家國情懷中的家國意識以地域和傳統為連接載體,地緣、物緣和文化是維系家國情感的媒介,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景觀和共有的記憶和傳統能夠激發人的家國情感,家國情懷也往往以此為情感基點;民族主義以民族和信仰為連接載體,民族認同和共同信仰是維系民族主義情感的媒介,政治訴求是民族主義的特性。其次,二者文化內涵相異。家國情懷所包含的家國情感是一種復雜情感的綜合體,雖然其中也包含有民族情感,但除此之外還有國家情感、家園情感、故土情感等其他復雜感情;民族主義的情感則主要集中于對本民族身份的認同和對政治的訴求,相對而言較為單一。再次,二者指向性有別。雖然家國情懷和民族主義都是屬于集體意識,但是家國情懷是一種開放的集體意識,其內容涵指更為寬泛,家、國、天下都是其情感指向,因而家國情懷具有更強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民族主義是一種相對封閉的集體意識,局限于本民族的集體范圍,情感基點是與本民族相關的事和物,因而其特定指向性更強。最后,二者的偏重點不同。雖然二者都屬于社會意識形態范疇,但家國情懷更為偏重于道德層面,包含對社會關系的道德評判;民族主義則偏重于政治層面,包含維護本民族利益的政治訴求。
基于“民族主義解決問題的辦法主要是訴諸人類放蕩不羈的情緒,而不是訴諸人類那點本來就十分有限的理性稟賦”[7](P265),也正是因為民族主義的排他性和封閉性,加之民族情感具有感性化的特點,如果對民族主義把握不好,很容易陷入狹隘民族主義的泥淖而走向極端化。狹隘民族主義以本民族的利益為中心,對其他民族具有極強的排斥性,為了實現本民族利益可能不擇手段,不計后果,是一種危險的社會意識。如果任其發展,情感主體將有可能被打著民族利益和愛國主義的旗號所迷惑,甚至利用國家政權,做出損害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的事情,構成霸權主義或沙文主義,最終也將損害到自身的利益。因此,民族主義者尤其是狹隘民族主義者不能被看作是具有家國情懷的人,只能說是打著家國旗號的投機者和陰謀家。
三、共同體意識與家國情懷的一致與差異
家國情懷作為一種具有開放和包容意識的愛國、愛家的心境和胸懷,是一種人文主義的情懷。家國情懷在本質上具有內外兼容性,并不局限于地域意義或政治意義上的對國家的熱愛,而是情感主體對于家園、故土、祖國甚至于整個地球的依戀情感,對于家庭養育、國家培育、地球承載滋養的一種感恩之情,是一種自發的共同體意識。因而從共同體意識的研究出發,通過對二者差異性和同一性的比較,可以發掘這種情愫存在的哲學基礎。
第一,共同體是具有共生共存關系、共同性質、共同思想信念和情感維系的人的群體。滕尼斯以社會為對照說明了共同體的特征:“共同體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會不過是一種暫時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體本身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生機勃勃的有機體,而社會應該被理解為一種機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8](P54)由此看來,共同體是一種具有共生共存關系的人的群體,并由某種共同而又具有約束力的思想信念和情感維系。成員對共同體充滿依戀和尊敬,并能夠自覺承擔某些義務來維護共同體的聲譽和利益。在邁克爾·泰勒看來,共同體形態至少存在三種特性:其一,共同體成員有共同的信仰與價值觀;其二,共同體成員間的聯系是直接的,不需要政治權威等媒介的作用,也是多元的,即帕森斯理論中提到的“復合型”;其三,成員間是一種普遍的、強有力的,深程度的聯系,是不經過精密計算的共享、貢獻和互助[9](P25-33)。可見,共同體內部應該是一種和諧、平等、互助、共贏的關系,個體之間的信仰和價值觀念具有一致性和趨同性。
家庭、村落、國家都是典型的共同體形式。家庭是血緣共同體,是家庭(或家族)成員通過血緣的紐帶聯系在一起,在享受權利分配的同時承擔著對于家庭的責任和義務。成員能夠自覺遵守家庭秩序,維護家庭名譽和利益,具有較強的親情感和歸屬感,并且這種情感不以時間和空間的轉換而轉移。因此,情感是維系以血緣為基礎的家庭共同體的主要介質。村落是生活共同體,是以地緣為紐帶而形成的社會群體,具有典型的社會生活形式,并且通過長期的共同相處,形成較為固定的鄉規民約、風俗習慣和管理模式。這種社會共同體的成員生活于較為穩定持久的“熟人社會”,擁有共同的記憶,有較為一致的情感取向和價值追求。個體在較為固定的社會環境中成長,形成較為固定的語言、思維模式和生活習慣,這些方面不會因為時間和地點的轉換而徹底消除。國家是以人民為紐帶而形成的民族共同體。在同一國家中,公民個體對于民族國家在文化和政治上趨于認同。在國家主權、領土、傳統、信仰等方面具有認同感,對于共同體這一集體具有歸屬感并從中獲得安全感。
當然,除了家庭、村落和國家,還會有各式各樣的共同體形式。由此看來,共同體具有層級性,各個共同體之間又具有一定的交叉性。隨著全球化的加劇,各個國家、民族之間的交往加深,相互之間構建起了前所未有的依賴關系。形成了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共同體、政治共同體、文化共同體、生態共同體等等,這說明當今世界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合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人類的利益已經打破了國界,正在走向全球一體化,整個人類的命運被緊密聯系在一起。宏觀看來,世界各國人民最高層面、最大限度地形成公共意識已成為可能,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具有了實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10]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一種高層級的共同體形式,是從“類整體”思維層面來構建的一種高級共同體,是實現馬克思“自由人聯合體”的必經之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基于對全球化趨勢的深度把握、對人類共同面對的各種危機的隱憂而提出的價值理念和治理方略,是建立在各種文明相互尊重、互相交流、和諧共存的前提和基礎之上的共生有機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明之間要對話,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11](P524)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在尊重主權的前提下謀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在尊重差異的前提下尋求國際關系中的最大公約數,是實現人類利益最大化的可行路徑,其最終目的是促進人類的整體發展和進步。因而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利益共同體,也是情感共同體、道德共同體,是人類整體利益和全球倫理的有機統一。
第二,共同體意識是一種公共意識和公共精神,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是其最高層面。共同體意識是基于共同體中公共的價值觀念、文化認同、理想追求而形成的一種公共意識。共同體的公共特性是共同體意識形成的基礎,共生與共享是共同體意識的核心。共生關系意味著個體之間的相互依存和密切聯系,是一種興衰相通、榮辱與共的關系,正是因為這種共生關系,使得個體之間去除分歧,最大限度地形成公共意識。共享是共同體意識形成的最終目標,共享的目標促進著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和發展。這種公共意識從精神實質上來看又是一種公共精神,它“包括了獨立人格精神、社會公德意識和責任意識、自制自律的行為規范、善待生命社會的慈悲胸懷,它所折射出來的價值理念、生活方式具有持久深遠的影響,本質是和諧的”[12]。共同體意識也是基于共同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情感的一種社會意識,蘊含著和諧、持久、合作、互助、共贏、共享的價值理念。
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是人類公共意識和公共精神最高層面的體現。這種公共意識以人類的共同發展和進步為價值追求,包含尊重差異、擱置分歧,消除傲慢和偏見、摒棄零和思維和冷戰思維,最大限度地發掘彼此之間的同一性等人類“整體性”思維,目的在于應對人類共同面對的各種機遇和挑戰,謀求人類的和平發展與共同進步。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是一種“類意識”,是全球倫理觀的體現,反映出人與人、人與世界之間相互依存的整體性聯系。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對于促進人類的整體進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要我們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攜手努力、共同擔當,同舟共濟、共渡難關,就一定能夠讓世界更美好、讓人民更幸福。”[11](P482)
第三,共同體意識與家國情懷具有同一性。共同體意識與家國情懷兩種社會意識在一定層面能夠統一起來。首先,共同體意識和家國情懷都屬于一種公共意識。共同體和特定的家庭、民族、國家等都是群體的凝聚單位,都是一種公共存在。公共存在需要一定的公共意識來維護。共同體意識與家國情懷正是維護不同公共存在的公共意識。家國情懷中的“家國天下”思想是其公共意識的內在體現,同時也蘊含著公共價值取向。共同體意識和家國情懷都以團體公共利益的維護為其價值選擇,二者都體現了一種共生、共贏、共享、和諧、合作和擔當的價值觀念,都是整體意識、合作意識和責任意識的有機統一。
其次,共同體意識和家國情懷都蘊含著個體與集體之間關系的和諧統一。從唯物史觀看來,雖然人的特殊性是作為個體的存在,但是社會性是人的本質屬性。馬克思說,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3](P135)。人的社會性存在就是人的普遍性的體現,也就是人的公共性存在。因此,人的社會存在是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統一,為社會意識所反映。共同體意識和家國情懷都屬于社會意識,都包含著人的個體意識和群體意識的辯證統一,也就意味著對個人與集體之間矛盾關系的合理解決。
其三,家國情懷本身就屬于一種共同體意識。家國情懷在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體現了“家國一體”政治模式下個人對集體公共利益的服從與維護,傳統家國情懷中所蘊含的忠孝、禮義等傳統倫理思想是共同體意識的反映。雖然家國情懷在當今時代已經有了新的內涵,其中所包含的個人與集體間的關系更具合理性,但它仍然是屬于共同體意識,由于其情感指向為家庭、民族、國家這幾種特定的共同體,所以它是針對于特定共同體的特定的情感,其本質與共同體意識的本質相同,是共同體意識中的一種特殊形式。由于涉及到國家和民族情感,并且與政治和意識形態緊密相連,因而家國情懷可以看作是共同體意識在政治與意識形態層面的表達。
第四,共同體意識與家國情懷也具有差異性。共同體意識與家國情懷又存在多方面的不同。首先,二者屬性不同。共同體意識是中性的,不帶有政治色彩和特定民族傾向,任何個體都能夠具備或培養共同體意識,因而共同體意識較家國情懷更為中立,更為開放。而且共同體小到家庭血緣共同體,大到人類命運共同體有不同的層級,每一層級由于其聯系載體的不同而構成不同性質的共同體,因而不同共同體意識的內容和價值選擇也不盡相同。家國情懷是有特定所指的公共意識,這種公共意識特指對家鄉、故土、國家的愛念之情和責任擔當,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家國情懷又是與國家利益緊密相連的觀念上層建筑,是一種政治與意識形態的表達,具有較強的限定性。
其次,二者外延有別。共同體意識較家國情懷的外延更大。共同體意識的所指可以超越地域、民族、文化的限度,散居在地球上任何角落的人們只要有利益共同點就可以聯合起來組成共同體,隨之產生基于該共同體的共同體意識;家國情懷是在中國社會歷史環境中產生的,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這一情感專門指向由中華民族組成的中國這一特定共同體,因此,家國情懷是一種有局限性的存在,是一種維護特定共同體利益的意識形態,也是一種有對立面的存在,其愛憎情感明顯,對待與之相對立的情感表現出極其憎惡的情緒。
其三,二者實現的條件有差異。家國情懷是當前可以追求的,也是應該追求并且能夠實現的一種共同體意識。只要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不管其身處何處,也無論貴賤,都可能產生強烈的家國情懷,并且這一情感可能伴隨其終生存在。而共同體意識達成的條件有差異,形成普通共同體意識的條件并不高,其形成條件甚至要低于形成家國情懷的條件,只要有相關的連接載體就可能形成某一類別的共同體意識,并且這種意識可能隨著連接載體的消失或者共同體的解散而消亡。但是,共同體意識的最高形態——天下意識,即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其連接載體是人類的整體利益,在全人類的范圍內要求各個國家或者各個利益主體擱置爭議與分歧,是“基于‘利益攸關性’‘同命相連’‘共同發展’建構真實的、平等的、互利的真正共同體”[14]的意識,是人類一種美好的愿景,其形成則是一個長期的目標,必須經過整個人類整體的長期努力才能形成,目前還不具備完全實現的條件。
四、共同體意識下家國情懷的堅守與超越
基于共同體意識和家國情懷的差異性和同一性,將二者放置于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加以分析,我們能夠發現,堅守和超越家國情懷與共同體意識是辯證統一的。
堅守家國情懷的基本緣由是國家還將長期存在。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15](P297),它將隨著階級的消亡而消亡。但是國家的消亡是一個歷史過程,在短時間內難以實現。現階段雖然我們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并得到了一定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但是從全球整體層面來看,社會主義還是作為矛盾的特殊性存在,與資本主義的階級矛盾難以在短時間內消除,國家的存在還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加之經濟全球化程度還沒有達到一種極高的程度,各種“逆全球化”的思潮還很盛行。因此,短時間內要構建一種“天下大同”的政治共同體還不具備條件。列寧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16](P6)在民族國家林立的當今世界,構建維護國家這一特定共同體利益的意識形態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而家國情懷正好是這種意識形態的典型代表。家國情懷作為一種國家共同體意識是一種典型的觀念上層建筑,家國情懷的培育能為政治上層建筑提供良好的保障和有益的補充。
家庭和國家作為獨立存在又相互關聯的集體,是辯證統一的關系,二者之間既有同一性,也有斗爭性,是作為矛盾的對立面存在的。同樣,作為集體的家庭和國家與個人或與整個世界又都構成矛盾的對立面。在認識這些矛盾時,如果忽視同一性,放大斗爭性,就會產生不合理的家國意識,也不是真正的家國情懷的應然狀態。如果從共同體意識的角度來認識家國情懷,則可以突破家國意識的局限性,使之與全球意識、人類整體意識、天下意識主動對接,促使家國情懷能夠做到上下兼容。
共同體意識蘊含著合理的矛盾觀,在承認矛盾雙方對立性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找尋二者的同一性,是一種求同存異的思想。從這一思想出發,就能較好地找到家國意識與個體意識、家國意識與全球整體意識之間的契合點。共同體意識能夠促使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家庭和國家等集體之間擱置分歧和對立,樹立維護集體利益的整體意識,這就是家國情懷。共同體意識也能夠促使國家與國家之間擱置爭議與分歧,樹立全球整體意識,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達到國家之間和諧、共贏和發展狀態,真正構建和而不同的國家關系,最終實現天下大同的理想社會。
人類社會發展已經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一方面,人類正共同面對著諸多發展機遇,如太空探索、海洋開發、生物工程、互聯網建設、人工智能等等。要把握這些發展機遇,光靠某個國家、某些民族,其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樹立“類主體”意識,從人類整體利益出發,充分調動全世界的力量形成合力,才能很好地把握機遇,趨利避害,促進整個人類的和平和發展。另一方面,人類社會在快速發展的同時,全球問題已經擺在了全人類的面前,諸如環境惡化、資源匱乏、生態危機、核威脅、恐怖主義、重大傳染疾病、金融風險等全球公共危機已經遍布全世界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領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置身于這些全球性公共危機之外。基于全球性公共利益和公共危機的普遍性,人類命運共同體實際上已經具備現實存在的聯系載體,即人類整體利益。但是只有讓全世界人民都有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能夠自覺維護人類整體利益,人類命運共同體才能真正形成。只有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才能讓人類從容應對各種全球性的機遇和挑戰,同時,也只有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才能讓人類的先進文明成果為全人類所共享。可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形式上看似乎是對家國情懷的超越,實質上與家國情懷是一脈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