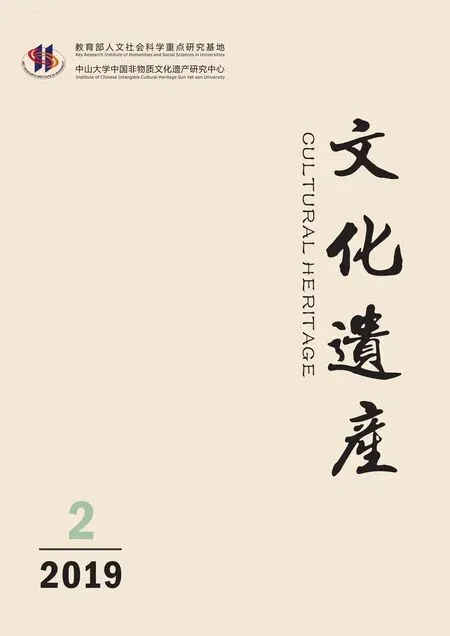傳統工藝核心技藝的本質與師徒傳承*
謝崇橋 李亞妮
傳統工藝保護的重要目標之一,是要努力讓傳統工藝實現順利傳承,所以非遺保護相關部門出臺了各種政策措施,幫助掌握非遺技藝的傳承人帶徒傳藝。常見的措施有給師傅發放津貼、為傳承人提供帶徒傳藝的場地,舉辦作品展示、展銷會和其他宣傳推廣活動等等[注]文化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律法規資料匯編》,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3年。。其中工作做得細致、扎實的,甚至還幫助傳承人進行社會招徒,組織相關項目的傳藝活動[注]其中北京市西城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和北京聯合大學已經為北京的部分瀕危非遺項目連續多次招徒和舉辦培訓活動,產生了較大社會影響。另外,2016年起,教育部已開始設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藝術傳承基地”,組織一些高校進行非遺等傳統文化相關的傳承活動。。這些政策措施對工藝技藝傳承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因為大多數政策措施的理論基礎在于重視作為施藝者的師傅在傳承活動中的作用,因而總是把鼓勵、支持和資助師傅帶徒傳藝的活動放在首位,而忽略對徒弟在工藝傳承過程中地位的準確認識。因此,這些政策措施的實施過程中,核心技藝的傳承仍面臨兩難境地:一方面,設立非遺保護政策措施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希望工藝技藝能夠順利傳承甚至發揚光大,理應包括核心技藝的順利傳承;另一方面,因核心技藝的傳承通常涉及到師傅的實際利益,這些政策措施和各級執行部門卻又不能明確要求師傅毫無保留地傳授核心技藝。而且,在很多研究者從事傳統技藝研究的過程中,對核心技藝也是避而不談或者一筆帶過,未觸及核心技藝的本質,或者對只注重討論施藝者的傳承意識而非過程、方法,對技藝傳承的受藝者——徒弟一方重視不夠。
一、“核心技藝”的本質
(一)“民間傳說”中的“核心技藝”
有關工藝的民間傳說中有不少血淚史,比如為了做成瓷器、鐵鐘、鐵劍,夫妻或子女獻身爐火(后來轉換成用指甲蓋或頭發等物代替血肉),其中最典型的如“龍鳳瓷床”一類的傳說[注]高等學校民間文學教材編寫組:《民間文學作品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第109-112頁。。類似這樣的女童祭窯類母題表達的文化內涵在于,因為某項工藝中的核心技藝很難解決,長期鉆研、反復試制也不能實現,于是破解關鍵環節難題時就需要某種特殊的、非常規的,甚至是神秘力量的方法。在這類傳說中,完成核心技藝的工作似乎比較困難。在有關工藝技藝的另外一些行業傳說中,師傅總是有一套絕活輕易不外傳,或者因為有“教會徒弟餓死師傅”的擔心,會對徒弟“留一手”,工藝做到最關鍵的時候,就找個理由把徒弟支走,一轉眼就完成了自己的作品,讓徒弟總是學不到核心技藝。[注]凝若:《教會徒弟,吃飽師傅》,《職業》2012年第8期。這些傳說似乎存在悖論:一方面核心技藝非常不容易解決,另一面核心技藝環節又能在一瞬間完成,似乎非常簡單。我們是不是可以這么理解:對于沒有掌握核心技藝的人來說,核心技藝難以突破;對于知道其中“秘密、訣竅”的人來說,核心技藝其實非常容易掌握。復雜工藝的核心環節,關鍵點其實并不多。事實果真如此嗎?難以突破的核心技藝難道就是皇冠上的那顆珍珠,需要時刻精心守護,一不小心就會被人摘走嗎?或者是否可以這么認為:傳統工藝的核心技藝,對有些人來說容易掌握,對另外一些人可能無法領會?假若師傅總是留一手,那么核心技藝又如何實現傳承?
(二)“核心技藝”是否存在
《三國演義》中有關于諸葛亮做木牛流馬的故事,曹操派人搶去幾件木牛流馬也無法仿制出來。《墨子·魯問》中有魯班削竹木以為鵲三天三夜不落的記載。傳統手工藝的魅力,往往就在于它們擁有類似諸葛亮的木牛流馬、魯班的竹鵲這類“機巧”“匠心”。這類“機巧”應該可以看作是該工藝的核心技藝,喪失該技藝的核心成分,該工藝要么會喪失存在的價值,要么失去傳承的必要性。
木牛流馬、三日不落的竹鵲已不存在,后世有一些科技工作者也曾試圖用現代手段復原這些器具,不過仍然有些人會懷疑這種物件是否曾經出現過。但這類有確切記載或者還有實物存在但卻已經不知當初制作方法的物件[注]比如北京故宮博物院保存有實物的盤金毯以及明清斷紋家具等的關鍵制作技藝就曾失傳,雖然經過當代工藝師傅的研究后能夠仿制出相似的物件,但今天的制作方法是否與這些物品當初的制作方法完全一致,仍然難以斷定。分明是在告訴我們:的確有一些核心技藝失傳了。這些技藝為什么失傳?今天仍在流傳的很多手工藝,真正掌握其核心技藝的人也只是從業者中的少數,傳承下來的技藝為什么也只有少數人掌握?當我們真正面對傳統手工技藝的傳承人,尤其是那些瀕危傳統工藝技藝的傳承人和他們的項目時,就會有較為清晰的看法。比如傳統造紙,“抄紙”環節是核心技藝之一,任何人都能毫無遮掩地看師傅操作甚至動手參與這個環節,但師傅能輕而易舉地抄出厚薄均勻,韌性一致的紙張,而旁觀的人卻做不到。不是師傅不傳,而是學習的人并不容易領會到。
圖1本文作者謝崇橋(右)在安徽涇縣中華宣紙文化園體驗抄紙技藝(孫亞紅攝)
陶瓷制作工藝中,很多人認為其核心技藝是各種配方,比如泥的配方、釉料的配方,其實都是相對比較容易傳授和掌握的技藝,甚至可以說只是技術,與抄紙這類能看能學卻不一定能掌握的核心技藝有一定差別。傳統陶瓷制作工藝中真正算得上核心技藝的,要算是手工拉坯、燒窯的火候控制等環節,旁觀者同樣可以看師傅怎樣操作,卻不能輕易掌握該技藝。手工拉坯是一項誰都可以看,可以學的工藝,包括景德鎮無數從事陶瓷制作的工匠,其中拉坯做得好、水平高的并不多,不少工匠甚至只從事專門器皿的拉坯工作而不“跨界”做其它器皿,比如做茶杯的不去做大缸,做大缸的也不做茶杯。掌握拉坯這樣的核心技藝并不是只要師傅認真教,徒弟就能學會的,它需要徒弟的悟性。同樣,盡管現在有了能夠控制溫度和時間的電窯,真正優質高檔瓷器的燒制仍然要靠高水平的師傅而不是僅憑機械控制。一般人可能會認為那是經驗,但有些從事了多年的相關工作的人,卻未能做出高水準、品質優的作品,有人從業幾年就做出被大家公認的佳品,僅僅用“經驗”來解釋明顯難以服人。
圖2景德鎮藝人在通過拉坯成型制作大型器皿(謝崇橋攝)
如果核心技藝只是技術,它應該容易被傳授和掌握。無論保密工作做得多好,在世代相傳的過程中,泄密也在所難免,至少很難做到讓一個跟隨師傅多年的徒弟也掌握不了該核心技藝。但事實是,在很多傳統工藝的傳承過程中,不少跟隨師傅多年的徒弟,最后仍然做不出能與師傅媲美的作品。
(三)“核心技藝”不同于“關鍵技術”
那種徒弟看一眼就能學會的技巧,或者某種特殊的配料,我們可以稱之為“關鍵技術”。“關鍵技術”與“核心技藝”最重要的區別,就是“關鍵技術”可以量化和傳授,“核心技藝”不可量化,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需要徒弟自己領悟。
凡是認可核心技藝特殊性的人,就會特別重視它,并且往往強調在傳統工藝傳承發展過程中,應注意保留核心技藝,比如民藝專家徐藝乙先生就認為傳統工藝在現代化、機械化過程中,核心技藝還是應該保留人工操作。徐先生還在文章中提及日本“曾經規定傳統工藝生產過程中,不是主要工序的可以采用機械,但是所占比例不要超過20%”[注]徐藝乙:《傳統工藝的現代化須保留核心技藝》,《搜狐網》,2017年8月8日,http://www.sohu.com/a/163242138_289194,下載時間2018年10月9日。,以此作為例子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徐先生之所以強調保留核心技藝的手工操作,是要強調“人”的作用。而人是多樣并且存在差異的,并非只要是由人來操作,就能完成核心技藝的工作并達到一定水準。正是因為人的差異,才會有手工藝品質量、藝術水準的高低,如果不用區分人的能力強弱,只要由人來操作就行,事情會變得簡單很多。如果不同的人操作的結果不會形成差別,讓機器來做應該能比人做得更好。那么,為什么強調核心技藝必須由人來操作?就是因為在制作環節上,不同的人操作會有不同的結果。機器制作完成的產品的藝術性跟工藝大師親手操作完成的作品的藝術性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四)“核心技藝”的藝術性本質
現代機械生產已經能代替人完成大量工作,智能生產還在進一步提升機器的工作能力,所以很多人擔心機器在未來會不會完全取代人。也有相當一部分人認同,在藝術品的創作方面,機器不可能完全代替人[注]林命彬:《智能機器的哲學思考》,吉林大學2017年博士學位論文。。3D建模打印已經能滿足個性化定制的需要,能因人而異地滿足客戶需求進行制作,做出來的產品也會越來越精美。但藝術品之所以不同于機器制作的產品,或者說不同的人制作出來的藝術品之所以有高下之分,還在于藝術品中的藝術成分、藝術水準有高低之別。為了描述繪畫作品藝術水準的高低,中國傳統藝術理論家用“傳神”“氣韻”“意境”等詞語來表述、現代藝術理論家用“繪畫性”等詞匯來描述,都有道理,卻仍然難免顯得不準確或者太過模糊。作品“藝術性”難以琢磨,讓不少對藝術不敏感的人甚至懷疑它的存在,尤其是在本來是為實用而生的傳統工藝作品之中,但只要我們認可藝術品的存在價值,就應該能接受藝術水準有高下之分的觀點。機器不能代替藝術家的根本原因,就是無法做出“傳神”的、高藝術水準的作品,本質上就是“藝術性”的問題,核心技藝所反映出來的“藝術性”之高低也恰恰是該工藝品類能否被人接受、欣賞的原因。
正是因為這種差別是“藝術性”而不是“技術性”的差別,所以才存在無法言說、難以傳授的情況。作品優劣的差別可能就是一條線的走向,一種顏色的鮮艷與灰暗,一塊面積的大小與形狀的細微差別,能意會卻無法用明確的語言解釋清楚。藝術家、有悟性的手工藝人和普通技術人員完成的作品的主要差別,并不是技術上的差別,而是這種“藝術性”的差異。核心技藝是工藝締造者的創造,也可能積累了歷代傳承人的創造,是精華,不是簡單的技術,是技術的升華。
反對核心技藝難以傳授的最典型例子要算歐陽修《賣油翁》中的那句“無它,唯手熟爾”的名言,把高超的射箭技藝與穿過錢幣孔倒油這樣的“高難度”動作全部歸結為“熟練”而沒有其他原因。如果真如“賣油翁”所言“唯手熟爾”,似乎旁觀者練一練也就能掌握的話,箭術的高超就不能成為古代戰將令人羨慕的本領,從事抄紙、拉坯、燒窯的師傅也就沒必要受到他人特別的敬重。但事實正好相反,從事這些傳統工藝環節的師傅往往因為其掌握著他人難以掌握的技藝而有著特殊地位。本文這樣的表述無意否定在掌握技藝過程中“反復練習”的重要性,大書法家王獻之的書法技藝也是要以“十八缸水”的練習為基礎的,但如果不管是誰,只要練完十八缸水就能成為一代書法大家,書法技藝也就沒什么值得推崇的了。
(五)“核心技藝”與個體的領悟
把現有的知識體系分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是一種有利于我們了解那些隱藏在表面之后的道理、規律的分類方法。“核心技藝”因為通常難以直接言明,所以容易被當成“隱性知識”,從而區別于那些能直接傳授的“顯性知識”。但“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的分類方法,容易遮蔽“核心技藝”從師傅到徒弟的傳遞過程中徒弟自己“悟”的重要性。而徒弟“悟”的過程,更類似于波蘭尼(Michael Polanyi)所說的“默會”[注]秦文、王永紅:《波蘭尼的個人知識理論與教育思想探析》,《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0年第4期。。盡管波蘭尼因為要強調對“默會”這一現象的發現而把所有的知識都看作“默會知識”似乎有點夸大其詞,但任何知識的學習都與學習者個體的領悟能力具有強相關性是不能否認的。正是因為這樣,每個人掌握的知識才會或多或少存在這個人自身的特殊性,而不是與他人完全沒有差別,這恐怕才是波蘭尼斷言所有的知識都是個人知識的根本原因。對應于“顯性知識”的“隱性知識”并非波蘭尼所說的“默會知識”或“個人知識”,還因為即便是隱性的、難以言傳的知識,仍然可能被強調成客觀的,是師傅甚至是師爺、師祖一代代傳承下來的,這樣就缺少或者否定了師傅和徒弟在傳承中的主觀意識和作用。事實上,如果缺少師徒的主觀意識,核心技藝的傳承幾乎不能實現。
二、核心技藝傳承的難點
(一)師徒傳承中師傅的困境
不能否認核心技藝傳授過程中師傅的作用。在很多傳承人口述史中,有不少工藝傳承人都在擔憂后繼無人,特別是在非遺代表性傳承人進入保護目錄之后,作為代表性傳承人的師傅們在現有政策和資金的支持之下更愿意找尋真正的后繼者;或者家族傳承式的傳統工藝,長輩也希望后輩能將技藝真正傳承下去。但核心技藝本來難以傳授,不要說師傅不愿意傳授會導致徒弟難以學會,即使師傅愿意傳授,如果沒有恰當的教學方法,也會令相當多的徒弟望洋興嘆。傳統工藝的師徒傳承不同于一般技術的學習,師傅為了有效傳授核心技藝,必須根據徒弟的特點設計教學方法,因材施教。
學者孫發成把傳統工藝的傳承與控制論中的黑箱理論聯系起來,認為“師傅所掌握的核心技藝、個人經驗和訣竅,對于初學的徒弟來說毫無疑問是一個‘技藝黑箱’(甚至這個“黑箱”內的某些知識連師傅也沒有意識到),徒弟掌握師傅本領的過程就是一個“技藝黑箱”逐漸變“白”的過程。”[注]孫發成:《傳統工藝傳承中的“技藝黑箱”》,《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6月26日第6版。“技藝黑箱”的比擬一方面說明了核心技藝的不可言說之特性,另一方面也說明核心技藝傳承存在不易為師傅控制的因素。核心技藝的“黑箱”能夠變白,技藝就能順利傳承,但核心技藝的黑箱“變白”并不容易。多數情況下,徒弟不能掌握核心技藝的緣由都被歸咎于師傅不愿意教,似乎只要師傅愿意教,“黑箱變白”就不是問題。師傅卻說:“不存在不愿意教的問題,遇到問題了,一點撥‘就像窗戶紙,一點就破’。沒遇到問題,怎么說?說了也沒用。”[注]2017年8月2日本文作者訪談北京彩繪京劇臉譜傳承人時,傳承師傅所講。這里師傅所說的“問題”,應該是徒弟在學習和制作過程中遇到并提出來的問題,不是師傅人為設定的“提問”。學習同樣的傳統工藝,未必每一個徒弟都能遇到和提出同樣的問題。師傅的點撥,往往是在針對徒弟提出的具體問題時才格外有效。傳統工藝傳承過程中經常見到的是,師傅費盡心力想把“要領”傳授給徒弟,徒弟卻怎么也不能領會。
核心技藝之所以成為核心技藝,“難教、難學”是重要特性之一。或者說,對有些領悟力強的人來說,師傅一點就通,但另外一些學徒則可能掌握不了其中的訣竅,達不到技藝應有的高度。比如夾江造紙,其核心技藝是抄紙,有研究者對之進行了如下描述:
撈紙前,用竹竿將槽下的紙漿攪拌懸浮,使之達到適當的濃度,開始用紙簾撈紙。……抄撈紙張時,將紙簾放在簾床上,四處繃緊,雙手持簾床,斜著從后方向浸入槽內,平提出,由左向右平移,同時用右手抬起簾床,使漿水由右向左成二十度角流過紙簾,再由后向前斜向浸入槽內,令右上角方向進入漿液,再由右向左下角流出。如此左右傾斜浸漿,目的在于使紙在簾子里分布均勻。[注]謝亞平:《四川夾江造紙技藝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國藝術研究院2012年博士學位論文,第60頁。
這個核心技藝并不對觀眾保密,但不是看看文字或者只要能實際操作就可以掌握的。
抄撈成紙是造紙過程中最藝術最神奇的一環,也是最為關鍵的一道工序”,“過去,紙工拜師學藝,主要學的就是抄紙的技術,一般學習三年才能出師。[注]謝亞平:《四川夾江造紙技藝可持續發展研究》,第60頁。
之所以能向公眾公開,其實就因為它不容易掌握,對于很多人來說,不是師傅幾句話就能教會的。但對于領悟力強的人來說,則有可能通過觀摩和實踐就掌握這項技藝,當然,師傅不失時機的準確“點撥”更有利于他們快速掌握技藝要領。
筆者曾認真觀察了幾位工藝師傅如何向學生們傳授技藝,明顯能感覺到師傅“點撥”和徒弟“悟性”之間的微妙關系。很多時候不是師傅不愿意傳授核心技藝,而是師傅恰當的指導方法以及徒弟能否領悟其中的奧妙成為徒弟能否學成的關鍵。彩繪京劇臉譜傳承人佟師傅對學員的指導過程讓人明顯感覺到,決定臉譜繪制水平高下的核心技藝就藏在造型的細節之中。曲線如何才能顯出“勁道”,顏面如何才能顯得耐看,眼瓦如何表現才能傳神等等,具體到一根線的粗細,一塊顏色的面積大小,一根邊緣線的走向都會影響到最終效果,能否將這些細節做到“傳神”,就是彩繪京劇臉譜的核心技藝。師傅邊講述邊示范,不能說不盡心,更談不上有所保留。但從學員的作品中仍能看出來不同學員掌握的程度有顯著差異。京派內畫鼻煙壺傳承人楊師傅在教授學生內畫的過程中,除了傳授基本的繪畫技法,會用大量時間跟學員交流如何鑒賞內畫的心得體會,甚至討論如何鑒賞藝術品和如何做才算得上“藝術地生活”等問題。北京磚雕傳承人張師傅會因為幾個學員采用復印的方式而沒有按他的要求徒手繪制樣稿,氣得飯都吃不下。北京宮燈傳承人翟師傅對學員非常寬容,但學員制作的很多宮燈部件他都不聲不響地一件件親自“修形”給學員們看。
很多工藝師傅都曾跟我表露出比較一致的觀念:并不是每個跟他們學習過的人都能成為他們的徒弟。為什么?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能真正掌握這項技藝。在手工藝傳承過程中每個徒弟掌握得程度如何,離不開手上的練習,但更重要的依然是徒弟的領悟力。
“技藝黑箱”之喻的另外一層含義,就是即使師傅愿意傳承核心技藝,徒弟也不一定就準確掌握了解密“技藝黑箱”的方法。一個好的師傅要傳授核心技藝,不是簡單地告訴徒弟應該如何按部就班地完成每一道制作工藝技藝,而是根據徒弟自身特點,注重對徒弟悟性的培養,或者更直接一些,注重培養徒弟對核心工藝環節的感受。這些師傅可能會把把工序中涉及到核心技藝的部分變成一些基本訓練,然后通過這些基礎性的訓練讓徒弟的感受力得以提升。京派內畫鼻煙壺的楊師傅跟學員探討“如何才算藝術地生活”、如何鑒別古董書畫的贗品和真品;彩繪京劇臉譜佟師傅反復在多種材料上示范和講解眼瓦上一條曲線的畫法、造成的感受差異,磚雕張師傅不讓學員復印而堅持讓他們手繪磚雕樣稿,宮燈翟師傅親“修形”給學員看,都不是簡單向學生傳授技藝,而是圍繞核心技藝鍛煉學生的感受力;有些傳統木匠師傅會讓剛入門的徒弟反復磨制工具和鑿孔,看似沒做什么有用的物件,實際上也是希望徒弟能感悟到木工制作中的“分毫不差”的核心技藝藝術美特性。這種帶徒過程中經常用來鍛煉徒弟感受力的方法常被工藝師傅稱作“磨性子”,磨好了就是悟到了核心技藝中的藝術性,磨不成功,就很難掌握該核心技藝。也就是說,師傅即使掌握了如何傳授核心技藝的方法,仍然不能決定徒弟是否能真正理解和接受核心技藝。
(二)師徒傳承中徒弟的“悟性”
因為核心技藝的藝術性特點,使得徒弟能掌握核心技藝,不僅僅是師傅教的結果,更是徒弟自己悟的結果。據彩繪京劇臉譜傳承人佟老師回憶,她當年在工廠跟師傅學彩繪京劇臉譜技藝的時候,自己和師傅在廠里的本職工作都不是這個項目。師徒二人都是因為感興趣才做這件事,完全是業余時間學習和制作,佟老師根本沒想到將來會專門從事這項技藝,更沒想到自己會成為師傅的唯一傳人。但師傅臨終前不僅把自己祖傳的臉譜圖冊傳給了她,還特意留下了一個證明文書,證實佟老師是自己的真傳弟子[注]2017年8月2日本文作者訪談北京彩繪京劇臉譜傳承人時,傳承師傅所講。。老師傅為啥這么做?很可能就是發現佟老師在學習過程中已經掌握了繪制臉譜的核心技藝,能夠將該工藝傳承下去。相反,為什么有些徒弟跟著師傅多年,卻仍然得不到師傅的真傳?可能不是師傅刻意不教,而是徒弟領悟不到核心技藝,師傅也沒法認可這個得不到真傳的徒弟。
現實中能看到很多傳承人的學藝過程并不是師傅主動教的結果,而是自己主動學(甚至是偷學)的結果。相當多的手工藝人學習、從事多年的工藝制作,最終也沒有制作出什么精品,無法成為該技藝的真正傳人,而有些手工藝人,只是跟幾位師傅“非正式學習”了一段時間,卻能做出令業內認可的優秀作品,原因何在?純粹的技術問題不難解決,作品藝術性產生的力量超越技術產生的力量才能感動受眾,而作品的藝術性高低與作者的悟性高低緊密關聯。
手工藝如此,藝術如此,其他事項又何嘗不是呢?在《個人知識》這本著作中,波蘭尼分析了醫生通過解剖圖、器官結構圖來了解骨骼肌肉,以及類似于用地圖表現地球表面構成這樣的幫助人們理解聚合體的方式告訴我們,圖表和演示“只能給人們提供理解它的線索,但理解本身卻必須通過艱難的個人領悟行為才能獲得,而個人領悟行為的結果則必定是不可言述的。”[注][英]邁克爾·波蘭尼:《個人知識》,徐陶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3頁。強調個人領悟的重要性,并認為個人領悟的結果是“不可言述的”,就意味著工藝中最核心、最值得注意的技藝(在波蘭尼那里都算作知識的范疇),往往是一般人“學不來的”,如果人人都能夠學到,都能領悟,都會仿造,“核心”就不再神奇,也就無法成為“核心技藝”了。
反過來,我們不妨推斷,每位掌握核心技藝的師傅,以及每項工藝的締造者,也應該是非常有悟性的。該工藝的核心技藝可能是締造者的創造,也可能積累了歷代傳承師傅的創造,是精華,不僅僅包含可以直接傳授的技術,更包含技術的升華——藝術。而該工藝的締造者和傳承者,就是那個能將技術升華為藝術的人。
三、徒弟與核心技藝的傳承
(一)作為傳承者的關鍵素養
首先,要能夠抓住師傅語言、示范行為的核心。技藝的傳承過程,很多環節無法做到標準化傳授,核心技藝因為其難以言說的特性更不可能用標準化的語言和示范傳授給徒弟,所以師傅的傳藝過程其實是圍繞核心技藝“旁敲側擊”進行的,師傅的“旁敲側擊”是否能敲擊到關鍵點自然重要,徒弟能否抓住師傅語言、示范行為的核心,也就是核心技藝的本質,對于徒弟能否掌握核心技藝同樣關鍵。為了充分領會師傅語言、示范行為的核心,波蘭尼強調應該“毫無批判”地向師傅學習:
通過范例來學習就是服從權威。你服從師傅是因為你信任師傅的行為方式,盡管你無法詳細分析和解釋該行為的有效性。在師傅的示范下通過觀察和模仿,徒弟會在不知不覺中學會了那種技藝的規則,包括那些連師傅本人也不是很明白的規則。一個人要想吸收這些隱藏的規則,就只能完全信服地去模仿另一個人[注][英]邁克爾·波蘭尼:《個人知識》,第54頁。。
波蘭尼“毫無批判”地向師傅學習的觀點看似與近現代以來被尊崇的一般教育原則不符,所以招致不少批評。但本文認為,波蘭尼的此段表述意在強調徒弟在未能充分了解技藝的各種細節之前,必須對師傅充分信任。在信任的基礎上徒弟才有可能全身心地觀察和學習,才能“聽得進去”師傅的話,才能“看得清楚”師傅的示范,才有可能在不知不覺的狀態下學會那些難以言說的技藝。如果一開始沒有對師傅的信任,或者缺乏對技藝的“虔誠”態度,是難以學會核心技藝的。
其次,要能夠體會到比技巧更深一層的“藝術”。有關工藝傳承的地方性傳說中有不少徒弟沒有領會核心技藝的“藝術性”而導致不良效果的反例。在義烏、東陽、金華、湯溪、蘭溪等地的工藝傳說類型中,“徒弟施師傅的法術,而得到的卻是相反的效果”[注][德]艾伯華:《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王燕生、周祖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56頁。,這里所說的法術,其實可能是“神化”了的工藝手段。徒弟既然敢于用“師傅的法術”,說明徒弟也不是任意胡來,至少他認為自己所用的法術來自師傅。但又顯而易見,“師傅的法術”不那么簡單,其中有更深一層的訣竅、秘密。徒弟掌握了“師傅的法術”,卻沒有掌握其中的“秘密”和“訣竅”,也就是核心技藝的本質,問題出在何處?極有可能就在于這里的“秘密”和“訣竅”其實是比技巧本身更復雜,更需要“悟”的“藝術”,徒弟掌握了一般技巧,卻沒有領會其中的“藝術”,所以不得要領。徒弟如果要成為技藝的傳承者,必須體會到“師傅的法術”中的“藝術”成份,才有可能正確運用該項技藝,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徒弟自然無法傳承師傅的技藝。
最后,必須對師傅的技能技巧“有所發展”。“學我者生,似我者死”[注]《學我者生,似我者死》,《北京社會科學》1986年第4期。,“你將來靠什么超過我?[注]2018年9月13日,北京雕漆工藝美術大師已經出師的弟子馬寧在給學生講述雕漆文化和自己的從藝經歷時提及師傅曾經的教導話語。”這類話語可以說是師傅給徒弟最為中肯的忠告了。因為徒弟的學習如果只能達到對師傅的模仿而不能有所突破,極有可能只是“形似”而非“神似”。或者即使達到了某種程度的神似而不能有所發展,也完全可能會因為時代的發展而顯得“不合時宜”,最后被徒弟自己所處的時代淘汰,所以在技藝傳承過程中,將師傅的技藝加以發展以適應新時代是非常必要的。盡管有些師傅在教授技藝的過程中嚴格要求徒弟按部就班,但到了后期還是希望徒弟有所發展。沒有發展師傅技藝的徒弟,很難真正傳承技藝,也不符合師傅帶徒的初衷。“徒弟到了能自由想樣子的時候,就差不多學會(技藝)了。”[注]2017年8月5日本文作者對北京宮燈傳承人翟玉良師傅的訪談。——北京宮燈傳承人翟玉良師傅如是說。
(二)徒弟與師傅的關系格局
在師徒關系格局中,師傅占據優勢地位,有悟性的徒弟往往能對師傅的個人利益有所助益[注]韓翼、周潔、孫習習、楊百寅《師徒關系結構、作用機制及其效應》,《管理評論》2013年第7期。,但這樣的徒弟又未必愿意長期處于幫助師傅而不自立門戶的位置,從而與師傅的愿望相違背。利益問題而導致師徒關系不合的情形可能是師傅輩的人發出“教會徒弟餓死師傅”感嘆的起因。但是,如果發生徒弟的作品更受消費者歡迎這樣的情形不能簡單歸罪于徒弟,更不能歸因于是核心技藝傳授給了徒弟。如果徒弟僅僅是學會了師傅的技藝而沒有超越師傅,絕不至于會令師傅“沒有飯吃”。其實質通常是徒弟的能力已經超越了師傅,或者徒弟發展了技藝,更符合時代的需要。否則,客戶怎么會不愿意購買師傅的作品或服務?一位北京雕漆國家級工藝美術大師在他的徒弟出師時給徒弟提出問題:“我的作品總是在展廳的中央,你如何能讓自己的作品也擺到中央來?如果擺不到中央位置,你怎么能超過我?”[注]2018年9月13日,北京雕漆工藝美術大師已經出師的弟子馬寧在給學生講述雕漆文化和自己的從藝經歷時所說。能給自己的得意門生提出此類問題的師傅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不存私心的好師傅,他可以想方設法向徒弟傳授自己所掌握的核心技藝,但他無法直接教給徒弟如何超越自己的方法,因為很可能師傅也不知道徒弟如何做才能超越自己,這需要徒弟本人去創造、去悟。徒弟靠什么超越師傅?除了年輕,精力和體力條件優越一些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徒弟個人的悟性。有悟性的徒弟,很容易領會師傅的口傳心授,也有更多的可能性拓展核心技藝。我們不鼓勵徒弟搶師傅的飯碗,但如果徒弟總是不能超越師傅,工藝如何能傳承和發揚?
(三)資助和找尋悟性好的徒弟
既然徒弟的悟性對核心工藝傳承如此重要,創造條件吸引悟性好、有潛質的年輕人加入徒弟行列就不失為良好策略,但某個領域學徒的多寡和優劣通常與預期的回報有關,如果某項工藝到了只有真正喜愛的人才愿意學的地步,該技藝也離瀕危不遠了。現在的通常做法是,資助那些瀕危技藝項目大師們的傳承活動,鼓勵他們帶徒傳藝,但僅僅師傅愿意教,如果沒有徒弟死心塌地愿意學,傳承狀況仍然難以改善。或者即使有幾個徒弟愿意學,卻缺少悟性,師傅費勁心力也不能讓他們領會核心技藝,到頭來師傅恐怕也不太愿意承認這是自己的真傳徒弟。
怎么辦?資助徒弟(含學員、愛好者等)應該成為一種策略。即使暫時看不到該工藝技藝的美好未來,至少讓他們感覺到學這項技藝是被重視、有價值的。資助學員和一般愛好者,首先可以鼓勵更多的人加入到學習工藝技藝的行列,有了較多的學員之后,才更有可能發現悟性好的徒弟——真正能悟到核心技藝,成為技藝的下一代傳承人。現行各級政策措施中資助師傅的情況已經非常普遍,資助徒弟的情形仍然非常少,而在正規的學校教育體系中,比如在各類高校中設立獎、助學金制度已經非常成熟。非遺傳承人或者工藝師傅的培養過程中,資助徒弟,讓他們能靜心學習非常重要,尤其是讓那些有潛力、有悟性者被發現和得到資助,不失為有利于傳統工藝順利傳承的有效策略。
師傅不教怎么辦?本文當然不是要建議取消對師傅的資助而轉向資助徒弟,而是認為在傳承過程中,師傅的教和徒弟的學同樣重要,理應都得到相應資助而不應偏頗。而且,師傅愿不愿意傳藝,跟資助師傅或資助徒弟并非直接對應關系。或者說,現實中對某些師傅的不當資助可能反而讓師傅珍視自己的技藝而不愿傳授。資助徒弟并以徒弟對技藝的掌握程度作為資助效益的評價指標,促使師傅和徒弟都愿意積極投身于該技藝的傳承過程,會使鼓勵師傅傳承技藝有了目標對象并且容易落到實處。從師傅的角度而言,并沒有多少師傅甘愿祖師爺或者自己創立的獨特技藝消失在自己手中,德藝雙馨的傳統工藝大師都愿意自己的技藝發揚光大。對于很多工藝師傅來說,沒有傳人就如同沒有兒女,沒人愿意學才是師傅真正的無奈。沒人學,或者找不到理想的徒弟,師傅只能“不傳”,連可供選擇的其他途徑都沒有;有人愿意學,尤其是有悟性的徒弟愿意學,師傅往往被觸動,也更愿意教,技藝傳承就水到渠成。
四、結語
傳統工藝核心技藝的本質在于其難以言傳的藝術性,在傳統工藝技藝的傳承保護過程中,師傅傳授至關重要,是核心技藝的源頭,但也要特別關注到徒弟的悟性對核心技藝傳承的重要影響,傳統上我們對師傅的作用關注較多而往往將徒弟置于被動位置。將著眼點從師傅轉向徒弟,將資助對象從僅僅關注師傅轉向師傅和徒弟并重,明確徒弟在傳承過程中的重要性,能讓我們意識到未來人才培養的根本問題不僅僅在于作為師傅輩的長者的傳授過程,而在于作為徒弟輩的未來一代是否有很強的領悟力。那么,在面向未來的教育體系中,注重孩子們領悟力的培養理應得到重視
傳統工藝傳承的關鍵問題之一是未來人才的培養問題。培養下一代的領悟力,成為傳統工藝傳承的關鍵。師傅不應只關注技術本身的傳授,還要用各種方式提升徒弟的藝術感受力。沒有感受力好、領悟力強的未來人才,核心技藝難以傳承。有了領悟力強的徒弟,師傅的核心技藝不僅容易被傳承,也可能被創造和得到新的發展。并且,本文雖然主要圍繞傳統工藝和非遺技藝展開討論,但現代科技的核心技術,也不是標準化的、很容易被傳授的技術,而是同樣存在不可言述的藝術因素,要掌握這類核心技術,也需要領悟力強的未來一代傳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