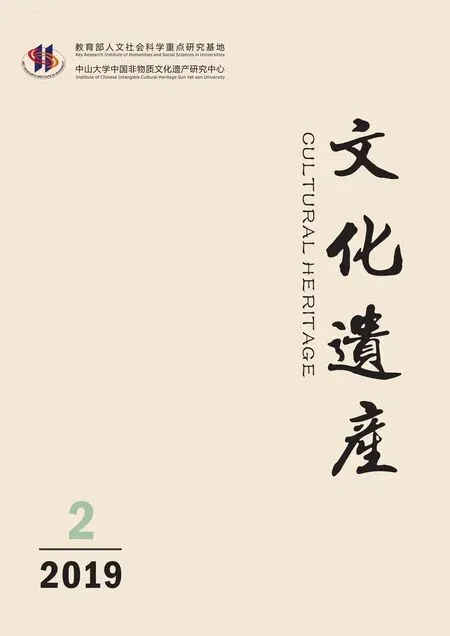“經(jīng)驗(yàn)中心研究法”的理論與方法意義
——基于對(duì)哈弗德超自然信仰研究的探討
孫艷艷
在西方宗教學(xué)領(lǐng)域,曾有從“宗教”向“宗教性”回歸的趨向,并引發(fā)學(xué)者對(duì)宗教經(jīng)驗(yàn)的關(guān)注。[注]如[德]西美爾:《現(xiàn)代人與宗教》,曹衛(wèi)東等譯,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美]威廉·詹姆斯:《宗教經(jīng)驗(yàn)之種種》,尚新建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年;[加]威爾弗雷德·坎特韋爾·史密斯:《宗教的意義與終結(jié)》,董江陽(yáng)譯,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但由于信眾宗教經(jīng)驗(yàn)的神秘性、主觀性與科學(xué)研究所追求的客觀性之間的距離,關(guān)于宗教經(jīng)驗(yàn)的探討一直是一個(gè)比較棘手和敏感的話題。美國(guó)宗教心理學(xué)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宗教經(jīng)驗(yàn)之種種》(1902)是較早將各種宗教經(jīng)驗(yàn)本身作為研究對(duì)象的著作。而早期的宗教現(xiàn)象學(xué)家如奧托(Rudolf Otto)和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則分別致力于探究宗教經(jīng)驗(yàn)的神秘力量、特殊情感與宗教經(jīng)驗(yàn)的原始內(nèi)涵。其中詹姆斯和奧托以基督教的神秘經(jīng)驗(yàn)為主要對(duì)象,伊利亞德則跳出了西方主流的基督教研究,對(duì)原始信仰材料以及東方的神秘信仰如瑜伽和薩滿教興趣濃厚,由此啟發(fā)人們關(guān)注那些不為制度性宗教和知識(shí)界所看重的宗教經(jīng)驗(yàn)。[注][美]米爾恰·伊利亞德 :《薩滿教——古老的入迷術(shù)》,段滿福譯,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8年。而美國(guó)民俗學(xué)者大衛(wèi)·哈弗德(David J. Hufford)關(guān)于超自然信仰的研究也是主要關(guān)注制度性宗教之外的超自然信仰,并通過對(duì)信仰者的經(jīng)驗(yàn)本身的重點(diǎn)關(guān)注,提出了“經(jīng)驗(yàn)中心研究法”。這一研究方法的提出首先是在美國(guó)民間信仰研究傳統(tǒng)的脈絡(luò)下進(jìn)行的,同時(shí)也與宗教學(xué)領(lǐng)域的宗教經(jīng)驗(yàn)研究形成一種呼應(yīng)。
目前,中國(guó)也有越來越多的學(xué)者關(guān)注民眾的宗教性,即關(guān)注民眾宗教實(shí)踐中的身體經(jīng)驗(yàn)與細(xì)微感受,如楊德睿、陳進(jìn)國(guó)等學(xué)者提出修行人類學(xué)的倡議,其中楊德睿從人類學(xué)的宗教認(rèn)知/傳承的角度關(guān)注信眾的感性經(jīng)驗(yàn),并以此回應(yīng)格爾茨“聚焦于精神氣質(zhì)之陶治機(jī)制與生效過程”的呼吁。[注]楊德睿:《影像的神力:高淳的廟會(huì)與禳解法》,《文化遺產(chǎn)》2018 年第6期。專注于靈媒研究的張超也將關(guān)注點(diǎn)從靈媒的民俗治療轉(zhuǎn)向了靈媒的感覺經(jīng)驗(yàn)世界。[注]張超:《制造日常生活恐慌:女性靈媒的危險(xiǎn)感知、民俗醫(yī)療與賦權(quán)文化體系》,《社會(huì)學(xué)評(píng)論》2018年第3期。以日常生活經(jīng)驗(yàn)和地方性知識(shí)為關(guān)注點(diǎn)的民俗學(xué)者們也開始關(guān)注民眾的身體經(jīng)驗(yàn)與感受,如劉鐵梁較早提出“感受民俗學(xué)、勞作模式等具有身體維度的概念”[注]彭牧:《身體與民俗》,《民間文化論壇》2018年第5期。;彭牧則引入西方的身體民俗學(xué)理論,關(guān)注民眾的“體知”經(jīng)驗(yàn),闡釋身體感受與民俗的天然而深刻的關(guān)聯(lián)。[注]彭牧:《民俗與身體——美國(guó)民俗學(xué)的身體研究》,《民俗研究》2010年第3期。在此背景下,筆者重點(diǎn)梳理哈弗德的“經(jīng)驗(yàn)中心研究法”的理論內(nèi)涵,進(jìn)而發(fā)掘其對(duì)民俗學(xué)民間信仰研究的啟發(fā)意義。
一、民間信仰研究范式的轉(zhuǎn)變
基督教作為西方社會(huì)主流的制度性宗教之一,以其神圣權(quán)威和理性權(quán)威對(duì)世俗社會(huì)形成了較為強(qiáng)大的控制力,并對(duì)其它信仰形式具有話語(yǔ)霸權(quán),民間信仰就在此語(yǔ)境下被看作迷信或異端而飽受貶斥。自十八世紀(jì)啟蒙運(yùn)動(dòng)以來,在理性至上思潮的影響下,民間信仰與制度性宗教都遭受嚴(yán)厲打擊,其中前者更甚。由此,在宗教理性與科學(xué)理性的雙重?cái)D壓下,民間信仰不可避免地被認(rèn)為是錯(cuò)誤的與非理性的。
基于文化進(jìn)化論理論,人類學(xué)最初對(duì)民間信仰的關(guān)注,多將其視為“遺留物”。而宗教學(xué)作為一門學(xué)科,“更感興趣的是宗教制度化的歷史進(jìn)程和語(yǔ)言產(chǎn)品,對(duì)人們實(shí)際上如何過宗教生活的方式缺乏真正的興趣”。[注]Leonard Norman Primiano,“Vernacular Religion and the Search for Method in Religious Folklife”,Western FolkloreVol. 54, No. 1.1995,p.41.美國(guó)民俗學(xué)對(duì)民間信仰的研究雖深受人類學(xué)、宗教學(xué)的影響,但也形成了自己的歷史發(fā)展脈絡(luò),即“從記錄整理零碎片段的迷信觀念,到把握民間信仰的文化整體,再到關(guān)注民眾日常生活中的活態(tài)宗教實(shí)踐”。[注]彭牧:《從信仰到信:美國(guó)民俗學(xué)的民間宗教研究》,《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
需要指出的是,在民俗學(xué)對(duì)民間信仰的研究中,制度性宗教或官方宗教總是如影隨形,成為民間信仰研究的參照點(diǎn),形成一種二元對(duì)立的兩層級(jí)模式,而且民間信仰總是被認(rèn)為低于并模仿官方的制度性宗教。而在以基督教為代表的制度性宗教研究中所形成的信仰與實(shí)踐二元對(duì)立模式[注]在這一二元對(duì)立模式中,“其中信仰是根基和推動(dòng)力,具優(yōu)先性,而儀式實(shí)踐只是信仰的表達(dá)與體現(xiàn)” 。參見彭牧:《從信仰到信:美國(guó)民俗學(xué)的民間宗教研究》。,也深刻地影響著以實(shí)踐為主要特征的民間信仰研究。為了突破這雙重的二元對(duì)立的束縛,二十世紀(jì)八九十年代,哈弗德適時(shí)地提出“經(jīng)驗(yàn)中心研究法”,注重對(duì)個(gè)人信仰經(jīng)驗(yàn)進(jìn)行研究。他認(rèn)為信仰經(jīng)驗(yàn)本身即是形成與保持信仰的動(dòng)態(tài)過程;并強(qiáng)調(diào)人們的信仰經(jīng)驗(yàn)本身融合了信仰觀念與儀式行為,可以直接作為民間信仰研究的對(duì)象來看待。[注]Hufford,D.J.The Terror That Comes in the Night:An Experience-Centered Study of Supernatural Assault Traditio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2.;"Folk Healers",in Richard M. Dorson(ed.), Handbook of American Folklor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3):306-313.;"Folklore and Medicine",in Michael Owen Jones(ed.), Putting Folklore to Use , 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4):117-135.;"Beings without Bodies: An Experience-Centered Theory of the Belief in Spirits",in Barbara Walker(ed.), Out of the Ordinary: Folklore and the Supernatural, 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a):11-45.;"The Experience-Centered Analysis of Belief Stories: A Haunting Example in Honor of Kenny Goldstein",in Roger D. Abrahams and Michael Robert Evans et al.(eds.), Fields of Folklore: Essays in Honor of Kenneth S. Goldstein, Bloomington,IN: Trickster. (1995b):55-89.而另一位民俗學(xué)者倫納德·普里米亞諾(Leonard Norman Primiano)則提出“通俗宗教”(vernacular religion)的概念,并由此引發(fā)人們對(duì)活態(tài)宗教實(shí)踐的關(guān)注。[注]Leonard Norman Primiano,1995.由此,至少在個(gè)人信仰經(jīng)驗(yàn)與活生生的宗教實(shí)踐的層面上,二人的研究開始打破民間信仰與制度性宗教以及信仰觀念與儀式實(shí)踐之間的二元對(duì)立,直至最終共同完成了民間信仰研究范式的根本性轉(zhuǎn)變。其中哈弗德提出的“經(jīng)驗(yàn)中心研究法”成為民間信仰經(jīng)驗(yàn)與實(shí)踐研究的一種重要的理論和方法。
二、哈弗德的“經(jīng)驗(yàn)中心研究法”
“經(jīng)驗(yàn)中心研究法”是哈弗德對(duì)一項(xiàng)超自然信仰個(gè)案長(zhǎng)達(dá)十年研究的結(jié)晶。在其代表作《夜幕下的恐怖:對(duì)超自然攻擊傳統(tǒng)的一個(gè)經(jīng)驗(yàn)中心的研究》(1982)中,哈弗德經(jīng)過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在加拿大紐芬蘭,很多人都有過被“老巫婆”(The old hag)[注]中國(guó)也有此類經(jīng)驗(yàn),俗稱為鬼壓床或鬼壓身。下文提到“The old hag”這一超自然攻擊傳統(tǒng)時(shí)將統(tǒng)稱其為“鬼壓床”。攻擊的親身經(jīng)歷。他們通常是感覺有人或東西出現(xiàn)在房間里,或覺得有人(通常認(rèn)為是女巫)壓在他們的胸口上,偶爾也會(huì)有一種不同尋常的對(duì)死亡的恐懼感。在這些恐怖情形中,受害者常常試圖喊叫卻喊不出來,試圖站起來卻發(fā)現(xiàn)自己無法動(dòng)彈。哈弗德在田野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不僅紐芬蘭人有此類經(jīng)驗(yàn),世界不同地區(qū)甚至不同時(shí)代的很多人都有過此類經(jīng)驗(yàn)。但以往很少有學(xué)者關(guān)注這類經(jīng)驗(yàn),它們被想當(dāng)然地認(rèn)為是當(dāng)?shù)匚幕姆从郴虺尸F(xiàn),即有過被超自然攻擊經(jīng)驗(yàn)的人只是在經(jīng)歷他的文化教他如何去經(jīng)驗(yàn)而已。[注]Donald Ward,The Terror That Comes in the Night:An Experience-Centered Study of Supernatural Assault Traditions by David J. Hufford",in Western Folklore, Vol. 43, No. 4. 1984,pp.274-276.
哈弗德對(duì)這類經(jīng)驗(yàn)給予了極大關(guān)注,并提出以經(jīng)驗(yàn)為中心作為田野作業(yè)的調(diào)查方法,即在對(duì)原材料進(jìn)行理論闡釋與建構(gòu)之前,對(duì)曾遭受超自然攻擊的受害者所表述的經(jīng)驗(yàn)本身進(jìn)行現(xiàn)象學(xué)的描述與分析。換言之,在取得受訪者信任和理解的前提下,作者對(duì)受訪者所經(jīng)歷的鬼壓床經(jīng)歷不斷地進(jìn)行追問,激發(fā)受訪者進(jìn)一步描述和還原當(dāng)時(shí)的情景與感受,由此展示出充分而又豐富的關(guān)于經(jīng)驗(yàn)的細(xì)節(jié)材料。在此基礎(chǔ)上,作者總結(jié)出這一類經(jīng)驗(yàn)所體現(xiàn)出來的主要特征和次要特征,以及這些特征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如當(dāng)時(shí)的睡姿是仰臥的,確認(rèn)自己處于清醒的狀態(tài)(并非做夢(mèng)),能睜開眼睛,聽到了腳步聲,有壓迫感、恐懼感但卻無法動(dòng)彈等等。作者以?shī)A敘夾議的寫作風(fēng)格,將這些原材料以及一些深入的訪談過程與作者的分析一起直接呈現(xiàn)在文本中。在《夜幕下的恐怖》一書中,作者以上述方式呈現(xiàn)了36個(gè)研究個(gè)案,對(duì)人們所宣稱的能夠支撐其超自然信仰的親身經(jīng)驗(yàn)做了充分的直觀呈現(xiàn),以此接近人們表述模式背后的真實(shí)感覺。[注]Hufford,D.J.1982,p.xix.以至于有評(píng)論者說,僅僅這些經(jīng)驗(yàn)描述本身已足以體現(xiàn)本書的主要價(jià)值。[注]Donald Ward,1984,pp.274-276.
盡管對(duì)經(jīng)驗(yàn)材料進(jìn)行了盡可能詳盡的描述和分析,但作者非常謹(jǐn)慎于對(duì)這些經(jīng)驗(yàn)材料進(jìn)行理論闡釋與建構(gòu)。因?yàn)槔碚撋系慕忉寫?yīng)該只建立在對(duì)所要解釋的東西進(jìn)行深入描述的基礎(chǔ)上,而且某人可能會(huì)對(duì)所要解釋的東西無意中進(jìn)行許多創(chuàng)造。[注]Hufford,D.J.1982,p.134.作者在訪談中也注意到,當(dāng)人們描述個(gè)人與超自然的遭遇時(shí),注意力會(huì)迅速集中在經(jīng)驗(yàn)本身,而不是對(duì)經(jīng)驗(yàn)的解釋。[注]Hufford,D.J.1982,p.13.
事實(shí)上,人們從來沒有明確地將他們相信的東西陳述為命題(Propositions)。大部分民間信仰的自然載體是故事,它通過講述發(fā)生了什么事來顯示什么是真實(shí)的。由于這一過程融合了信念和人們的一些推理和暗示,因此,要描述和理解這一隱性的和嵌入性的信念,研究者必須推斷出它們,并將它們陳述為命題。即信仰觀念本身是研究者們推論、構(gòu)建出來的。[注]彭牧:《從信仰到信:美國(guó)民俗學(xué)的民間宗教研究》。因此,哈弗德認(rèn)為,研究者必須確保所述的命題或主張得到那些信仰持有者的同意。在認(rèn)知的意義上,將某種人們不同意或不理解的信念強(qiáng)加給他們是錯(cuò)誤的。[注]Hufford,D.J.1995a,p.20.這也即是哈弗德所提倡的“本土接受原則”。[注]Hufford,D.J.1995b,p.58.而人們講述的故事,即個(gè)人經(jīng)驗(yàn)敘事“所體現(xiàn)的,正是人們保持信仰的狀態(tài)和過程,也即信的過程本身”。這一過程也是“人們?cè)庥鲂叛觥岩?接受信仰與堅(jiān)持/放棄信仰這一持續(xù)不斷的動(dòng)態(tài)過程”。[注]彭牧:《從信仰到信:美國(guó)民俗學(xué)的民間宗教研究》。因此,研究者在推論、構(gòu)建信仰觀念之前,首先應(yīng)該認(rèn)真看待人們的經(jīng)驗(yàn)敘事,并在對(duì)個(gè)人經(jīng)驗(yàn)敘事的分析中呈現(xiàn)“信”的過程。
正是在對(duì)人們的超自然信仰經(jīng)驗(yàn)的動(dòng)態(tài)過程進(jìn)行徹底全面細(xì)致描繪的基礎(chǔ)上,哈弗德注意到人們對(duì)超自然信仰的精確觀察與正確推理。他由此認(rèn)為,多數(shù)民間信仰的精神是理性的,它們是從經(jīng)驗(yàn)中理性地發(fā)展而來的。即這些信仰是基于觀察而進(jìn)行的正確推理。[注]Hufford,D.J.1995a,p.11.例如關(guān)于鬼壓床經(jīng)驗(yàn)的描述表明,一大批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顯然認(rèn)為自己在做夢(mèng),然后花費(fèi)相當(dāng)大的努力去確認(rèn)夢(mèng)的假設(shè)是否站得住腳。以羅恩(Ron)為例,在經(jīng)歷過超自然攻擊之后,羅恩問他的室友和他的兄弟們是否在他打瞌睡的時(shí)候進(jìn)到房間里來。這些攻擊的受害者通常都會(huì)采取這樣的行動(dòng),試圖為他們經(jīng)驗(yàn)的某一部分找到一個(gè)合理的自然解釋。這種關(guān)注也表明這種經(jīng)驗(yàn)的強(qiáng)烈而又清醒的主觀印象是與普通的夢(mèng)有所區(qū)別的。[注]Hufford,D.J.1982,p.66.
哈弗德之所以強(qiáng)調(diào)“超自然信仰與準(zhǔn)確地觀察和正確地推理有關(guān)”這一論點(diǎn),是因?yàn)樽詥⒚蛇\(yùn)動(dòng)以來,大部分關(guān)于超自然信仰的調(diào)查通常都被“這些信仰是錯(cuò)誤的”的觀念所控制,學(xué)者們很輕易地就宣稱這些超自然信仰的信眾缺乏將正確的命題與錯(cuò)誤的命題區(qū)分開來的理解能力,或缺少理解邏輯規(guī)則的能力等等。哈弗德表示,他所提倡的經(jīng)驗(yàn)中心研究法并不試圖證明這些解釋是不正確的,只是想說明這些解釋在什么情況下才是正確的,同時(shí)也說明糟糕的觀察和錯(cuò)誤的推理并不能解釋所有的超自然信仰。[注]Hufford,D.J.1982,p.xviii.但需注意的是,哈弗德通過對(duì)鬼壓床經(jīng)驗(yàn)的案例分析推出的這一論點(diǎn),并不暗示所有的民間信仰都有這種關(guān)聯(lián),且這種關(guān)聯(lián)也不能作為某種民間信仰真實(shí)性的依據(jù)。[注]Hufford,D.J.1982,p.xviii.
雖然哈弗德的主要著眼點(diǎn)在經(jīng)驗(yàn)本身,注重個(gè)人經(jīng)驗(yàn)敘事的分析,并將“信仰實(shí)踐的過程放在了與信仰觀念完全同等的理論位置之上”,[注]彭牧:《從信仰到信:美國(guó)民俗學(xué)的民間宗教研究》。但他還是小心地嘗試著從經(jīng)驗(yàn)敘事中提煉出某種信仰觀念。在對(duì)經(jīng)驗(yàn)的描述中,哈弗德認(rèn)為不是信仰產(chǎn)生了經(jīng)驗(yàn),而是經(jīng)驗(yàn)構(gòu)成了信仰,“長(zhǎng)期以來,人們一直認(rèn)為民間信仰在自我實(shí)現(xiàn)的過程中創(chuàng)造了經(jīng)驗(yàn)(和經(jīng)驗(yàn)的虛幻的外觀),……但恰恰相反的是,一種傳統(tǒng)的信仰實(shí)際上似乎是產(chǎn)生于一種特殊的經(jīng)驗(yàn),并且這一經(jīng)驗(yàn)的細(xì)節(jié)是獨(dú)立于先前的信念或知識(shí)”。[注]Hufford,D.J.1995a,pp.13-14.在此基礎(chǔ)上,哈弗德提出了“核心經(jīng)驗(yàn)”的概念,認(rèn)為正是這類“核心經(jīng)驗(yàn)”產(chǎn)生了那些“核心信仰”。[注]Hufford,D.J.1995a,p.29.
哈弗德對(duì)“核心經(jīng)驗(yàn)”這一概念設(shè)定了嚴(yán)格的標(biāo)準(zhǔn),首先這種經(jīng)驗(yàn)是對(duì)精神的直觀;其次這種經(jīng)驗(yàn)獨(dú)立于當(dāng)事人之前的信仰、知識(shí)和目的;再次,這種經(jīng)驗(yàn)本身有一種穩(wěn)定的感覺模式。[注]Hufford,D.J.1995a,p.34.比如,“瀕死體驗(yàn)”是一種核心經(jīng)驗(yàn),而“相信人死靈魂仍在”則是一種與之相關(guān)的核心信仰;再如,讓人動(dòng)彈不得的馬納襲擊或曰鬼壓床經(jīng)驗(yàn)是一種核心經(jīng)驗(yàn),而“與某些神靈遭遇具有威脅性”的觀念則是一種與之相關(guān)的核心信仰。[注]Hufford,D.J.1995a,p.29.
核心經(jīng)驗(yàn)具有獨(dú)立于某一文化傳統(tǒng)的屬性,它如同一個(gè)元素可以自由地或顯或隱地與其它文化元素相結(jié)合,從而構(gòu)成世界各地形態(tài)各異的信仰觀念和民間信仰傳統(tǒng)。哈弗德在《沒有身體的存在:關(guān)于神靈信仰的經(jīng)驗(yàn)中心理論》一文中,以圖表的形式形象地展示了某種“核心經(jīng)驗(yàn)”經(jīng)由一系列“文化過程”從而構(gòu)成不同形態(tài)的文化闡釋或世界觀。[注]Hufford,D.J.1995a,p.32.這里的“核心經(jīng)驗(yàn)”以獨(dú)立的形態(tài)或顯或隱地呈現(xiàn)在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中,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哈弗德對(duì)經(jīng)驗(yàn)進(jìn)行結(jié)構(gòu)分析的一種嘗試,其中也包含著經(jīng)驗(yàn)與文化傳統(tǒng)的辯證關(guān)系。
三、個(gè)人經(jīng)驗(yàn)與文化傳統(tǒng)的辯證關(guān)系
在《夜幕下的恐怖》一書中,哈弗德注意到,那些對(duì)鬼壓床這種傳統(tǒng)完全無知的人與熟悉這種傳統(tǒng)的紐芬蘭人,遭受超自然攻擊的經(jīng)驗(yàn)的方式是相同的,并表現(xiàn)出一些共同的經(jīng)驗(yàn)特征。如美國(guó)文化中就沒有這樣的傳統(tǒng),他們的文化無法解釋這種經(jīng)驗(yàn),甚至沒有語(yǔ)言可以描述它,只能用一種類比的方式勉強(qiáng)描述自己的經(jīng)驗(yàn),但他們卻與有著鬼壓床傳統(tǒng)的加拿大紐芬蘭人擁有非常相似的經(jīng)驗(yàn)。哈弗德禁不住疑問,為什么處于不同文化傳統(tǒng)語(yǔ)境中的人,所體驗(yàn)的內(nèi)容和方式如此一致?
對(duì)此,彭牧曾敏銳地指出:“盡管哈弗德在書中強(qiáng)調(diào)他的經(jīng)驗(yàn)中心研究法主要是理論闡釋之前的調(diào)查方法,但從全書整體來看,經(jīng)驗(yàn)已成為他考察民間信仰的關(guān)鍵所在。因?yàn)槿珪闹饕獑栴}是探討鬼壓床的身體經(jīng)驗(yàn)是否和文化相關(guān)。”[注]彭牧:《從信仰到信:美國(guó)民俗學(xué)的民間宗教研究》。哈弗德對(duì)這一問題的回答是,“與鬼壓床相關(guān)的這一現(xiàn)象構(gòu)成一種具有復(fù)雜性和穩(wěn)定模式的經(jīng)驗(yàn),這一經(jīng)驗(yàn)?zāi)軌虮蛔R(shí)別并區(qū)別于其他經(jīng)驗(yàn)。……這一經(jīng)驗(yàn)?zāi)J郊捌浞植硷@然獨(dú)立于清晰的文化模式的存在而存在。在有關(guān)超自然攻擊的各種傳統(tǒng)的發(fā)展中,這種經(jīng)驗(yàn)本身起了重要的、雖然不是唯一的作用。而該經(jīng)驗(yàn)被描述(持有)和解釋的方式則深受文化因素的影響。”[注]Hufford,D.J.1982,p.245.即經(jīng)驗(yàn)本身可以獨(dú)立于文化而存在,而關(guān)于經(jīng)驗(yàn)的描述與解釋方式則與文化有關(guān)。
這一反主流、反傳統(tǒng)的論斷引起了關(guān)于“文化來源假設(shè)”(Cultural source hypothesis)與“經(jīng)驗(yàn)來源假設(shè)”(Experiential source hypothesis)的爭(zhēng)議。哈弗德將關(guān)于鬼壓床傳統(tǒng)的解釋分為六種類型,每一種類型都涉及文化在經(jīng)驗(yàn)的形成以及經(jīng)驗(yàn)的描述過程中的作用,也即涉及一個(gè)共同的問題——個(gè)人經(jīng)驗(yàn)與對(duì)超自然事件的解釋的關(guān)系。在這些解釋中,經(jīng)驗(yàn)要么是傳統(tǒng)的虛構(gòu)的產(chǎn)品,要么是受傳統(tǒng)影響的想象的主觀經(jīng)驗(yàn)(甚至這種影響是偶然的)。哈弗德稱這種觀點(diǎn)為“文化來源假設(shè)”,它在不同的傳統(tǒng)中會(huì)有不同的含義。例如,夢(mèng)以及因吸毒或患精神病所引起的幻覺都可能受傳統(tǒng)的影響,反過來它們也可能會(huì)有助于這一傳統(tǒng)的持續(xù)和發(fā)展。這種假設(shè)將導(dǎo)致一種預(yù)測(cè),即關(guān)于鬼壓床的第一手和二手的經(jīng)驗(yàn)描述應(yīng)該出現(xiàn)在一定的傳統(tǒng)中。[注]Hufford,D.J.1982,pp.13-14.但這一假設(shè)和預(yù)測(cè)在下面的事實(shí)面前是站不住腳的,即有很多經(jīng)歷過鬼壓床經(jīng)驗(yàn)的人,卻從未聽過鬼壓床或任何其他人曾有過類似的經(jīng)驗(yàn),并對(duì)超自然信仰沒有基本的信仰或興趣;他們也不是紐芬蘭人,沒有受到該地超自然傳統(tǒng)的強(qiáng)烈影響;而且從地理環(huán)境、教育背景和職業(yè)等因素來看,他們也不可能是這一傳統(tǒng)信仰的持有者或承擔(dān)者。[注]Hufford,D.J.1982,p.40.
而共享鬼壓床傳統(tǒng)的知識(shí)和功能的人較容易互相討論這一經(jīng)驗(yàn),如在紐芬蘭,深受鬼壓床這一堅(jiān)定有力傳統(tǒng)影響的人可以直接談?wù)撨@樣的經(jīng)驗(yàn),就如同這一傳統(tǒng)已經(jīng)為這些極為具體的關(guān)于它們意義的陳述做好了準(zhǔn)備。[注]Hufford,D.J.1982,p.107.那些不知道鬼壓床傳統(tǒng)或從未聽說別人有這種經(jīng)驗(yàn)的人,通常會(huì)出現(xiàn)勉強(qiáng)或拒絕談?wù)撨@種經(jīng)驗(yàn)的現(xiàn)象。首先由于其文化中缺乏鬼壓床傳統(tǒng),他們?cè)诒硎鲞@一超自然襲擊經(jīng)驗(yàn)時(shí)會(huì)面臨一種表達(dá)的困難,通常會(huì)運(yùn)用類比的方式,比如,說這種經(jīng)驗(yàn)與夢(mèng)相似;其次他們對(duì)于公開這一經(jīng)驗(yàn)有一種不安和壓力,怕被別人嘲笑為荒誕不經(jīng)或認(rèn)為自己精神有問題。對(duì)聽者反應(yīng)的顧慮正好說明了運(yùn)用類比的方式來表述這一經(jīng)驗(yàn)的優(yōu)勢(shì),即它能夠使講述者掌控公開這一經(jīng)驗(yàn)的程度,如果聽者認(rèn)為荒誕不經(jīng),講述者就可以將之當(dāng)作不切實(shí)際的夢(mèng)境來談,畢竟這種經(jīng)驗(yàn)的確與睡眠有一定關(guān)系;如果聽者回應(yīng)自己也曾有相似的經(jīng)驗(yàn)或其他強(qiáng)烈支持性的反饋,講述者就能公開更多關(guān)于這一經(jīng)驗(yàn)的私人性的細(xì)節(jié)。[注]Hufford,D.J.1982,pp.52-53.
既然不同文化中的人均有相似的鬼壓床經(jīng)驗(yàn),哈弗德進(jìn)而提出,有些信仰的產(chǎn)生是來自某種特殊的經(jīng)驗(yàn),而且這種經(jīng)驗(yàn)細(xì)節(jié)并不依賴于先前的信仰和知識(shí)。[注]Hufford,D.J.1995a,p.28.哈弗德還強(qiáng)調(diào)這種經(jīng)驗(yàn)本身與人的種族、宗教背景或其他因素?zé)o關(guān)。通過對(duì)鬼壓床這一超自然攻擊經(jīng)驗(yàn)的研究,并在質(zhì)疑“文化來源假設(shè)”的基礎(chǔ)上,哈弗德提出“經(jīng)驗(yàn)來源假設(shè)”,即有些信仰來自于經(jīng)驗(yàn),而不是相反。為了確認(rèn)“經(jīng)驗(yàn)來源假設(shè)”的驚人發(fā)現(xiàn),哈弗德在北美大陸——這里關(guān)于鬼壓床傳統(tǒng)知識(shí)實(shí)際上是不存在的,其他類似的超自然攻擊傳統(tǒng)也沒有紐芬蘭的鬼壓床傳統(tǒng)普遍——尋找到大量的關(guān)于超自然襲擊經(jīng)驗(yàn)的第一手陳述資料,并繼續(xù)對(duì)之描述和分析。[注]Hufford,D.J.1982,p.46.由此得出“這一經(jīng)驗(yàn)?zāi)J郊捌浞植硷@然是獨(dú)立于清晰的文化模式的存在而存在的”的結(jié)論。雖然“經(jīng)驗(yàn)來源假設(shè)”并不排除某種文化模式可能會(huì)影響經(jīng)驗(yàn)的可能性,包括持有這一經(jīng)驗(yàn)或經(jīng)驗(yàn)內(nèi)容的某些方面的可能性,但它將任何這樣的(文化的)影響降低到了次要的位置。[注]Hufford,D.J.1982,p.46.
由此可見,文化來源假設(shè)需要被重新檢視。文化傳統(tǒng)對(duì)經(jīng)驗(yàn)的很多解釋可能是不正確的,或經(jīng)不住新的實(shí)際經(jīng)驗(yàn)的檢驗(yàn)。所以,對(duì)經(jīng)驗(yàn)的發(fā)現(xiàn)和強(qiáng)調(diào),某種程度上是對(duì)傳統(tǒng)觀念的一種矯正,讓我們重新審視被我們理所當(dāng)然地接受的文化傳統(tǒng):這些文化并非靜態(tài)的不可更改的權(quán)威,而是動(dòng)態(tài)的,被新鮮的流動(dòng)著的經(jīng)驗(yàn)所不斷地更新著、建構(gòu)著的。
關(guān)于信仰、文化和經(jīng)驗(yàn)之間的關(guān)系,哈弗德承認(rèn)大部分信仰來自文化,但并不是所有的信仰都來自文化,有一些信仰確實(shí)來自某種特殊經(jīng)驗(yàn)。哈弗德以伽利略和哥白尼發(fā)現(xiàn)“日心說”為例,認(rèn)為我們普通人對(duì)于地球圍繞太陽(yáng)轉(zhuǎn)動(dòng)這一知識(shí)的信仰是父母或老師告訴我們的,它主要依賴于文化的傳遞,但伽利略和哥白尼的觀察卻與他們從文化中所學(xué)的“地心說”知識(shí)是相沖突的。當(dāng)然,如果沒有已有文化知識(shí)(包括語(yǔ)言),以及他們的生物身體(如眼睛、大腦等)的幫助,他們也不可能有“日心說”的新發(fā)現(xiàn)。但是他們這一新的知識(shí)信仰既不是來自文化傳遞,也不是根源于他們的生理身體,而是主要來自于他們特殊的經(jīng)驗(yàn)和對(duì)周圍環(huán)境的正確觀察。[注]Hufford,D.J.1995a,p.21.
在這里,哈弗德并沒有完全否定文化的作用,而是更加突出強(qiáng)調(diào)了新的經(jīng)驗(yàn)與觀察的地位,即舊有的文化是前人的經(jīng)驗(yàn)與觀察,是文化基礎(chǔ),當(dāng)然需要學(xué)習(xí),但新的文化的發(fā)現(xiàn),也需要親身的經(jīng)驗(yàn)與親自的觀察,否則就只能永遠(yuǎn)停留在舊有的文化權(quán)威層面。換言之,作者在此提醒我們注意,文化和經(jīng)驗(yàn)各自所擔(dān)任的角色,即文化本身是由前人的經(jīng)驗(yàn)積淀而成,但它固定下來后很容易形成文化傳統(tǒng)或文化權(quán)威,對(duì)新的經(jīng)驗(yàn)而言,文化既是基礎(chǔ),也是束縛。而新的經(jīng)驗(yàn)則是創(chuàng)新的動(dòng)力,只有站在文化基礎(chǔ)上的新的觀察與新的經(jīng)驗(yàn),才會(huì)有新的發(fā)現(xiàn),并發(fā)展為新的文化。在這個(gè)意義上,可以說哈弗德向我們更清晰地展示出了個(gè)人經(jīng)驗(yàn)的創(chuàng)造性作用及其與文化傳統(tǒng)的互動(dòng)機(jī)制。
哈弗德自己也曾強(qiáng)調(diào):“經(jīng)驗(yàn)中心研究法是對(duì)其他研究方法的補(bǔ)充,而非替代,……它是一種更好地去獲得隱藏在特定的超自然信仰背后的經(jīng)驗(yàn)知識(shí)的努力,并開始考慮這些經(jīng)驗(yàn)在這樣的信念中的作用。”[注]Hufford,D.J.1982,p.256.哈弗德提醒我們,很多精神信仰的確來自經(jīng)驗(yàn)、并被經(jīng)驗(yàn)所支撐和保持。現(xiàn)實(shí)生活中,也確實(shí)有很多人是因?yàn)橄扔辛烁鞣N各樣與信仰有關(guān)的經(jīng)驗(yàn),才與信仰發(fā)生進(jìn)一步的關(guān)聯(lián)的。
除此之外,哈弗德也讓我們看到以往對(duì)經(jīng)驗(yàn)的種種傳統(tǒng)解釋所導(dǎo)致的誤解與偏見。如傳統(tǒng)觀念認(rèn)為超自然信仰多是非理性的、荒謬的,是由身體或精神的疾病所致。對(duì)此,哈弗德指出:“我自己的工作和其他調(diào)查者表明,這種超自然經(jīng)驗(yàn)和信仰比通常想象的更為常見,而且它們與精神病理學(xué)或社會(huì)越軌沒有任何引人注目的相聯(lián)系起來的方式。這對(duì)于年輕人、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還有更加孤立的通常被認(rèn)為是主要的超自然信仰持有者的群體來說都是真實(shí)的。”[注]Hufford,D.J.1982,p.80.可以說,哈弗德的經(jīng)驗(yàn)中心研究某種程度上具有使民間信仰去污名或正常化的作用。同時(shí)某些民間信仰的民間醫(yī)療功能也是不可忽視的,如死去的親人的造訪,它對(duì)人們悲傷的撫慰、心理的平衡等具有生物醫(yī)療所難以企及的功效。哈弗德的另一個(gè)重點(diǎn)關(guān)注領(lǐng)域即民間醫(yī)療,可以說是他關(guān)于超自然信仰研究的一種應(yīng)用。[注]Hufford,D.J.1983;Hufford,D.J.1994.
但對(duì)經(jīng)驗(yàn)本身的強(qiáng)調(diào)易陷入經(jīng)驗(yàn)還原主義而低估實(shí)際信仰情形的復(fù)雜性。哈弗德對(duì)此也有清醒的認(rèn)識(shí),并指出經(jīng)驗(yàn)中心研究理論的目的并不是敵視文化和文化闡釋,或“將文化驅(qū)逐出對(duì)信仰的討論,相反,它是活躍和澄清這一討論,把我們對(duì)文化的作用的理解,放在合理而又系統(tǒng)的觀察的基礎(chǔ)上。需要特別提醒的是,這樣的基礎(chǔ)具有一種效果,即保護(hù)傳統(tǒng)的信仰和描述不被學(xué)者們僅僅(解釋)轉(zhuǎn)化成文化的習(xí)俗和隱性的信仰”。[注]Hufford,D.J.1995a,p.34.盡管人們對(duì)哈弗德的經(jīng)驗(yàn)中心研究理論存在一些質(zhì)疑,但他對(duì)經(jīng)驗(yàn)本身的強(qiáng)調(diào),對(duì)經(jīng)驗(yàn)在信仰中作用的肯定,以及提出的個(gè)人經(jīng)驗(yàn)作為超自然信仰來源的假設(shè)等,值得我們借鑒和進(jìn)一步思考。
綜上所述,美國(guó)民俗學(xué)者進(jìn)行宗教研究的標(biāo)志之一,是他們嘗試公平對(duì)待信仰和活生生的經(jīng)驗(yàn)。民俗學(xué)者或許還沒有挑戰(zhàn)基本術(shù)語(yǔ)的命名,但是他們?yōu)榇蜷_學(xué)術(shù)的視野已經(jīng)做了很多開拓性工作,使人們看到更多人類信仰體系背后的經(jīng)驗(yàn)因素。他們這樣做不是通過心理學(xué)分析信仰和信仰者,而是通過認(rèn)真對(duì)待人們所說、所感、所經(jīng)歷。[注]Leonard Norman Primiano,1995,p.41.
四、“經(jīng)驗(yàn)中心研究法”的理論與方法意義
哈弗德通過對(duì)超自然攻擊、神秘體驗(yàn)、神奇的治愈、死者對(duì)悲傷者的安慰性造訪、瀕死體驗(yàn)和鬼屋等信仰進(jìn)行的以經(jīng)驗(yàn)為中心的研究,提出某些精神信仰是基于那些有信仰經(jīng)驗(yàn)的人的理性和經(jīng)驗(yàn),這一關(guān)于精神信仰中經(jīng)驗(yàn)因素合理性的結(jié)論是激進(jìn)的和復(fù)雜的。[注]Hufford,D.J.1995a,p.19.而其“經(jīng)驗(yàn)來源假設(shè)”對(duì)文化的傳統(tǒng)解釋也具有一定的挑戰(zhàn)性和顛覆性。不過,這并非無源之水,它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呼應(yīng)了宗教學(xué)領(lǐng)域中的宗教經(jīng)驗(yàn)研究。同時(shí),它對(duì)民俗學(xué)的民間信仰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啟發(fā)意義。
如前所述,制度性宗教與民間信仰之間的二元對(duì)立的兩層級(jí)模式,以及以基督教為代表的制度性宗教研究中所形成的信仰與實(shí)踐二元對(duì)立模式,這雙重的二元對(duì)立對(duì)缺少經(jīng)典并以實(shí)踐為主要特征的民間信仰及其研究造成排斥與擠壓,民間信仰由此被認(rèn)為是錯(cuò)誤的與低級(jí)的。當(dāng)西方以具有系統(tǒng)性教義與嚴(yán)密性組織制度的基督教為典范的“religion”概念及其研究范式引入中國(guó)后,它也改變了中國(guó)宗教譜系的格局,如曾經(jīng)作為諸“教”典范和參照坐標(biāo)的“儒教”因不符合“religion”的界定而降到了邊緣甚至異類的位置,[注]陳熙遠(yuǎn):《宗教——一個(gè)近代中國(guó)文化史上的關(guān)鍵詞》,《新史學(xué)》2002年第13卷第4期。廣大民眾的民間信仰活動(dòng)因無獨(dú)立的組織和經(jīng)典而被視為“迷信”,只有在中國(guó)社會(huì)中結(jié)構(gòu)性地位并不突出的佛、道教被視為西方意義上的“宗教”。可見,“religion”概念及其研究范式本身隱含著等級(jí)與偏見,難以真正理解中國(guó)本土宗教實(shí)踐,特別是影響最為廣泛的民間信仰。為了擺脫“religion”概念及其研究范式的影響,學(xué)者們嘗試從中國(guó)本土宗教概念以及宗教實(shí)踐中發(fā)掘其自身的思維模式與運(yùn)行機(jī)制,進(jìn)而尋求更具有解釋力的本土理論。[注]如彭牧:《religion與宗教:分析范疇與本土概念》,《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5期;梁永佳:《“宗教”的命運(yùn)與中國(guó)農(nóng)村宗教復(fù)興》,《社會(huì)》2015年第1期。
哈弗德的“經(jīng)驗(yàn)中心研究法”以及它所呼應(yīng)的宗教經(jīng)驗(yàn)研究,也可以成為我們探索中國(guó)本土宗教實(shí)踐的一種理論工具。因?yàn)檫@一理論本身就是對(duì)基督教及其研究范式的一種反抗,它關(guān)注的核心不是具有教義與組織制度的“宗教”,而是人的內(nèi)在的宗教體驗(yàn),即“宗教性”。后者是不同信仰傳統(tǒng)的共通之處,也是可以展開平等對(duì)話之處。該理論平等看待所有的信仰傳統(tǒng),其背后所蘊(yùn)含的是相互尊重與包容的價(jià)值理念。它努力于消除偏見,為民間信仰“去污名”,如哈弗德肯定超自然信仰中具有理性因素;[注]顧笛安(Diane E.Goldstein)在此基礎(chǔ)上,也嘗試論證人們關(guān)于超自然信仰的經(jīng)驗(yàn)敘事大體上是合乎邏輯與情理的。參見[美]顧笛安《科學(xué)理性主義與超自然經(jīng)驗(yàn)敘事》,姚虹芳、朱丹譯,《文化遺產(chǎn)》2015年第6期。同時(shí)它也嘗試打破不同“宗教”的界限,深入信眾的內(nèi)心深處,關(guān)注其“信”的狀態(tài)與過程,充分尊重信眾的主體性與創(chuàng)造性。
此外,該理論也同樣試圖消除人們對(duì)經(jīng)驗(yàn)知識(shí)的偏見。在十九世紀(jì)晚期至二十世紀(jì)初這一時(shí)代轉(zhuǎn)型時(shí)期,技術(shù)經(jīng)驗(yàn)已逐漸代替生活經(jīng)驗(yàn)成為權(quán)威的來源。科學(xué)知識(shí)的發(fā)展使人們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來源于人們自身實(shí)際生活經(jīng)驗(yàn)的知識(shí)和洞見,通常被認(rèn)為是幼稚的和幻想的。[注]Hufford,D.J.1995a,p.25.對(duì)此,哈弗德指出,現(xiàn)代世界的問題不在于知識(shí)活動(dòng)與理性太多,科學(xué)知識(shí)與理性分析和基本的精神信仰并不矛盾,真正的問題在于我們看待什么是知識(shí)活動(dòng)以及誰(shuí)擁有正確推理的能力這一問題的視野太狹隘。[注]Hufford,D.J.1995a,p.40.
而以“關(guān)注和欣賞日常生活經(jīng)驗(yàn)與意蘊(yùn)”[注]彭牧:《從信仰到信:美國(guó)民俗學(xué)的民間宗教研究》。為訴求的民俗學(xué)學(xué)科,則應(yīng)有自覺和責(zé)任去拓展人們的視野。由于民俗與身體經(jīng)驗(yàn)的天然聯(lián)系,其中蘊(yùn)含著大量的“體知”知識(shí)或經(jīng)驗(yàn)知識(shí),因此,民俗學(xué)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的社會(huì)尋找更民主地分享文化權(quán)威的方式。而個(gè)人信仰經(jīng)驗(yàn)正是以身體為載體的,以經(jīng)驗(yàn)為中心的信仰研究,更多地突出身體如何塑造文化的一面,而不是被動(dòng)地被文化刻寫的一面[注]彭牧:《身體與民俗》。,因此,“經(jīng)驗(yàn)中心研究法”必然尊重身體化的經(jīng)驗(yàn)知識(shí)。這與民俗學(xué)的訴求相應(yīng),可以為民俗學(xué)與民間信仰研究提供一個(gè)有益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