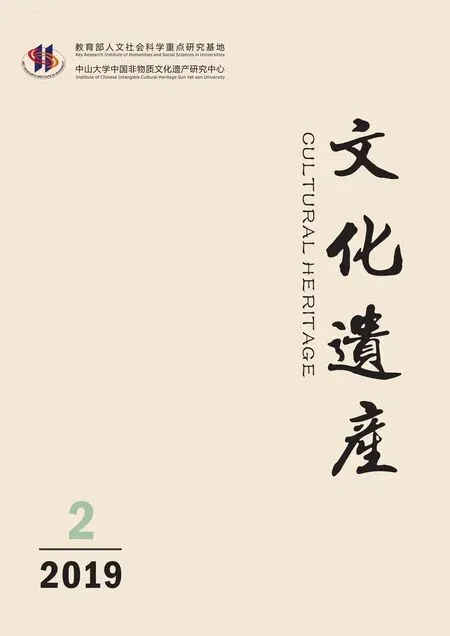相聲藝術傳承的階段性特征
馮文龍
近年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層面,戲曲、曲藝的傳承、發展取得了豐碩成果,然而繁榮背后也存在傳承不完整、發展不均衡的缺憾。以相聲為例,相聲藝人郭德綱及其所在的德云社標榜“恢復傳統”,在商業演出中上演了眾多傳統相聲,受到市場關注。另外,郭德綱通過各種方式與梨園名角合作演出:2018年9月即先后參演《秦香蓮》(前飾王延齡,后飾國太)和《西漢三斬》(飾彭越、英布、韓信)等大戲,又與京劇名家陳少云、裴詠杰,河北梆子名家王少華、婺劇新秀李烜宇聯袂出演京梆婺大戲《薛剛反唐》,一趕二飾演徐策及程咬金,并在演出后補行拜師儀式,拜入京劇麒派趙麟童先生門下。尊重傳統,戲曲功底深厚,并從傳統戲曲與曲藝中汲取營養,恰恰是郭德綱及德云社成功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更多相聲藝人以面向未來、開拓創新的姿態,創作、表演了一系列新相聲。兩相對比,郭德綱等人走過了一條與同行不同的藝術道路。不同傳承方式之間的相似性與差異性,傳承過程中的經驗與教訓,值得我們反思。而當我們回望相聲作為一個曲藝門類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郭德綱等人與同行之間的差異,主要體現為對傳統的不同態度,即“接續傳統”與“藝術革新”的不同取向。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是人類個人、群體、集體所創造并為后代人不斷傳承的活態的精神財富。相對于物質文化遺產而言,它具有傳承性、精神性、活態性、實踐性等特點,它是在人類世代實踐中存在的精神財富。”[注]宋俊華:《文化生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文化遺產》2012年第1期。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相聲在存續、發展過程中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這多存于相關學術著作,如薛寶坤《中國的相聲(增訂本)》《薛寶坤曲藝文選》、倪鍾之《中國相聲史》,以及相關藝人的回憶錄或傳記,如薛寶坤《侯寶林評傳》、侯錱《一戶侯說》、馬季《一生守候》等,而對于階段性特征產生原因,不同發展模式的成敗得失,尚缺乏系統總結,對于相聲傳統的存續與突破,尚缺乏清醒認識。本文從非遺的視角審視相聲,通過對其發展歷程和各階段特征的簡要梳理,總結、反思其發展的得與失、傳統的價值與意義,以期為相聲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活態傳承,提供思路與借鑒。
一、相聲的傳統
作為曲藝的一個門類,相聲在表演內容、表演方式、語言技巧等方面形成了鮮明特色。為避枝蔓,本文以相聲與曲藝、戲曲的關系為切入點,剖析、闡發相聲“傳統”的形成、斷裂與接續。
作為源自社會底層的藝術形式,“相聲”與同屬民間曲藝的評書、蓮花落、快板等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在相聲形成的時期,在北京還有戲曲(如昆曲、皮黃、梆子等)、曲藝(如各種大鼓、時調、八角鼓、蓮花落等)、雜技、民間歌舞(主要是在民間各種“花會”中)及某些體育項目(如摔跤、武術等),它們之間相互補充,構成群眾的文藝消費市場。”[注]倪鍾之:《中國相聲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4頁。這種不同藝術門類“相互補充”的格局延續了相當長的時間。因為彼此聯系緊密,所以1938年侯寶林拜師朱闊泉時,就按當時的規矩請了“說評書的、唱蓮花落的、變戲法的、練把式的這四門的師傅,一門各來一位”[注]侯寶林:《侯寶林自傳》,侯錱主編:《一戶侯說》,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7年,第64頁。。正是這樣的藝術格局豐富了相聲的表現形式,也形成并且強化了相聲表演以普通市民的生活和情趣為中心的民間色彩。為了謀生,相聲演員形成了一系列基本功,成為他們在曲藝演出競爭中安身立命的資本。侯寶林將相聲基本功歸納為十二項,分別是:第一、開場詩;第二、會說“門流兒”;第三、白沙撒字;第四、會唱太平歌詞;第五、會說一個人的(就是單口相聲);第六、會捧;第七、會逗;第八、會說三人相聲。第九、會要錢;第十、雙簧;第十一、口技;第十二、數來寶。[注]侯寶林:《侯寶林自傳》,第97頁。這些技藝反映了當時相聲演員的地位和相聲演出的基本面貌,也顯示了曲藝在相聲演員藝術風格中的重要地位。
除了與曲藝的聯系,相聲與戲曲的關系更加密切。“相聲和京劇結緣就始自‘窮不怕’朱紹文、云里飛這一代……是他們最早把京劇融匯到相聲里,豐富了相聲的表演內容”[注]梅京:《京劇與相聲》,《戲曲藝術》1999年第1期。,《空城計》《黃鶴樓》《汾河灣》《關公戰秦瓊》《改行》等傳統相聲中均有對戲曲和曲藝的生動模仿。這來自于舊時相聲藝人的成長經歷和生存環境。如《戲劇雜談》堪稱侯寶林代表作,“他能把這個相聲說好,得益于他的戲曲功夫和在天橋的熏陶”[注]劉紅慶:《江湖江山各半生》,濟南:齊魯書社2010年,第45頁。。侯寶林的藝術造詣,是在社會底層的摸爬滾打中逐步練就的。而在說相聲之前,他曾在鼓樓市場戲班謀生:“在鼓樓市場這地方,我唱了一年多……所有我們那場子唱的戲,幾乎沒有我不會唱的,而且生、旦、凈、末、丑都會。”[注]侯寶林:《侯寶林自傳》,第50頁。搭班唱戲的經歷,奠定了侯寶林在藝術方面的深厚功底。這是當時包括相聲演員在內的江湖藝人的普遍經歷,反映了相聲最初的演出環境和相聲藝人的生存環境。相聲演員學唱戲曲、曲藝,最初只是在相聲不景氣的時候賴以謀生的手段;后來則演變為一種藝術的自覺,使之成為豐富相聲表現形式、招徠觀眾、提升競爭力的手段。
除了對“戲曲”“曲藝”的模仿,相聲(以及其他曲藝形式)演員有時也要反串登場,而且往往戲路很寬,能夠勝任多個行當。如侯寶林曾說:“曲藝演反串,這已有比較久的傳統,曲藝演員全臺人幾乎有一半能演京戲……像《捉放宿店》這樣的戲,一共三個角色,這三個角色我都能唱。我唱過呂伯奢,唱過陳宮,也唱過曹操,反正短那個角色,我就唱哪個。《法門寺大審》我一般都能唱,我唱過趙廉,唱過賈桂……《四郎探母》呢?我是前面去太后,中間趕楊宗保,《回令》時再改回來,還是太后。這樣唱,又是青衣,又是小生。”[注]侯寶林:《侯寶林自傳》,第122頁。除了全臺反串,有時也會與戲曲演員同臺演出。如在天津演《甘露寺》的時候,侯寶林等人請了梆子演員葛文娟、王漢森等參與,采用了京梆兩下鍋的演法。[注]侯寶林:《侯寶林自傳》,第124頁。盡管反串演戲多是曲藝進入低潮時的無奈之舉,但這充分顯示了以侯寶林為代表的相聲藝人豐厚的藝術積淀,也對相聲作品的內容和演出形式、演出風格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在曲藝出現低潮的時候,侯寶林甚至演過話劇,包括由陳泉翻譯的法國獨幕劇《欺騙》(演出時改名為《結婚前奏曲》),以及《情天血淚》《梁上君子》等。侯寶林強調:“話劇的語言藝術,也幫助我說好相聲”。[注]侯寶林:《侯寶林自傳》,第85頁。話劇雖不屬于曲藝,但同樣豐富了侯寶林相聲的語言藝術。
不論是學唱戲曲、曲藝,還是反串演戲,侯寶林都強調“對中求好”“精益求精”。如著名的傳統段子《空城計》并非侯寶林的原創,但經過他的改動更加合理:
以前別人說《空城計》,是說“城樓”這一場。四個龍套出場,前兩人走到臺中間站一下,一人往左邊,一人往右邊,后兩人上場也是如此,這不對……“城樓”這一場,臺上大邊兒(左邊)是諸葛亮、琴童和城樓;司馬懿帶兵上來,唱:“大隊人馬奔西城”,他應該站小邊兒(右邊),四個龍套站一字兒,沒有一邊兩個的站法。原來相聲不合理就在這地方,我把這一場改成過場,就合理了。[注]侯寶林:《侯寶林自傳》,第78頁。
侯寶林并不以“歪”“怪”吸引觀眾,而是通過對藝術的嚴肅打磨強化舞臺效果。豐富的曲藝、戲曲甚至話劇的演出經歷,使侯寶林對舞臺表演有更為深刻、準確的理解。其精湛的功力不僅征服了觀眾,而且得到了周信芳、梅蘭芳等名角的認可。當然,也有一些藝人的做法與侯寶林不同:“常寶堃反串的一些戲,雖然都是臨時學來的,但演得滑稽。我看過他的兩個戲,一個是《法門寺》,他演宋巧姣,他沒有青衣嗓子,是正扮,可是他加上一些與唱詞毫無關系的動作手勢,也能搞出噱頭來,逗人笑;一個是《連環套》,他演竇爾敦,你看了不能不說他有功夫。”[注]侯寶林:《侯寶林自傳》,第83頁。常寶堃等人在反串演出中往往求新、求異,實現“逗觀眾笑”的目的。雖然與侯寶林的嚴肅化處理不同,但可見反串演戲是當時相聲藝人的普遍選擇。
二、傳統的斷裂
侯寶林等藝人在民國時期的演出中所形成的“傳統”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存續。在舞臺實踐層面,新中國成立后,相聲的地位和演出環境發生了變化,國家權力對相聲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相聲由謀生手段升格為受到國家領導人和普通百姓認可和關注的“語言藝術”。曲藝和戲曲的功底不再是作為“相聲演員”的必要條件,這首先在演員藝術背景上割裂了相聲與戲曲、曲藝的關聯。在侯寶林之后的相聲藝人,往往沒有興趣和功底在相聲中學唱戲曲、曲藝,也很少再有機會參與戲曲的演出。如薛寶坤所言:“新中國成立以后培養的兩三代演員,基本上并不掌握傳統節目。他們沒有三冬兩夏的科班式學習,沒有在‘地上’為一般市民觀眾表演的經驗,因而也沒有‘撂地’競爭時所必須掌握的相當數量的傳統節目。他們當中較早的一代(如馬季、趙振鐸等)只是在繼承傳統高潮的六十年代,曾經耳濡目染受過傳統的熏陶,甚至一度下過工夫掌握過并不很多的節目。個別‘門里出身’的中青年演員(如天津馬志明、趙偉洲等)對傳統雖然諳熟,但也缺少實踐的機會,難以刻意的追求。‘推陳出新’觀念的片面理解使當代相聲演員大多輕視傳統,認為它所能提供的只是一些言語技巧、形式套式,對傳統的精神或精髓則無暇無力或無心無意顧及了”。[注]薛寶坤:《相聲及喜劇性曲種通論》,見薛寶坤《薛寶琨曲藝文選》,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3年,第196-197頁。刻意追求創新,對傳統節目、傳統精神的淡漠和忽視,造成了舞臺演出的斷層。
而影響更深遠的是內容的斷層。在新的政治環境和文化環境下,政府和藝人都期待新的演出內容:政府希望相聲能夠反映“新的時代”,滿足群眾“新的需要”;而藝人希望通過新的作品來趕超前人,體現其自身價值。然而,20世紀五十年代之前在社會底層累積起來的作品,至少有相當一部分是無法承擔這樣的歷史使命的。隨著這相當一部分作品被選擇性擱置(甚至毀棄),相聲舞臺迫切需要新的作品補充進來,于是,與傳統的存續相比,新作品的創作更加緊迫,創作新段子成為當時的藝術主流,相聲與戲曲、曲藝漸行漸遠。
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侯寶林“與著名作家老舍等人密切合作, 創作和改編出一大批既自然本色、又清新高雅、質量上乘的優秀相聲段子。”[注]田莉:《侯寶林的相聲藝術及其文化史意義》,《中國文化研究》2003年春之卷。而以馬季等為代表的相聲藝人在創作方面有著更高的自覺性。與侯寶林等先撂地、后走上舞臺相比,馬季等相聲藝人是在新政府的關懷、關注和關照下成長起來的,特殊的政治氛圍和文化環境讓馬季這些年輕的“文藝工作者”有了更加強烈的“創新”和“趕超前人”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跟老藝人相比,我是建國后的第一批新文藝工作者,多一些文化知識,對新事物的敏感和接受能力強。我想,只有運用自己長處,發揮優勢,另辟蹊徑,才能超越前輩。”[注]馬季:《一生守候》,北京:團結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頁。追求創新成為當時“新文藝工作者”的普遍追求,而創作新相聲成為馬季等人趕超前輩的突破口:“要想超過或者趕上前輩們,就應該從創作上下手,下決心,在創作上有所突破”。[注]馬季:《一生守候》,第29頁。
如前所述,在特殊的政治氛圍中,傳統作品并不能滿足現實的需要,這在客觀上為新段子的創作、演出提出了要求,也創造了條件。據馬季回憶,20世紀六十年代初,馬季、于世猷曾下鄉數月,創作了《畫像》《跳大神》《黑斑病》三個段子;又針對足球比賽中球迷的不理智行為,創作了《球場上的丑角》,均得到認可。馬季認為,“正是這些不斷出現的新的‘現實生活’……使我積累了創作和演出‘應時’相聲的經驗,也迫使我學會了如何利用傳統去為現實服務”。[注]馬季:《一生守候》,第57頁。“利用傳統為現實服務”已不僅是一種內在的藝術追求,而成了一種特殊背景下外在的政治任務。經過努力,馬季等人創作、演出了《友誼頌》《宇宙牌香煙》《五官爭功》等三百多個相聲段子,一度深受聽眾和觀眾的歡迎。從這些節目名稱中,不難看出其創作、演出“新”的特色,這構成了當時相聲演出的主要內容,奠定了相聲演出新的格局。
然而此消彼長,對新的追求造成了演員對“傳統”(包括傳統段子和傳統演出形式)的疏離。馬季也曾演過《找堂會》《扒馬褂》等作品,但真正讓他立足于相聲界,為人所熟知的卻是那些創作于各個時期,體現時代特色的新段子。“廣播說唱團的幾位老藝術家,回憶整理了‘四大本’……幾乎傳統相聲的百分之八十全在里邊,而且都是精品,他(指馬季)下了很大的功夫全都背下來了。他很早就下決心,幾年之內,相聲作品創作要自給自足。”[注]張伯苓:《馬季生前與身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6頁。廣播說唱團整理的“四大本”,能否涵蓋“傳統相聲的百分之八十”,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馬季之后的相聲藝人似乎并沒有興趣和毅力去“背”這些老段子,遑論演出。而馬季本人在“背下”這些老段子之后,由于主觀和客觀的原因,也未能將其全部呈現于舞臺,而是將其轉化為創作新段子的參照物和藝術資源。傳統作品的繼承和傳統風格的存續,最終讓位于新作品的創作。
從藝術發展的角度,馬季等人在相聲新舊變革時代的選擇維護并提升了相聲的品位與地位,卻也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與傳統的關系。伴隨著創作新相聲以滿足“時代需要”的努力,傳統段子的演出空間被大大壓縮。這種情況在改革開放后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因為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文化的多元化,相聲演員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迎接新的生活和市場競爭而更加復雜,“傳統”被進一步壓制。但在多元化的演出市場,相聲“亦步亦趨”的“追趕”不僅沒能滿足時代和觀眾的更高需求,反而使觀眾更加懷念被長期擱置的老段子。
據馬季弟子姜昆講述,在天津考察小劇場時,曾應觀眾要求背“老段子”:
有人開始講了:《報菜名》會嗎?底下又有人講:“《八扇屏》來一段!”……我一口氣背完了以后,一身汗。完了以后一位老同志站起來,姜昆,七十四了,他是說自己七十四歲了,知道你們不說這個,有耳福。[注]姜昆:《馬季老師給我的思考》,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4年,第194頁。
現場觀眾要求姜昆表演老段子,正說明天津觀眾對老段子的認同和需求。而姜昆曾坦言,“我的老師是馬季,馬季的老師是侯寶林,我們不能算是一個流派,但是是這個師承關系,我們的相聲作品中極少有‘貫口’,就是噠噠噠大段背誦的那種極少運用……我們這一代幾乎不說貫口。”[注]姜昆:《馬季老師給我的思考》,第194頁。對“改革出新”的刻意追求,導致了對傳統的割舍,也割裂了相聲與其他藝術形式尤其是戲曲的密切聯系。正如傅謹所言,“人們雖然都說要在對傳統的繼承與創新之間保持一種不偏不倚的辯證關系,在實際運作中卻總是予以創新以更重要的價值,并且經常是以全盤否定的方式無情地丟棄傳統。”[注]傅謹:《關于“推陳出新”的斷想》,見傅謹《薪火相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50頁。在緊跟時代潮流,與時俱進的觀念之下,侯寶林等人所尊崇的與戲曲保持密切聯系的藝術特色,被多數演員所舍棄。畢竟,戲曲、曲藝都無法代表時代潮流,而戲曲、曲藝所需要的藝術功底,也考驗著相聲演員的毅力和天分。于是不論在廣播還是電視,聽眾、觀眾都聽到、看到了一大批所謂反映現實生活的“新相聲”,最終也默認了傳統斷裂的事實。
三、接續傳統的嘗試與成效
在眾多曲藝院團相聲藝人通過緊跟生活潮流創作、表演相聲的同時,郭德綱等民間藝人通過另外一種方式吸引了大批年長以及年輕的觀眾。他們固然也創作新段子,但主要是恢復、整理久別舞臺的傳統段子,并在演出中加入對戲曲和十不閑蓮花落、西河大鼓等曲藝形式的學唱,甚至反串戲曲演出,不論演出內容還是演出形式,都與數十年前侯寶林等人的藝術活動遙相呼應。在相聲演出的效果層面,郭德綱及其德云社無疑是成功的。接續傳統,恰恰是其成功的秘訣。
(一)演出內容與風格的接續
在演出內容上,德云社整理、演出了大量傳統相聲段子,以及十不閑蓮花落、快板書等曲藝形式,并上演了大量反串戲。出版于2006年的《非著名相聲演員》,即列舉了德云社上演的大批傳統段子及曲目:其中單口相聲有《君臣斗》《丑娘娘》等長篇,《珍珠翡翠白玉湯》等短篇;對口相聲有《八扇屏》《地理圖》等貫口,《升官圖》《生意經》等平哏,《八大吉祥》《批三國》等文哏,《五行詩》《打燈謎》等子母哏,《學四省》等倒口,《八大改行》《汾河灣》等柳活;群口相聲有《扒馬褂》《秦瓊賣馬》等。另外,還有《白蛇傳》《秦瓊觀陣》等太平歌詞,《發四喜》《十里亭》等十不閑蓮花落曲目,《雙鎖山》《單刀會》等快板書曲目,[注]郭德綱:《非著名相聲演員》,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6年,第124-128頁。種類繁多。在近年來的商業演出中,郭德綱及德云社又將更多的傳統段子搬上舞臺。在深入發掘傳統劇目的同時,郭德綱等人也有意識地接續了相聲界舊有的演出習俗,如開場之前唱十不閑蓮花落等,這不僅滿足了老觀眾聽傳統段子的愿望,也讓年輕觀眾了解了“相聲”的另外一種面貌。
除了學唱戲曲、曲藝,在反串演戲方面,郭德綱與侯寶林也有相似之處。據《非著名相聲演員》所列的《郭德綱藝術簡歷》,郭德綱自幼學習評書、相聲、快板、梆子、評劇,并曾登臺演出[注]郭德綱:《非著名相聲演員》,第122頁。,在正式說相聲后,也曾主演評劇《鍘判官》,并以德云社為班底,在各種場合演出傳統戲曲劇目,如2006年上演京、評、梆大戲《劉墉鍘閣老》(郭德綱前以丑扮李堂,后以老生扮劉墉);2006年3月,上演評劇《秦香蓮》(郭德綱前以老生扮王延齡,后以花臉扮包拯),同年5月上演京劇《豆汁記》;2010年上演《法門寺》,郭德綱扮演劉瑾,其義子陶陽則反串小太監賈桂和縣太爺兩角。[注]郭德綱:《過得剛好》,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3年,第229-236頁。前文提到的《秦香蓮》《西漢三斬》《薛剛反唐》也是郭德綱與梨園名家共同呈現的大戲。郭德綱在戲曲演出中的活躍,在某種程度上接續了侯寶林、常寶堃等人反串唱戲的傳統。2016年8月,以京劇為演出內容的民營麒麟社成立,郭德綱、陶陽等以此為平臺,向觀眾奉獻了《劉墉打鑾駕》《西漢三斬》等經典劇目。這都體現了德云社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接續傳統的嘗試。
(二)對相聲界傳統習俗的接續
除了演出內容和演出風格的繼承,作為來自民間的相聲藝人,郭德綱及德云社在拜師、班社管理、藝術傳承等方面上幾乎全盤接納了相聲的“舊”傳統。“相聲的拜師分授業和拜門兩種:授業是從頭教起,至少要三年零一節才能出師;拜門則是帶藝投師,拜師的目的就是為了取得相聲藝人的表演資格,一般一年算畢業。”[注]劉紅慶:《江湖江山各半生》,濟南:齊魯書社2010年,第53頁。2004年,郭德綱拜師侯耀文,與1938年侯寶林拜師朱闊泉頗為相似,都屬于“拜門”。郭德綱對師承關系極為看重,作為弟子,他對侯耀文、金文聲及張文順等前輩藝人推崇備至,甚至在德云社后臺供奉遺像,“初一十五,后臺老少紛紛叩拜”[注]郭德綱:《過得剛好》,第29頁。。德云社依然保持著磕頭拜師的傳統,并恢復了建國后已相對少見的“引保代”三師。郭德綱門下弟子按照“云鶴九霄龍騰四海”八個字排序、取藝名,在演出時多以藝名登臺,而不稱本名。
人員管理方面,德云社確立并維系了家族式的班社制度。2016年,《德云社家譜》公布,《家譜》中詳列相聲門、西河大鼓門各科弟子藝名、本名、籍貫等,更追溯歷史,繪制《德云社相聲演員師承關系》圖表。同時強調了“德云社十大班規”:“一不準欺師滅祖,二不準結黨營私,三不準在班思班,四不準狂妄無恥,五不準誤場蹲工,六不準刨活陰人,七不準吃空挖相,八不準帶酒上臺,九不準賭博嫖亂,十不準打架斗毆”。[注]參見“德云相聲網”相關介紹,網址:http://bbs.guodegang.org/portal.php?mod=view&aid=4953, 查詢日期:2019年3月4日。對比民國時著名京劇科班富連成《梨園規約》中“在班思班(永不敘用)”“臨時誤場(不貸)”“口角斗毆(責罰)”“當場陰人(不貸)”[注]唐伯弢撰,白話文審校:《富連成三十年史》,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53頁。等條目,可見其“班規”與舊時班社存在一定的淵源關系。在介紹各科弟子時,《家譜》以紅筆加了“備注”,言辭頗為激烈,如在“云”字科之后,家譜云:“另有曾用云字藝名者二人,欺天滅祖悖逆人倫,逢難變節賣師求榮,惡言構陷意狠心毒,似此寡廉鮮恥令人發指,為儆效尤,奪回藝名逐出師門。”又云:“X云X,幾進幾出頗多反復,念有悔改之心,摘字查看,望自思過。”在“鶴”字科的介紹中,又有“X鶴X……欺師滅祖手段卑劣,革除師門。X鶴X……背師行事性質惡劣,清門。X鶴X……違背行規,清門”。[注]參見“德云相聲網”相關介紹,網址:http://bbs.guodegang.org/portal.php?mod=view&aid=4953, 查詢日期:2019年3月4日。從這些頗顯江湖氣息的班規和處罰方式上,可見在德云社的管理及日常演出中,師徒父子的江湖道義實際超越了現代契約精神。盡管在經歷了各種風波之后,德云社有意識地由“班社”向“企業”轉變,但德云社藝人之間依然以班社為平臺,以師徒父子的道德觀念來維系和約束。在師徒關系上,郭德綱的弟子往往是與郭德綱同輩的于謙、高峰等人的義子,而于謙、高峰的弟子又往往拜郭德綱為義父。作為師傅、班主和義父,郭德綱在德云社藝人中擁有絕對權威。
在傳承方式上,德云社仍崇尚口傳心授的方式。郭德綱直言:“我認為相聲傳授必須遵守口傳的獨特方式,不能使用流水線形式的教學方式,否則是不可能領略到這個行業獨特的魅力的。不同的劇場、不同的氛圍、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服裝,同樣一句話都有不同的表現方法,很難。”[注]郭德綱:《過得剛好》,第269頁。這種傳承方式,與郭德綱個人的藝術成長經歷是密不可分的,而馬三立、侯寶林、常寶堃等相聲名家的成長確實不是通過“流水線式的教學”來完成的。
由此,德云社對相聲傳統的接續是全方位的,不僅反映在對傳統段子的整理、演出上,也反映在對班社管理、傳承方式的延續上。
四、接續傳統的反思
王霄冰曾提出:“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中產階級的懷舊心理日增,他們在享受現代化的同時也開始回過頭來尋求回歸傳統。”[注]王霄冰:《民俗主義論與德國民俗學》,《民間文化論壇》2006年第3期。德云社對傳統的接續,一方面順應了普通觀眾在藝術層面對傳統相聲的認同,另一方面也迎合了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社會公眾的“懷舊心理”。這是其演出成功的文化背景和社會心理基礎。
相聲演員參與戲曲演出,德云社并非個例。2008年,相聲、評書、京劇同臺演繹《烏盆記》,先由馬志明、黃族民表演經典馬派相聲,然后評書藝術家單田芳表演評書《烏盆記》,最后是由京劇名家鄧沐偉、王珮瑜和相聲名家馬志明共同上演京劇《烏盆記》,正延續了曲藝與京劇的密切聯系。
從相關商業演出的觀眾反響來看,傳統相聲依然受歡迎,相聲演員參加的戲曲演出依然有市場,太平歌詞、快板、十不閑蓮花落等傳統曲藝形式征服了一大批年輕觀眾,相聲儼然在“傳統”的旗幟下,又占據了文化市場一席之地。而如果聯系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或許可以提供這樣一種思路:當相聲貼近市場,活態傳承,才能真正滿足觀眾的需求與欣賞趣味;接續傳統,或許比沒有根基的“創新”更能體現其藝術生命力。郭德綱之于相聲,與張火丁之于京劇,都昭示了堅守傳統的藝術價值。
然而在“繁榮”背后,我們又不得不思考“傳統”存續與變革的問題。首先是存續。相聲一方面是活生生的文化市場競爭的參與者,有“文化商品”的屬性,但另一方面又有“文化遺產”的屬性。如前文所述,作為當前相聲商演的支柱性力量,德云社采取的仍是傳統的班社管理方式,那么班社制度與現代社會能否長期和諧共存?德云社相聲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郭德綱、于謙、高峰等核心成員的藝術功底,在技藝傳承方面,郭德綱反復強調口傳心授的意義,而比較抵觸“流水線式的教學”,那么德云社的“成功”,能否長期存續?其演出的火爆與班社體制、口傳心授的傳承方式是否存在因果聯系?藝術的接續是否以班社體制、口傳心授為必要條件?在人才培養方面,師徒口傳心授的傳承方式能否適應文化市場競爭的節奏?當班社管理之類藝術“外圍”的東西與現實社會相齟齬,相聲在現代社會的文化競爭中,該以何種方式傳承這些相聲劇目和基本技藝?我們認為,存續傳統應專注于藝術層面,深入挖掘、整理傳統段子(事實上,受各種條件限制,依然有大量傳統段子亟待挖掘、整理和演出),存續傳統的演出技藝,包括曲藝、戲曲等經典唱段,豐富演出內容。而對于藝術以外不適應現代社會要求的陳規陋習,則應在不影響藝術存續的前提下,予以革除或改進。
其次是變革。有學者強調,“郭德綱及其德云社的火爆是以整個相聲行業的冷清來襯托的”,[注]施愛東:《郭德綱及其傳統相聲的“真”與“善”》,《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這也提醒我們,德云社的模式并非放諸四海而皆準。事實上,當前的相聲演出面臨著比20世紀上半葉更加激烈的文化競爭,觀眾的欣賞趣味更加多元化。作為一個藝術門類,一個仍然活躍于舞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僅僅是接續傳統是不夠的,突破與革新是必由之路。如姜昆曾感嘆,“想起現在的一些年輕人在舞臺上把老先生扔掉的東西一一撿回來,獵奇、顛覆,打著‘恢復傳統’的名義,拾牙慧,撿垃圾,心疼啊!”[注]姜昆:《馬季老師給我的思考》,第181頁。所言并非杞人憂天,接續傳統不等于照單全收,泥沙俱下,而應有所選擇,有所揚棄。黃永林先生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是對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世代相傳的非物化形態的即精神 (技藝) 層面文化的動態保護,不是機械地、被動地封存式保護,而是活態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要適應不斷變化著的社會文化環境而得以傳承”[注]黃永林:《“文化生態” 視野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文化遺產》2013年第5期。。侯寶林對相聲品位的提升有目共睹。在20世紀40年代,侯寶林便清醒地認識到,盡管一些內容不健康的相聲能夠轟動一時,但“這只是一時現象,觀眾對藝術是有鑒賞能力的,要演,還得演些正經的東西”,[注]劉紅慶:《江湖江山各半生》,濟南:齊魯書社2010年,第83頁。出于這樣的藝術自覺性,侯寶林改革了一些傳統節目,“把相聲從地攤上弄到大雅之堂”,[注]姜昆:《馬季老師給我的思考》,第156頁。使相聲從糊口技藝升格為語言藝術。可以說,沒有對傳統的揚棄和突破,沒有對內容和風格的凈化,相聲的藝術品位和地位是無法得到提升的。然而刻意強調創新,甚至以背離傳統為代價追逐時尚潮流,只會將創新變成“無根之水,無本之木”,相聲傳統曾經的斷裂危機已經昭示了這一點。薛寶坤先生曾言:“現實只是傳統的繼續而不是他們的斷離,傳統中那些最本質和鮮活的東西在現實中還是那么有生命力。對待傳統不只有推陳出新、除舊布新一種方式,還可以有溫故知新、存舊立新另一種方式。”[注]薛寶坤:《中國的相聲》(增訂本),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5年,第208頁。對傳統的“變革”,應以“敬畏”和“繼承”為前提,“相聲要發展,但絕不是完完全全的‘革故鼎新’。欲使其發展,就必須走‘先繼承,再發展,在繼承中求發展’的路。”[注]高玉琮:《傳統相聲的回歸與相聲藝術發展》,《文藝研究》2003年第2期。在對待傳統的態度上,侯寶林為后輩做出了榜樣:認清歷史發展趨勢,不盲目追求轟動效應,以嚴肅端正的態度對待藝術,剔除其中不健康、不為觀眾所接受的成分,而對其中有益的、符合觀眾需要的成分精益求精,從而實現藝術品位的提升和藝術價值的凸顯。正如田莉所評論的那樣,“作為一種文化現象, 侯寶林相聲藝術的文化史意義,不僅僅在于他為后人留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相聲段子, 更在于他為后人摸索出了一條發展通俗文化的正確道路。”[注]田莉:《侯寶林的相聲藝術及其文化史意義》,《中國文化研究》2003年春之卷。相聲所兼具的文化“商品”和文化“遺產”屬性,要求我們應以更加審慎的態度對待傳統的“變革”。
非物質文化遺產需要保護,但切忌僵化、封閉。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方面,對傳統的接續與揚棄,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概念。近年來“傳統相聲”的復蘇無疑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傳承有較強的示范意義。但另一方面,相聲兼具文化遺產和文化商品的雙重屬性,片面僵化地重復前人并不能推動相聲繼往開來,而舍棄傳統的內容和風格,亦步亦趨地求新求變,則將失去發展的根基。郭德綱及德云社在演出市場的口碑,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敬畏和接續傳統”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重要意義。接續傳統只是相聲發展的階段性工作,正本清源,有所突破,活態傳承,才是相聲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應因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