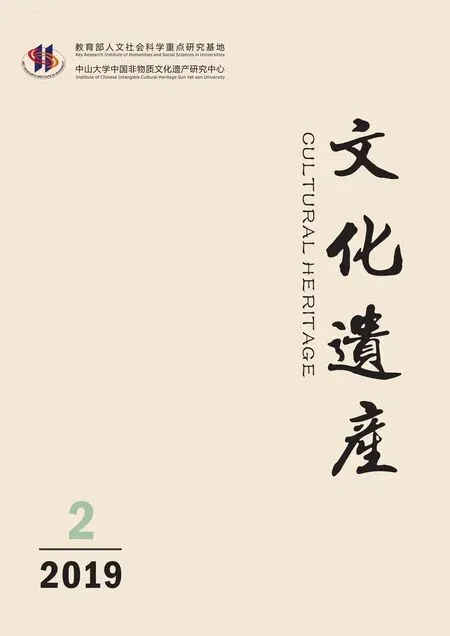論演戲酬神對清代禁戲政策的消解*
張天星
清代是中國古代禁毀戲曲最頻繁的朝代,清代統治者把觀念性禁戲與制度性禁戲相結合,將禁戲力度和規模推至高峰。但是清代禁戲為何屢禁不止、愈禁愈演?這是清代戲曲研究難以回避的重要問題。目前,學界認為清代禁戲屢禁不止現象的主要原因有:觀眾喜愛觀劇[注]張勇風:《中國戲曲文化中的禁忌現象研究》,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6年,第264-277頁。;清朝對社會監管力度減弱、社會道德觀念松動[注]劉 慶:《管理與禁令:明清戲劇演出生態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23-246頁;金坡:《愈禁愈演:清末上海禁戲與地方社會控制》,《都市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作為主要消費群體的商人偏好淫戲的娛樂訴求[注]魏兵兵:《“風流”與“風化”:“淫戲”與晚清上海公共娛樂》,《史林》2010年第5期。;夜戲難禁是由于鄉村經濟的發展、商人階層崛起、日漸奢靡的消費文化以及利益驅使的復合產物[注]姚春敏:《控制與反控制:清代鄉村社會的夜戲》,《文藝研究》2017年第7期。。這些觀點皆有根有據,豐富了對清代禁戲屢禁不止現象的認識。但綜合來看,仍缺少風俗視角,特別是演戲酬神習俗的視角。有學者認為清代行政權威力量無法同約定俗成的民俗民風相對抗是迎神賽會難以禁止的根本原因[注]榮 真:《中國古代民間信仰研究—以三皇和城隍為中心》,北京:中國商務出版社2006年,第98頁。。該觀點啟示我們:清代禁戲屢禁不止與風俗習慣關系莫大,因為迎神賽會,一般皆要演戲。于此,本文從演戲酬神習俗著眼,考察清代演戲酬神如何能消解官方禁戲政策,以深化我們對清代禁戲屢禁不止現象的認識。
一、習俗相沿,消解禁令
演戲酬神是通過演戲的方式祈神、敬神、酬神,根據演出場地和目的一般可分為廟會戲、還愿戲、行業戲和祠堂戲四種。演戲酬神在清代一般例所不禁,要因有四:其一,演戲酬神源于先秦已成定制的賽社習俗,風俗相沿,根深蒂固,難以革除;其二,清代統治者倡導神道設教,“‘神道設教’,通行于古今中外。清史或近代史表明,滿洲列帝,對這一點格外認真。”[注]朱維錚:《重讀近代史》,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第180頁。清代官員發現百姓“多不畏官法,而畏神誅;且畏土神甚于畏廟祀之神。”所以要有意提倡,培養百姓的鬼神敬畏意識,“司土者為之擴而充之,俾知遷善改過,詎非神道設教之意乎?”[注](清)汪輝祖:《學治臆說》,見《官箴書集成》第5冊,合肥:黃山書社1997年,第28頁。其三,演戲酬神的娛樂功能符合圣人一張一馳之教,有利于社會秩序穩定;其四,演戲酬神的商業功能有利民生。從這些因素出發,清代官方對演戲酬神一般采取例所不禁的管理政策。雍正四年(1726),朝廷承認民間演戲酬神的合法性:“在民間有必不容己之情,在國法無一概禁止之理。”[注](清)蔣良驥撰,鮑思陶、西原點校:《東華錄》,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第447頁。乾隆元年,乾隆朱批否定了廣西右江總兵潘紹周請禁賽神的奏折:“民終歲勤勞無一日之樂事,豈非拂民之性哉?將此諭亦告督撫知之。”[注]哈恩忠編選:《乾隆初年整飭民風民俗史料》(上),《歷史檔案》2001年第1期。乾隆甚至批評奏請禁迎神賽會,“屬不經之談。”[注]廣西壯族自治區通志館、廣西壯族自治區圖書館:《〈清實錄〉廣西資料輯錄》(一),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3頁。在不礙農事、無妨治安、不演違禁劇目的前提下,演戲酬神“不在禁限”。[注]丁淑梅:《中國古代禁毀戲劇編年史》,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66頁。由于清代官方對演戲酬神采取寬禁政策,加上多神信仰遍及華夏、觀劇娛樂蔚然成風,清代中后期演戲酬神相比前代,愈加繁盛,因為祀神不演戲,“無以體神心而娛神志。”[注]杜海軍輯校:《廣西石刻總集輯校》(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777頁。清代中后期也是官方禁戲最頻繁的時期,令統治者始料不及的是,如火如荼的酬神演戲卻成了消解官方禁戲政策的“化骨綿掌”,從根本上抵消禁戲法令,造成禁令難以執行。措其大端,主要表現在搬演夜戲、喜演情色戲、婦女觀劇、偏好地方戲等方面。
(一)夜間酬神習俗消解夜戲禁令。清代禁演夜戲屬全國性法令,雍正十三年(1735),朝廷首次頒布夜戲禁令。乾隆二十七年、嘉慶七年、嘉慶十六年,清廷又先后重頒夜戲禁令。清代之所以禁演夜戲,要因有二:一是道德風化之憂。夜晚觀劇,男女混淆,危及男女之防的倫理道德秩序。二是社會治安之虞,“恐致生斗毆、賭博、奸竊等事。”[注]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第20頁。清代地方官把禁止夜戲作為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舉措:“不唱夜戲,地方可省無數事端,村鄰可免許多拖累。”[注]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增訂本)》,第103頁。對不實力奉行查禁夜戲的地方文武官員,《欽定吏部處分則例》規定:“罰俸一年” 。[注]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增訂本)》,第20頁。但實際執行中,夜戲禁令屢被演戲酬神者違反,尋其要因,除鄉村夜戲監管較城鎮松懈、民眾夜晚娛樂需求驅動等因素外,夜間祀神習俗與夜戲共生亦關系莫大。
清朝各地一般皆有夜間祀神傳統,夜戲亦如影隨之。元宵節一般認為源自先民歲首用火祭祀、驅邪避難的儀式,元宵習俗的基本面貌于隋代定型,唐代元宵金吾不禁成為傳統:“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注]陳伯海:《唐詩評匯》(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27頁。降至清代,元宵持續時間比明代更長,有的為15天,有的甚至達到19天。元宵節前后,夜戲盛行,相沿成俗,如乾隆三十五年《光州志》、乾隆《蓬溪縣志》、嘉慶十五年《績溪縣志》等方志的“風俗”或“時令”卷,皆有張燈演劇的記載[注]彭恒禮:《元宵演劇習俗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48頁。。清朝中后期,其俗不讓前代。紹興元宵節前后,各廟皆張燈結彩,兼有演戲敬神,“通宵達旦,熱鬧非常。”[注]《蘭亭問俗》,《申報》1898年2月12日第2版。安徽祁門元宵前后“行儺演劇。”[注]周巍峙主編;卞利、湯奪先本卷主編:《中國節日志·春節·安徽卷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4年,第174頁。南昌每屆元宵前后,賭賽燈戲,更有扮演高腳戲,卜晝卜夜,舉國若狂[注]《春燈類志》,《申報》1880年3月11日第2版。。元宵之外,各地酬神夜戲名目亦復不少,嘉定縣城每逢豐稔之年,必于二月中賽迎燈會,抬閣搬演雜劇[注]《寶燈類志》,《申報》1885年4月17日第3版。。溫州東岳廟元帥會每于三月三日夜出廟,又須十余日方能蕆事,所到之處,懸燈結彩,百戲雜陳[注]《賽會紀盛》,《申報》1882年6月2日第2版。。甚至官方還是夜戲酬神的組織者,在廣東海陽,正月有青龍廟安濟王會,迎神出巡,“大小衙門及街巷各召梨園奏樂迎神”“凡三夜,四遠云集”。[注]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第7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95頁。為俯順民意,地方官還要維護治安、保障夜戲秩序。廈門中元節各處盂蘭盆會稱為普度,每值普度,金吾不禁,道路為戲臺攔阻,全街大小戲臺至少十余處,舉國若狂,徹夜通宵。官方派遣文武委員,按段梭巡,維持治安,并不禁止[注]《秉公無私》,《申報》1893年9月11日第2版。。廈俗四月十五日為五殿閻王誕辰,各酒館飯店因每年宰殺雞鴨,深恐愆尤,每屆是日,攔街搭臺,搬演夜戲,“笙歌徹夜,裙屐如云”。[注]《鷺江談屑》,《申報》1892年5月28日第2版。廈門官方對攔街搭臺、酬神夜戲的許可,是法令對人情習俗的屈從。一旦夜戲酬神成為向例,官方禁止,則會遭到地方力量的抵制,禁令遂成具文。寧波城內,每于九月迎賽大廟菩薩,并循例搬演夜戲。1878年,寧波知府諭令只許迎神,不許夜演,當菩薩駕駐醋務橋行宮時,年例該處于九月十三、十四兩日夜演。該處某巨紳并不赴府署商請,公然違令,于十三日當街搭臺,雇班夜演,觀者塞途。觀望者聞之,十四日夜紛紛開臺,城中夜戲竟達十余處[注]《違禁夜演》,《申報》1878年10月15日第2版。。“某巨紳”之所以敢公然違抗夜戲禁令,除了自恃其勢力外,顯然還有夜間酬神習俗的憑借,紛紛開臺,則法難責眾矣。1888年九月,寧波城內夜晚舁神出巡、搬演夜戲的習俗仍在循例舉辦[注]《甬上近聞》,《申報》1888年10月28日第2版。。演戲酬神之所以能突破夜戲禁令,民眾夜間娛樂欲求雖說是違禁的動力之源,但夜間循例酬神才是合理借口。官方若不能革除夜間祀神習俗,則禁止夜戲不亦難哉!
(二)酬神演戲兼具的娛神娛人習俗消解情色戲禁令。情色戲屬于所謂的淫戲。從一些禁令、日記、報刊、小說提及的演戲酬神劇目中,可知一批違禁的所謂淫戲在酬神劇場上盛演不息,如《賣胭脂》《殺子報》《翠屏山》《珍珠衫》等[注]《演戲酬神》,《申報》1896年3月26日第3版。《戲場肇禍》,《申報》1895年8月14日第9版。《古潞雜言》,《申報》1897年6月23日第2版。《潞河錦纜》,《申報》1897年5月13日第2版。《戲場肇事》,《申報》1898年10月31日附張。,它們基本屬于包含情色關目的愛情劇,甚至神廟劇場,生旦“相摟相抱,陽物對著陰戶,如雞食碎米,杵臼搗蒜一般”,[注]齊文斌主編:《明清艷情禁毀小說精粹》卷3《妖狐艷史》,延吉:延邊出版社2000年,第181頁。當眾宣淫。但這僅是冰山一角,酬神劇場還上演許多今天已不知名目的葷戲和淫穢關目。清代道德之士指責酬神劇場“淫戲”風行:“聞各處演戲敬神者,靡不點粗俗淫蕩各劇。”[注]《論酬神宜禁淫戲》,《申報》1892年12月4日第1版。并痛心疾首地呼吁不要“點淫戲敬神明。”[注]鴛湖知非氏:《淫戲為害》,《申報》1879年6月25日第3版。此類指責雖不乏偏見,但許多也確屬實情。
撇開情色劇目和淫穢關目娛樂性強、戲班和伶人迎合觀眾趣味不談,搬演情色乃至淫穢關目還是先秦祀神娛神和婚戀禮俗的遺存,源遠流長。先秦社祭除土地崇拜外,在交感巫術的啟示下,還融入了生殖崇拜,先民認為社祭時男女交媾可以促進風調雨順、土地增產。社祭中有神附體的尸,《左傳·莊公二十三年》記載魯莊公不聽曹劌勸諫,到齊國觀看社祭,其實是想觀看尸女表演,“所謂‘尸女’,即女人呈裸體,獻身生殖神,可與任何人進行性交祭祀。”[注]陳炎主編:《中國風尚史·先秦卷》,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15年,第280頁。尸女獻身于神,既是生殖崇拜,也是娛神方式。原始巫術認為神與人一樣有癖好,有情欲,祭神要投其所好,當然需要以色相媚神娛神。春社之日是男女奔者不禁之時,燕、齊、宋、楚等國神社祭祀時,“男女之所屬而觀”。[注](清)畢沅校注,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6頁。所謂“屬而觀”,就是男女青年集在一起觀看性交表演,然后分散擇偶野合[注]宋公文、張君:《楚國風俗志》,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62-263頁。。伴隨倫理道德觀念漸漸加強,此類性表演在秦漢以后的社祭中慢慢淡去,但從未消失,在部分地區的演戲酬神中仍屬保留節目,即神愛看戲,且喜看葷戲。山西上黨奶奶廟的喜神不僅愛看戲,而且要看葷戲,即表現男女調情故事的喜劇,如《鬧五更》《秀才聽房》之類的劇目[注]劉文峰:《志文齋劇學考論》,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4年,第208頁。。神廟在搬演葷戲時,要提前清場,不讓婦女和兒童觀看,因為這些葷戲多私媾之事,婦女兒童不宜觀看[注]曹飛:《敬畏和喧鬧:神廟劇場及其演劇研究》,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1年,第140頁。。潞城縣賈村碧霞宮(俗稱奶奶廟)演劇的習俗是先在廟內戲臺開演約一個小時的隊戲,然后廟外戲臺的大戲才能開演。隊戲表演中總要加入一些內容粗俗、表現男女性愛的葷戲,“一般不準婦女、小孩觀看。”[注]段友文:《黃河中下游家族村落民俗與社會現代化》,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503頁。湖南沅澧地區在求子、上鎖、婚喪壽慶、禳災祛疾、祈蠶等的儀式中,都要搬演情色內容的葷戲,以便向儺神祈求[注]王蔭槐:《嘉山孟姜女傳說研究》(下卷),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01頁。。諸如此類說明,演戲酬神中兩情相悅乃至猥褻鄙俗的表演習俗淵源有自,它是上古祭祀以色娛神和生殖崇拜風俗的遺存,“當戲劇脫離祭祀儀式,走出神廟時,插科打渾、猥褻俚俗的一面依舊保留不變……葷穢表演仍然比比皆是。”[注]白秀芹:《迎神賽社與民間演劇》,中國藝術研究院2004年博士論文,第34頁。貌似莊嚴的酬神劇場,并不排斥情色表演,甚至色情表演還是必備節目。今天看來,清代酬神劇場流行的“淫戲”,一類屬于愛情戲,可以通融;一類則是低俗淫穢的葷戲,盡管有上古遺風,但大庭廣眾,公開搬演,的確誨淫。官方和道德之士指責演戲酬神“所演之戲,半多淫靡”[注]《云間雁信》,《申報》1890年9月8日第2版。,不無道理。
(三)全民參與酬神習俗消解禁止婦女觀劇禁令。清代禁止婦女看戲的禁令、行動、族規、閨訓和社會輿論紛紜:“清代禁毀戲劇觀演活動,有一個突出的方面,就是對婦女觀劇的禁阻。不但家訓閨箴、女德女教中充斥著婦女勿看戲的言論,官方文告、朝廷諭旨也屢屢禁止女性觀眾出入戲場。”[注]丁淑梅:《中國古代禁毀戲劇編年史》,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520頁。北京、蘇州、杭州等城鎮戲園直至清末仍禁賣女座,上海租界戲園售賣女座還曾引發過激烈爭論。但有清一代,婦女出入酬神劇場風氣之興盛,遠邁前朝。清初王應奎見到的江南曠野演戲酬神“觀者方數十里,男女雜沓而至”,“約而計之,殆不下數千人焉”。[注](清)王應奎:《柳南文鈔》卷四《戲場記》,轉引自陸萼庭《昆劇演出史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1頁。這種情形在清中后期愈發不可收拾,戲曲繁盛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南方省份姑且不論,以京畿地區為例。京畿風氣素稱良謹,演戲酬神時,婦女觀眾如癡如狂。1891年3月,通州東海子街演戲祀神 ,“婦女觀劇,另有看臺,粉白黛綠咸得列坐其中,大家閨秀則障以蝦須簾,花枝隱現。”[注]《潞河鯉信》,《申報》1891年3月23日第2版。1893年3月28日,通州北街恭祀水火二神,雇京都義順和班演戲四日,“檀板甫敲,簪裾紛至,看臺三百余間,尚不能容。”[注]《潞水春鱗》,《申報》1893年4月11日第2版。可以說,從北到南,由城鎮到鄉村,在堅持男女分區的前提下,清代婦女可以自由出入酬神劇場。孕婦不宜看戲聽曲的禁忌也被一些婦女拋之腦后,如腹大如瓠、即將臨盆的婦女,也彳亍觀劇[注]《平山堂茗話》,《申報》1893年7月27日第2版。。更甚者,竟有觀劇婦女于劇場產子[注]《戲場產子》,《申報》1874年1月27日第3張。。如此風氣說明:演戲酬神,婦女往觀,乃清代婦女休閑生活之常態。
婦女參與全民酬神傳統悠久,相沿成俗。上古社祭家家參與,人人踴躍,一國之人皆若狂,婦女概莫能外。春秋戰國時期,燕、齊、宋、楚等國神社,每屆社祭,都活躍著女性身影:“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注](清)畢沅校注,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6頁。社祭從一開始就沒有排斥女性。其俗代沿,當社祭成為民俗節日之后,婦女還能偷得一日閑,外出游樂,唐代婦女每逢社祭:“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樹下行。”[注](唐)張籍:《張籍詩集》,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第78頁。直到晚清,全民迎神賽會的傳統仍盛行不輟,如1889年四月初八日,天津府縣牒請城隍厲壇赦孤,神鬼出巡,“道上游人如蟻,大家閨秀,則靚妝艷服,掩映于湘竹簾前,而小家碧玉,則露面拋頭,幾于在坑滿坑,在谷滿谷。”[注]《鬼會》,《申報》1889年5月21日附張。迎神賽會,傾城婦女外出游觀,沿襲的正是傳統習俗。
一般認為,迎神賽社興起于宋代,作為集體狂歡活動,婦女不但參與其中,而且還可出入賽社劇場,劉克莊《聞祥應廟優戲甚盛》二首之一云:“游女歸來尋墜珥,鄰翁看罷感牽絲。”[注](宋)劉克莊:《后村先生大全集》卷21,清抄本。《即事》三首之一云:“抽簪脫褲滿城忙,大半人多在戲場。”[注](宋)劉克莊:《后村先生大全集》卷21,清抄本。明代開始,禮教對婦女的禁錮趨于嚴格,盡管有等文人呼吁禁止婦女看戲,但官方禁止婦女看戲的法令并不多見,明代婦女看戲所受阻力相對較小,如杭州春臺戲“士女縱觀,闐塞市街。”[注](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年,第366頁。蘇州春臺戲,“士女傾城往觀,歲以為常。”[注](清)褚人獲輯撰:《堅瓠秘集》,見《清代筆記小說大觀》(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945頁。入清以后,演戲酬神,婦女往觀,從未間斷,并隨著頻繁的演戲酬神而觀劇機會更勝前朝。婦女往觀演戲酬神,一般能得到官方或家人的許可。清代北京、蘇州、杭州等城鎮的戲園,皆禁售女座。但這些地方,婦女偏可以觀看廟社演戲,如“杭垣戲園禁婦女看戲,惟廟社演劇,則不在禁例,而婦女之伴綠攜紅,約群同往者,固不特小家碧玉,巨室青衣等而已也。”[注]《婦女觀劇受辱》,《申報》1874年12月17日第3版。說明杭州地區大家閨秀、小家碧玉皆可觀看廟會戲。1890年秋,黃梅知縣先期出示,嚴禁婦女看會,以免滋生事端,會期已過,方準婦女入廟觀劇,“連日鬢影衣香,粉白黛綠,呼姨挈妹,絡繹于途。”[注]《柴桑秋色》,《申報》1890年10月16日第2版。清代官員對婦女出入酬神劇場的允許,是對千百年來全民參與賽會習俗的遵行。
(四)演戲酬神偏好地方戲消解了地方戲禁令。清代中期開始,伴隨地方戲的興起,出現花雅之爭,官方和正統文人從堅持雅正文化政策的立場出發,對地方戲實行查禁抑制的管理政策,“直到清代后期的同光年間,執政者始終嚴格查禁花部亂彈、地方戲等,查禁灘簧、花鼓戲、評彈的禁令屢屢頒行。”[注]趙維國:《教化與懲戒:中國古代戲曲小說禁毀問題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1頁。寧波串客、髦兒戲、花鼓戲、采茶戲、蹦蹦戲、東鄉調、灘簧、香火戲、黃梅調、七子班等地方戲既被官方頻繁查禁,也被道德之士口誅筆伐。令官方和道德之士意想不到的是,由于酬神劇場是地方戲觀演的重要場所,例所不禁的演戲酬神反而為花鼓、采茶等地方戲提供了大量演出機會。如官方查禁的采茶戲,南昌、新建等縣屬各鄉,“借口春賽秋報,或遇神誕,”雇演采茶戲[注]《移風易俗》,《申報》1899年5月12日附張。。嘉道以來,福建官方嚴禁七子班,但在廈門等地演戲酬神的競爭中,雇七子班相對便宜,“其無力雇官音大班者,則雇傀儡戲及本地七子班以代之。”[注]《鷺島紀聞》,《申報》1887年5月23日第3版。七子班也從未缺席泉漳地區的演戲酬神活動。花鼓戲是清代中后期官方查禁次數最多、查禁地區最廣的地方戲,也是愈禁愈演。湖北楚北、武漢各鄉間如值歲收稔豐,農民每于上元節斂錢玩燈、演唱花鼓,謂可保一方平安,“此風由來久矣。”[注]《禁演淫戲》,《申報》1882年3月21日第2版。江蘇華亭縣鄉村春間迎神賽會搬演花鼓戲的傳統始則于乾隆年間,光緒初年,仍盛演不衰[注]《(光緒)重修華亭縣志》卷二十三《雜志》,光緒四年刊本。。花鼓戲等地方戲既有參與酬神的傳統,又能諧于里耳,且戲價更廉,場地要求不高,“小班價廉,鄉間易演。”[注]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頁。在官方禁阻和輿論的打壓聲中,酬神演戲為地方戲提供了大量堂而皇之的演出機會。
酬神演戲偏好地方戲根源于酬神賽會的鄉土情結和傳統。演戲酬神的表演人員來源,不外三種:一是外聘戲班,二是本地土班;三是民眾自演自娛的扮演。不論哪一種來源,都面臨一個“諧于耳”即民眾聽得懂的檢驗。并且既曰演戲酬神,不僅要諧于民眾之耳,而且要諧于神之耳,“凡神依人而行,人之所不欣暢者,神聽亦未必其平和也。”[注](清)江永:《律呂新論》,吳釗等編:《中國古代樂論選輯 》,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1年,第388頁。所以演戲酬神要盡量入鄉隨俗、采用地方民眾皆能聽懂的土音,而這正是地方戲之優長。又者,漢代以來,民間迎神賽社中社火表演傳統從未間斷,與社火關系密切的采茶、花鼓、秧歌等地方戲,自然而然融入到迎賽隊伍之中,成為迎賽習俗,或用“小童扮演地戲,雜入會中”[注]《楊王廟會》,《申報》1876年3月14日第2版。,或花鼓、秧歌等競相出會[注]《都門紀事》,《申報》1885年7月25日第2版。,或唱灘簧、演傀儡相互比賽[注]《蕪湖瑣綴》,《申報》1886年8月26日第1版。,或敲鑼前導、演唱花鼓[注]《袁江尺素》,《申報》1885年4月20日第2版。。迎神賽會有扮演地方戲傳統,觀眾甚至神靈有地方戲偏好。于是,被官方查禁和輿論抨擊的地方戲紛紛在演戲酬神的劇場上搬演。迎神賽社不僅是地方戲滋生、成長的溫床,而且還是地方戲遭遇禁阻時的護身符。
二、利益裹挾,對抗禁令
酬神演戲對清代禁戲政策的消解,不僅表現在習俗和法律的沖突上,還表現在觀演者、組織者乃至監管者的多種利益訴求與禁戲政策的抗衡上。在這些利益訴求的驅動下,例所不禁成為違禁觀演的幌子,“有司官差役往查,輒托名酬神愿戲,或又稱春祈秋報,農民例申虔福。”[注]《違制演戲》,《新報》1881年6月14日第2版。法難責眾,禁管困難。
其一,全民藉演戲酬神的娛樂需求對抗禁令。清代從官方到民間,從封疆大吏到里巷細民,從行業會首到廟祝觀主,無不借故演戲酬神、享受觀劇之樂。每逢官方認可的神誕乃至祈雨禳災,演戲酬神,官員親自參加,奉行如常[注]《演戲酬神》,《申報》1880年10月28日第2版。。官員升遷、軍隊檢閱,也多演戲酬神之舉[注]《演劇酬神》,《申報》1886年11月17日第3版;《茸城雁帛》,《申報》1886年11月9日第2版。。民間廟會戲、行業戲、祠堂戲、祈雨戲等一般按村社行業,攤派戲資,全民參與、藉酬神以滿足娛樂之需。攤派遵循一定標準,乾隆四十五年樊先瀛《保泰條目疏》提到,山西鄉村戲會,按地畝人丁牲畜攤派戲資,“由來已久。”[注]丁淑梅:《中國古代禁毀戲劇編年史》,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12頁。蕪湖中江一帶漁戶每屆仲夏醵資演戲、以邀神貺,所費是按照春末夏初所捕鰻魚的尾數抽厘[注]《漁家樂》,《申報》1894年7月15日第3版。。清末民初河南懷慶府地方演戲酬神,敬火神按房屋多寡攤派;敬關帝、財神由店鋪捐資;敬土地、龍王按地畝多少分攤;敬老君、祖師由工匠出資;奶奶會按兒女多少或向求兒求女者征收;牛王會由各飼牛戶分擔;馬王會則為“馬出錢、牛管飯”。其他逢節日演戲均按地畝、人口分擔[注]王建設:《從豫西北遺存古戲樓看清末民初懷慶府地區戲曲活動》,《戲曲研究》2012年第3期。。分攤戲資是民眾融入村社集體或行業組織,享受權利和履行義務的重要途徑。晚清不少教案的導火索即是由教民不愿攤派戲資而引燃,說明試圖與全民性演戲酬神對抗的后果往往是極其嚴重的。[注]需要注意的是,戲資一般并非單獨收取,在農村,戲資往往和看青支更、演戲酬神、修理廟工、村莊團練等費用一起收取,如果個人不繳納這些費用,屬自絕于村落族群之舉。。酬神劇場,舉國若狂,清初但凡某處演戲酬神,“哄動遠近男婦,群聚往觀,舉國如狂”,[注](清)陳宏謀輯:《五種遺規》,北京:線裝書局2015年,第252頁。清代中后期酬神觀劇更加興盛,“遠近來觀、萬人空巷”[注]《上海巡局瑣案》,《申報》1892年4月19日第3版。“男女老幼、人海人山”[注]《平湖秋月》,《申報》1893年8月19日第3版。面對這種狂熱的觀劇享樂場面,禁阻無異于焚琴煮鶴、大煞風景,殊招人怨。
其二,集體性演戲酬神的組織者眾多,各懷利益以對抗禁令。集體性演戲酬神組織者主要有士紳、地保、差役、會首、執事、廟祝、棍徒、班主、商販等,藉演戲獲利者不乏其人。據目的之不同,可將他們分為三類:一是清正廉明的組織者。演戲酬神是基層社會或行業生活中的公益盛事,一次成功的演戲酬神活動,既可展示族群、村落或行業的凝聚力,也可彰顯組織者的領導魄力,進而提高組織者在基層社會的威信和聲譽。為了贏得和保持良好威望,他們會認真循例組織好每一次演戲酬神。二是從中斂錢的組織者。演戲酬神的費用或按戶醵資,或從族群、村落和行業公款中撥設專款,組織者則可乘機從演戲酬神費用中斂錢肥己,“科斂民財,半充囊橐。”[注]《禁搭臺演戲告示》,《中國古代禁毀戲劇編年史》,第334頁。他們會積極張羅、奔走前后,甚至對不愿醵資者,“逞兇嚇唬。”[注]《廣東海康縣北和圩碑禁戲文》,《中國古代禁毀戲劇編年史》,第498頁。藉廟觀演戲酬神、增加香火錢的廟祝觀主也可歸于此類,他們會因演戲酬神之際大獲香資而歡喜無量[注]《帝京雜記》,《申報》1886年5月4日第2版。,鼓動附和。三是開場聚賭的組織者。清代賭風極盛,“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編氓徒隸,以及繡房閨閣之人,莫不好賭。”[注](清)錢泳:《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578頁。演戲可以招集多人,聚賭抽頭,“欲圖聚賭,必先謀演戲。”[注]來蝶軒主:《請弛青浦縣屬朱家角鎮戲禁意見書》,《申報》1911年6月25日第3張第1版。于是,棍徒“借各廟神誕為名,妄稱酬應演戲,因而大開賭場。”[注]《道札嚴禁演戲賭博》,《申報》1906年10月16日第17版。賭棍人等也是演戲酬神的積極組織者。當然,這三類組織者并非判然區分,現實中,組織者為斂錢、為聲譽、為聚賭的目的往往兼而有之,他們或為地方實力派、或本就是不安分之徒,一旦遇禁,常會鼓動觀眾,與禁阻者為難。因人多勢眾,官府往往只得折中妥協、息事寧人[注]《眾怒難犯》,《申報》1878年6月1日第2版;《穗垣瑣事》,《申報》1884年9月13日第3版。。
其三,禁戲的監管者常藉酬神演戲牟取私利,知法犯法。清代基層社會禁戲的監管者主要是紳士、差役、地保等,他們藉演戲酬神謀取私利屬普遍現象:有的紳士和縣差營役得規包庇,致使府縣對違禁演戲毫無聞見[注]《高安賭風甚熾》,《新聞報》1907年7月19日第4版。;有的府縣差役向諸班主收取規例,預為關照[注]《演戲紀始》,《申報》1882年3月11日第2版。;有的州縣衙門差役常持十禁牌下鄉開展禁戲等事,實則藉以斂錢,地保也從中勒索[注]《地保勒索》,《新聞報》1897年9月17日第9版。。在清代禁戲告示和輿論中,對紳士徇隱、差役包庇、地保容隱之類的警告和指責不勝枚舉,組織者、觀演者和監管者串通姑縱、中飽隱瞞,“比比皆然也。”[注]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16頁。說明從官府到民間對此現象皆心知肚明,只是力有不及而已。監管的乏力和故縱,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演戲酬神成為違反官方禁戲政策的溫床,禁者自禁、演者自演。
由于集體性演戲酬神一般多或少地裹挾著娛樂、酬神、聲望、斂錢、陋規、賭錢、商業等多種利益訴求,一旦開演,任何禁阻都可能致干眾怒,清代中后期,禁戲活動中經常發生毆差抗官的群體事件,原因即在于此。1895年秋,袁州游橋地方藉賽會演戲聚賭,差役得賄包庇,袁州知府惠格只得親自帶領親兵數人往禁,賭徒恃眾拒捕,觀眾一呼百應,將親兵毆成重傷,惠格頭額也被擊破、血流如注[注]《太守被毆》,《申報》1895年11月5日第2版。。清人認為春祈秋報、村社演戲賽會之事,有管理之責的地方官最害怕“逆民志而啟爭端。”[注]《論南昌大儺》,《申報》1879年7月9日第1版。可謂一語中的。當演戲酬神成為民眾堂而皇之的習俗和多種利益訴求的集合體之后,官方禁戲法令就會被消解乃至公然違反,“鄉村信神,咸矯誣其說,謂不以戲為禱,則居民難免疾病,商賈難免風濤,是以莫能禁之。”[注](清)湯來賀:《內省齋文集》卷七,清康熙刻本。官方和道德之士只能徒喚奈何。
結語
演戲酬神對禁戲政策的消解不盡上述,還包括女伶演劇、男女合演等禁令的違禁,特別是活躍在酬神劇場上的民間小戲,在劇種、劇目、女伶登臺、男女合演等方面,較全面地挑戰官方禁令:“春秋佳日,鄉間報賽,演戲酬神,所演淫戲,亦時有之,甚至有一男一女,扮演花鼓淫戲,萬人空巷,舉國若狂。”[注]《論淫戲之禁宜嚴于淫書》,《申報》1896年9月15日第1版。違禁的花鼓戲在酬神劇場搬演,女伶登場,甚至男女合演。當然,演戲酬神也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向禁戲法令的遵從,如酬神劇場嚴格男女分區觀劇、一些地方立碑禁演夜戲或花鼓戲[注]徐宏圖:《浙江戲曲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年,第238頁;周立志編著:《史說益陽》,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94頁。、組織者承諾不演戲聚賭和扮演淫戲[注]來蝶軒主:《請弛禁青浦縣屬朱家角鎮戲禁意見書》,《申報》1911年6月25日第35版。等,但筆者認為相比演戲酬神對禁戲政策的消解而言,此等舉措收效甚微。有研究者認為,古代迎神賽會具有強烈的狂歡精神,表現出反規范性,對傳統規范“具有一種潛在的顛覆性和破壞性。”[注]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北京:生活·新知·讀書三聯書店2002年,第134頁。此有以之言。本文探討可見,作為迎神賽會衍生節目的演戲酬神亦具有反規范性,主要表現為對官方禁戲政策的違反。更關鍵的是,地無論東西南北,人無論男女老少,一年之中,酬神觀劇競繁,成為戲曲觀演常態,組織者、觀演者和監管者的酬神、娛樂、斂錢、聚賭、陋規等諸多利益訴求又裹挾其中,法難責眾。各地酬神演戲“殆無虛日”“無日無之”[注]清人常用“殆無虛日”“無日無之”來形容各地演戲酬神之頻繁,如:“浦郡自二月以來,城鄉村鎮演戲祀神者殆無虛日。”(《古潞近聞》,《申報》1887年5月22日第11版)“杭垣各社廟臺戲無日無之。”(《臺戲弛禁》,《申報》1878年6月6日第2版)地搬演,意味著官方禁戲政策也被常態化地違反,國家法令的強制性、規范性、普遍性被撕裂的千瘡百孔,相關禁戲法令焉能樹立權威、認真執行?
演戲酬神對清代禁戲政策的消解,本質上是習俗與法律之間的矛盾。習俗是法律的基礎,在社會秩序的維護上可以對法律起到輔助作用。習俗一旦形成,就融入人們的意識和行為之中,歷久相傳,具有牢固性,法律很難滲入習俗的內部、規范習俗。習俗對社會成員具強烈的行為制約作用,具有剛性,在法律實施中突顯阻礙作用,特別是當習俗成為慣例后,就會“以不同意的方式來對抗偏差。”[注][德]韋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顧忠華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5頁。如果立法沒有考慮到習俗的牢固性和剛性,當法律與習俗發生沖突時,民眾會自覺不自覺地選擇習俗,由此導致執法成本提升乃至法律根本無法執行。以今日的后見之明看,清代官方對演戲酬神一般采取例所不禁的管理政策,是對習俗的尊重,卻沒有顧及到演戲酬神本身與搬演夜戲、喜演情色戲、婦女觀劇、偏好地方戲等習俗同生共長、難以剝離,而這些習俗與官方相關禁令又是矛盾抵牾的,由是造成習俗對抗禁令,加上打著例所不禁幌子的多種利益博弈其中,更增加了禁令的執行難度。清代演戲酬神對禁戲法令的消解也啟示我們,法治滲入習俗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立法和執法應充分考慮到習俗的剛性,既要看到習俗與法治存在轉化互補之處,也要看到二者相互沖突的地方,實現法治與習俗的良性互動。國家法治如此,文藝管理的立法與執法亦該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