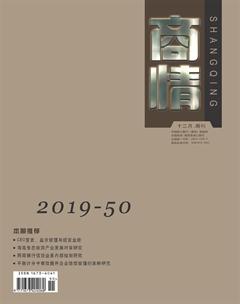中國金融創新結構內部形式的動態關系研究
林文浩 王璟怡 王學龍 李自磊



【摘要】本文通過構建結構VAR模型對中國金融創新結構內部6種創新形式之間的動態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金融制度創新對于機構、市場、工具、技術和管理等創新形式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管理創新對制度創新有促進作用。其理論機制在于:市場導向的制度創新,促進高效率的工具、機構和市場創新;交易效率的提升,加快分工細化,帶動技術創新;金融創新可能引發金融風險和管理失效,因此需要管理創新,而管理創新又為制度創新創造條件。本文的政策含義是,堅持市場導向,深化金融制度創新,加強市場約束機制;堅持功能導向的金融創新,促進金融業回歸本源。優化金融創新結構,加強金融管理供給,維護金融創新和金融管理的結構平衡。
【關鍵詞】金融創新結構 金融創新結構指數 創新形式的動態關系
一、引言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出現了大規模的金融創新。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歷了多個階段的金融創新形式相互促進,持續涌現。201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堅持“回歸本源、優化結構、強化監管、市場導向”的四個原則。這表明在研究中國金融創新時,不能僅僅關注創新的數量,還要重視創新的結構,因為創新結構與金融效率、金融結構和金融穩定具有密切聯系(李健,2004)。為深化對于中國金融創新結構的認識,本文將建立一個結構VAR模型,實證分析金融創新結構內部形式之間的動態關系。
根據金融體系構成要素,本文認為金融創新包含6種創新形式:(1)制度創新,反映中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金融制度改革;(2)機構創新,反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設立或引進的各類新型金融機構;(3)市場創新,反映中國設立或引進的新類型或新層次的金融市場;(4)工具創新,反映中國設立或引進的新型金融工具;(5)技術創新,反映中國金融與科技融合的創新,例如互聯網金融的出現等;(6)管理創新,反映中國金融調控、金融監管、金融經營管理方面的創新。根據屬性不同,將金融創新分為原始創新和擴散創新。
本文以中國金融創新結構指數,描述6種金融創新形式的動態變化。該指數是從結構視角出發,分類匯總1979年-2015年中國金融創新事件之后,綜合運用“事件研究法、綜合評價法和加權算術平均指數法”計算獲得的(李健,林文浩,2017)。由于該指數是基于事件研究法編制的,它可以厘清各種創新形式的邊界,直接度量每種金融創新形式的變化,改變了現有文獻通常以金融總量數據(如私人部門貸款規模/GDP的變化等)間接代理金融創新變量的方式,為研究金融創新結構內部形式的動態關系創造了條件。
本文的啟示是,市場導向的制度創新,促進了效率導向的工具和機構創新;新型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的發展,帶動了有組織的金融市場的形成;同時,制度創新提高了交易效率,促進了專業分工,加快了技術創新。最后,制度創新可能放大金融風險,或使原有金融管理失效,因此需要開展與各種創新形式相適應的管理創新,而管理創新將為制度創新的深化提供條件。基于結構VAR模型的實證結果支持理論分析的主要觀點。
二、文獻綜述
金融創新是指金融領域內部通過各種要素的重新組合和創造性變革所創造或引進的新事物(李健,1998)。約束引致假說(Silber,1983)、監管辯證法(Kane,1978,1981)、交易成本理論(Hicks,1975;Niehans,1981)、技術進步論(Merton,1995)以及制度經濟學的金融成本理論從不同視角解釋了金融創新的動因。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利用不完全市場和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與產業經濟中的創新理論解釋金融創新與擴散(Pesendorfer,1995)。
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開始關注影響金融創新動態過程的因素。Ben-Horim and Silber(1977)和Sametz(1987)研究金融創新動態過程的決定因素。Silber(1983)、Cross(1986)主張對金融工具、市場及技術等創新形式的成因進行分類或建模, Finnerty(1988)歸納了推動金融工具創新的10類因素。Abiad and Mody(2005)研究了影響金融制度創新動態過程的主要因素。
關于金融創新對經濟的影響,Silber(1983)、Miller(1986)、Van Horne(1985)、Ross(1989)認為金融創新將使市場更有效率或更完全。Allen and Carletti(2006)、Acharya and Naqvi(2012)、Bolton et al.(2012)、Henderson and Pearson(2010)認為金融創新可能放大金融風險,增大金融脆弱性。Dan Awrey(2013)認為需從供給側出發完善金融創新理論,促進金融創新和金融管理的結構平衡。
改革開放后,李健(1998)、吳敬璉(2002)、周小川(2015)等研究了中國金融改革創新的歷程和影響。王廣謙(2002)指出中國金融改革創新過程中需要關注金融結構問題。王仁祥、楊曼(2015)測算金融創新質量指數,并基于國際比較得出中國金融創新過程中的結構性問題。李健、林文浩(2017)編制中國金融創新的結構指數,實證分析影響金融創新結構動態變化的因素。
現有文獻表明,很少有學者從結構視角入手研究金融創新結構內部形式的動態關系。為此,本文將運用結構VAR方法,分析金融創新形式之間的動態關系,深化對于金融創新結構的認識。
三、金融創新結構內部形式的動態變化
為了更精確地反映金融創新結構內部形式的動態變化,本文首先按照金融創新事件發生時間,將李健、林文浩(2017)中國金融創新事件庫中每年的創新事件分解到各個季度,使金融創新形式的年度序列變為季度序列。然后按照金融創新結構指數的編制方法,獲得6個新的金融創新結構子指數,以反映金融創新結構內部形式的長期和短期變化。
(一)金融創新形式的長期趨勢
從金融創新內部結構的累計變化看,機構、市場、工具、制度、管理和技術等6種創新形式對金融創新結構變化的累計貢獻呈現“持續上漲、交替領先、呈現分化”的特征。分階段看,1979年-1993年,6種創新形式相對比重震蕩調整,趨勢不明;1994年-2004年,機構、市場和工具創新占比下降,制度、管理和技術創新占比上升;2005年-2015年,6種創新形式相對比重呈現穩定。截止2015年末,機構、市場和制度創新占比都在24%左右,管理、工具占比都在11%左右,技術創新占比在6%左右。
(二)金融創新形式的季度變化
從金融創新內部結構的季度變化看,6種創新形式的季度變化特征不同。首先,機構、工具、制度和管理創新以連續的小幅創新為主;市場創新、技術創新以離散的大幅創新為主。然后,在1979年-2015年的148個季度中,制度創新在多達48個季度中是季度變化值最大的創新形式,高于其他創新形式,這可能揭示出制度創新對其他創新形式的重要影響。最后,6種創新形式季度變化的周期波動,有時重疊,有時繼起,為探索各種創新形式的動態關系提供了啟示(見表1)。
四、金融創新形式之間的影響機制分析
在描述了金融創新形式的動態變化特征后,本文將分析每種金融創新形式對其他創新形式的影響機制。
(一)金融制度創新
金融制度創新過程塑造著一國的金融創新結構。Abiad and Mody(2005)認為金融體系高度壓抑的國家傾向于保持現狀,但經過初始的制度創新后,進一步創新的傾向加大。相對于其他創新形式,制度創新將提供一種框架性的激勵或約束。一方面,制度創新為其他創新形式的出現提供制度空間;另一方面,一些與現行金融制度沖突的金融創新將受到約束。
改革開放后,我國實施了漸進式的金融體制改革,逐步打破“大一統”的計劃金融體系。伴隨金融法律法規的推陳出新,新制度的激勵和舊制度的約束引發了大量金融創新。未來,伴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金融體制不斷完善,制度創新的主導性將逐步減弱,市場內生的創新形式的重要性將逐步增強。
(二)金融工具創新
新的金融工具之所以能夠替代或補充原有的金融工具是因為它能更有效地完成金融業務,或者成本較低,或者既好又便宜。Finnerty(1988)認為法律或規章的變動、稅收不對稱、交易費用減少、代理成本減少、風險再分擔或降低某種風險、利率水平及波動、價格和匯率水平及波動、學術研究、會計利益、技術進步等10類因素引發了金融工具創新。
中國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內生出種類繁多的金融需求,各類金融機構不斷創新金融工具,拓寬金融業務,滿足社會日益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多類型、多層次的金融市場為新型金融工具的發行流通提供了交易平臺。微電子技術的應用為金融工具創新和擴散提供了技術支持。此外,金融工具創新也離不開與之相適應的金融管理創新。因此,金融工具創新與其他創新形式具有密切聯系。
(三)金融機構創新
金融機構創新通常伴隨著體制改革、業務更新、市場開拓以及管理和技術的創新。新型金融工具(業務)直接催生了新型金融機構。中國金融創新的歷程反映了機構創新與其他創新形式的聯系。以中國原四大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造為例,在創新國有控股和外資股、企業股、個人股混合所有制的銀行治理結構的同時,四家大型銀行在全球開拓市場,開展經營管理創新和業務工具創新,廣泛使用新技術,利用十幾年時間就躋身全球前五強,見證了多種創新形式組合的力量。
(四)金融市場創新
金融市場創新既與金融工具、機構和技術創新聯系緊密,又與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息息相關。從中國經驗看,市場創新首先是金融體制改革的產物。改革開放以來,金融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形成了多類型、多層次的市場體系。得益于市場創新,新工具有了交易場所,新機構有了業務機會,新技術有了應用領域,新管理有了實施對象。盡管目前國內金融市場仍然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但不能否認市場創新所取得的突出成就,這也表明需要進一步推動制度、管理和技術創新,來促進金融市場的持續發展。
(五)金融管理創新
金融管理創新涵蓋金融監管、金融調控和金融經營管理領域的創新。Dan Awrey(2013)認為金融創新的需求側理論過分地強調金融創新對市場的完善,建議從供給側出發完善金融創新理論,促進金融創新和金融管理的結構平衡。
從中國金融創新的經驗看,伴隨社會主義金融體制逐步完善,以及機構、市場、工具、技術等創新形式的發展,管理創新的重要性也隨之提升。處理好創新、風險和管理的關系,實現好管理創新與其他創新形式的結構平衡,將使金融業遠離“一放就亂、一控就死”的情況,實現金融創新平穩有序地進行。
(六)金融技術創新
不同于制度創新在金融創新過程早期階段的重要影響,技術創新在金融創新的整個過程中都很重要,它可以使其他創新形式更容易產生,這一點符合“技術能夠讓人們更好地做事”的本質功能。從國際經驗看,自1965年以來,以微電子和計算機為基礎的信息技術革命對金融業產生了深刻影響。其中,證券業變化最大,銀行業也受到較大影響,保險業變化較小(Sametz,1987)。
從國內情況看,技術創新與其他創新形式關系緊密。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伴隨金融制度創新不斷推進,金融交易效率日益提高,金融業分工愈加細化,使金融技術創新突飛猛進。另一方面,技術創新通過金融與科技的融合,倒逼金融機構、市場和工具創新,并對管理創新提出新的要求。同時,技術創新還有益于培育創新進取、開放包容的市場環境,為深化金融制度創新創造條件。
五、金融創新形式動態關系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選取和數據說明
1.結構VAR模型
Sims(1980)建立了VAR模型,但簡化式VAR的脈沖響應函數并不唯一,而且簡化式VAR無法揭示經濟結構(即變量之間沒有當期影響)。Sims(1981,1986),Bernanke(1986),Shapiro and Watson(1988),Blanchard and Quah(1989)將經濟結構重新納入VAR模型中,允許變量之間存在當期影響,形成結構VAR(以下簡稱SVAR)方法。本文選取SVAR方法分析金融創新結構內部形式的動態關系。
2.變量選取
理論分析闡明了6種金融創新形式之間的影響機制(例如,制度創新促進其他各種創新形式;工具創新促進機構創新,機構創新促進市場創新;制度創新與管理創新相互促進等)。在影響機制分析的基礎上,本文將以6種金融創新形式作為研究對象,實證分析金融創新形式之間的動態關系。6種金融創新形式分別被定義為JG(機構創新)、SC(市場創新)、GJ(工具創新)、ZD(制度創新)、GL(管理創新)、JS(技術創新)。
3.數據說明
本文以6種金融創新形式1979年第1季度至2015年第4季度的季度事件數作為實證分析的基礎,數據源自更新的中國金融創新事件庫(李健,林文浩,2017)。同時,為了保證研究的連貫性,還選取6個金融創新結構子指數作為對照數據進行實證分析。
按照表2中前兩列所示,本文設定了兩組數據。其中,第一組數據為6個金融創新結構子指數(下轄金融創新和原始創新兩類子指數),第二組數據為6種創新形式的季度事件數(下轄金融創新和原始創新兩類事件數)。無論是創新結構子指數還是創新季度事件數,金融創新類數據中包含了原始創新和擴散創新事件,因此比原始創新類數據的范疇更大。
考慮到金融創新的設計、實施到完成通常存在長短不一的時滯,本文假設“一年之計在于春”,將每年4個季度中出現金融創新事件都歸集到第1季度,使其他三個季度的創新事件數0。
(二)結構VAR模型設定
1.平穩性檢驗
建立結構VAR模型,需要對相關變量時間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PP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兩組、兩類數據共4種情況下,代表6種金融創新形式的時間序列都是平穩的,見表2。
2.最佳滯后階數
在SVAR模型設定前,需確定最佳滯后階數。本文采用LR、FPE、AIC、SC、HQ五個準則對SVAR模型的滯后期進行選擇,檢驗結果見表3。綜合考慮檢驗結果和季度數據的特點,本文將滯后期長度設定為4。
3.模型設定
SVAR模型設定為以下形式:
2.模型估計結果
此外,本文還按照相同的識別條件,使用其他三種數據進行估計。其中,“金融創新季度事件數”組下的“原始創新”類型數據(即JG04、SC04等)和“金融創新結構子指數”組下的“原始創新”類型數據(即JG02、SC02等)兩種數據的估計結果相似,基于它們獲得的矩陣A的15個元素中,10個元素的估計值為負,5個元素的估計值為正,但估計值為正的元素大多不顯著。10個估計值為負的元素,經移項后,意味著當期效應為正,反映了創新形式之間的促進關系,符合理論預期。最后一種數據[“金融創新結構子指數”組下的“金融創新”類型數據(即JG01、SC01等)]的估計結果完全不顯著,不再討論。
(四)脈沖響應分析
1.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
圖1中的結構脈沖響應函數,是基于“金融創新季度事件數”組下的“金融創新”類型數據(即JG03、SC03等)計算獲得的。當本文將數據種類替換為“金融創新季度事件數”組下的“原始創新”類型數據(即JG04、SC04等)或“金融創新結構子指數”組下的“原始創新”類型數據(即JG02、SC02等)時,上述金融創新形式之間的兩兩關系,除上文中“小標題‘(8)其他創新與市場創新”中描述的關系有所弱化外,其他關系仍然成立。結合3種數據下的結構脈沖響應函數和4種數據下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本文繪出金融創新結構內部形式之間的“兩兩關系”,見圖2。
(五)穩健性檢驗
SVAR模型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內生變量順序的影響,為了檢驗基于上述識別條件估計所得結果的代表性,本文對SVAR模型進行了穩健性檢驗,即將公式(3)中的內生變量重新調整為以下順序:JS、GL、ZD、SC、JG、GJ。經過檢驗,新的假設下脈沖響應函數所反映的各變量之間的動態關系與前文是相似的,這反映了本模型的穩健性。但是變量順序的調整不是隨意的,在違背理論分析和簡化VAR計量結果的情況下,任意擾亂變量排序,會導致SAVR模型估計結果的不再顯著。
六、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構建SVAR模型,以1979年第1季度至2015年第四季度6種金融形式的創新事件數(及其對應的6個金融創新結構子指數)作為樣本,對中國金融創新結構內部創新形式的動態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金融制度創新促進工具、機構、市場、技術和管理創新,管理創新對制度創新有反作用。具體而言,市場導向的制度創新,促進了高效率、低成本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的發展;效率導向的金融工具和機構創新,推動了有組織的金融市場的發展;伴隨制度創新不斷推進,金融交易效率提升,金融業分工細化,推動了技術創新;最后,制度創新可能放大金融風險,或使原有金融管理失效,因此需要開展與其他創新形式相適應的管理創新,而管理創新將為深化制度創新提供適宜的環境。
根據以上結論,為優化中國金融創新的結構,提出如下政策建議:本文的政策建議在于,第一、堅持市場導向,深化金融制度創新,加強市場約束機制,為金融原始創新、內生創新提供更加適宜的金融制度空間,提升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第二、堅持功能導向的金融創新,穩步推進制度和技術創新,完善金融工具、機構和市場體系,促進金融業向本源回歸。第三、優化金融創新的結構,加強金融管理的供給(如加強金融監管,改善金融調控,健全市場規則,優化經營管理等),維護金融創新和金融管理的結構平衡,防范背離金融功能的異化金融創新,沖擊到金融系統的穩定。
參考文獻:
[1]陳強.高級計量經濟學及Stata應用(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高鐵梅、王金明、陳飛等.計量經濟分析方法與建模(第三版)[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
[3]李健.中國金融發展推動力研究[J].金融研究,1998,(7):1-8.
[4]李健.中國金融發展中的結構問題[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5]李健、林文浩.中國金融創新結構的指數度量與影響因素[J].金融論壇,2017,(4):13-29.
[6]唐雙寧.深入學習鄧小平金融思想,做好新時期金融工作[EB/OL].http://www.financialnews.com.cn/yw/jryw/201408/t20140821_61549.html,2017-08-27.
[7]王廣謙.中國金融發展中的結構問題分析[J].金融研究,2002,(5):47-56.
[8]王仁祥、楊曼.中國金融創新質量指數研究——基于“技術-金融”范式[J].世界經濟研究,2015,(7):3-13.
[9]吳敬璉.銀行改革:當前中國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J].中國經濟周刊,2002,(12):15-19.
[10]《中國金融年鑒》編輯部.中國金融年鑒[M].北京:中國金融年鑒雜志社有限公司,1986-2014.
[11]周小川.金融改革發展及其內在邏輯[J].中國金融,2015,(19):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