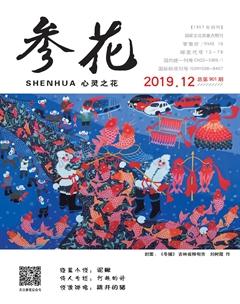情緣沱江河
夏文光
歲月流逝,沱江河見證了校園占地由三百多畝到兩千八百余畝的歷史變遷。站在新居西華苑二十六樓的陽臺,俯瞰沱江河及沿岸,翠綠中,清水漫流;高樓間,列車飛馳。
六十年代初的一張黑白照,是我生命來到這個世界的最初影像。父親抱著襁褓中的我,欣悅的笑容被定格在那一瞬間。
小時候,溪中每一個回水灣,一撮箕下去,可以撈到少則兩三條、多則十余條被大家叫“川川”的小魚。溪水中,我洗過衣、捉過螃蟹、劃過“木板船”……當然,也被溪流沖走過一雙塑料涼鞋,在溪中被玻璃劃傷過腳,傷心于溺水而亡的一個幼兒園小朋友……我就是聽著沱江河的濤聲,浸潤在沱江河的氣息中長大的。
小學時,我必須沿著小溪邊的羊腸小道步行三里多才能到達學校——紅光六小。小溪從學校門前流過,上學,順流而下;放學,逆流而返。溪水陪我一起走過了五年的春秋冬夏,載著童年的歡歌笑語、嬉笑怒罵。
六十年代后期,我家從原來居住的平瓦房搬到了一幢教工宿舍的三樓。站在廚房的陽臺,三十米開外就是那條沱江小溪,打開臥室的窗戶,百米遠就是沱江河在校園的“第一灣”。陽春三月,河對岸滿眼是綠油油的麥苗和黃燦燦的油菜花編織的錦緞,沱江河就像這錦緞上舞動的一條銀色飄帶。七十年代,我家又搬到教工宿舍四幢一樓,沱江小溪離窗戶只有幾米遠,夜晚常常伴著溪水的嘩嘩聲進入夢鄉。
從小我的記憶中,家里一直就吃的是自來水,只有偶爾停電時,我們才用桶到河里去提水,含沙的水用白礬將其沉淀漂清就能食用。九十年代前,學校的自來水雖然來自地下的機井,但毗鄰沱江的機井必定少不了沱江河水的浸潤。
九十年代,我家搬至教工宿舍十三幢三樓,緊鄰沱江河校園“第一灣”,沱江河將校園分為新老校區,十三幢就矗立在沱江河十米開外的北岸,夾岸云柳碧紗,花木茂盛。
上善若水。如今,西華的“一江三湖十二橋”已成為四川高校校園一道獨特的風景。二百多畝的水面,波光粼粼,悠悠沱水,水潤西華,懷城湖、文淵湖、天籟湖為校園增添了萬般靈動與嫵媚,體味著這番美景,學生們也不無自豪地戲稱這景致為“西華的馬爾代夫”。
沱江河滋潤著校園也滋潤著我的心靈,將我對沱江情懷中滋長的文學靈感銘刻在西華新校區十二座文化橋上。十二座文化橋三百多個橋欄上,鐫刻有我的創意雕塑和辭賦《西華賦》。歲月悠悠,沱江河與我如影隨形,在我每一篇受到師生肯定和喜愛的詩文中,總能尋覓到沱江河的蹤影。如《西華賦》:“枕古蜀百頃沃土,攬都江一泓清流。”《西華文化橋賦》:“綿延千古都江水,奔涌而來;蜿蜒數里沱江河,滾滾東去。”
沱江河!你流淌在我生命的記憶中,流淌出許多故事,我與你的情緣常常不經意間涌上心頭、洋溢筆尖。
(作者單位:西華大學)
(責任編輯 劉冬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