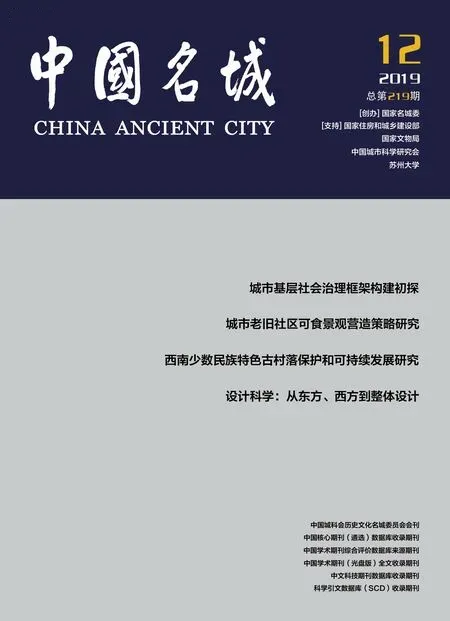傳統聚落文化記憶對公共空間形態的構建特征研究*
——以貴州安順雷屯為例
周 紅 王夢妮
20世紀末,德國學者揚·阿斯曼首次提出了“文化記憶”這個概念,“它包含了共同的價值體系和行為準則,而這些對所有成員都具有約束力的東西又是從對共同的過去的記憶和回憶中剝離出來的。”[1];“文化記憶包括一個社會在一定的時間內必不可少且反復使用的文本、圖畫、儀式等內容,其核心是所有成員分享的有關政治身份的傳統,相關的人群借助它確定和確立自我形象,基于它,該集體的成員們意識到他們共同的屬性和與眾不同之處。”[2]簡單來說,文化記憶在經過一些矛盾與沖突之后,具有選擇性和傾向性。經過時間累積的不斷開放以及不斷重建循環之后由集體的記憶提煉下來,它代表著區域內集體所有成員的價值體系和行為準則,兼顧所有人的情感和利益,具有最高的約束力;區域內全體成員形成一個統一的共識,強化一個具象的身份,并能在集體性事件上保持一致的意見并且能夠采取統一的行動。
公共空間的概念最早在西方學術上采用,哈貝馬斯的理論曾敘述公共空間是公共領域的載體和外在表現形式,即各種自發的公眾集會場所和機構的總稱[3]。二十世紀以來,在我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下,研究與關注“公共空間”領域的學者越來越多。當一定的社會組織形態與人際交往的結構方式具有了某種公共性,并在物質空間中相對固定下來時,就形成了公共空間[4]。它是居民可自由出入的,進行日常社交活動、參與公共事務等社會生活的主要的場所,容納與承載村民公共生活及鄰里交往的物質空間。傳統村落公共空間的構建反映了基層鄉村居民的公共娛樂精神狀態,能為新時期美麗鄉村公共空間和文化娛樂生活的建設的研究帶來思路。綜上所述,村落公共空間形態,它不僅是公共空間的外在表現形式、分布特征以及公共空間的形體環境。同時,它具備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屬性,反映出了社會生活與場所精神的環境與秩序。
貴州省安順市雷屯的公共空間的分類可分為物質空間和非物質空間兩類。物質公共空間是指在相對固定的某個特定的物質空間而展開的村民思想交流的場所,這類交往空間通常是具體的、有形的[5]。根據開放程度分為開放型公共空間、半開放型公共空間。如果更全面來理解,聚落內的公共空間還包括庭院、門檐下等一些半私密性公共空間,而本文對屯堡公共空間的探討則基于一個開放的層面。非物質空間是指傳統村落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約定俗成的活動形式,這類空間的空間形態是抽象的、無形的,且是不固定的,它因民俗活動而生[2]。如跳地戲的場壩空間、唱山歌的山頭、紅白喜事儀式等等。
1 安順雷屯概況
雷屯的地理區位是貴州省安順市黔中地區的七眼橋鎮,東經 106°10′,北緯 26°21′,北臨水洞口村,南接小山村,處在以屯軍山與麒麟山為主的山地環抱的盆地內。安順雷屯位于中國華南喀斯特地貌核心部位,氣候一年四季溫和舒適,冬無嚴寒,夏無酷暑,有豐富的地下水源。它處在發育最集中、最成熟、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帶。全村行政區面積12.0Km2,村域總面積為1.8Km2,其中,傳統村落重點保護面積為0.056Km2,現有住戶大約823戶。雷屯目前還是一個未完全被現代化發展同化的古村落,主要依靠著原始農業為生,是安順地區眾多保存完善的特色屯堡之一(當地的方言“堡”字的發音念做pu,上聲)(圖1)。
貴州安順雷屯建于明洪武年間,是貴州軍事防御的重要戰地之一,大量南方地區移民隨調北征南政策來到安順雷屯,并在嚴厲的軍籍制度下筑城安居。貴州歷代俗稱“山地之國”,在元朝以前,貴州地區未被完全開化,一直被稱為 “蠻夷”之地,發展緩慢且生產落后。明朝統治后,其并沒有完全控制西南地區,從戰略的角度考慮,貴州的穩定關系到云南邊防的鞏固和西南政局的穩定,于是開始派重兵防守,并且實行的強制的調北征南政策,及軍籍管理制度,沿線修整驛道,設立衛所。當地的喀斯特地形地貌使得石頭材料隨處可見,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營建思想造就了雷屯建筑的石質建造風格技藝,延綿不斷的石頭建筑構成了一道頗為壯觀的亮麗的風景線。在空間裝飾中,如鋪地,建筑雕花,龍、鳳、魚、獸則運用于各家各戶,婦女服飾“鳳陽漢裝”的頭飾、耳飾乃至腰帶、掛飾、鞋子都是當地居民重要的非物質遺產。在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的雙重影響下,雷屯軍民一心,逐漸沉淀出了雷屯固有的文化記憶,并影響了雷屯一代又一代人。
2 雷屯的文化記憶解讀
2.1 “平衡共生”的喀斯特地貌記憶
貴州約13萬平方公里都是喀斯特地貌,分布面積占全省總面積的80%以上,是我國喀斯特區域最為集中及典型省份。雷屯就建立在貴州喀斯特地形之上,地形與地質條件決定下的生存困境,使雷屯居民必須要在聚落選址意識、構筑物空間的適應性、構筑物結構與材料的應對等方面去尋求與自然關系的平衡。喀斯特地貌的典型特征是地勢陡峭,地形破碎,覆土層薄,平坦的地面在喀斯特山區非常稀少,盡管降雨量充沛,水資源豐富,但土質稀薄調蓄功能差,水資源分布不均,導致存在一定的旱澇災害。惡劣封閉的環境使得他們安貧守舊,形成一種低層次的人地共生平衡關系。喀斯特文化是喀斯特地區的人們智慧對環境的適應、利用與改造的結果,脆弱的環境和落后的生產方式使得人們緊緊依附于自然,衍生出對自然的崇敬、崇拜,形成信仰及圖騰。
2.2 “征南平邊”的軍事防御記憶
雷屯源于明洪武年間的征南部隊,明朝平定中原后派30余萬大軍鏟除前朝殘余勢力以拓展疆土,經貴州一路南下,掃平云南;后命征南部隊沿湖湘至云南的驛道上就地駐扎,昔日人煙荒蕪的喀斯特地貌地區瞬間集聚了大量軍士,各自分成各個屯兵點進行駐守,而雷屯是當時八大核心屯軍點之一。初期雷屯因此形成,其軍事防御記憶是其村建立的前提,他們具有強烈的家國榮譽感,是強大且光榮的軍事勝利者。他們及其后裔在身份、權力和文化上都較之于當時的貴州的原居民先進,顯示出強弱之分,華夷之分、文野之分。軍營式管理使得雷屯聚落的整體風貌充滿的很強的防御性風格。村落中地戲文化大部分都是古代征戰故事,從另一方面也是在宣傳和暗示自身祖先的光輝戰績給自己一個強大的背景記憶,不僅在本村落,而是在各個村落都互相傳承。祖先“王朝武士”的將軍身份永遠成為他們記憶的源頭和族群認同的歷史文化基礎。
2.3 “江南祖地”的儒家禮制記憶
由于明朝初年為了穩定西南地區局勢以拓展疆土而實行的調北征南政策,大批江南地區移民隨政策遷入貴州安順雷屯,明朝實行軍籍制度,及行軍打仗時,軍人家屬隨軍出征,亦隨軍家屬隨駐軍屯駐,其帶有原籍地的濃厚文化記憶,促進了西南邊陲的穩定和發展。在對雷屯的調研中,絕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的祖籍是明代“調北征南”時從老家江南移民來的,在祖輩口耳相傳中很明顯的感受到提及入黔祖先是軍人身份的自豪感。他們隨政策來到“蠻荒”之地要依靠自身攜帶的先進文化生存,而當時的江南是經濟富庶之地和文化繁榮之區,也是明初政治中心,展現出了一種落差和對故鄉江南的思念,也使他們固化了對祖源地的地域認同。即便至清代康熙年間衛所制度解體,屯堡內軍人身份轉為農民,并與后來的漢族移民相比逐漸邊緣化,但他們仍“不忘初心”,執著地保留著對“江南”的記憶。
2.4 “軍事信仰”的民俗文化記憶
在雷屯公共空間的職能中民俗活動和宗教儀式是必不可少的,當然還包括一些其他的節慶活動。雷屯有非常多的祭祀活動和寺廟建筑。寺廟祭拜對象不僅僅局限神靈,還有許多崇敬、崇拜的軍事人物。另外,每家每戶中基本有祠堂、神龕,上面寫有“天地君親師”或“天地國親師”,體現了根深蒂固的儒家禮制文化的思想。其二,每個月都有佛事,由已婚女子參加。民俗活動重點體現在地戲文化。地戲又稱“跳神”,不僅在安順地區以及周邊地區盛行,還包括布依、仡佬、苗等少數民族中流行。地戲的題材大多為古代戰爭類型,內容基本上為精忠報國的英雄故事。村民通過對正史類人物“忠、義、勇”的主題精神的描刻與演繹來傳達本村落的歷史和信仰。雷屯地戲除十年動亂外,從未間斷。還有著名的“抬汪公”儀式類活動,基本在吉昌屯舉行。還有其他的一些如跳花節、四月八、六月六等節慶活動[5]。
3 文化記憶對雷屯公共空間形態構建特征分析
“文化記憶有其固定點,它的范圍并不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這些固定點是過去一些至關重要的事件,其記憶是通過文化形式(文本、儀式、紀念碑等)以及機構化的交流(背誦、實踐和慶典)維持的,我們稱之為‘印跡形象’(figures of memory)。”[6]這里所指的印跡形象是文化記憶的具象表達,我們能夠清晰的理解文化記憶不僅僅是簡單的口頭交流或是書本記載,而是由潛意識中的具體象征載體傳承,其象征載體在整體上按照一定的結構秩序和空間布局共同構建了一個系統完整的文化記憶公共空間。通過公共空間的各種文化記憶活動達到對傳統村落結構和精神意義上的整合,從而到達地方身份認同和文化連續性的目的,文化記憶對雷屯公共空間形態的構建主要呈現以下特征:
3.1 圍合式空間場地特征
“場景的圍合是造成到訪者具有場所感的關鍵,進而也是塑造文化記憶的關鍵。”[7]傳統雷屯村落公共空間形態是圍合式的,客觀上與喀斯特地貌文化記憶的適應性有關,精神上又與移民軍事化文化記憶的防御性有關。屯堡的選址尤為重要,一般遵循“靠山不據山,傍水不進水”的風水法則,符合圍合式的空間場地特征,雷屯把麒麟山、屯軍山、三岔河等喀斯特地貌環境要素作為村落邊界條件加以利用,形成自然圍合邊界。然后加以非連續性的村口、迎星門、石橋等人造的象征性圍合邊界,作為村落邊界的標識入口空間,它們與民居的建、構筑物有不同的形式與體量,共同暗示與界定了村落的領域,形成邊界的場所性、多樣性和層次感。主街是屯堡聚落最重要的中心性公共空間,其中場壩與主街后半部分重合,呈一個圍合空間,是早期居民進行軍事演練、社會交往、文化娛樂、宗教祭祀等的主要活動場地。還有一些停留性公共空間,如樹下、水井旁、道路節點等利用樹蔭、周圍構筑物的圍合自行構成一小塊范圍,日常生活中人們使用頻繁,容易停留于此進行閑適的交流。
3.2 中心性空間序列組織特征
多山、起伏的喀斯特地形地貌文化記憶與依山而建的村落宏觀格局塑造了因地制宜、與地勢協調發展的公共空間形態,軍事管理的衛所空間組織特征與儒家正統文化記憶造就了雷屯村落半封閉式的核心性公共空間與單中心塊狀街巷組織。雷屯的場壩核心位置——一種標志性的、與村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和在重要民俗慶典中擔任重要角色的公共空間類型[8]——以中心放大空間向周圍有序發散,有且只有一個中心圈。單中心性場壩公共空間是雷屯空間序列的始發點,使村落在整體上或者局部呈現出了一種內聚的形式,是雷屯的公共生活的匯聚點和精神凝聚的核心,讓人們通過場壩空間來把握雷屯的布局、結構與秩序。雷屯場壩處于主街北向末端,空間寬敞與主街重疊,主要道路通向寨門,以輻射的方式與支巷垂直相連,街巷以及建筑肌理密致均勻有序化排列分成一塊一塊狀,強調上下級主次秩序的維護,這是軍事駐軍屯的顯著特點之一。中心重要性公共建筑布置寬敞,巷道內民居建筑布置緊湊密集,有條不紊,軍事化安駐營既是征戰時的大本營,又是防御組織的戰營(圖2)。
3.3 防御式街巷空間形態特征
“征南平邊”的軍事防御記憶使得雷屯從建屯初始就以確保防御的需求來進行整體規劃與構建的,巧妙地利用當地復雜的喀斯特地形,通過街巷組織的聯合性以及封閉性,利用主次街巷形式設防、巷道交叉節點設防、尺度造成的精神設防。雷屯由入口進入主街直通場壩空間,地形平坦開闊,在主街上中下設有3座古箭門樓,門樓上設有瞭望臺,可觀每個角落動向,戶戶相連巷巷相通,首尾相顧視線一覽無余,侵入者無處可藏,突然的行蹤暴露也給與了一定的精神壓力。主街與場壩連接各個支巷,與寬闊的主街大尺度有所不同,雷屯支巷面寬通常最多兩人并行,兩邊建筑高約2-4米不等,是急劇收窄的狹隘小尺度空間,兩邊建筑不開窗或開高窗,窗洞很小,墻面隱蔽處布置有槍眼,壓抑的尺度給人一種警惕、危險的心理信號,人們往往不會在這里長時間逗留。支巷中還分布著大量的各式各樣的防御式交叉節點,其中還有大量的節點空地,形成甕城,給人以迷惑性,大多最終為盡端路或者通向后山的逃生路。內部道路如同迷宮縱橫交錯蜿蜒曲繞,節節相扣,又能相互聯系構成了一個嚴謹的易守難攻的戰略防御建筑體系。
3.4 軸線式公共構筑物布局特征
在“江南祖地”的儒家禮制記憶與軍事管理的衛所空間組織特征雙重影響下,相較于大部分南方其他村落自由曲折的街巷布局,具有規整對稱的軸線式街巷布局與是雷屯的典型特征,團狀是喀斯特傳統鄉村最主要的形態[9]。雷屯的主街布置在全村中心的主要中軸線上,主街末端通向永豐寺,長約100米,上寬約13米,下寬約7米。良好的尺度保證了居民能容納全村村民舉行大規模的公共娛樂活動,寬闊的視野給人熱鬧,愉快的場所感受,人們愿意長時間逗留,聚集人氣。主街的長度又能保證村民井然有序的進行祭祀儀式類活動,寬闊延長的場所空間能給人莊嚴、肅靜的場所感受。與兩側各支巷垂直相連且道路等級明確且構成尺度差異明確、層次分明的主次街巷體系,主街比較寬、次街道比較窄,整體街巷形態結構清晰有序,巷道串聯村內各個院落。街巷布局各種主要建筑如永豐寺和戲臺沿主街布置坐落在主軸線上,坐北朝南,并緊鄰場壩。反映出雷屯軍事衛所式的結構嚴整、主次分明、層層圍護,進一步強化烘托公共空間的重要性,體現出了儒家思想中的高度與等級觀念。永豐寺一寺之內同時供奉三教神像,前殿供關羽,二進院落中的文昌閣,供奉文昌帝君,二殿正殿供如來與觀音,后殿內供玉皇大帝,是一個釋道儒三教合一集功能及意義的復合性綜合體典型廟宇,其空間意義是多層次多功能的,反映了雷屯村民祭祀對象的適用性和混雜性特征(圖3)。
3.5 空間尺度收放自如的喀斯特地形適應特征
雷屯的公共空間形態為適應喀斯特地形地貌特征而變化,而軍屯的屬性又決定了雷屯空間尺度的收放不僅具備了交通性能,還有防御和活動的多功能屬性。結合這些功能需求,首先,會選擇合適的開闊地形建立場壩空間,并連接主街,其次再布置合理的街巷系統。空間的收與放主要體現在主街與支巷的形態上。由雷屯屯門進入呈一個“收”的空間,南北走向的主街近二分之一三岔路口處局部放大,寬度近擴大一倍 ,是雷屯最重要的場所之一,是“放”的空間,為居民民俗活動所用,受外圍建筑層層包裹的狀態下,具有聚集人氣和安全意識的作用。支巷空間收與放的特征主要體現在適應山地空間的高差變化,以及防御性功能。另外,與主街的功能一樣,每一個支巷的入口和岔道都是防御的重點,因而均為收的空間。有些支巷在順應地形的情況下,在岔路的局部布置中加一個“放”的空間,形成甕城防守進攻,也用于迷惑闖入的敵人。總而言之,在地形狹窄處收,地形寬闊處放,在高差錯落的地面收,地形平坦寬闊的地面放,在轉角的地面收,直行的地面放,在有軍事防御的節點收,有民俗活動的場所放等(圖4)。
4 結語
文化記憶不是靜止的,在不同時空也有著不同的解讀,可能面臨入侵與遺失,一方面這些文化記憶影響了屯堡居民對公共空間的構建,另一方面公共空間又反向地強化了他們對文化記憶的理解,在“城市化”進程大背景之下,新農村建設的腳步加快,越來越多的村莊受其模式化影響,喪失其自身文化記憶,最終顯現出“千村一面”的情況。而公共空間是一個村莊鄉村風貌、地域特色的外在體現,也是傳承村莊文化記憶、延續人們鄉愁記憶,找尋身份認同的內在部分。研究一個地域的文化記憶對公共空間形態構建的影響對我國新農村公共空間的營造與設計是十分必要的。村落居民與環境之間的聯系的確立,安全感的產生,對村落內涵體驗的深度和強度,對場所的安全感與歸屬感,新農村建設富有個人標簽,均是通過文化記憶的營造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