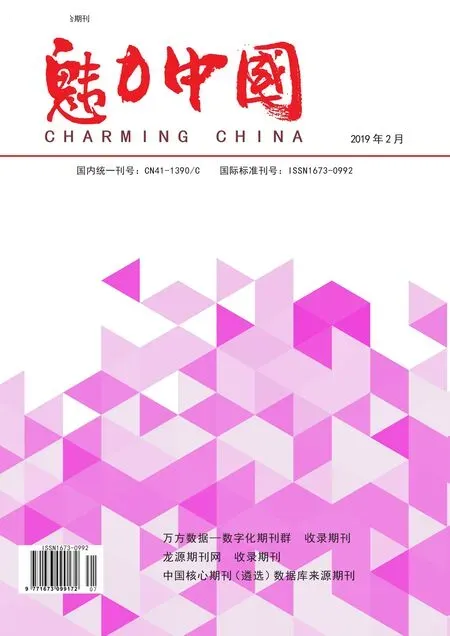故園與城市化進程關系研究
蔡健
(蘇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江蘇 蘇州 215004)
蔣勛曾在回憶錄中寫到:由于自己年少時曾輾轉于多地,所以對于故鄉的概念極為模糊。但當他坐上飛機,看著故鄉的輪廓逐漸遠去直至不見時,一種不舍油然而生,于是他這才發覺這才是他的故鄉。
由此可見,故鄉的概念多立于個人感性之上,而非單純的地理概念。你的故園,應為你心心念念,魂牽夢縈的地方。
揆諸當下,城市化進程迅速,為了保證安全性,房屋大多深院鐵柵,隔離于外世,但也同時隔離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系,隔離了人與一切美食和景物之間的聯系,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孤島”。安全性自然得以保證,但房屋因此也只化為了單純的地理概念,一個單純的可供居住的地皮。
雅各布斯曾經說過,城市人彼此之間最深刻的關系,莫過于共享一地理位置。但是,所謂家園,并非一個單純的物理空間,而是一個和地點聯結的精神概念,代表一群人對生活屬地的集體認同和相互依賴。應當作為人們借以寄存自身精神的凈土,能夠脫離于外界的紛擾和喧囂,能夠使你獲得心靈的平靜和精神的安定,能夠做一次更好的出發。而一旦家園僅僅為寄存肉體的場所,那么我們的精神,我們的鄉愁又何以安放呢?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論述過這么一個觀點:中國人的社會是一個極具人情味的可大可小的圈子。對于一個社會而言,極為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聯系。但當城市用地界,用柵欄將你與你懷念的元素分隔開來,所謂的圈子也會隨之瓦解。而一旦圈子瓦解,就意味著一切值得寄托的物件紛紛隨之而去,只留下一個茫然無措的肉體立于原地。
當代人最缺憾的問題并非思歸而不得歸,交通的便利早已縮短了空間的距離,過去再難以到達的地方如今不過轉瞬即至。但當人們不再擔心距離,卻迷失了方向。我們應當回到何處?我們更像是一塊編了號的磚,一塊在城市中漂移而不知所措的磚。城市在給予我們肉體所需一切的同時,卻又在不知不覺中竊取了精神得以寄托的地方。
孤獨的人們需要心底的歸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