館藏輝縣出土的殷商青銅器族徽文字探微
饒勝 周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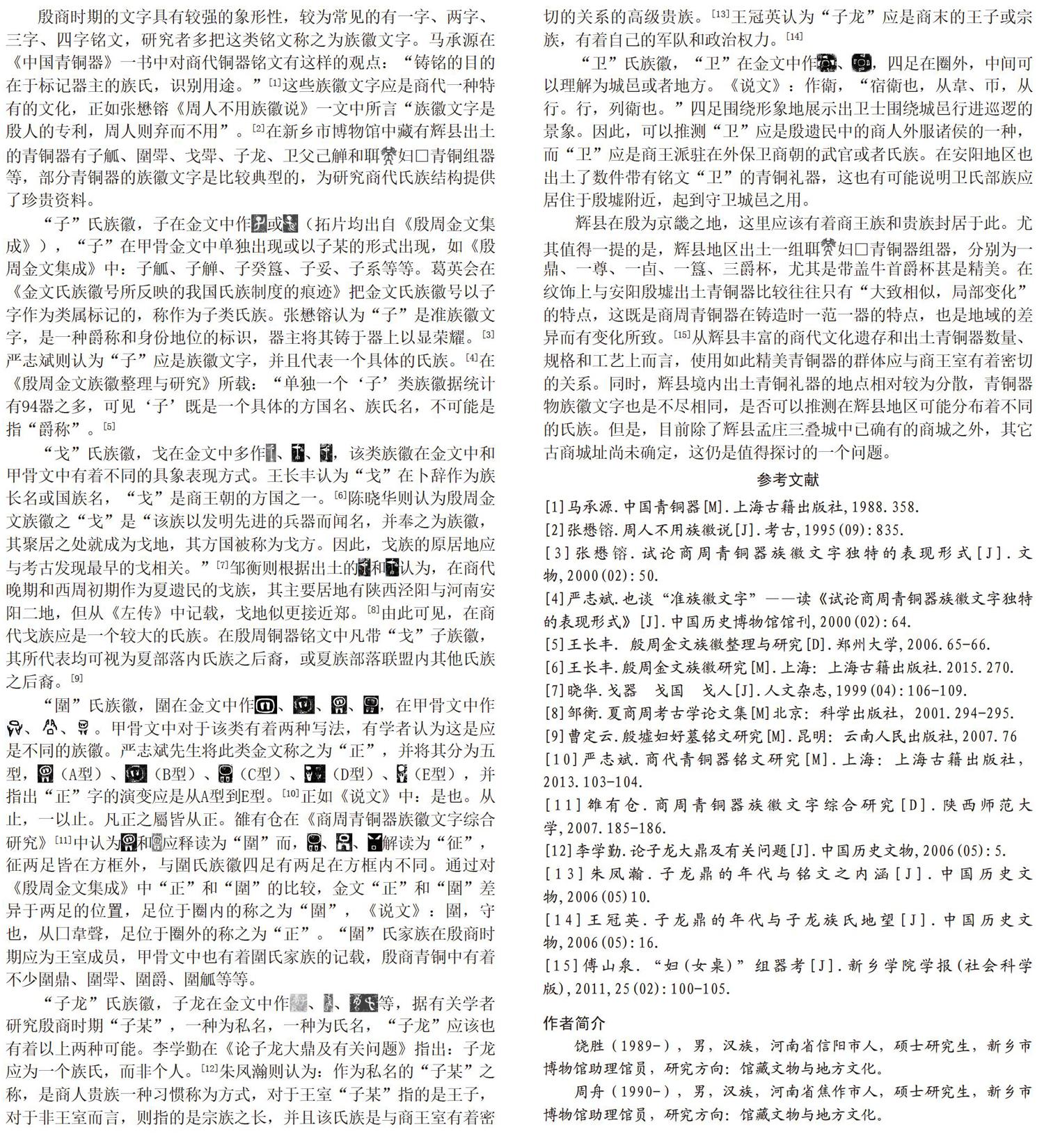
摘 要:輝縣在殷屬于畿內之地,在商周考古發掘研究中有著重要的位置。文章對館藏輝縣出土的青銅器族徽文字作以簡要梳理,以期窺探殷商時期輝縣的商代文化性質。
關鍵詞:輝縣;殷商;青銅器;族徽文字
殷商時期的文字具有較強的象形性,較為常見的有一字、兩字、三字、四字銘文,研究者多把這類銘文稱之為族徽文字。馬承源在《中國青銅器》一書中對商代銅器銘文有這樣的觀點:“鑄銘的目的在于標記器主的族氏,識別用途。”[1]這些族徽文字應是商代一種特有的文化,正如張懋镕《周人不用族徽說》一文中所言“族徽文字是殷人的專利,周人則棄而不用”。[2]在新鄉市博物館中藏有輝縣出土的青銅器有子觚、圍斝、戈斝、子龍、衛父己觶和聑婦□青銅組器等,部分青銅器的族徽文字是比較典型的,為研究商代氏族結構提供了珍貴資料。
“子”氏族徽,子在金文中作或(拓片均出自《殷周金文集成》),“子”在甲骨金文中單獨出現或以子某的形式出現,如《殷周金文集成》中:子觚、子觶、子癸簋、子妥、子系等等。葛英會在《金文氏族徽號所反映的我國氏族制度的痕跡》把金文氏族徽號以子字作為類屬標記的,稱作為子類氏族。張懋镕認為“子”是準族徽文字,是一種爵稱和身份地位的標識,器主將其鑄于器上以顯榮耀。[3]嚴志斌則認為“子”應是族徽文字,并且代表一個具體的氏族。[4]在《殷周金文族徽整理與研究》所載:“單獨一個‘子類族徽據統計有94器之多,可見‘子既是一個具體的方國名、族氏名,不可能是指“爵稱”。[5]
“戈”氏族徽,戈在金文中多作、、,該類族徽在金文中和甲骨文中有著不同的具象表現方式。王長豐認為“戈”在卜辭作為族長名或國族名,“戈”是商王朝的方國之一。[6]陳曉華則認為殷周金文族徽之“戈”是“該族以發明先進的兵器而聞名,并奉之為族徽,其聚居之處就成為戈地,其方國被稱為戈方。因此,戈族的原居地應與考古發現最早的戈相關。”[7]鄒衡則根據出土的和認為,在商代晚期和西周初期作為夏遺民的戈族,其主要居地有陜西涇陽與河南安陽二地,但從《左傳》中記載,戈地似更接近鄭。[8]由此可見,在商代戈族應是一個較大的氏族。在殷周銅器銘文中凡帶“戈”子族徽,其所代表均可視為夏部落內氏族之后裔,或夏族部落聯盟內其他氏族之后裔。[9]
“圍”氏族徽,圍在金文中作、、、,在甲骨文中作、、。甲骨文中對于該類有著兩種寫法,有學者認為這是應是不同的族徽。嚴志斌先生將此類金文稱之為“正”,并將其分為五型,(A型)、(B型)、(C型)、(D型)、(E型),并指出“正”字的演變應是從A型到E型。[10]正如《說文》中:是也。從止,一以止。凡正之屬皆從正。雒有倉在《商周青銅器族徽文字綜合研究》[11]中認為和應釋讀為“圍”而,、、解讀為“征”,征兩足皆在方框外,與圍氏族徽四足有兩足在方框內不同。通過對《殷周金文集成》中“正”和“圍”的比較,金文“正”和“圍”差異于兩足的位置,足位于圈內的稱之為“圍”,《說文》:圍,守也,從囗韋聲,足位于圈外的稱之為“正”。“圍”氏家族在殷商時期應為王室成員,甲骨文中也有著圍氏家族的記載,殷商青銅中有著不少圍鼎、圍斝、圍爵、圍觚等等。
“子龍”氏族徽,子龍在金文中作、、等,據有關學者研究殷商時期“子某”,一種為私名,一種為氏名,“子龍”應該也有著以上兩種可能。李學勤在《論子龍大鼎及有關問題》指出:子龍應為一個族氏,而非個人。[12]朱鳳瀚則認為:作為私名的“子某”之稱,是商人貴族一種習慣稱為方式,對于王室“子某”指的是王子,對于非王室而言,則指的是宗族之長,并且該氏族是與商王室有著密切的關系的高級貴族。[13]王冠英認為“子龍”應是商末的王子或宗族,有著自己的軍隊和政治權力。[14]
“衛”氏族徽,“衛”在金文中作、,四足在圈外,中間可以理解為城邑或者地方。《說文》:作衛,“宿衛也,從韋、帀,從行。行,列衛也。”四足圍繞形象地展示出衛士圍繞城邑行進巡邏的景象。因此,可以推測“衛”應是殷遺民中的商人外服諸侯的一種,而“衛”應是商王派駐在外保衛商朝的武官或者氏族。在安陽地區也出土了數件帶有銘文“衛”的青銅禮器,這也有可能說明衛氏部族應居住于殷墟附近,起到守衛城邑之用。
輝縣在殷為京畿之地,這里應該有著商王族和貴族封居于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輝縣地區出土一組聑婦□青銅器組器,分別為一鼎、一尊、一卣、一簋、三爵杯,尤其是帶蓋牛首爵杯甚是精美。在紋飾上與安陽殷墟出土青銅器比較往往只有“大致相似,局部變化”的特點,這既是商周青銅器在鑄造時一范一器的特點,也是地域的差異而有變化所致。[15]從輝縣豐富的商代文化遺存和出土青銅器數量、規格和工藝上而言,使用如此精美青銅器的群體應與商王室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輝縣境內出土青銅禮器的地點相對較為分散,青銅器物族徽文字也是不盡相同,是否可以推測在輝縣地區可能分布著不同的氏族。但是,目前除了輝縣孟莊三疊城中已確有的商城之外,其它古商城址尚未確定,這仍是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
參考文獻
[1]馬承源.中國青銅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58.
[2]張懋镕.周人不用族徽說[J].考古,1995(09):835.
[3]張懋镕.試論商周青銅器族徽文字獨特的表現形式[J].文物,2000(02):50.
[4]嚴志斌.也談“準族徽文字”——讀《試論商周青銅器族徽文字獨特的表現形式》[J].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2000(02):64.
[5]王長豐. 殷周金文族徽整理與研究[D].鄭州大學,2006.65-66.
[6]王長豐.殷周金文族徽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70.
[7]曉華.戈器 戈國 戈人[J].人文雜志,1999(04):106-109.
[8]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294-295.
[9]曹定云.殷墟婦好墓銘文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76
[10]嚴志斌.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03-104.
[11]雒有倉.商周青銅器族徽文字綜合研究[D].陜西師范大學,2007.185-186.
[12]李學勤.論子龍大鼎及有關問題[J].中國歷史文物,2006(05):5.
[13]朱鳳瀚.子龍鼎的年代與銘文之內涵[J].中國歷史文物,2006(05)10.
[14]王冠英.子龍鼎的年代與子龍族氏地望[J].中國歷史文物,2006(05):16.
[15]傅山泉.“婦(女桌)”組器考[J].新鄉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25(02):100-105.
作者簡介
饒勝(1989-),男,漢族,河南省信陽市人,碩士研究生,新鄉市博物館助理館員,研究方向:館藏文物與地方文化。
周舟(1990-),男,漢族,河南省焦作市人,碩士研究生,新鄉市博物館助理館員,研究方向:館藏文物與地方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