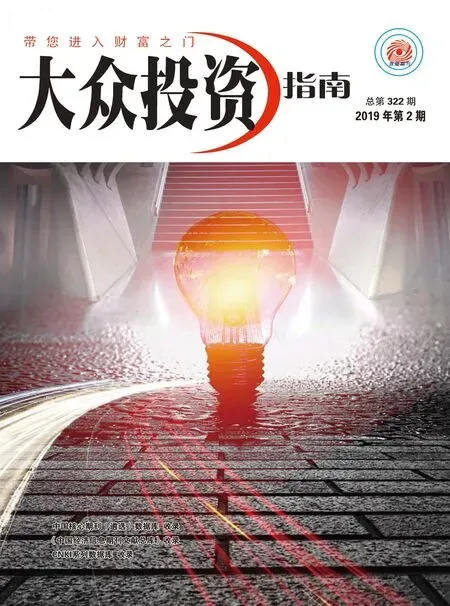對賭協議中投資方的賬務處理文獻綜述
王婷婷
(重慶理工大學會計學院,重慶 400054)
引言
以2005年蒙牛與摩根士丹利、英聯和鼎輝簽訂的對賭協議為先鋒,中國企業開始與國內外風險投資機構或非金融機構簽署對賭協議。通過條款設計,對賭協議可以有效保護投資人利益,但對賭協議在中國資本市場還沒有形成制度設置,法律也沒有明確規定,投融資雙方對于對賭協議涉及的會計處理仍在摸索中前進。本文回顧了對賭協議會計處理相關研究文獻,總結了對賭協議中投融資雙方的會計確認、初始計量和后續計量等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從三個方面評價了對賭協議中會計處理方式的研究現狀,就六個方面提供了研究展望,以期探索未來對賭協議會計的研究方向。
一、對賭協議及其分類
采用對賭方式激勵被投資企業提高經營業績或者促使其在規定期限內上市,是風險投資機構(VC)、私募股權投資機構(PE)和并購投資機構(A&Q)以及其他股權投資人(以下統稱“投資方”)常用的投資策略。對賭協議是投資方與被投資方(或被投資方實際控制人)在協議中針對未來不確定性情況進行一種約定,約定實現,投資方可以行使某種權利,否則,被投資方行使某種權利,對賭協議有以下分類:
(一)業績對賭和上市對賭
對賭協議根據對賭標的可分為業績對賭和上市對賭。早期常見的對賭協議中,投資人與被投資企業控制人約定:當企業的業績達到或未達到約定目標時,控制人與投資人之間支付現金或贈送(或低價轉讓)股份,這是典型以業績承諾為主的觸發機制,即業績對賭。隨著股權投資人越來越多的以上市方式退出,以約定期限上市的對賭協議即上市對賭隨之增加。
(二)單向對賭和雙向對賭
按照對賭協議的單雙向性不同,對賭協議分為雙向和單向對賭。如果被投資企業在限定期限內未實現約定,那么針對控制人的賭約觸發機制啟動,投資人執行相關“處罰”條款,以保證自身利益,即為單項對賭。雙向對賭則在單向對賭協議基礎上,約定如果被投企業達到了所約定的條件,投資人給予實際控制人相應激勵或利益。現有研究中,關于雙向對賭安排的討論較少,大部分學者討論單向對賭安排的賬務處理。
(三)業績補償和股權補償
對賭協議按實現賭約方式可分為業績補償和股權補償,業績補償型對賭協議不涉及股權變化。該類協議約定被投企業未能實現對賭目標時,控制人按照約定給予投資人一定數量的貨幣補償。或者被投資企業完成預期業績,投資人向被控制人給予業績補償。股權補償型對賭協議會涉及股權調整,股權補償又可分為股權回購、股權調整,股權調整還包括了股權稀釋。實務中通常以業績補償和股權回購作為實現賭約的方式。
二、投資方的賬務處理
(一)投資方的初始確認
1、初始投資定性
對賭協議是否與主合同拆分,定性為負債還是權益,多數學者認為應該將對賭協議作為主合同的附屬協議處理。股權回購對賭方面,王海燕(2014)認為融資方增資擴股并與投資方對賭的經濟實質是增發及出售以現金結算的看跌期權組合,增資事項確認為權益投資,計入長期股權投資;購入的看跌期權確認為衍生工具。彭明(2016)認為作為投資方來說,主合同是一項權益性質的表現,而嵌入衍生工具包括可能出現的股權轉讓和現金等價物補償,是一項負債性質的表現,從謹慎性、實質重于形式等原則出發,支持將衍生金融工具與主合同分拆處理,以客觀反映對賭協議的價值。但是,彭明認為如果是單向調解發生的可能收益則無須反映。
劉曦(2015)建議,最佳情況是在簽約時點對存在混同的及評判標準和標的進行準確分拆;若簽約時點不能準確分拆,先按照單一金融工具分類規則進行分類和計量,待之后條件變更導致重分類或結算選擇權既定時,再進行后續分拆,分拆時以公允價值進行計量。李宏(2013)、孫剛(2014)否定了將對賭協議作為金融工具的應用,而是將其認定為或有事項,此種做法也得到了證監會的認可。
2、期權價值確定
朱元甲(2015)從衍生金融工具角度將對賭條款的股權投資協議理解為混合金融工具,主合同為股權投資,價值調整約定為衍生工具。但是初始投資時,朱元甲認為投資方是基于被投資方未來良好的經營狀況和發展前景做出的決策,沒有信息證明該項看跌期權屬于實值期權。因此,他將該看跌期權的初始價值視為零,不會計分錄中體現。陳移伯(2013)、王海燕(2014)等學者將投資方提供的增資事項確認為權益投資,計入長期股權投資;將購入的看跌期權確認為衍生工具,其中王海燕沒有給出期權定價方式的建議。但是,繆潔(2014)在案例處理中使用布萊克-斯科爾斯模型對此期權予以定價,并提供了各指標的取值考慮,是一個值得借鑒的期權定價方式。
(二)投資方的后續計量
1、完全實現對賭目標
陳移伯(2013)認為,當且僅當被投資方完全實現對賭目標時,投資方才正式確認一項長期股權投資,減少此前的交易性金融資產和長期應收款。被投資方控股股東也相應地減少兩項負債,正式轉讓一部分長期股權投資給投資方。繆潔(2104)在被投資方完成對賭目標時將看跌期權轉為一項權益。
2、基于業績對賭的業績補償
后續計量的主要爭論焦點在于兩個方面,其一,被投資方沒有達到業績目標時,投資方在收到被投資方的業績補償時如何處理,是計入營業外收入還是直接增加長期股權投資成本,又或是作為公允價值變動處理。段愛群(2013)認為“業績承諾補償”類似于“對賭協議”,她認為投資方收到補償金額,應該增加長期股權投資成本。與其處理方式一致,顏曉燕、劉章輝、鄒琳(2017)將海南航空收到的盈利補償款沖減了長期股權投資成本,并對其計提相應的減值準備,而陳移伯將該盈利補償計入營業外收入。劉擁軍(2015)則認為投資方收到被投資方支付的業績補償款,應視為對最初股權投資成本高估多支付價款的調整,沖減長期股權投資成本。
3、基于上市與否的股權回購
陳移伯(2013)認為投資方應該將被投資方實際控制人回購的股權金額依次沖減交易性金融資產、長期應收款,不夠沖減的計入投資收益。朱元甲(2015)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39號——公允價值計量》,將期權在每個會計計量日按照公允價值計量確認投資損益,并建議股權投資機構跟蹤被投資企業的經營管理狀況,評估條款價值。
三、對賭協議投資方的會計處理研究現狀評價與未來展望
(一)對賭協議會計處理研究現狀評價
關于對賭協議的定義和分類,理論界的爭議主要存在關于對賭主體的規定,其中繆潔、王海燕等人按簽約方的不同將對賭分為投資方與被投資企業之間的對賭、投資方與被投企業的大股東或者管理層之間的對賭,以朱元甲為代表的學者依據法律實踐認為對賭協議是投資人和被投企業控制人在初始投資時,鑒于對企業未來價值判斷的不確定而簽訂的調整機制。筆者認為,每一項對賭安排都有其特殊性,“海富案”是個例,不應成為所有形式對賭安排的參考標準,而貿然據此限制對賭協議主體顯然不妥。
關于對賭標的,中國資本市場基于業績目標的對賭比較普遍,專家學者對業績對賭的會計處理方法的討論也比較多。而對于其他形式對賭比如股權補償等的會計處理方式的討論較少。而且,學者對現有案例為基礎進行會計處理探討,抑或者是設定不超過兩種形式的對賭安排予以會計處理討論。但是,筆者認為,模擬案例過于理想化、標準化,現有的對賭協議會計處理方式的探討比較單一,不具說服力。而且,現有研究中對賭協議會計處理中初始確認討論較多,后續計量討論少,彭明、劉曦等就對賭協議初始計量和分類方面進行了討論。
關于投資方的賬務處理,分歧在于不同的對賭主體是否會導致不同的賬務處理方式。在王海燕等學者認為投資方與被投資方直接對賭、投資方與被投資方實際控制人對賭,投資方的賬務處理是不同的,前者視為定向增發和看跌期權的組合,需要進行期權定價,后者是股權性投資與初始價值為零后續根據公允價值計量的衍生工具的投資組合。但是在繆潔、陳移伯看來,不論何種對賭安排,投資方的賬務處理并無差別。朱元甲在投資方初始確認時將投資金額計入交易性金融資產,業績補償條件觸發時作為公允價值變動調整損益。而在對賭期間,如果由于其他原因導致的公允價值變動是否應該調整交易性金融資產的賬面價值,不調整則不符合會計準則的要求,調整則難以與業績補償款進行合理劃分,顯得兩難。
另外,部分研究將對賭協議作為期權來處理,將其定性為一種衍生金融工具。將期權初始價值直接確認為零的處理方式顯然并不符合會計謹慎性和實質重于形式原則,也未將對賭協議的價值公允體現出來。筆者認為應該對期權進行定價,但定價模式不一,無風險利率、凈利潤年度波動率等一系列參數也難以假定,實務中期權定價存在較大的困難,而如果無法準確定價,后續的會計處理就缺乏可靠依據。
(二)對賭協議會計處理研究展望
隨著經濟環境和資本市場的不斷變化,由于對賭協議簽訂的特殊性和條款設計的復雜性,對賭協議會計處理的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立足于現有的研究,未來的對賭協議會計處理研究可以從以下方面展開:第一,法律視角約束條款的設計,管理者角度保護自身權益,會計準則角度提供修訂建議,多方面多角度研究對賭,促進學科交融。第二,不限于業績補償,而研究多種形式的對賭安排,比如股權調整、股權稀釋、管理層去向等;第三,現有研究傾向于對賭協議的初始確認,之后的研究可以注重其后續計量,尤其是被投資方的后續計量。其中,如果被投資方達到業績目標,被投資方應該如何處理收到投資方給予的現金等價物補償。第四,將對賭安排作為衍生工具處理,可以有哪些期權定價模型,每一種模型的差異在哪里,對后期的業績補償和股權回購有什么影響。如果確認為或有事項,又應該使用哪一種定價模型。第五,投資方和被投資方是否應該對賭安排中的項目計提減值準備。第六,是否應該對單向和雙向的對賭協議分開進行會計處理探討,又是否會影響權益和負債的劃分,進而影響初始確認和后續計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