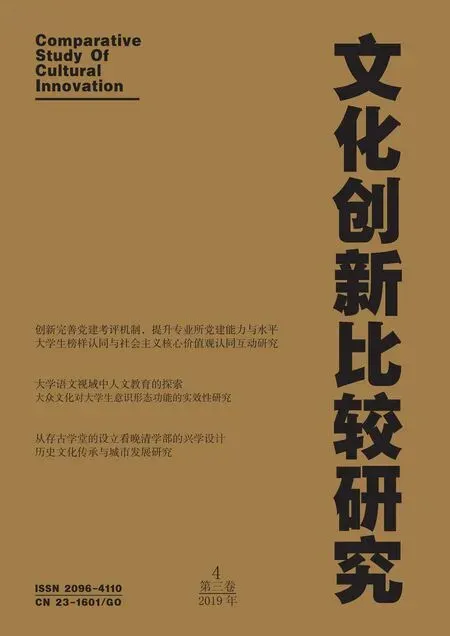雙重敘事策略下的《莎菲女士的日記》
李姝宏
(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四川成都 611756)
丁玲是五四文壇女作家中極具個性的一位,而《莎菲女士的日記》則是其在這一時期的絕對代表作。《日記》描寫了“五四”運動后北京城幾個青年的生活和愛情,其日記體裁的書寫形式使得小說顯得別具一格。文本以大膽的筆觸刻畫出女主角莎菲倔強的個性以及反叛精神,表達出作者強烈的個性意識和,成為女性文學的經典之作。莎菲的形象在主流評價中被認為是擁有以自立、自尊、自強主體人格意識為代表的現(xiàn)代女性形象。然而事實究竟如何?莎菲是否果真一個徹頭徹尾的女性主義者?
雖然距離小說初次發(fā)表的時間已經80年有余,但是《日記》中反映出來的女性的獨立自主、女性權威是否真實存在等問題仍極具現(xiàn)實意義。
美國女性主義敘事學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蘭瑟是創(chuàng)始人之一,她將結構主義敘事學和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進行有效對接,創(chuàng)立女性主義敘事學。女性主義敘事學作為后經典時期的敘事學不再僅僅局限于結構主義敘事,而是將觸角伸進了更為廣闊的文化研究的領域,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多元化分析文本。
蘭瑟在《虛構的權威》中提出女性聲音等術語是早期女性主義敘事學框架建立的重要理論。通過對女性敘述聲音等的關注,理論主要探討如何建立起女性權威,與《日記》中想要傳達的內核極為相似。
“公開型聲音”(public voice)和“私下型聲音”(private voice)的敘事方式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公開型聲音”是指向虛構世界外的受述者發(fā)出聲音的敘述者,而“私下型聲音”則相反,是指向虛構世界內的受述者發(fā)出聲音。“公開型聲音”所表述的含義與“私下型聲音”所表述的含義不一致,甚至相反即為雙重敘事。在蘭瑟所研究的性別領域,雙重敘事則是指公開所代表的和實際上所代表的性別立場的差異,“公開型聲音”才是作者真正想要表達的聲音。《日記》由于其體裁特殊,雙重敘事的特點尤為明顯。
1 《日記》中的雙重敘事
在《日記》中,從“私下型聲音”而言,受述者實質就是敘述者,即莎菲。但跳出虛構的世界,就“公開型聲音”而言,其受述者實為讀者,作者只是披著日記體裁的外衣讓人物更為剖白式地敘述。
從“私下型聲音”而言,文本的敘述角度和語言都是男性占著主導。男性中心主義傳統(tǒng)仍統(tǒng)治著從始至終一直屬于他們的領地。首先,從敘述角度而言,雖然故事中唯一的敘述者是莎菲,其敘述內容卻幾乎全都關于男性,無不直接或間接地籠罩在男性影響下。莎菲喜歡、陶醉、享受的,是得到男性的愛慕。不論是她一見鐘情的凌吉士,還是對她一心一意的葦弟,兩個人對她的關心和愛,她都想得到。其次,小說仍舊是采用的“女性語言”。例如,在一月十七號的日記中:“我想:也許我是發(fā)狂了!假使是真發(fā)狂,我倒愿意。我想,能夠得到那地步,我總可以不會再感到這人生的麻煩了吧……足足有半年為病而禁絕了的酒,今天又開始痛飲了。明明看到那吐出來的是比酒還紅的血。但我的心卻像有什么別的東西主宰一樣,似乎這酒可在今晚致死我一樣,我是不愿再去想那些糾糾葛葛的事……”文本展示出一個陷入情網無法自拔的女性的深情獨白。在傳統(tǒng)觀念中,男性都是以事業(yè)為重,不應該被兒女之情羈絆,只有女子才會如斯。除此之外,其語言本身也是帶著女性常有的松軟與優(yōu)柔,如“足足”“糾糾葛葛”等疊詞的運用等。
但是“私下型聲音”只是作者為了擺脫男性中心主義的束縛不得不以此偽裝的手段,其真正想要表達的是“公開型聲音”。
從“公開型聲音”而言,文本敘述角度和語言都是女性占主導,以莎菲視角為唯一視角,展現(xiàn)出莎菲高揚自我的女性之聲。首先,從敘述視角而言,文本的唯一發(fā)聲者只有莎菲。莎菲就是主導,掌握絕對權威,決定了故事發(fā)展。她就是核心,她擁有全部話語權。始終貫穿的是莎菲的想法、感受與愿望,其他人都是沉默的。例如,在十二月二十四的日記中:“葦弟看見我笑了,便很滿足。跳過床頭去脫大氅,還脫下他那頂大的皮帽來。假使他這時再掉過頭來望我一下,我想他一定可以從我的眼睛里得些不快活去。為什么他不可以再多的懂得我些呢?”。敘述以莎菲視角展開。葦弟的滿足是“我”自認為的他很滿足,透過“我”的眼睛看,中間存在莎菲猜測或自以為是的可能。同時,莎菲發(fā)問責怪葦弟沒能夠多懂得她一些,小說以她的角度展示出全都是葦弟的過錯。事實不能得知,只能從莎菲的敘述中推測。莎菲是文本中的神,主宰一切。其次,文本縈繞著“男性語言”。莎菲不再依附、臣服于男權中心主義的威嚴之下,努力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例如,在第八則日記中:“我要著那樣東西,我還不愿意去取得,我務必想方設法設計讓他自己送來。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過是一個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們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無條件的獻上他的心,跪著求我賜給他的吻呢。”莎菲對凌吉士一見鐘情,但她維持著作為女性的驕傲與倔強,沒有失去自我。她明白和愛情相比,作為一個與男性平等的女性更為重要。自我意識是使人得以有意義存在于這個世界的最基本前提。雖然她也使用女性小計謀來讓凌吉士主動追求自己,但當她全面了解凌吉士后,努力控制住了處于愛情盲目階段的自己,理智對他說了不。
從“公開型聲音”而言,仿佛是女性立場占主導地位。女性意識得到彰顯,聲音得到表達,權威得到構建。但如果女性權威真的已經建構,為什么作者要采用日記體的體裁呢?離開獨特體裁這一切還會存在嗎?
2 日記體中的女性權威
丁玲在采用日記體的時可能原因很多,但不論她是否意識到,日記體被認為更加符合女性氣質,潛意識中順從了男性中心主義,局限于體裁之內。莎菲擁有的一切是因為日記體的賦予,體裁的特點決定敘述角度只能是她,別人無法替代。離開了日記體,莎菲的聲音并非如此權威。
五四時期最大的發(fā)現(xiàn)便是對女人和兒童的發(fā)現(xiàn)。這一點,在1918年《新青年》刊登的周作人《人的文學》中便有相關的論述。“歐洲關于這‘人’的真理的發(fā)見,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紀,……第二次成了法國大革命,第三次大約便是歐戰(zhàn)以后將來的未知事件了。女人與小兒的發(fā)見,卻遲至十九世紀,才有萌芽。……中國講到這類問題,卻須從頭做起,人的問題,從來未經解決,女人小兒更不必說了。”周作人所說的這類問題,在中國雖說并沒有解決,但關注卻不少。早在《人的文學》發(fā)表之前,《新青年》就征集并刊登了有關“女子”問題討論的文章,只是由于其沒跳出舊思想框架,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直到周作人翻譯日本女作家謝野晶子的《貞操論》以及胡適的《貞操問題》發(fā)表,引入與之前完全不同的思想,才顛覆傳統(tǒng)觀念,帶來巨大沖擊,在當時引起激烈爭論。
受五四潮流的影響,丁玲從女性視角進行寫作,發(fā)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記》。對“女人”的發(fā)現(xiàn)幾乎和五四同步進行,《日記》發(fā)表的時間則是1928年。其中約有十年時間。十年對于幾千年的封建思想顯得格外微不足道不足以破除舊觀念。
女性仍依附于男性權威下,看似獨立自主。所以,丁玲采取日記體裁的小說形式實際是迫于傳統(tǒng)男性中心主義壓力,是不得已的選擇,即使看來擲地有聲,仍是被壓制。且這些看來的擲地有聲也只能僅僅存在于日記體之中。
不僅是《日記》,《埃特金森的匣子》《朱麗埃特·蓋茲比夫人致友人亨麗埃特·凱普萊夫人》以及18世紀一系列英美的小說中都存在此類現(xiàn)象。女作家們采用日記體方式,迂回艱難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希望為女性平等爭取一席之地。但是又處處受到限制。所以這帶來一個問題:女性權威是否真的存在?
3 結語
關于這一點,蘭瑟在《虛構的權威》中有過相關論述。她認為,女性的權威本身就是不存在的,是依附于男性權威下的產物。即使女性權威真的建構起來,那也只不過是替代男性權威之后的權威,有朝一日還會被替代。歸根究底,權威是虛構的。女性的權威實際上并不存在。
這就走到福柯的理論:所有的一切外在事物都是建構的,除了建構,我們一無所有。事物不再被假定存在著一個固態(tài)的、統(tǒng)一的本質,而事實可能是,事物更像是一種液態(tài)的事物,其形狀由容納它的容器所決定,而這個容器很大程度上就是主體所置身的制度與文化。沿著這條路繼續(xù)往下走,又有巴特勒等理論家對于身體本身的論述。身體畢竟還是不能夠被消滅,它是生理上實實在在的存在之物。
女性的權威是否真的存在?從女人的發(fā)現(xiàn)到現(xiàn)在一百多年的時間了,男女不平等的現(xiàn)象仍不一而足。家庭中傳統(tǒng)重男輕女傳宗接代的觀念,社會中職場上的性別歧視等。如今我們仍舊在喊著男女平等,我們仍舊在呼號,在追求,在期待。可能真的如丁玲所講:“‘婦女’這兩個字,將在什么時代才不被重視,不需要特別的被提出呢?”也許真的當“婦女”這兩個字不再被單獨提出,女性意識、女性聲音、女性權威不再被時時掛在口中,女性的權威就真正建立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