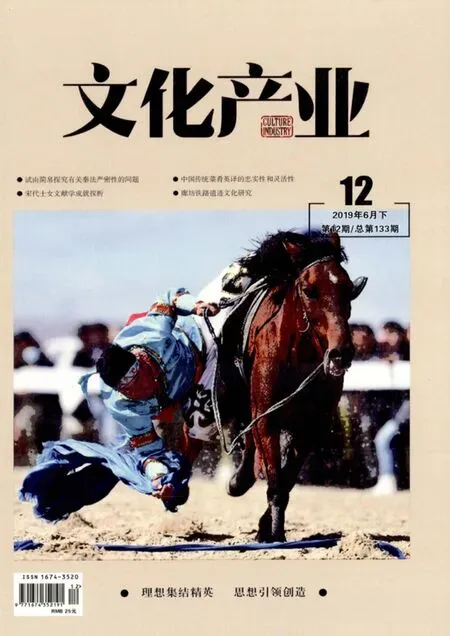廊坊鐵路遺跡文化研究
◎吳 鵬 王詠梅 余安安
(廊坊師范學(xué)院文學(xué)院 河北 廊坊065000)
作為一座有著悠久歷史文化底蘊(yùn)的名城,廊坊不僅有著農(nóng)耕文明所帶來(lái)的豐厚的歷史文化土壤,同時(shí)也在近代歷史的淬煉中獲得工業(yè)文明的洗禮。在一系列工業(yè)文明的遺跡中,“三角地”等文化遺跡無(wú)疑是廊坊人自我身份認(rèn)同的標(biāo)志之一。作為京滬鐵路的遺產(chǎn),它一方面為年邁的安次縣提供了新的活力,讓本處于京津之間的一個(gè)小鎮(zhèn)一躍成為拱衛(wèi)京畿的門戶;另一方面,也讓這個(gè)不起眼的縣城迎來(lái)了大量的外來(lái)人口,擴(kuò)充了經(jīng)濟(jì)實(shí)力,促進(jìn)了連接京滬鐵路上幾大文化圈在此地的融合。研究這些“文化符號(hào)”是尊重廊坊的文化史,重塑廊坊的文化記憶并以此引領(lǐng)未來(lái)廊坊文化建設(shè)的重要問(wèn)題之一。
一、廊坊鐵路遺跡的產(chǎn)生與現(xiàn)存狀況
廊坊市由于其身在京津之間,地處京津、冀南、東北文化圈中心地帶,并在歷史中長(zhǎng)期處于游牧、農(nóng)耕民族文化交流地,獲得了豐厚的文化積淀。這種地域的優(yōu)勢(shì)延伸至20世紀(jì),伴隨著京滬鐵路(津浦鐵路)、京奉鐵路(京山段)的修筑完畢,使得這座城市融入現(xiàn)代、連接全國(guó)的進(jìn)程得以加速。到了21紀(jì)初,小小的廊坊已經(jīng)成為名震京華的重鎮(zhèn),大量的外來(lái)人口伴隨著高鐵的再次建成而涌入這座環(huán)京的城市中,廊坊的城市發(fā)展突飛猛進(jìn),使之愈發(fā)活力四射。在城市的發(fā)展中,廊坊市經(jīng)歷了一次工業(yè)文明的洗禮,使得原有的街道文化獲得了改造而煥發(fā)新生的機(jī)會(huì)[1]。與之伴隨而生的老槐樹(shù)、老天橋、老站房、三角地成為第一代因鐵路的修筑而走進(jìn)廊坊歷史記憶中的文化景觀。
隨著廊坊經(jīng)濟(jì)實(shí)力的增長(zhǎng),越來(lái)越多的新、老廊坊人開(kāi)始尋找自己成長(zhǎng)的文化記憶,珍視自己的文化歷史、尊重廊坊發(fā)展過(guò)程中所遺留下來(lái)的各種設(shè)施,成為全體廊坊人的共識(shí)。如今,這些鐵路遺跡或在城市的發(fā)展中淡出了人們的視野,許多工業(yè)遺跡并未得以妥善保存,甚至新建的鐵路文化公園周邊的開(kāi)發(fā)也有相當(dāng)多的問(wèn)題,這都需要我們的政府、全體廊坊人民在未來(lái)的生活中對(duì)自己的歷史予以足夠的認(rèn)識(shí)。我們現(xiàn)在可以看到,很多工作都在有效地進(jìn)行,期待未來(lái)的廊坊能有更好的進(jìn)步。
二、廊坊鐵路遺跡的文化記憶與作用
新老廊坊人都將廊坊鐵路遺跡作為歷史的文化記憶符號(hào)而重新拾起。尤其是老一代廊坊人,在外打拼的經(jīng)歷使得他們的生活聚焦于自己的移民生活背景中,對(duì)故鄉(xiāng)難以割舍的情懷與對(duì)廊坊給予其發(fā)展的感激,融合于這座移民城市中,而作為最初記憶的鐵路記憶附屬設(shè)施成為自己最初寄托夢(mèng)想的地方,有些特定地區(qū),如三角地等,甚至還對(duì)早期移民的生計(jì)有著重大作用。南來(lái)北往的商客、奔流不息的列車,使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聚集在一起,對(duì)這座城市的發(fā)展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由此,鐵路成為連接他們與故鄉(xiāng)之間重要的紐帶,鋼軌像風(fēng)箏線一樣緊拽著自己的心和故鄉(xiāng),多少游子將汗水灑在了這一片熱土之上,多少次痛苦與快樂(lè)和著老槐樹(shù)上的明月只訴衷腸。這些早期移民或是來(lái)了又離開(kāi),或是留在了這片土地上,但無(wú)論如何,都讓第二故鄉(xiāng)的名稱永遠(yuǎn)留在了自己的心上。而給他們生活留下最深刻記憶的,無(wú)疑就是那個(gè)拉來(lái)他們靈魂的列車,并融入老鐵路遺跡中,成為他們揮之不去的記憶[2]。
隨著高鐵時(shí)代的到來(lái),新一代廊坊移民走入這片土地。許多人夢(mèng)在京津,身在廊坊,生活在廊坊,他們?yōu)檫@片土地帶來(lái)了高鐵時(shí)代的效率和京津“候鳥”似的穿梭,他們渴望在這片土地上獲得家園的感覺(jué)。于此,在老廊坊的記憶中找到能夠容納自己移民身份的承載物,以寄托身在廊坊的情思,是新一代廊坊人對(duì)自己身份認(rèn)同的重要標(biāo)志。
三、鐵路文化的現(xiàn)代“延伸”
事實(shí)上,不論在廊坊還是其他“火車?yán)瓉?lái)的城市”,都具有類似的文化現(xiàn)象。作為河北省會(huì)的石家莊市在近代的崛起也和正太鐵路與京廣鐵路的交匯有關(guān)。在石家莊和廊坊的文化建設(shè)中,分布著無(wú)數(shù)個(gè)與鐵路相關(guān)的設(shè)施,這些設(shè)施或是借著原有的鐵路遺跡而被改造成懷舊的文化場(chǎng)所,或是在文化建設(shè)中借著某些相關(guān)的設(shè)施成為人們寄托過(guò)往歲月的念想。
在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數(shù)市區(qū)多家“三角地”“廊坊站”為名的飯店了。據(jù)筆者對(duì)飯店所有人的采訪而言,這些人往往是廊坊市的初代移民,他們的父輩隨鐵路來(lái)到廊坊,對(duì)這個(gè)城市和故鄉(xiāng)有著深厚的感情。而這些移民的后代大多居住在廊坊站附近,生于斯、長(zhǎng)于斯的生活經(jīng)歷讓他們對(duì)這個(gè)城市的鐵路文化記憶頗多。許多人都能清晰地記住“三角地”“老槐樹(shù)”和關(guān)于車站的種種故事,他們的成長(zhǎng)經(jīng)歷伴隨著記憶,現(xiàn)已經(jīng)被牢牢地凝聚在現(xiàn)代的物質(zhì)文化上。甚至許多當(dāng)年在老三角地所吃過(guò)的極為普通的食品,也成為現(xiàn)代濃縮了歷史記憶的美食,受到了這些消費(fèi)場(chǎng)所中眾多消費(fèi)者的追捧。在“情懷”中,聰明的經(jīng)營(yíng)者把其作為了文化的產(chǎn)品,成為當(dāng)今文化市場(chǎng)的“美食”。很多人動(dòng)情地對(duì)這一段牽扯著遙遠(yuǎn)的故鄉(xiāng)與生長(zhǎng)于此的廊坊之間的記憶發(fā)出感慨。
不僅這些文化場(chǎng)所的經(jīng)營(yíng)者認(rèn)同這些鐵路文化的相關(guān)附屬物,許多新廊坊人也在這些場(chǎng)所消費(fèi)的同時(shí),為這座城市帶來(lái)了新的文化血液。許多顧客認(rèn)為,讓他們?cè)谶@些文化場(chǎng)所消費(fèi)的最初動(dòng)力就是他們的“移民”身份。第一次來(lái)到陌生的城市,在魂?duì)繅?mèng)繞的家鄉(xiāng)和身在他鄉(xiāng)的記憶中,最能讓他們思念的就是火車站了。因此,許多人在這些消費(fèi)場(chǎng)所消費(fèi)的不是相關(guān)的“物質(zhì)”,而是在消費(fèi)自己的情懷。
除此之外,城市的規(guī)劃和管理者也在鐵路文化上下足了功夫。為了承載廊坊的歷史文化,鑄就新一代廊坊市文化的記憶,廊坊市政府特意復(fù)建了“天橋”“老火車站”等相關(guān)的設(shè)施,作為鐵路文化公園。同時(shí)也在城市的規(guī)劃中彰顯了鐵路文化的傳承。尤其在高鐵時(shí)代,哪一個(gè)規(guī)劃者有眼界能在規(guī)劃中具備文化的戰(zhàn)略眼光,哪一個(gè)城市就能在未來(lái)的發(fā)展中擁有一批具備心念家鄉(xiāng)的高素質(zhì)人才。這樣的城市必然具備發(fā)展的潛能,也必然擁有未來(lái)的希望。
應(yīng)該說(shuō),在這一個(gè)角度上,廊坊的文化市場(chǎng)彰顯了它包容、積極的一面。一個(gè)有著豐富歷史文化內(nèi)涵的城市在現(xiàn)代文明的洗禮中衰落的有之,大放異彩的有之。但是將移民文化以鐵路這種精神文化的載體深入到人的歷史記憶中,并以一種代際傳承的方式,構(gòu)建自己文化認(rèn)同的城市,應(yīng)該說(shuō)廊坊以一種自覺(jué)的方式彰顯了自己的魅力。在未來(lái)的高鐵更加發(fā)達(dá)的時(shí)代,廊坊將有更多的鐵路設(shè)施得以興建,這一方面對(duì)廊坊的文化建設(shè)、城市認(rèn)同提出了挑戰(zhàn),另一方面也是一個(gè)機(jī)遇,可以借此將廊坊的記憶重新植入到現(xiàn)代廊坊的文化建設(shè)中。在21世紀(jì)的城市中,城市之魂永遠(yuǎn)植根于來(lái)自人內(nèi)心深處的文化認(rèn)同感,這一方面需要我們新、老廊坊人共同努力,也需要我們?cè)絹?lái)越多的移民融入這座城市的發(fā)展中,并通過(guò)現(xiàn)代鐵路的建設(shè),將新、老廊坊在文化的記憶中串聯(lián)起來(lái),共同創(chuàng)造出美好的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