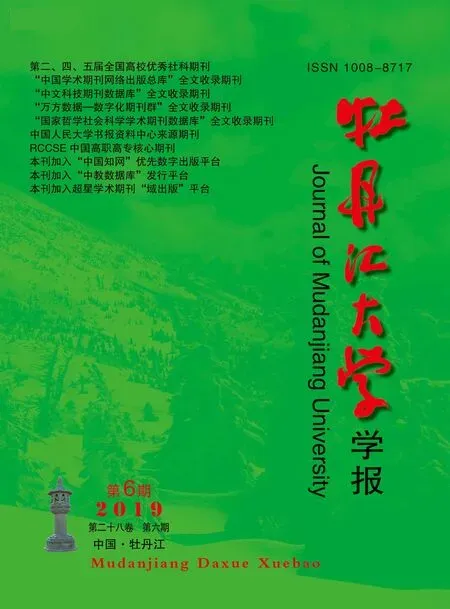從庫恩的“范式”理論與阿爾都塞的“總問題”理論比較看現代西方科學與哲學的相互影響
楊 松 雷
(重慶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重慶 400054)
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哲學和科學的關系是比較復雜的。在古代,哲學是知識的總匯,科學完全包含在哲學之內。自邏輯經驗主義興起之后,人們又把哲學當作“形而上學”完全拒斥,認為哲學不但不能促進科學的發展,反而會妨礙科學的發展。科學哲學中的歷史主義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興起之后,促使人們開始重新反思科學和哲學的關系。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作為一名科學家及科學哲學家的庫恩提出了“范式”理論,力圖證明科學的發展是離不開人們的世界觀、價值觀等屬于哲學方面的東西。與此同時作為哲學家的阿爾都塞提出“認識論斷裂”“總問題”理論,力圖證明馬克思哲學是“科學”。二者的理論形成一個有趣的對應。
一、托馬斯·庫恩的“范式”理論的緣起及內容
從啟蒙以來,理性確立了其主導地位,認為只要沿著理性走下去,科學也能發展到很高的水平,人們便能達到對真理的把握。尤其是近代西方邏輯經驗主義興起以后,更認為科學的發展是一個有脈絡、連續性的積累進步過程。科學具有確定性、規范性、普遍有效性等特點,科學與人們的世界觀、價值觀、社會背景等因素并無關聯。
隨著近代科學的飛速發展,科學哲學從十八世紀上半期也發展起來,其發展過程大致可以說是從邏輯經驗主義到批判理性主義再到歷史主義,也就是從邏輯經驗主義的完全拒斥形而上學發展到歷史主義向哲學的回歸。庫恩是科學哲學中的“歷史主義”一派創始人。庫恩通過“范式”理論指出,科學的發展不是純粹理性和純粹邏輯的指引下的連續積累進步過程,科學的發展是與社會、歷史因素緊密相聯的。他指出,人們堅持的某種科學,是“科學共同體”所共同信仰的“范式”。什么是“范式”呢?庫恩指“這些著作之所以能起到這樣的作用,就在于它們共同具有兩個基本特征。它們的成就空前吸引一批堅定的擁護者,使他們脫離科學活動的其他競爭模式。同時,這些成就又足以無限制地為重新組成的一批實踐者留下有待解決的種種問題。凡是共有這兩個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稱之為‘范式’”。[1]如牛頓物理學,愛因斯坦相對論都可以稱為某種“范式”。而“科學共同體”是指“其成員都是從相同的模型中學到這一學科領域的基礎的,他爾后的實踐將很少會在基本前提上發生爭議,以共同范式為基礎進行研究的人”。[2]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庫恩認為一個理論是否是科學,并不是由其中的內在邏輯、是否合乎理性來判斷的,而是建立在能否成為 “科學共同體”信仰的“范式”。
庫恩認為,科學的進步并不是單向的連續的知識的積累與提高。而是新的“范式”的建立,舊的“范式”的破除。新舊“范式”之間是本質的區別而不是量上的自然過渡,“范式”之間是不可通約的,它們之間沒有公約數,只有質的差別。范式的變革不可能是知識的直線積累,而是一種創新和飛躍,一種科學體系的革命。庫恩認為科學發展脈絡是:前科學時期——常規科學時期——反常與危機——科學革命——新的常規科學時期。其中常規科學時期就是科學知識的漸進積累過程,這時“范式”還能對當下問題作相對較好的解釋,“科學共同體”成員只是對“范式”補充完善。但如果在發生反常與危機的時候,舊有“范式”始終無法給予解決,人們會審視舊有“范式”,進而發生科學革命,建立新的“范式”,這個新“范式”“能較好地解釋導致老范式陷入危機的問題。對新“范式”來說,“如果這一主張能夠合理的實現,那么它通常可能就是一個最有效的主張。”[3]從而成為相應“科學共同體”成員所信賴的新“范式”。
二、阿爾都塞“總問題”理論的緣起及內容
在理性主義興起以后,在認識論問題上大部分哲學家總認為認識是直線型的,是在繼承中取得發展,借用柏格森的說法,時間是一個綿延的過程,生命也是一個綿延之流。而認識也是連續性的,即使有否定,也是在繼承基礎上的否定。從以往的認識來看,哲學家們基本上都認為認識的發展是個綿延的、連續的、有本質的聯系。
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阿爾都塞的老師法國籍哲學家及科學家巴什拉認為,在科學研究中不存在單一的直線性的進化,反而是在同過去決裂、斷裂中發展的。他強調,“認識論斷裂”是科學發展中最重要的規律,反對 “綿延說”“連續說”,認為“時間不在流失,時間在爆裂”。 作為巴什拉的學生,法學哲學家阿爾都塞進一步發展了巴什拉的“認識論斷裂”,并借鑒雅克·馬丁的“問題式”,提出“總問題”“征候閱讀法”等,并用這些理論來研究馬克思哲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阿爾都塞指出,“確定思想的特征和本質的不是思想的素材,而是思想的方式,是思想同它的對象所保持的真實關系,也就是作為這一真實的關系出發點的總問題。”[4]“‘總問題’的概念與唯心主義地解釋思想發展的各種主觀主義概念的不同之處,正是總問題的概念在思想的內部揭示了由該思想的各個論題組成的一個客觀的內在聯系體系,也就是決定該思想對問題作何答復的問題體系……總問題的本質不是它的內在性,而是它同具體問題的關系。”[5]“總問題”的作用是“在思想的內部確定著各具體問題的意義和形式,確定著這些問題的答案。”[6]阿爾都塞為什么要提出“總問題”呢?他指出“因為,說一種思想是一個(有機的)總體,這僅僅就敘述而言是正確的,而就理論而言則不然,因為這種敘述一旦被改變為理論,就有可能使我們只想到毫無內容的空洞整體,而想不到整體的特定結構。相反,如果用總問題的概念去思考某個特定思想整體……我們就能夠說出聯結思想各成分的典型的系統結構,并進一步發現該思想整體具有的特定內容,我們就能夠通過這特定內容去領會該思想各‘成分’的含義,并把該思想同當時歷史環境留給思想家或向思想家提出的問題聯系起來。”[7]而且“任何理論就其本質來說都是一個總問題,都是提出有關理論對象的全部問題的理論的、系統的母胚”。[8]
從以上可以看出,在阿爾都塞看來,各哲學家思想之間、理論之間之所以不同,正是由于“總問題”不同而區分開來的。每個哲學家思想深處所藏的 “總問題”不同,也造成了個體之間對“同一對象”的不同解讀,從而形成了不同的理論體系,并進一步用這個理論體系解讀整個社會問題和社會關系。
三、庫恩的“范式”理論與阿爾都塞的“總問題”理論比較
庫恩和阿爾都塞要解決的問題恰恰是相反的——一個要證明科學的“哲學性”,一個解決哲學的“科學性”。二者是相反相成的,從相反方向證明同一個問題——科學和哲學相互之間的借鑒、補充和融合。二者存在以下相似性:
第一,在相反的方向上達到殊途同歸
庫恩首先是一個科學家,但在他對科學史的研究中發現,科學的發展不是純粹理性和純粹邏輯的指引下的連續積累進步過程,科學的發展是與哲學、歷史等因素緊密相聯的。庫恩指出,“范式”對“科學共同體”的成員具有精神支撐調節作用,會影響到科學研究者的心理、情感、信念和思維方式等。阿爾都塞是一個哲學家,他要解決的是馬克思哲學的“科學性”問題。阿爾都塞把“認識論斷裂”“總問題”的理論運用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因為從1845年開始,馬克思開始同一切把歷史和政治歸結為人的本質的人道主義理論徹底決裂了……并重新確立了一個新的理論總問題,一種系統向世界提問的新方式,一些新原則和一個新方法。這種新發現導致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科學的誕生。”[9]這樣,阿爾都塞通過“認識論斷裂”“總問題”把成熟時期的馬克思和青年時期的馬克思區分開來,把馬克思和其他哲學家區分開來。
第二,理論結構的相似性
庫恩的“范式”理論和阿爾都塞的“總問題”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 “范式”和“總問題”都可以看作一個相對封閉的結構,都因其特殊性與其它的 “范式”或“總問題”嚴格區別開來。“范式”之間是質的差別,是不可通約的。而“總問題”之間由于對象、內部結構、提問方式的不同,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理論。有趣的是,二者都曾以拉瓦錫克服燃素說發現氧氣作為自己的例證。(這點可參見阿爾都塞:讀《資本論》,李其慶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第136—141頁。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第 49—53頁。)阿爾都塞在舉例之后指出,“‘使倒立著的全部化學正立過來’的含義是毫不含糊的,那就是改變理論的基礎,改變化學的理論總問題,用新的理論總問題來代替舊的理論總問題”。[10]而庫恩在舉例之后說,“需要有一次重要的理論修改以使拉瓦錫看到他看到的東西,也是為什么普利斯特終其漫長的一生卻未能看到它的根本原因。”[11]
第三,理論旨趣的相似性
“范式”與“總問題”的相似性還體現在,二者都會導致新的理論的產生和對事物不同的解釋。新的“范式”與“總問題”之所以與舊的 “范式”或“總問題”不同,在于新的“范式”和“總問題”具有兩方面的特點:其一,它們能更好地解釋、解決舊的 “范式”和“總問題”要解決的問題;其二,它們不但能較好地解釋、解決舊的“范式”和“總問題”所不能解決的問題,還能解釋、解決新出現的問題。庫恩指出,在常規科學內,人們利用已有的“范式”,可以解決一系列難題,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如果舊有“范式”不能解決反常問題,發生危機,又會出來新的“范式”取代它,進一步解決新的難題。阿爾都塞認為,正是因為新的“總問題”的確立,才把馬克思哲學與人道主義等區分開來,把馬克思與費爾巴哈等區別開來,把馬克思與斯密、李嘉圖等區別開來,以“剩余價值”學說這個“總問題”實現了理論革命,最終形成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科學”。“這樣,馬克思就成為可以同伽利略和拉瓦錫相比的科學的奠基人。”[12]
四、從“范式”與 “總問題”比較看現代西方科學與哲學的相互影響
阿爾都塞把科學主義引入哲學研究,而庫恩則把哲學、歷史等因素引入到科學研究中。盡管屬于不同的領域,他們的思想與作用卻是如此的相似,他們對科學與哲學及其研究方法的相互影響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哲學與科學的關系上,科學利用自身的發展模式得到飛躍式的發展,有把哲學遠遠拋在后面之勢。哲學也需要借鑒科學的方法,爭取自己的“合法化”。一方面,科學的發展加深了人們對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本身的認識,為包括哲學在內的各門學科提供了知識基礎;另一方面,哲學本身的研究也需要借鑒科學的研究方法。正如賴欣巴哈所說的,“一種對哲學進行科學研究的方法,不僅現在有,而且一直就有,……是要指出哲學已從思辨進展而為科學了。”[13]
而在科學發展的過程中,把哲學當作“形而上學”完全拒斥。人們在對科學的期望中,總是企圖把科學建構成為獨立于歷史、永恒的對自然界或人類社會的認識。從“范式”理論與“總問題”理論的相反相成可以看出,哲學和科學之間并不存在一道不可跨越的鴻溝,人們認為科學的發展完全與哲學無關,科學應該完全拒斥“形而上學”的觀點是錯誤的。正如另一位科學哲學家伊姆雷·拉卡托斯指出的那樣,如果人們對科學的期望是要科學提供絕對確定的東西,這種對科學的理解是“直接由神學繼承過來的標準加以判定:它必須被證明是確鑿無疑的。科學必須達到神學未達到的那種確實性”。[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