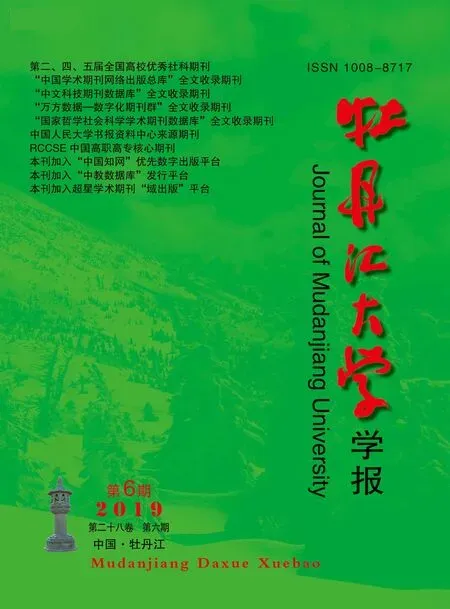場(chǎng)域、差異:晚清以來(lái)英美小說(shuō)翻譯規(guī)范的變遷
袁 輝 徐 劍
(中國(guó)礦業(yè)大學(xué)外文學(xué)院, 江蘇 徐州 221116)
晚清以來(lái)外國(guó)小說(shuō)譯介最直觀(guān)的特點(diǎn)就是數(shù)量大、重譯多。從譯本形態(tài)上看,形成了晚清、民國(guó)、建國(guó)初期和新時(shí)期四個(gè)翻譯歷史場(chǎng)域,各時(shí)期譯本體現(xiàn)了鮮明的時(shí)代訴求與翻譯規(guī)范變遷。
一、用夏變夷
小說(shuō)譯介開(kāi)近代外國(guó)文學(xué)翻譯的先河,1897年,嚴(yán)復(fù)、夏曾佑在《國(guó)聞報(bào)》上發(fā)表“本館附印說(shuō)部緣起”的長(zhǎng)文,倡導(dǎo)大規(guī)模地翻譯外國(guó)小說(shuō)以滿(mǎn)足文學(xué)與社會(huì)的需要。
中國(guó)傳統(tǒng)小說(shuō)從語(yǔ)言上可分為文言和白話(huà)兩種,從體裁上可分為筆記體、傳奇體和話(huà)本體,上述兩種語(yǔ)體三種文體是傳統(tǒng)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的基本規(guī)范。五四前的譯者,多采取中國(guó)小說(shuō)的傳統(tǒng)規(guī)范翻譯外國(guó)小說(shuō),比如魯迅早期的翻譯,就與后來(lái)很不相同。
魯迅早年翻譯《月界旅行》等小說(shuō)均采用章回小說(shuō)的體裁,形式上增添了中國(guó)章回小說(shuō)獨(dú)特的回目,在章回結(jié)尾,還常常補(bǔ)上解文詩(shī)句和收?qǐng)鎏自?huà),如第二回:
社長(zhǎng)還沒(méi)說(shuō)完,那眾人歡喜情形,早已不可名狀……正是:莫問(wèn)廣寒在何許,據(jù)壇雄辯已驚神!欲知以后情形,且待下回分解。[1]
當(dāng)時(shí)的小說(shuō)翻譯因?yàn)檠赜弥袊?guó)傳統(tǒng)小說(shuō)的體裁,往往給譯文增加了原文沒(méi)有但由于體裁變化所帶來(lái)的內(nèi)容。另一方面,將原著原樣裝入中國(guó)舊小說(shuō)的體裁里也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刪減改易“用夏變夷”在所難免。魯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說(shuō):“凡二十八章,例若雜記。今截長(zhǎng)補(bǔ)短,得十四回。初擬譯以俗語(yǔ),稍逸讀者之思索,然純用俗語(yǔ),復(fù)嫌冗繁,因參用文言,以省篇頁(yè)。其措辭無(wú)味,不適于我國(guó)人者,刪易少許。體雜言龐之譏,知難幸免。”[2]我佛山人譯《電術(shù)奇談》,在附記中亦有類(lèi)似表達(dá)。[3]這個(gè)時(shí)期用夏變夷最為成功的小說(shuō)翻譯家要數(shù)林紓。
“規(guī)范”本質(zhì)上是社群的主流行為,具有穩(wěn)定性,但也會(huì)受到挑戰(zhàn),當(dāng)挑戰(zhàn)主流翻譯規(guī)范的力量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huì)形成規(guī)范變化,曾經(jīng)的主流翻譯規(guī)范會(huì)被邊緣化甚至消失,新的規(guī)范則開(kāi)始成為主流。總體上看,晚清的翻譯規(guī)范是在五四前后發(fā)生根本變化的,但不同文類(lèi)的翻譯規(guī)范則變化有早有晚,在晚清翻譯規(guī)范發(fā)生根本變化前,已有一些對(duì)既成規(guī)范的“破壞者”。與林紓同時(shí)代的著名譯者周桂笙就是小說(shuō)革新的推動(dòng)者,他通過(guò)外國(guó)小說(shuō)的翻譯為中國(guó)小說(shuō)革新提供了借鑒的榜樣。1903年他在《毒蛇圈》的譯者序言中談到中外小說(shuō)體裁規(guī)范上的不同,解釋他“照譯”小說(shuō)原作的原因:“我國(guó)小說(shuō)體裁,往往先將書(shū)中主人翁之姓氏、來(lái)歷,敘述一番,然后詳其事跡于后,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詞章、言論之屬,以為之冠者,蓋非如是則無(wú)下手處矣。陳陳相因,幾乎千篇一律,當(dāng)為讀者所共知。此篇為法國(guó)小說(shuō)巨子鮑福所著,其起筆處即就父母(女)問(wèn)答之詞,憑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元,從天外飛來(lái),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亂起。然細(xì)察之,皆有條理。自非能手,不敢出此。顯然,此亦歐西小說(shuō)家之常態(tài)耳,爰照譯之,以介紹于吾國(guó)小說(shuō)界中,幸弗以不健全譏之。”[4]周桂笙指出中西小說(shuō)寫(xiě)法的不同,對(duì)于國(guó)人來(lái)說(shuō),初讀西方小說(shuō)的安排,或許會(huì)覺(jué)得“突兀”混亂,細(xì)讀則會(huì)發(fā)現(xiàn)其中的妙處與高明。他指出這是“歐西小說(shuō)家之常態(tài)”,即西方小說(shuō)的創(chuàng)作規(guī)范,周桂笙為了文學(xué)譯介的目的,翻譯時(shí)不再以中國(guó)傳統(tǒng)小說(shuō)的體裁為模板加以修改變化。
周桂笙的翻譯實(shí)踐,在晚清民初都還處于挑戰(zhàn)傳統(tǒng)規(guī)范的階段,要扭轉(zhuǎn)主流翻譯規(guī)范絕非易事。一方面,成功的翻譯容易被不斷地復(fù)制,另一方面成功的翻譯又會(huì)以讀者期待的方式進(jìn)一步鞏固主流翻譯行為。錢(qián)鐘書(shū)在評(píng)價(jià)林紓的翻譯時(shí)就曾說(shuō)周桂笙的翻譯沉悶乏味,接觸了林譯,才知道西洋小說(shuō)會(huì)那么迷人。與林譯相比,寧可讀原文,也不愿讀后出同一作品的‘忠實(shí)’譯本,而且林紓譯本里的不忠實(shí)或“訛”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們外語(yǔ)水平低。[5]我們認(rèn)為林譯在當(dāng)時(shí)符合大多數(shù)讀者對(duì)小說(shuō)的期待規(guī)范,是其譯作深受歡迎的重要原因。
晚清的翻譯規(guī)范,主要還是體現(xiàn)了公眾對(duì)譯者翻譯行為的期待,這種期待一方面延續(xù)了大眾既往的閱讀習(xí)慣,另一方面也通過(guò)肯定那些符合大眾閱讀習(xí)慣的譯本,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了翻譯規(guī)范自身的約束力量。晚清時(shí)期各種文類(lèi)的翻譯基本上都依循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樣式,跳出小說(shuō)翻譯的范圍看,“用夏變夷”的譯法具有普遍性。
二、西學(xué)為用
民國(guó)時(shí)的中國(guó)社會(huì)恰好處在規(guī)范激烈沖突的時(shí)期,源自傳統(tǒng)與當(dāng)代、東方與西方的各種規(guī)范競(jìng)爭(zhēng)社會(huì)體系的主導(dǎo)地位。文學(xué)和翻譯的子系統(tǒng)也是如此。從規(guī)范論的視角看,晚清至民國(guó)同樣存在三類(lèi)不同規(guī)范,但它們?cè)谙到y(tǒng)中的位置關(guān)系發(fā)生了變化。晚清國(guó)門(mén)未開(kāi)之時(shí),文學(xué)典范是我們今天所說(shuō)的古典文學(xué)。作為絕對(duì)強(qiáng)勢(shì)的規(guī)范,其核心地位直至西方炮艦將國(guó)門(mén)打開(kāi)之后才逐漸失去。五四前后是新舊規(guī)范的位置發(fā)生徹底變化的時(shí)期,中國(guó)文學(xué)的經(jīng)典規(guī)范發(fā)生了新舊更迭,“西學(xué)為用”是這一時(shí)期的主基調(diào),翻譯導(dǎo)致中國(guó)文學(xué)產(chǎn)生三個(gè)方面徹變,一是語(yǔ)言形態(tài),二是文體體裁,三是文學(xué)文類(lèi)。中國(guó)文學(xué)規(guī)范系統(tǒng)的演變與重構(gòu),離不開(kāi)翻譯活動(dòng)的參與。新規(guī)范的建構(gòu)是個(gè)漸進(jìn)的過(guò)程,翻譯在其中不僅起到了觸媒作用,還發(fā)揮了樣板示范作用。作為中國(guó)文學(xué)規(guī)范的組成要素,外國(guó)文學(xué)翻譯規(guī)范經(jīng)歷了由依循中國(guó)文學(xué)規(guī)范到中國(guó)文學(xué)規(guī)范與外國(guó)文學(xué)規(guī)范交織雜合,再到創(chuàng)制出現(xiàn)代翻譯文學(xué)規(guī)范的過(guò)程。
規(guī)范的更迭演變是新舊規(guī)范相互競(jìng)爭(zhēng)的過(guò)程,這種競(jìng)爭(zhēng)表現(xiàn)為這一時(shí)期的小說(shuō)譯本既受新規(guī)范的影響,又有舊規(guī)范的痕跡,這是事物演變過(guò)程中的典型特征。以轉(zhuǎn)型時(shí)期《維克斐牧師傳》的譯本為例,我們注意到,三十年代伍光建所譯的《維克斐牧師傳》(1931年出版),在語(yǔ)言上逐步擺脫文言的束縛,且非常“應(yīng)時(shí)”地譯出了一些歐化的句子,雖然還殘存著一些文言,但總體上已經(jīng)非常接近后一時(shí)期的語(yǔ)言特征。然而這個(gè)轉(zhuǎn)變過(guò)程對(duì)伍光建先生而言似乎并非易事,我們以伍光建譯本的章節(jié)標(biāo)題為例加以說(shuō)明。[6]
第一回 敘維克斐牧師家庭 這一家人面貌思想大略相同(老牧師閑享家庭樂(lè))
第二回 家庭不幸 君子不為貧賤所移 (好辯論兩親家失和)
第三回 移居 幸福原是自召 (白且爾客店遇牧師)
……
原著的章節(jié)命名比較接近漢語(yǔ)小說(shuō)形式,伍光建先生認(rèn)為離理想的漢語(yǔ)小說(shuō)標(biāo)題仍有距離,于是在原標(biāo)題后又自擬了一個(gè)標(biāo)題。自擬的標(biāo)題因循舊俗,沿襲了章回體小說(shuō)的傳統(tǒng)。這種譯法是規(guī)范更迭時(shí)期典型的翻譯雜合現(xiàn)象。舊規(guī)范是逐步退出的,新規(guī)范的確立也是個(gè)漸進(jìn)過(guò)程,由弱小到分庭抗禮直至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維克斐牧師傳》于1958年曾經(jīng)重新修訂再版,新修的譯本在譯文標(biāo)題上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不再使用“回”目,而代之以“章”,刪去了伍光建先生依據(jù)章回體小說(shuō)傳統(tǒng)自擬的標(biāo)題,修改了部分標(biāo)題的譯文。
翻譯行為受到多種力量的牽引,由于伍光建的譯本經(jīng)歷了漫長(zhǎng)的翻譯過(guò)程,從小說(shuō)體裁的選擇上看,譯者經(jīng)歷了糾結(jié)的過(guò)程,充分體現(xiàn)了譯者從中國(guó)傳統(tǒng)小說(shuō)體裁切換到西方小說(shuō)規(guī)范的艱難。
三、正本清源
建國(guó)初期翻譯領(lǐng)域還存在很多亂象,政府加強(qiáng)了翻譯工作的組織領(lǐng)導(dǎo),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翻譯為革命服務(wù)、為創(chuàng)作服務(wù),端正譯風(fēng),提升翻譯質(zhì)量。1950年《人民日?qǐng)?bào)》發(fā)表“用嚴(yán)肅的態(tài)度對(duì)待翻譯工作”的文章,1951年發(fā)表了毛澤東修訂的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guó)語(yǔ)言,為語(yǔ)言的純潔和健康而奮斗”,1954年茅盾、郭沫若等又在全國(guó)文學(xué)翻譯工作會(huì)議上發(fā)表系列講話(huà),奠定了新中國(guó)成立后翻譯規(guī)范的基礎(chǔ)。其中既包含職業(yè)道德規(guī)范,也包含操作規(guī)范,并指明了為什么譯、譯什么、怎么譯、譯者具備怎樣的條件才能譯,對(duì)這個(gè)時(shí)期的翻譯起了很大的影響作用。
文學(xué)翻譯規(guī)范開(kāi)始再造,翻譯界對(duì)翻譯態(tài)度、譯者責(zé)任感、譯者修養(yǎng)和翻譯技術(shù)的關(guān)系問(wèn)題進(jìn)行了大討論。這些討論旨在構(gòu)建翻譯的“責(zé)任規(guī)范”,為新中國(guó)的翻譯規(guī)范明確了內(nèi)涵,與前一時(shí)期自發(fā)調(diào)節(jié)翻譯行為的情況有很大不同。在翻譯“質(zhì)量規(guī)范”的重建上,一方面對(duì)文學(xué)翻譯標(biāo)準(zhǔn)中的政治化進(jìn)行糾偏,另一方面強(qiáng)化了翻譯語(yǔ)言的規(guī)范性。茅盾作了“為發(fā)展文學(xué)翻譯事業(yè)和提高翻譯質(zhì)量而奮斗”的報(bào)告,成為當(dāng)時(shí)文學(xué)翻譯語(yǔ)言規(guī)范的指導(dǎo)思想,他提出文學(xué)翻譯不是單純技術(shù)性的語(yǔ)言外形的變易,每種語(yǔ)文都有自己的語(yǔ)法和語(yǔ)匯使用習(xí)慣,不能把原作逐字逐句,按照原來(lái)的結(jié)構(gòu)順序機(jī)械地翻譯過(guò)來(lái),這種譯文不僅在一般翻譯中不該存在,在文學(xué)翻譯中更不能容許。茅盾總體上表達(dá)了歸化翻譯的主基調(diào),反對(duì)機(jī)械硬譯的辦法,贊同有限度地吸收外語(yǔ)的句法特點(diǎn)和有限度的漢語(yǔ)歐化,并認(rèn)為適當(dāng)照顧原文形式與保持譯文是純粹的中國(guó)語(yǔ)言,完全可能而且有必要。此外,譯本選擇上鮮明的階級(jí)性也是建國(guó)初期翻譯規(guī)范的特點(diǎn)。規(guī)范是價(jià)值觀(guān)的體現(xiàn),也反映意識(shí)形態(tài)的變化。新中國(guó)成立,文學(xué)翻譯在服務(wù)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事業(yè)的同時(shí),也發(fā)揮了政治教化的功能。在譯本的選擇上,代表共產(chǎn)主義意識(shí)形態(tài)的蘇聯(lián)文學(xué)作品以及資本主義國(guó)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國(guó)家的進(jìn)步文學(xué)作品,都是翻譯出版的選擇對(duì)象。翻譯規(guī)范的階級(jí)性變得更加鮮明。
在翻譯規(guī)范得以整肅和重塑的情況下,外國(guó)小說(shuō)的譯介質(zhì)量有了保障,組織性加強(qiáng),亂譯也得到糾正,修正了語(yǔ)言過(guò)度歐化的現(xiàn)象,漢語(yǔ)純潔性也得到了保障。我們以《傲慢與偏見(jiàn)》兩個(gè)時(shí)期的譯本來(lái)說(shuō)明這種變化,篇幅所限,僅取小說(shuō)的一段譯文為例。
王科一1955年譯本:盡管班納特太太有了五個(gè)女兒幫腔,向她丈夫問(wèn)起彬格萊先生這樣那樣,可是丈夫的回答總不能叫她滿(mǎn)意。母女們想盡辦法對(duì)付他——赤裸裸的問(wèn)句,巧妙的設(shè)想,離題很遠(yuǎn)的猜測(cè),什么辦法都用到了;可是他并沒(méi)有上她們的圈套。最后她們迫不得已,只得聽(tīng)取鄰居盧卡斯太太的間接消息。她的報(bào)道全是好話(huà)。據(jù)說(shuō)威廉爵士很喜歡他。他非常年輕,長(zhǎng)得特別漂亮,為人又極其謙和,最重要的一點(diǎn)是,他打算請(qǐng)一大群客人來(lái)參加下次的舞會(huì)。這真是再好也沒(méi)有的事;喜歡跳舞是談情說(shuō)愛(ài)的一個(gè)步驟;大家都熱烈地希望去獲得彬格萊先生的那顆心。[7]
董仲篪1935年譯本:無(wú)論如何,背納特太太幫助她五個(gè)女兒討論此事使她丈夫滿(mǎn)意背格累先生說(shuō)的。他們以各種方法進(jìn)攻他--用明顯問(wèn)題,冷靜態(tài)度;但他閃避一切技巧,他們最后不得不接受二把手鄰人路斯太太的消息。她的報(bào)告很有益。威廉先生喜歡他。他是很年輕,奇美極相配人,并且冠美一切,他意想第二次會(huì)聚同住很大團(tuán)體。沒(méi)什么再很可喜!愛(ài)好跳舞是發(fā)生戀愛(ài)一定的階段;背格累先生的心蘊(yùn)蓄住活躍的希望。[8]
王科一是那個(gè)時(shí)代最高水平的翻譯家之一,他的譯本在語(yǔ)言上適度回歸了漢語(yǔ)語(yǔ)言規(guī)范,尊重原文的表達(dá)習(xí)慣,但不為原文的句法結(jié)構(gòu)約束,在忠實(shí)原文和通達(dá)順暢上取得了較好的平衡。譯文與原文的對(duì)應(yīng)性較好,既根據(jù)漢語(yǔ)語(yǔ)法的需要及時(shí)調(diào)整語(yǔ)言結(jié)構(gòu),同時(shí)也不對(duì)原文做隨意的剪裁編排。董仲篪的譯文從翻譯方法看是以原文為導(dǎo)向的,語(yǔ)言結(jié)構(gòu)比王科一的譯文更貼近原文,總體上句子結(jié)構(gòu)的歐化勝過(guò)詞匯層面的歐化。董仲篪的譯本在詞匯風(fēng)格上值得一提,有那個(gè)時(shí)代很多翻譯的共同特點(diǎn),保留了不少文言詞匯的特征,形成一種比較獨(dú)特的雜合的翻譯語(yǔ)言風(fēng)格,即用歐式的句子結(jié)構(gòu)組織了一部分文言或淺近文言詞匯,這算得上是當(dāng)時(shí)歐化翻譯的一個(gè)特點(diǎn),在當(dāng)時(shí)的翻譯大家伍光建、梁實(shí)秋等人的翻譯中都很常見(jiàn),是影響較大的翻譯規(guī)范之一。今天的讀者或許更能夠接受王科一先生的譯本,原因是今天的翻譯規(guī)范更接近王科一的譯文。另外在人名、地名的翻譯上,王科一先生的翻譯更加煉字,音形義的結(jié)合更“雅”,這與五十年代對(duì)翻譯標(biāo)準(zhǔn)的討論不無(wú)關(guān)系。
四、百家爭(zhēng)鳴
新時(shí)期的翻譯實(shí)踐,大致以文革結(jié)束改革開(kāi)放開(kāi)始為起點(diǎn)。從翻譯行為上看,這一時(shí)期的翻譯規(guī)范有一些顯著的變化。
首先,在初始規(guī)范上,涉及譯本選擇的翻譯政策更加寬松,譯者、出版社對(duì)譯本的選擇相對(duì)自由,文學(xué)、教育以及市場(chǎng)的力量是更直接的譯本選擇因素。譯本的題材和選擇范圍都較以往擴(kuò)大,更好地體現(xiàn)了“百花齊放、百家爭(zhēng)鳴”的精神,英美文學(xué)翻譯的地位大幅提高,成為文學(xué)翻譯的絕對(duì)主流,這種情況與民國(guó)和建國(guó)初期不同。前兩個(gè)時(shí)期,蘇聯(lián)文學(xué)的翻譯始終占據(jù)這至關(guān)重要的地位,但新時(shí)期的翻譯格局發(fā)生了變化,極左意識(shí)形態(tài)對(duì)文學(xué)翻譯的影響減弱,中國(guó)翻譯史迎來(lái)了又一次翻譯高潮,展現(xiàn)了更為豐富的多樣性。
其次,市場(chǎng)因素導(dǎo)致了愈演愈烈的重譯行為。文學(xué)重譯的合理性存在于場(chǎng)域變遷對(duì)重譯本的需要,但是,改革開(kāi)放后的翻譯實(shí)踐場(chǎng)域出現(xiàn)了大量的重譯本,這些重譯行為只有少部分是由內(nèi)源性因素引發(fā)的,大部分翻譯行為都受控于市場(chǎng)因素,甚至是純粹的利益驅(qū)動(dòng)。從加入版權(quán)公約國(guó)之前的普遍重譯,到成為版權(quán)公約國(guó)成員后集中在經(jīng)典作品上的重譯,都很好地說(shuō)明了市場(chǎng)因素對(duì)翻譯行為翻譯規(guī)范起著重要的影響和引導(dǎo)作用。
翻譯的歷史實(shí)踐場(chǎng)域不同,譯本才可能產(chǎn)生較大的變化與差異,才能凸顯譯者的翻譯風(fēng)格。從內(nèi)部邏輯上看,同一時(shí)期、同一歷史實(shí)踐場(chǎng)域,并不需要大量的翻譯作品以幾乎沒(méi)有差異的形象同時(shí)登場(chǎng)。在國(guó)內(nèi)的學(xué)術(shù)界,有很多學(xué)者反對(duì)重譯,他們提出文學(xué)翻譯完全可以有定本的觀(guān)點(diǎn),這種反對(duì)不無(wú)道理。翻譯受市場(chǎng)這個(gè)看不見(jiàn)的手的控制,資本趨利的特點(diǎn)極可能導(dǎo)致非理性翻譯行為的發(fā)生。從翻譯的組織性上看,這個(gè)時(shí)期翻譯活動(dòng)的自由度提升而宏觀(guān)的組織計(jì)劃性降低。
再次,編譯改譯的形式與對(duì)象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編譯、節(jié)譯、改譯甚至改寫(xiě)的翻譯行為流行于晚清時(shí)期。縱覽現(xiàn)當(dāng)代翻譯史,總的趨勢(shì)是編譯、改譯等翻譯行為愈來(lái)愈少。在編譯改譯的案例中,晚清的林紓算得上是最成功的一個(gè)。林紓的編譯、改譯行為并不都是他和助手的語(yǔ)言能力不足而被動(dòng)造成的,有時(shí)他是刻意而為。林紓的時(shí)代正值國(guó)門(mén)初開(kāi),國(guó)人對(duì)國(guó)外的了解,被動(dòng)大于主動(dòng),林紓的編譯改譯,幅度大,文化與語(yǔ)言表達(dá)替換多,滿(mǎn)足了歸化的需要,更利于國(guó)人漸進(jìn)地了解西方文化,是外國(guó)文學(xué)中國(guó)化的一條捷徑。錢(qián)鐘書(shū)認(rèn)為這種方法仿佛做媒似的,能夠“使國(guó)與國(guó)之間締結(jié)了‘文學(xué)姻緣’”[5]。回到當(dāng)代,改譯、編譯并非不存在,只是呈現(xiàn)了新的形式:一是改譯大多表現(xiàn)為由意識(shí)形態(tài)原因引發(fā)的刪節(jié);二是編譯、改譯、改寫(xiě)的目標(biāo)讀者群主要是青少年,作為外國(guó)文學(xué)素養(yǎng)的初級(jí)讀物出現(xiàn),這些作品的讀者主要不是成年人,與林紓的時(shí)代已大為不同。隨著全社會(huì)外語(yǔ)水平的提高,編譯、改譯在文學(xué)譯介中的接受度也越來(lái)越低。
五、結(jié)語(yǔ)
總覽過(guò)去一百余年外國(guó)小說(shuō)翻譯的譯介出版,場(chǎng)域特征尤為突出,每個(gè)譯本多多少少的都帶有它那個(gè)時(shí)代的印記。在翻譯規(guī)范更迭中,外國(guó)小說(shuō)以差異化的形式實(shí)現(xiàn)了在中國(guó)歷史實(shí)踐場(chǎng)域的傳播。
- 牡丹江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對(duì)高校數(shù)學(xué)建模教學(xué)模式的分析與解讀
- 高職院校“功能性食品”課程的教學(xué)改革實(shí)踐
- Flash教學(xué)動(dòng)畫(huà)在生物教學(xué)中學(xué)生自主學(xué)習(xí)能力培養(yǎng)方面的作用
- 高職院校培育和踐行社會(huì)主義核心價(jià)值觀(guān)長(zhǎng)效機(jī)制研究
——基于思想政治理論課程視域 - 高職院校思政課專(zhuān)題式教學(xué)初探
- 以思辨能力培養(yǎng)為導(dǎo)向的英語(yǔ)報(bào)刊批判性閱讀教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