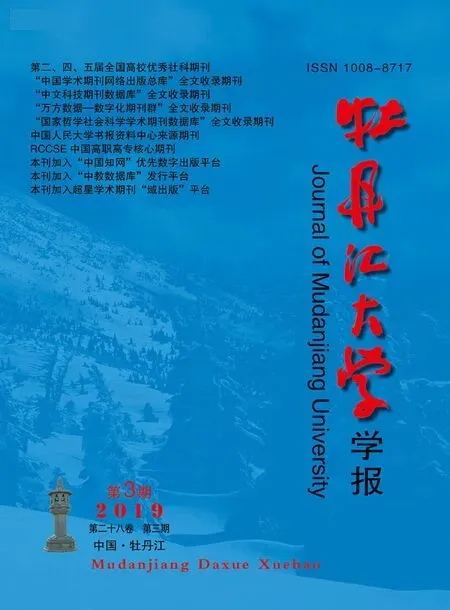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下的自由觀探賾
陳 書 宏
(貴州師范大學歷史與政治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關于人類自由的討論,在近現代思想家的思考中從未停止。“自由”也是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的核心概念,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出,人人生而自由,而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剝削奴役等不自由的現象,正是人性異化的體現。在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地將人從奴役中解放,消滅異化,實現人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社會圖景,正是馬克思主義自由觀的要旨。本文試以歷史唯物主義為主要線索,穿插馬克思主義自由觀,分析其自由觀思想的關鍵要素。
一、馬克思自由觀的形成與發展
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與馬克思所追求的全人類的共同解放密切相聯,并與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思想保持著內在統一的關系。
在18世紀的歐洲大陸西岸,英國通過殖民掠奪、工業革命等手段,率先完成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掀起了一場歐洲資本主義工商業化的浪潮。農耕文明逐漸被取代,物質資料生產實現了質的飛躍,國家與國家之間獨立的孤島局面也被逐一打破。伴隨著資產階級革命在歐洲如火如荼的展開,人類文明的思想之花也在各地綻放。關于自由的討論,啟蒙運動在伴有宗教色彩的自由意志思想上增添了理性的內容;德國古典哲學家為自由理念進行了形而上的論述;功利主義哲學家則將自由觀指向了經濟自由權利。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沖擊之下,平等、博愛的觀念逐漸被人遺忘,取而代之的是名利場上的角逐,自由也被異化為人與人之間的生存競爭。古典
政治經濟學為自由問題的研究提供了生產勞動的剩余價值這一新思路,空想社會主義則提供了人人平等自由的理想社會新理念。[1]5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之中,馬克思理論的自由思想得以誕生,并不斷地發展。
青年馬克思在攻讀博士學位時,其博士論文《論德謨克里特與伊比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區別》闡釋了一個從“原子偏斜”中實現個體在定在中的自由的道理。馬克思所關注的原子,并非一般物理學意義上的原子,古希臘哲人對“多元化”的解釋,認為雨滴般秩序運動的原子,在偶然原因的出現下,發生了原子偏斜運動,馬克思指出:“所以盧克萊修很正確地斷言,偏離運動打破了‘命運的束縛’……偏離運動是在它胸懷中的某種東西,這東西是可以對外力作斗爭并和它對抗的。”[3]20馬克思所強調的是,舊制度的枷鎖,不斷的遏制著人的自由意志,限制了個體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可能,而“偏斜”正是個體對舊秩序的否定,進而對自由發展的肯定與追尋。
在1843年至1844年期間,馬克思先后發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與《論猶太人問題》。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明確批判了黑格爾“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理性國家觀;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的論述,區分了兩種不同的解放,分別是“政治解放”與“人類解放”,政治解放所強調的是資產階級革命,而馬克思更注重的是將人類從一切壓迫中解放出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即“人類解放”。萊茵報之后,馬克思開始了《1844經濟學哲學手稿》(下文均簡稱為《手稿》)的寫作,大量閱讀經濟學著作,并對資本主義社會深入研究的基礎上,認識到現實中剝削與異化現象存在的事實。馬克思指出:“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5]53青年馬克思的思想核心,主要圍繞在個體的個性化活動中思考,社會中每一個如同原子的個體,在剝削與異化的環境下活動,所享的自由就大打折扣。
隨著馬克思與恩格斯對現實社會的深入考察,1846年,《德意志意識形態》(下文均簡稱為《形態》)橫空出世。《形態》奠定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形態》指出:“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2]531這里強調了,物質生產資料對現實活動中的人的重要性。歷史的推進與文明的延續,無法擺脫對生產生活資料的依賴,在社會發展不完善的階段,物質資料的匱乏,人們對自由生活的向往也無從談起。而實現自由的根本途徑就是依賴實踐活動,“沒有蒸汽機和珍妮走錠精紡機就不能消滅奴隸制;沒有改良的農業就不能消滅農奴制;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2]527人類在工業革命、近現代化制度改革等實踐活動中,對客觀事物與現象進行深入的改造和認識,事物與發展的必然規律得以揭示,并以此正確地指導人們的實踐活動,物質與思想均實現解放,自由的存在空間也得以生成。總而言之,《形態》所奠定的歷史唯物主義,作用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方方面面,也為自由解放的實現,提供了前提和依據。
二、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下的自由觀
《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2]502以往的哲學家,一般都是在形而上的層面上對世界的本源、現象進行解釋,其關注的焦點聚集在了凌駕于人類之上的超然理性力量,而沒有真正意識到,正是人在歷史中的活動,推動著歷史的發展。實踐活動作為人類改造客觀世界的方式,不僅是感性力量的推動,也是人類主體能動活動的作用,思維與存在并存,主體與客體的不分,現實生活中的人在實踐活動中實現了邏輯與歷史的統一。而自由是勞動者在社會發展中對“必然”的認識與把握,是人在勞動實踐中的必然需求。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哲學,馬克思對舊唯物主義批判時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觀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2]499而沒有將其作為人類的感性活動,通過實踐的方式去理解,馬克思認為,人類生活實踐的世界是“感性世界”,這是由現實中的人通過感性活動構造而成的,實踐作為貫穿于歷史與生活的主線,是歷史唯物主義核心概念,同時也奠定了解決自由問題的前提。將人類實踐活動作為探討自由問題的前提與基礎,是我們正確的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解決自由問題的重要途徑和關鍵因素。
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指出,社會的發展是不斷地對舊制度的顛覆,社會的發展經歷了奴隸社會、農奴社會、封建社會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更替。以分工的視角來觀察,最早的原始社會,分工主要集中為,以家庭為單位的自愿分工,在智力與工具水平的制約下,“分工起初只是性行為方面的分工”[2]534,在物質生產欠發達的背景下,生存與繁衍就成為古代社會發展的第一要務。隨后,私有制觀念的萌芽迸發,人們就開始不斷地搶占資源與物質生產資料,開始了上層建筑的構建,分工也不斷朝向精細化發展,物質生活、生產資料也在不斷擴充。但是,個體的需要與發展出現了“一些人靠另一些人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得到了發展的壟斷權;而另一些人經常地為滿足最迫切的需要而進行斗爭,因而暫時失去了任何發展的可能性。”[7]95在歷史的推演,揭示了各個階級存在的對立現實,雖然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在不斷地改進深化,但被統治階級沒有得到應有的需求,統治階級也在生產方式的限制下產生了局限性,就人類的總體視角來看,他們都是不自由的。
物質資料的豐富,并不足以證明,資本主義社會是社會發展的最終階段。個體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異化勞動狀態,導致了自由的不確定性。工人同自身的勞動產品相異化,資本家獲利愈豐,工人被剝削的也就愈深;工人同自身的生產活動相異化,工人沒有在勞動中實現自身的全面發展,反而勞動成為工人們的夢魘,工人在生產活動中飽受著精神與肉體的摧殘;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勞動本是作為人的類本質存在,每個人都應該自覺的從事生產勞動,但是從事勞動生產的目的,僅為謀取最低生存資料;基于上述的三種異化,其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相異化,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矛盾愈發突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愈加激烈。我們可以看到,勞動生產實踐本是人實現自由的前提和基礎,社會發展的不充分,勞動異化現象的突起,沒有可供自由發展的空間。馬克思認為,在人們不斷的深化勞動實踐的過程中,人的意識逐漸覺醒,在與資產階級的斗爭取得勝利后,就能向更高的社會階段邁進,從而實現個體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理想狀態。
三、馬克思主義自由觀的三個維度
我們認為,馬克思所期望的個體能夠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社會,其實質是人類的解放。通過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我們認識到,在人類歷史的演進過程中,人類的不自由,主要是由三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一是自然對人的束縛,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束縛,三是意識對人的束縛。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必然只有在它沒有被理解時才是盲目的。’”[6]120恩格斯在這里用黑格爾的觀點表達自由與必然的關系,我們認為,“必然”是事物運動發展背后的一般規律,我們充分把握好這一客觀規律,人類才能更好的發展。換句話說:“自由就是對于自然規律、社會規律和思維規律的把握。”[8]203
(一)正確把握自然規律
馬克思指出,意識不能夠脫離物質而獨立存在,不僅是意識,人類活動也需要依托物質基礎才能實現。人的發展,無法擺脫與自然進行物質交換的前提。因此,對自然界一般規律的正確把握,則是人類能夠獲得豐富物質資料的基礎。在人類智力發展的不完備階段,面對自然一無所知,種種無法解釋的自然現象,被人類神秘化并列為至上的權威。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勞動”這一人類固有屬性,不斷改進生產方式,提高生產力水平,改變社會狀態。人的自然蒙昧狀態并不是長存的狀態,在生產力水平的臨界點得以突破的同時,社會狀態自然會發生改變。生產力與認識是相應的,對自然規律的深入把握,人類也逐步擺脫自然的“束縛”,取得一個相對穩定的生存空間,自由的實現需要以物質作為依托,只有在人類掌握了發展規律,能夠進行高效的生產活動,才能解放自然對人的束縛。
從自然界中獲得解放,并不意味著要對自然進行支配與破壞。人類合理地利用自然界中的客觀規律,優化人類的生活與生產方式,對自然界有意識的進行合理保護,在人類自由意識的支配下,自覺合理地對自然進行開發。歷史文明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而自然資源的有限性與人類欲望無限性的沖突,勢必會形成未來人類發展的屏障。合理的分配利用自然資源,與自然形成一種和諧互補的關系,實現資源的可持續性利用,才有自由的無限可能。
(二)打破人與人之間的奴役關系
盧梭指出:“誰第一個把一塊土地圈起來,硬說‘這塊土地是我的’并找到一些頭腦十分簡單的人相信他所說的話,這個人就是文明社會的真正締造者。”[9]87私有制觀念的萌發,打破了古代原始社會的運作格局,使社會發展邁入了一個新臺階。與此相隨的即是私有制對人與人關系的破壞,勞動產品被少部分的財產私有者攫取在自己手中,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這種奴役與被奴役的關系,而人與人之間異化與奴役,正是喪失自由的體現。
當歷史步入18世紀的視野,社會運行的主要形式,呈現為以工商業為主的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通過經濟手段對社會的控制,占據了大量的物質生產資料。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細化,使得生產力得到顯著提升,斯密在《國富論》中舉出“制針業”的例子,一根細針的制作被精細化為多個流程,不同的制作工序,分配在不同的工人手中,工人長時間從事單一重復的作業。生產方式的改變,生產力的提升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成果,但與此同時,工人各自所具備的潛能,卻被這樣的模式所遏制。工人從事勞動,其目的自然是為了能夠在社會上生存發展,但他們所付出的勞動,并未得到等價的成果,資本家往往以最廉價的工資,換取最大的資本利益。也就是,工人所創造的成果越豐富,其被剝削的程度就越深。自身的潛能被遏制,缺少了自由的物質保障,工人就只能如同行尸走肉般的機器一樣活動,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沖突愈發變得尖銳。
《共產黨宣言》指出:“資產階級用來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卻對準資產階級自己了。”[4]34我們認為,生產方式的不斷變革,人的意識覺醒程度也會愈加深刻,歷史中存在的對立沖突,其核心就是物質分配的糾紛,物質的保證是自由的前提。社會的發展與生產力息息相關,只有當所有人自覺自愿的從事生產勞動,不斷革新生產方式,人與人之間的異化關系也會隨之消除,人也能有更多的自由活動機會,從而實現自身的自由發展。
(三)解除無知的束縛
從上述看來,我們認為,自然與社會對人所產生的束縛,其原因均是源自于人類的無知所造成的。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生產力的低下,造成社會發展的遲緩,人們的意識思維也陷入了僵化的環境,兩者相互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社會秩序的不穩定性,與人類的意識混亂蒙昧有著不可割裂的關系。在啟蒙運動以前,神權占據了絕對的統治地位。費爾巴哈指出,宗教的本質是人異化的結果,我們認為,在啟蒙運動以前,生產力相對薄弱,知識也惟神權支配,面對未知的恐懼,只能寄托于神秘的上帝所給與的啟示,宗教是人自身異化而來的結果,統治者利用神的權威,維護自己的統治,實際上是將人們的無知進一步的放大,而不是解放人的思想。
馬克思的發展觀指出,新舊事物的替換是必然的,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剩余價值的產生與物質基礎的不斷地積累作用在歷史當中,在生產資料積累到了一定的程度,社會就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例如蒸汽機的出現,社會原有的運行模式被新制度所替換。所以,在實踐中探索,在生產中革新,新鮮的思想血液得以不斷的注入,思想必然會得到自由的解放。
總而言之,自然規律、社會規律與思維規律三者,在人類的自由解放中,有著內在統一的關系。人類的自由解放,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歷史唯物主義所指出的三大決定論,揭示了社會存在與發展的必然規律,而現實中的個體正是要對這一系列必然的客觀規律,加以正確地認識,在勞動實踐中予以運用,才能使社會發展邁上更高臺階,以在現實中獲得應然的自由。